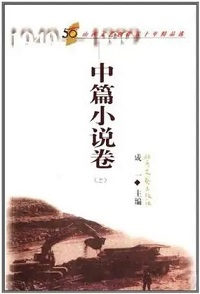01
辛弃疾最逗的一首词,肉麻至极,却被誉为哄妻典范
“暖男”这个词,用来形容苏轼、秦观、柳永应该都合适,但把它和词中之龙辛弃疾联系到一起,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儿怪。
毕竟,在后世眼里,辛弃疾是一个“武能马上定乾坤”的人物。
毕竟率50骑兵突袭5万金兵大营的事,不是一般文人干得了的。
而在辛弃疾的经典词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狂气和傲气。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沙场秋点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他的傲气和自负;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这是他的狂气。
因为这些词,让我们记住了铮铮汉子辛弃疾。
但是,在辛弃疾平生的600多首词作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首很不一样的作品。
这首词名叫《浣溪沙·寿内子》,是辛弃疾写给妻子范如玉的祝寿词。
在词中,面对真爱的辛弃疾,狂气和傲气都没了,只剩下甜言蜜语。
这首词的存在告诉我们:再狂傲的男人,面对真爱都可能变成个暖男。

《浣溪沙·寿内子》
南宋.辛弃疾
寿酒同斟喜有余,
朱颜却对白髭须。
两人百岁恰乘除。
婚嫁剩添儿女拜,
平安频拆外家书。
年年堂上寿星图。
这首词寥寥数十字,却堪称哄妻典范词。
从词意来看,这应该是在辛弃疾妻子范如玉50岁大寿时所写。
少年夫妻如今都已是年过半百的年龄,但辛弃疾对妻子的爱却不减当年。
词的上片,最逗人的是“朱颜却对白髭须”一句。
恍惚间,似乎能想象捋着花白胡子的辛弃疾,对着也已年纪不轻的妻子说:“夫人你还和当年一样美,而我却成了小老头啰!我配不上你了!”
在古代,50岁女子已是老去黄花,但辛弃疾居然还用上了“朱颜”二字,这样的宠溺真的是甜到“单身狗”了。
用自己来衬托妻子,我老君未老,这分明就是在说:就算你年纪再大,在我眼里也是一朵花!

词的下片,是投其所好的美好祝福。
妻子到了这个年纪,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家上下的平安,儿女能幸福,这一点辛弃疾怎会不知?
于是词的下片,就送上了最平凡却也是最美的“暖男”祝福:
我祝夫人年年有今日,年年都能收到儿女们报平安的书信,年年都能坐在高堂上受儿孙的拜贺。
辛弃疾一向爱用典故,但在这首词中却一个都没用。词风也一改往日的沉郁与悲苦,变得明快自然。
这就是面对真爱时的词中之龙,在妻子面前要什么狂气,要什么傲气,只要过大寿的她能开心,做一回小暖男又有何不可?
这样的词作在辛弃疾平生的600多首作品里,水平不算高,但却能令人会心一笑。
范如玉和辛弃疾相守多年,辛弃疾的600多首词作,有400多首是和她在一起时写下的,她见证了辛弃疾由沙场将士到词中之龙的转变。
关于她,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只知其也是一个名门之后。
中年后,辛弃疾饮酒过多,范如玉便在他窗户上写满了劝他戒酒的字眼。
后世只知李清照和赵明诚式的爱情,却不知辛弃疾和范如玉的感情,一点儿也不输给李赵二人。
02
直到11世纪的最后20年,词不被视为“文学”。
柳永在《玉蝴蝶》里写了这样的场景:“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写下来的词作要交给歌女,她们是专业的音乐人,歌声为文字赋灵韵。填词人的著作权是模糊的,是歌女们收集且保存了过往的歌词。

晏几道在给自己文集的自序里写道:“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小晏在宴席间兴致所至,小令一挥而就,草稿就交给了家班歌女。后来朋友故去,家境中落,家班散了,歌女们有了新雇主:“昔之狂篇醉句,遂与歌儿酒使流转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窜易。”他自己对这些作品是不看重的,形容为“狂篇醉句”。自从把词笺递给歌儿酒使,那些歌词不再是他的。歌女们各奔前途,歌词在传唱过程中也变得面目全非。当他的好友努力寻回这些散落的作品结成集,他再度读到自己的词作只感到陌生,掩卷怃然。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词的文本是不稳定的,有的词在表演过程中被修改过,有些作品被同时归在不同的作者名下,有些佚名的文本假托为名家之作。这些偏离于公共生活的感性话语,真诚地再现了被伦理纲常压抑的人类经验,是边缘化的,被轻视的,“为笑乐而已”。

11、12世纪之交,苏轼和他的门生们把填词提升为精英文学活动,苏轼明确地表达了“词就是诗”的观念。“作者论”的意识主导并影响了词文本的保存。比如《乐府雅词》收录欧阳修的83首词,编者直言悉数删除署名为欧阳修但他认为德行有亏的词。之后的《近体乐府》又过滤了一部分疑似欧阳修的词,编者认为这些过于香艳的俗词是欧阳修的政敌别有用心归到他名下的,以此中伤这位文坛领袖的形象。有一首被《近体乐府》删去却出现在《全宋词》里的《蝶恋花》,写新婚之夜:“几叠鸳衾红浪皱。暗觉金钗,磔磔声相扣。一自楚台人梦后。凄凉暮雨沾裀绣。”如此具体地描写欢好的细节,是不是欧阳修的“真作”?纵然欧阳修确凿地写了孟浪的艳词,“写风流”也未必等同于作者“真风流”。但是,在12世纪的编纂者看来,文学泰斗也是道德楷模,不该被看到这样浮浪的一面。

12世纪中期,成熟的印刷文化来临了,但道学化的时代氛围加剧了作品保存状况的偏颇和扭曲。在1149年写成的《碧鸡漫志》里,作者王灼把伦理评判和审美评判视为一体两面,他声讨柳永是鬼魅一般的“野狐涎”,认同朝廷对伤风败俗的曹组的词作全面封禁。然而,面对李清照,他的伦理信念和审美原则分裂了。王灼态度纠结,他无法否认李清照的天才,但他严厉批判她在作品和私生活中显露的“道德败坏”。王灼的判词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共识——
“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但“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但“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类比前朝男作者,“纤艳不逞淫言媟语如元白,侧词艳曲如温飞卿”,结论是“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这里含蓄的意思是,李清照浪费了她的才华,用错了地方,她写得那些惊世骇俗的词作,让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最露骨的作品显得微不足道。

王灼读到了什么让他作出这样的评语?今天的读者是再也看不到了,男作者对李清照的非议顽强地流传至今,她的作品却未能在时间长河里幸存。《梅苑》收了她的五首词,写梅花自然不会有淫言媟语。《乐府雅词》保留了她的23首词,有严重道德洁癖的编者一丝不苟地排查并剔除了她的侧词艳曲。面对被前赴后继的男性文人扭曲塑造后的“李清照”,今天的读者再也看不到她无所羞畏惧、肆意落笔时写下了什么。
03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这首词,写尽人生悲欢
《一剪梅·舟过吴江 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此词牌名为“一剪梅”,亦称“腊梅香”,得名于周邦彦词中的“一剪梅花万样娇”,为宋朝蒋捷所作。
宋,那样一个明丽清新的时代,连雨丝中都是柔柔的清墨香气,风姿款款的仕女,文采风流,她们才思敏捷不输于男子,一盏淡酒,一枝湖笔,顷刻间撒落出字字珠玑。
虞美人、念奴娇、翠楼吟、定风波,那些美妙空灵的词牌名,纤细秀丽得如同茶香浅浅,在唇齿间洇开,模糊成遐想万千,曲曲调调,丝丝绕绕,久而不散。
她们是《清明上河图》中走出的活色生香,汴京春光不胜,留得艳名一段香。那些与其相和的名士,温润如玉,常常在不张扬的浅笑中,便轻吟出传世的诗篇。连国君都如此,徽宗瘦金体,高宗翰墨志,都是史书上的字字千金。
可惜时不长久,越是美丽的物事便越是脆弱,南宋短短一百五十二年,终载不动许多愁。
蒋捷正生于南宋末年,那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政局动荡不定,民众疾苦不堪。他是忧国忧民的,本是度宗咸淳十年进士,满腹经纶、妙笔生花不能效忠社稷,于是他宁可放弃,宋亡而不仕,不以奴颜媚骨侍夷狄之君。

他不愿见那国破家亡的惨烈情景,可是他无能为力,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他渺小得甚至比不过一粒尘埃,他只能逃避,离开那物是人非的临安,逃避,逃避,一直逃避。
这词正写于临安附近的吴江,那江南水乡中,他乘一只小舟,青衫染就忧愁,青盏泼酒,听雨饮醉,他能去哪儿,要去哪儿,且不去管,只在水波一圈一圈荡漾中换得一日一日沉醉。
酒,有时真是一个好东西,得意时它能添上几分意气,失意时它能解得片刻忧愁,便连绝望也可以用酒来麻痹。国人的喜怒哀乐永远离不了那杯中物,区区一壶便是整个世界,李白在《将进酒》中写到: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闲时无事,执了银簪伴着一字一字敲来,随口念着都是豪情万丈。

李白横卧天子殿,手执琼浆半壶,醉眼睥睨权势,亦喜亦忧,亦正亦邪。他也是失望的罢,现实总不尽如人意,来,饮尽这一杯,再饮上一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他是忧伤的文人,所以用这样的豪迈潇洒来掩饰他的无言失落,那是长使男儿泪满襟的痛楚,是难济苍生的无奈。可他是堂堂丈夫,他永不儒弱,会大笑着来面对这一切,若是能醉得一分,那么,请让我借它卸下自己的伪装,只需片刻就已足够。
蒋捷亦是忧伤的文人,他的感情却是婉转细腻的,那生于江南的男子,骨子里都浸透江南的二月烟雨,脉脉氤氲的旧书香迷离了他的眼眸。他的伤感是十里西湖的水雾不散,在每一个月华如洗的静夜中呻吟挣扎。
他吟道:“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
一字一字,句句泣血,杜宇望帝,亦会动容。他只念着秋娘渡和泰娘桥,那是什么地方,令他魂牵梦萦,多情应笑。那里可有陌上美人青丝罗裙?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白居易说,“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蒋捷亦不能忘却相思,那梦中的人啊,她在何方,吹奏着银字笙,心字香绕,笙曲悠悠,他在这半醉半醒之间又听到了。
那张容颜,一如往昔,是心中不可碰的隐痛,他醉了,隔着江水伸出手去,却什么都触不到,只有一点余香在鼻间残逝。
那词中的女子或是他的知己,或是他结发不移的妻子,这都已不再重要,此刻她是他醉吟中的一个绮梦,在这乱世浮萍的年代,她是生是死,均是一个奢侈的答案。
蒋捷只是无奈,他只是吴江上漂泊的文人,连明天何至都尚未可知。再忆起当年执手相对之时,不得不叹一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私以为,只是这一句,已是绝唱,往者已矣,而繁花自开,烟雨自浓,谁又能是谁的谁?
你看,那些瑰丽平仄的诗歌,那些相思相慕的才子佳人,早在那铁蹄的践踏中神形俱散,我用这百无一用的前朝文字为你写下这百无一用的词曲,哪里有什么“故国之思”,哪里又有什么“黍离之悲”?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你记得吗?我曾许下诺言,要与你折梅听雪,赏花品酒,可如今,我只能在这江上独醉,笑着泪着,以癫狂破碎的语句念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那便是前朝,前朝,原来我所能眷念的一切,都只是前朝。可是它已入了我的血脉,非死而不能断,就让我痛醉,偷得半刻遗忘亦是侥幸。
我不知道为何那样一个年代会生出许许多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只道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宁可枝头抱香死的郑思肖;便连时年八岁的南宋小皇帝赵昊,国破后也由丞相陆秀夫抱着投海自尽。
或许那真是一个过于完美的时代,让所有人无法接受它的逝去,烟花风流,珠玉富庶,如今都是残破。
杜甫叹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蒋捷也是在一个春天,写下“一片春愁待酒浇”。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人物,竟有着同样的愁思,原来历史总是在重演,无论是瑰丽的盛唐还是清滟的南宋,不管它们有着怎样辉煌的出场,都要以这样忧苦的方式落幕,没有什么完美会永远存在。
一样的国破家亡,国是谁的国,而家只是我的家,如今她又在何方?愁,愁,愁,怎是一个愁字了得,当誓言遭遇战乱,那便是一句空言,凉薄得比不上一滴滑过脸颊的泪水,那样荒唐的笑话,竟是满口的苦涩,未语泪先流。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他在外流离漂泊,自叹身世不如一片枯叶,她却在家中苦苦等待,一种情愫,两地相思,唯有叹一句世事不尽如人意。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在每一个露水凝结的月夜,那总是入了骨的毒,一寸一寸染白华发,退尽红颜。
那些离情别意,读来终是无力。想当时之事,除了黯然神伤,唯余叹息。
来源:柳青、领刻文史,配图为资料图片,部分来自电视剧《清平乐》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