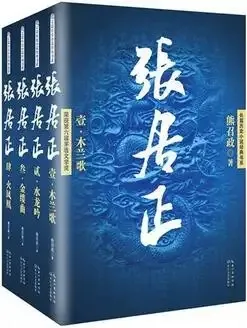11、准噶尔之梦
有人在问,《黑白天山》的主题是新疆民国史,为什么清朝占了这么大篇幅?清朝是中国边疆史的真正起点,把清朝对新疆的社会治理说清楚,才能把今天的新疆问题说清楚。清朝奠定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主权基础,也留下了很多隐患和问题,尤其东突,必须从清朝说起,才能还原出一些真相,让涉身其中的各个民族了解并且信服。虽然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有些账本,总得有人翻开,才能看见里面的黑与白。
我毫不掩饰自己对作家和知识分子们的痛恨,他们经常以狭隘的个人偏见,来定义历史。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统治阶级脚下的爬虫,以为他们在高山之巅,看见了世界和历史的全部真相。比如易中天,他说“乾隆是个王八蛋”,一个以文化大师自居的人,不应该说出这么种粗俗的话,这是对中华民族先祖们的大不敬,今天骂秦始皇和汉武帝,明天是不是就可以骂黄帝和尧舜?传统文化的基石就是这样被一点一点腐蚀掉的。易中天骂乾隆,说明他的历史研究有短板,他对乾隆皇帝的历史功绩并不了解。如果易中天对中国今天的法理边界有起码的认同,他都不敢说出如此轻薄狂躁的话来。从这一行为看,易中天的清史水平,相当于今天的自媒体水平,只不过他占了当过老师的便宜,嘴巴更能说一点。当然,他们还可以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的尊严”。
从康熙皇帝开始,世界地图就已经展挂在皇宫内院。这张图,分为东西两个半球,除了地名和今天的世界地图不一样,地理轮廓完全一致。一个封建皇帝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资讯,比知识分子们看见的世界更多元、更复杂、更宽泛,国家在不同阶段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和管理模式,只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闭关锁国,愚昧无知”,是历史戴在清朝皇帝头上的高帽子,如果把易中天这些人送回清朝,他们绝对比那个年代的官僚更愚昧、更无知、更加卖国,胡适和周作人都是他们的影子。
清朝到康熙、雍正时期,边疆意识和国家战略已经形成,最有力的证明是台湾和青藏的回归。但清朝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有效管理,则归功于乾隆,由乾隆皇帝一手策划完成。在此以前,康雍两朝仍然沿用明朝的边疆治理模式,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长期采用不同于内地郡县的“藩属”制度,“一国两治”,主权在国家,治理权交给当地的札萨克、伯克和土司们。一个国家,两种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对藩属地区做不到直接有效地管理,部落和部落斗争,部落和国家斗争,战乱不断,反叛不断。清政府好比一个大家长,反叛了去打,打完了撤回来,葫芦娃救爷爷,抢一回救一回,救一回打一回,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电视剧《雍正王朝》有一段被删减的台词,康熙把皇位传给雍正的时候,在病床上教导雍正,“朕在位六十一年,六十一年不容易,除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治理黄河,整治漕运。其实这些都不难,难的是我们要有征服人心的东西。我太祖太宗龙兴关外,马上得天下,靠的都是武功。可是要治理这九州万方,我们没有孔子,没有四书五经。朕这一生,兢兢业业地学习汉人文化,就是想要把国家治理得连那些汉人也真正信服,这就难了”。
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皇帝,百年经营,到乾隆继位时,满清统治集团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群体性文化自信,乾隆皇帝也有了傲视群雄、百无禁忌的资本,在文化领域,比汉族人更汉族;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比汉族人走得坚毅、更长远。乾隆皇帝打破汉民族对农耕文明与生俱来的天然自恋,走出长城,走出草原,走出荒漠和高山,完成新疆、青海、西南等地区的行政建设,使中央政权的行政管理直接、有效地延伸到今天的国家版图的绝大部分地区。从乾隆开始,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打破以长城为疆界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农耕与游牧、草原与海洋多元一体的国家。
在平准战争的前半段,乾隆皇帝对新疆的治理思考仍然没有成熟,抓获准噶尔末代汗王达瓦齐以后,乾隆皇帝宣称要“众建之而分其力”,意思是在新疆多分封几个蒙古汗王,瓦解蒙古在新疆的统治能力,从而达到“藩属治理”的目的。乾隆皇帝说,“朕视准噶尔众台吉与喀尔喀诸部落无异,凡事俱一体办理。四卫拉特台吉亦应照喀尔喀,每部落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乾隆皇帝最初的构想,仍然是参照蒙古模式,把准噶尔拆分为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派一位副将军领兵监督。他甚至已经公布了四大卫拉特台吉的任命通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啰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
阿睦尔撒纳改变了新疆行政建制的历史进程。阿睦尔撒纳是准噶尔汗国的带路党,率两万多部众投降清朝,鼓动清政府出兵讨伐准噶尔,企图借助清朝的军事力量铲除达瓦齐统治集团,自己出任准噶尔汗王。结果,他连拆分以后的四大汗王位置都没捞着一个,气急败坏,发动叛乱。被册封为汗王的辉特汗巴雅尔、绰啰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参与叛乱。
在阿睦尔撒纳平叛战争中,定边将军班第、定西将军策楞、参赞大臣鄂容安、参赞大臣玉保、副都统和起、副都统唐喀禄、领队大臣满福等众多战将血洒疆场。他们没有死在刺刀见红的战场上,多数人被准噶尔叛匪以投降的名义围捕和诱杀。乾隆皇帝龙颜震怒,认为准噶尔人阴暗狡诈,反复无常,不可相信,命令清军不再接受准噶尔人投降,对参与叛乱的准噶尔人格杀勿论。
准噶尔人反复叛乱,清政府任命的卫拉特台吉也参与其中,乾隆皇帝终于意识到,如果不以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加强对新疆的行政管控,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土崩瓦解。在这个背景下,乾隆皇帝决定,废除新疆“藩属”制度,对新疆实施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行政管理。
所谓的准噶尔灭族,和张献忠屠川一样,是有些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不实历史。清朝屯防伊犁的厄鲁特营中,有一万多归降投诚的准噶尔官兵。最早加入厄鲁特营的五百名准噶尔军兵,是清朝从哈萨克地区花钱赎买回来的出逃人员。就像今天不允许公开宣讲一些极端分裂组织的名称一样,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清政府不再允许准噶尔人继续使用“准噶尔”这个名称,把他们并入厄鲁特蒙古;清朝官方文献从此不再出现“准噶尔”这个词语,把他们归入厄鲁特蒙古;这是民族主义史学家强调准噶尔被灭族的主要原因。至于准噶尔人从此灭绝等等言论,更不靠谱,准噶尔人本来就是蒙古人当中的一支,准噶尔名称被禁以后,他们仍然以厄鲁特蒙古的身份存在。同治暴乱期间,在塔城、阿勒泰等地区抗击妥明回匪的蒙古骑兵,都是准噶尔人的后裔。
清军报复性杀人的情况是有的,也是公开的,有乾隆皇帝的诏书为证。但所谓车轮以上的准噶尔男丁被全部屠杀的情况,则不存在。准噶尔不是一村一镇,准噶尔人的活动范围东起哈密,西到哈萨克斯坦境内,在数千公里辽阔的荒原上,把一个种族赶尽杀绝,是老天爷也完不成的任务。这些绘声绘色的传说,多数来自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鼓动宣传。
准噶尔汗国消亡的原因很复杂,长城以北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天花,从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开始,内地军兵频繁出入草原地区,把天花传播到蒙古和新疆。乾隆平定准噶尔的时候,正是北疆地区天花流行的高峰期,一部分牧民感染天花病亡,一部分牧民躲避疫情逃往哈萨克和沙俄境内。魏源在《圣武记》中说,“计数十万户中,出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率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魏源从来没有到过新疆,他的记录也是道听途说,不能完全采信,但准噶尔地区天花大流行造成大量人口减员,是文字可见的历史事实。
平准战争结束后,清朝强迫准噶尔人往喀尔喀蒙古迁移。其中,杜尔伯特部落统治下的三车凌部被整体迁移到乌里雅苏台,达什达瓦部被整体迁移到今天的河北承德。这些文字记录充分证明,消亡的只是准噶尔这个名字,准噶尔人被分散到新疆各地和北方草原地区,一直存在,直到今天。
12、移民屯田
新疆有很多以“工”命名的地名,如乌鲁木齐的“头工、二工、三工、四工”,如昌吉的“五工、六工、七工(已不存在)、八工”,还有以地方命名的“中营工、羊毛工”等。“工”是清朝在新疆移民屯垦点,以引水灌溉渠为编号,被称为“工”。久而久之,“工”便成为一个生产单位(集体)的称号,类似于今天兵团体制下的国有农场,如“一场、二场、三场”、“一连、二连、三连”。
“中营工”以军屯点命名,分“上中营工、下中营工”。“羊毛工”这个名字就有说法了,这里的居民很多是青海回民的后代。如果说,“工”字后面折射着新疆早期的屯垦史,类似于“羊毛”这样的名称,则折射着新疆漫长而曲折的移民史。羊毛工早期移民,来自今天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羊毛沟村,迁居到新疆初期,仍然在使用原住地“羊毛沟”地名,后来各屯垦点名称统一,改称“羊毛工”。
“屯”和“工”的意思基本相近,都是屯垦居民点,如头屯、二屯、三屯。以“户”命名的地方,和移民区略有区别,一部分是军垦区,安置军兵家属的地方,有少量军兵驻扎,如昌吉的军户、兵户。一部分是城区商人们认领的家属屯垦区,一般都会有个后缀名,如商户地、商户塘。国家公有的屯垦单位,有一个“皇”字起头,像米东区的皇渠、皇工,类似于解放后的国营农场。
以数字命名的“户”,并非今天理解的多少户人家,“户”是“斛”的同音字,是古代的粮食计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石和斗之间,又切入了一个新的计量单位,一石等于二斛,一斛等于五斗。古代的一石粮食等于四百斤,等于今天的两百公斤。那么,一斛就是两百斤,等于今天的一百公斤。
按照土地面积推算出粮食产量,再按照每亩地八升征收粮租,推算出屯垦区土地总共应该上缴给国家的公粮数目,把这个数字固定下来,就是“户”的由来。比如,六户地,每年上缴六斛公粮;六户半,每年上缴六斛半公粮;上十八户和下十八户,每年分别上缴十八斛公粮。这些地方过去没有地名,久而久之,公粮征收数目就成了地名。以“工”和“户”命名的屯垦点,多数在今天的乌鲁木齐和昌吉地区。
清朝时期的新疆移民政策,很注重移民人口的文化感受和族群认同,这一点做得比现在好,他们很可能借鉴了宋辽金时期辽朝移民政策的成功经验。
辽朝设立上都、下都两个中央政府,上都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是王公贵族们的居住地,也是对草原游牧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下都在今天的北京市,由汉族官员组成中央政府,是对黄河以北农耕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为鼓励宋、金战乱区的汉人往辽国迁移,耶律阿保机极力宣称辽国代表中华民族正统地位,兴建孔庙,开科取士,按照汉族文化传统建设村庄和城池。为了照顾汉族移民的文化归属感,辽朝将农耕地区的行政区域与宋、金统治区域平行命名,你有河南,我也搞个河南;你有山东,我也整个山东。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集中在同一地区安置,河南人来了安置在辽朝的河南,山东人来了安置在辽朝的山东。再住下,州县镇村,一应俱全,只是小了一号,你是从哪个县来的,仍然安置在哪个县,这个所谓的“县”很可能就是一个村庄级规模。但移民们的文化疏离感被消解了,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拜的是同一个祖宗,敲锣打鼓唱大戏,日子过得和中原地区一模一样。
新疆地域辽阔,清朝做不到像辽朝那么细致的地方规划,但尽量保证人口集中迁移、集中居住,尽量采用原居住地名称,尽量保留原居住地文化。于是,在北疆广袤的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小一号的内地地名,如,以甘肃地名命名的兰州湾子、凉州户、凉州工、凉州滩、凉州渠、庆阳湖(早期称“庆阳户”)、山丹户、宁州(今宁夏中卫市)户、林州(今甘肃华池县)户、庄浪(今甘肃永登县)户、镇番(今甘肃民勤县)户、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工等;以陕西地名命名的陕西工、武功街、渭户(陕西渭南地区)地、渭户沟等;以其他省区地名命名的河南庄子、天津王庄、广东户、广东地、广东庄子、湖南村、山东地等。
除了乡村和屯垦地区,在城区内也出现大量的内地名称,和今天大中型城市街道地名交叉命名不一样,清朝时期新疆地名完全根据移民群居情况而定,比如奇台的“镇番街”,居住了一大批从甘肃民勤县迁移过来的商贩。比如乌鲁木齐南门的“山西巷子”,是山西票号的聚集区,山西商人曾经在那里结群居住,现在是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的主要聚居地。
纪晓岚被发配到新疆的时候,是清朝往北疆移民的高峰期。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杂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内地移民、地方命名的历史景象:“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府犹题旧里名”。纪晓岚在这首诗的后面作了注解,“户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来者,官府仍谓之某州户,相称亦然”。意思是说,移民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回不去了。官府为了安抚他们对家乡的怀念,从哪个州来的,就以哪个州在当地命名,他们对自己家乡的称呼一直没有改变。
你是哪里人?我是凉州人。你是哪里人?我是河州人。过去在凉州、河州,现在还在凉州、河州。几千里外的故乡已经改变了模样,这些刻在脑海里的州县和村庄,是对他们对远方故土最后的眷恋。但不管怎么说,像炉火般燃烧的文化深情,把我们的祖先留在了天山南北广阔的大地上,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开枝散叶。
从文化意义上说,清朝比现在做得好,他们以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完成了新疆收复以后第一批移民的动员和安置工作,并且让他们扎下根来,成为新疆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文化润疆,从清朝收复新疆的那一天已经开始,只不过,他们紧紧抓住了文化的根脉,我们今天连个毛都还没有摸着。
——维吾尔移民
清朝在新疆的移民屯田工作,由乾隆皇帝亲自规划,亲自主抓。平定阿睦尔叛乱后,乾隆皇帝指出:“惟明岁驻兵屯田,最关紧要。虽乌鲁木齐等处现在耕种,而伊犁尚属荒闲,倘被布鲁特等侵占,又须经理。朕意于伊犁等处驻扎索伦兵及健锐营兵两三千名,合之绿旗屯田兵丁,声威自壮”。
按照乾隆皇帝的最初构想,北疆地区的移民屯垦工作由打算盘出身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负责,他命令兆惠返回北京,讨论移民屯垦事宜。就在这个时候,大小和卓叛乱,兆惠率领四千军兵翻越天山奔赴南疆,一代战神才没有被犁铧和坎土曼埋没,再一次走向铁血疆场。
乾隆皇帝又把屯田任务交给他最为器重的陕甘总督黄廷桂,老成持重的黄廷桂拿出了一个让乾隆皇帝很不满意的方案,黄廷桂计划,从巴里坤到伊犁建设七座城池,并且提交了一份清单,要求移民两万五千人,要求提供籽种八千石、农具六千副、驼马耕牛一万五千头。乾隆皇帝被这个庞大的移民屯垦计划气歪了鼻子,下旨质问黄廷桂,一次性调集满汉军兵和维吾尔移民两万五千人,你怎么安置?乾隆指示,新疆屯垦先从伊犁开始,“至于屯田伊始,或派兵五百名防守,回人(维吾尔人)五百户耕作,计所获之粮,足敷食用,再议开扩”。
乾隆皇帝最终把伊犁屯垦的任务交给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乾隆在发给阿桂的谕旨中说,“伊犁向为准夷腹地,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乾隆告诫阿桂,驻军屯田是巩固国防建设的头等大事,一定要抓好工作,“不可苟且塞责,存早想京师之念”。种不好地,你别想早早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冬天,阿桂从阿克苏征召三百户维吾尔人,率领五百军兵,抵达伊犁,在伊犁河南岸的海努克(今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驻扎,拉开了新疆历史上屯垦戍边的划时代序幕。一代名将阿桂,大贪官和珅见了都要绕着走路的人,是新疆屯垦戍边历史上第一个农业生产队队长。
乾隆皇帝人在北京,却对伊犁的屯垦工作格外上心。他在下发给阿桂的诏书中,事无巨细,都做交代,“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部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参杂。额敏和卓系回部望族,应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娴习,主客相安,再回吐鲁番,方为有益”。清朝文献中的“回人”,指今天的维吾尔人。乾隆皇帝说,伊犁过去的农田,都由维吾尔人耕种,现在南疆地区已经平定,平准战争期间从伊犁逃往南疆维吾尔人要逐步迁移回来。吐鲁番额敏和卓是维吾尔人的首领,把他调到伊犁去,管理在伊犁屯田的维吾尔人。等到大家都学会耕种务农以后,屯田兵和维吾尔人的关系融洽起来,他再回吐鲁番。
从此以后,负责伊犁行政事务的阿奇木伯克一直由吐鲁番额敏和卓的后裔担任。伊犁同治暴乱期间的第二任暴匪首领迈孜木杂特,是吐鲁番额敏和卓的五世孙。
阿桂率领军民在伊犁屯垦种田的第二年,屯垦区迎来第一个农业大丰收。阿桂向朝廷禀报,“获粮食二万四千石,除种地者自用外,还可供上千人来年麦熟前食用”。阿桂提出扩大回屯规模,要求从喀什、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地再征召维吾尔人七百户,使伊犁维吾尔屯垦人数增加到一千户。乾隆批复同意,“伊犁再增回人千余,生齿更觉繁盛,亦于伊犁生计有益”。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屯垦区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平均每人收获粮食四十石。阿桂制订维吾尔人垦区粮食收成分配标准,“给籽种一石五斗,以交粮十六石为率”。从此以后,每户每年预留籽种一石五斗,上缴公粮十六石,余粮归耕种人各家所有,形成惯例。
从1762年开始,清政府加大南疆移民力度,在政策和利益的感召下,南疆维吾尔人纷纷迁往伊犁垦区。到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从南疆迁入伊犁的维吾尔人共6406户,20356口。维吾尔移民全部安置在伊犁河南北岸水源便利地区,设九个屯垦点,分布情况为:海努克600户,哈什500户,博罗布尔噶苏1100户,济尔格郎900户,塔什鄂斯坦400户,鄂罗斯坦600户,巴尔托海600户,霍诺海800户,达尔达木图500户。
伊犁垦区俗称“回屯”,实行定编定额土地承租制,长期沿用阿桂时期制订的粮租征收制度,以六千户为集体,核算、征收,每户每年纳粮16石,每年共征收公粮九万六千石,一成不变。维吾尔人自己开垦出来的荒地不征收公粮,分户、分家也不增加粮租,由阿奇木伯克负责征收,汇总以后,缴入官仓。
1804年(嘉庆九年),伊犁回屯的维吾尔人增长到34300口,伊犁将军保宁将厄鲁特蒙古散闲牧区划为耕地,增设了乌兰库图勒、泥勒哈、乌里雅苏图、春稽四个回屯点,增加4000石地租,公粮征收总额增长到每年10万石。
随着伊犁维吾尔人口不断迁入伊犁垦区,清政府组织八旗和绿营驻军修筑引水工程,增加农田种植面积。1840年(道光二十年),塔什图比引水工程完工,安置新增人口1000户,每年增收公粮16000石。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三道湾灌溉水渠建成,安置新增人口500户,每年增收公粮8000石。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阿尔布孜引水工程完成,安置新增人口500户,每年增收公粮8000石。这一年,伊犁地区的维吾尔人已经增长到8000余户,约47000余口;伊犁地区的维吾尔人屯垦点相应增加到17处,每年公粮征收12万8千石,仍然按照阿桂制订的每户每年16石,定额征收。
同治暴乱前,伊犁地区屯垦所得公粮,约占伊犁驻军用粮的四成左右。伊犁素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维吾尔人在伊犁屯垦种田,缓解了国家在伊犁驻军的一部分压力,也为自己开辟了一段时间相对富足的稳定生活。
——甘肃移民
伊犁维吾尔移民屯田开始以后,乾隆皇帝指示陕甘总督杨应踞,“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要求甘肃地方政府动员民众,前往北疆屯垦。乾隆认为,甘肃和新疆距离最近,肃州、甘州、凉州、兰州都在内地通往新疆的交通要道上,从甘肃向新疆移民,比内地其他省份长途辗转要便利得多。甘肃荒漠多,耕地少,地瘠民贫,河西走廊干旱少雨;北疆地广人稀,水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乾隆皇帝一厢情愿地认为,甘肃民众应该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前往北疆屯垦。
甘肃移民动员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清政府将新疆移民政策详尽到划拨土地亩数、房屋建造费用、路途盘缠费用、牲口车辆费用、皮衣铁锅费用、籽种及生活补助费用等,仍然无人相应,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关键时刻,老天爷帮了乾隆皇帝的忙。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起,甘肃连年遭遇旱灾,农业歉收,清政府一面救饥赈灾,一面催促甘肃往新疆移民。针对甘肃积欠政府官粮四百零四万石、库银一百三十二万两的问题,乾隆说,“似此日累月多,势将何所底止,是旧逋固不可不及时清厘,致令积疲不振”。他认为,移民不力,是因为甘肃民众对新疆缺乏了解,当地政府对新疆的农业生产条件宣传不到位,新疆“商民辐辏,风景不殊内地”。乾隆皇帝要求地方官员,广泛宣传新疆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从当地乡民中选派代表,前往北疆考察。
乾隆皇帝劝导甘肃往新疆移民,几乎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乾隆发布诏谕,向甘肃人民承诺,“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乾隆说,将来新疆人口增长了,生活富足了,国家会在这里设置郡县。你们往新疆迁移一个人,甘肃就能节省出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两头都能走向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甘肃再次大旱,朝廷划拨白银二百万两、粮食二十万石赈济灾民,从甘肃移民已经是当务之急,不能再等。乾隆皇帝指示陕甘总督杨应琚,命令他想方设法,劝谕灾民往新疆迁移,“使共知边外谋生之实利,自必熙攘趋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无依;即将来或遇歉收,而瘠土贫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实为筹备边氓生计之长策”。
首批甘肃移民来自安西、肃州,共206户,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秋天搬迁,历时两个月长途跋涉,于当年冬天到达乌鲁木齐安置。第二年,从张掖、山丹、民乐迁出居民264户,在乌鲁木齐安置。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从敦煌、玉门、肃州迁出180户,在巴里坤安置。这一年,又从肃州、张掖、敦煌迁出518户,在乌鲁木齐安置。
1765年(乾隆三十年),从肃州、高台迁出居民1300户,分别安置于乌鲁木齐、阜康、昌吉、罗克伦(昌吉市北部乡镇)。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到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从肃州、安西、张掖迁出居民1150户,分别安置在木垒、奇台、东吉尔玛太(木垒县东城镇)、葛根(奇台半截沟)、吉布库(奇台吉布库镇)。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以前,甘肃移民全部安置在北疆东部地区,重点填充乌鲁木齐。从1777年开始,迁入新疆的甘肃移民越来越多,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甘肃移民开始往乌鲁木齐以西的玛纳斯、呼图壁、土古里克(呼图壁大丰镇)等处安置。
伊犁地区请求安置部分甘肃移民,以求实现民族均衡,在中央廷议时被乾隆皇帝拒绝。乾隆皇帝朱批:“必须由乌鲁木齐一带安足,次及库尔喀喇乌苏、精河,逐渐安设,再至伊犁,始觉声势联络”。乾隆中后期,从甘肃湟中、河州等地区迁移大量回民,往伊犁定居。可见,在清朝早期的行政区域规划中,伊犁被定位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关于移民政策,乾隆皇帝指示,“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乾隆要求,移民到达屯垦点以后要有可居住的房屋,并能领到一年的生活口粮。要求分配给土地、家具和籽种,算账要宽裕,不能太拘促。户部根据乾隆皇帝指示,将移民政策进一步细化,除路途和农业生产费用外,每人分配可耕种熟地30亩,6年免征赋税;每户补贴搬迁安置费白银100两,按乾隆中期的粮食购买力换算,每两白银约合今天人民币750元,补贴费用折合今天人民币约75000元。
早期移民的数量和人口,在官方文献中精确到户数和人数。随着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甘肃到新疆的移民数量再没有准确数据。新疆官员上疏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有一些人口安置数字。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索诺木策凌上奏,“内地贫民节年搬眷来者已有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四户”。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上奏,“截至四十六年止,陆续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户”。
根据现有可查数据,截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从甘肃迁入新疆的移民人口约14000余户,50000余人。在政府组织移民期间,“所有农器籽种及种地马匹,俱系官办”,政府包揽了移民到新疆的一切生活负担,有房住,有粮吃,有地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伐木采煤,养育鸡豚,渐成村落,与内地无异”。消息传回甘肃,更多民众纷纷报名,要求迁移入疆,移民规模越来越大。
1880年(乾隆四十五年),清政府停止了持续二十年的政策性移民,鼓励甘肃民众自发移民,沿途提供生活接济,到点提供房屋、土地和籽种,生活费用向政府借支,不再发放安置费用。政府移民停止后,甘肃往新疆的移民反而有增无减,1795年(乾隆六十年),仅直隶迪化州管辖的北疆东部地区,人口统计已经到3万余户,17万2千余人。
由于地缘相近,风俗和饮食相同,甘肃是新疆人口迁入最多的省份。2018年,甘肃省武威市对新疆武威籍人口做过统计,截至当年,新疆三代以下的武威籍人口约243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武威市现存户籍人口143.7万。数据显示,从2018年开始,甘肃人口开始往东南沿海方向流动,新疆不再是甘肃人口流动的主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