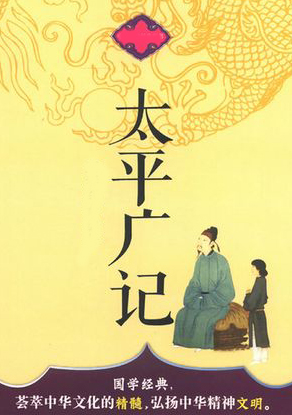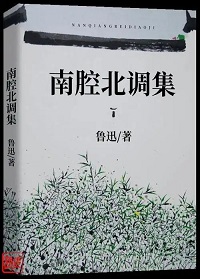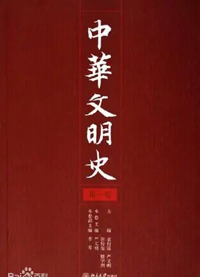二九 春秋两兵圣之田穰苴和《司马法》
说到诸子百家,人们很容易会想到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这些思想博大的风流名士,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各开门户,授徒讲学,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以上提到的这些学术门派,主要是靠笔写,靠嘴说,一代代传承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诸子百家中,还有一种著名的学术门派,之所以能传承千古,并发扬光大,依靠的并不是纵横驳辩,而是冰冷的刀枪剑戟,通过千百家血与火的融合,才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兵家。
儒、道、法、墨等家争的是政治模式和人性的善恶,没有唯一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兵家是诸家中唯一有客观答案的,不存在主观感性认知,只有一种冰冷的判断标准: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兵家相对来说,是一门比较封闭的学科,儒、道、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主要根植在广阔的社会之中。兵家生存的土壤只有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固定场所,这就是战场,一群男人为了杀死另一群男人的战场。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兵家,其实这个标准很简单,就像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可以各玩各的一样,有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才可称为兵家。战场上的名将未必是兵家,但兵家的思想理论一定会用在战场上,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可以称为名将的不在少数,但真正能称为兵家的,只有两个齐国人。
说到千古第一兵家,相信许多人会脱口而出:孙子!作为中国军事理论家的第一人,孙子在军事理论研究上的地位,堪比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不过,孙子并不是春秋时代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兵家,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孙子的老前辈,齐国第一名将司马穰苴。
孙子是中国最知名的军事理论家,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汉朝人看来,司马穰苴比孙子的分量更重,至少司马迁是这么认为的。在《史记》列传中,孙子和吴起挤在了一篇传记里,孙子传记的正文只有五百多字,司马穰苴则单独立传,正文字数是孙子正文字数的整整一倍。而且司马迁对司马穰苴的评价要高于对孙子的评价,司马穰苴虽然在后世的知名度不如孙子,但在当时的江湖地位,是孙子不可项背的。
司马迁推崇司马穰苴,并不是因为穰苴姓司马,穰苴本姓田,而且和孙子是同族,他们共同的祖先就是在公元前672年逃到齐国的陈国公子田完,即著名的田敬仲。田敬仲是齐国名臣,在齐国官场的势力盘根错节,特别是传到田釐子这一代。
田氏野心勃勃,为了收买民心,在收百姓赋税的时候,故意小斗进大斗出,赢得民心无数。齐景公是个老糊涂,对田釐子收买人心威胁齐国姜姓统治的做法视而不见,从而导致田氏势力不断坐大。贤相晏婴对此忧心忡忡,在齐景公面前劝了好几次,老头子一次也听不进去,气得晏婴跑到晋国诉苦:“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
齐景公时代的齐国,虽然勉强保持一线大国的地位,但早已没有齐桓公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气,内忧外患非常严重。齐景公倒是很注重与周边大国的外交关系,但国力下滑,根本无法阻止周边国家对齐国的军事骚扰,特别是晋国。
晋国称霸江湖百年,名将如云,但齐国已经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名将,经常被晋国一顿暴打,却无可奈何。晏婴给齐景公推荐了一个人选——田敬仲的后人田穰苴。
晏婴向来对田氏子孙保持警惕,想尽办法阻止田氏子孙坐大,但晏婴此次推荐田穰苴,完全是被齐国的衰落国势逼出来的。正如晏婴所说:“田穰苴虽然是田敬仲的庶孽子孙,国君不得不防,但田穰苴文能收揽英雄之心,武能威震强敌,是齐国栋梁大才,国势如此,现在只能重用田穰苴。”
齐景公已经被晋国的军事骚扰弄得焦头烂额,看样子他并不了解田穰苴的能力,只能死马权当活马医,把田穰苴请进宫里,当面测试田穰苴的军事能力。田穰苴没有辜负晏婴的期望,和齐景公一席长谈后,齐景公激动得差点抱住田穰苴大哭,这果然是个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齐景公)大说之,以(田穰苴)为将军”。
相似的场面,发生在二百多年后,困守汉中的汉王刘邦在听天才韩信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后,同样激动得不能自已。不过刘韩会谈是在拜将之后,而且要不是萧何几乎和刘邦撕破脸,逼得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刘邦才懒得搭理韩信这个胯下辱夫。从这一点上讲,刘邦还不如齐景公开明。
田穰苴此时的处境和韩信差不多,虽然都初掌军权,但都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新人,在军队中没有威望。一个在军中没有威望的将军,是永远不会打赢战争的,田穰苴和韩信都明白这一点。
关于如何在军中立威,韩信采取了从上而下的模式,即在战略上说服刘邦,具体办法就是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果然让刘邦惊为天人。而田穰苴则采取了从下至上的模式,即在军纪上做文章,以违反军纪的名义杀掉国君身边的宠臣,来达到立威的目的。
在不知不觉中,田穰苴给齐景公挖了一个坑,这个老家伙稀里糊涂就跳了进去。齐景公拜田穰苴为将,是因为西部的晋国和北部的燕国对齐国发起猛烈的进攻,现在是齐景公有求于田穰苴,所以田穰苴给齐景公提了一个要求。
田穰苴直截了当地告诉齐景公,说臣出身卑贱,在军中没有威望,以臣之名望,可能镇不住军队,请国君派出一位有地位的宠臣来做监军,通过这位监军发号施令。齐景公哪知道田穰苴肚里打的什么算盘,便派出他最宠信的大臣庄贾去给田穰苴站台摇旗。
田穰苴在辞别国君时,和庄贾约定,明日正午时分,我与大人在军营辕门前相见,不能迟到。田穰苴应该没有说迟到就军法从事,否则庄贾要是提前来了,田穰苴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庄贾平时骄纵惯了,并没有把田穰苴夹枪带棒的警告当回事,他不相信就算自己迟到了,田穰苴这个毛头小子敢把自己怎么着。当天晚上,庄贾和亲戚朋友们喝了个烂醉,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中午。
田穰苴当然希望庄贾来得越晚越好,只有这样,他才能杀庄贾以立威。等庄贾东倒西歪地闯进军营辕门的时候,田穰苴早已安排好了刀斧手,但田穰苴不能现在就动手,因为还要给庄贾定罪,动静一定要大,让所有人都看到,这才能起到宣传效果。
田穰苴先是厉声指责庄贾的迟到是严重违反军纪,然后给了庄贾自辩的机会,但这不过是田穰苴的欲擒故纵之计,庄贾说什么,田穰苴都要借他的人头立威。
这是田穰苴刻意安排的剧情,庄贾已经触犯了天条,神仙老子也救不了他。田穰苴有意要把事情弄大,他要让整支军队都看到他的强硬,只有这样,他才能立威,只有立威,军队才能在他的指挥下不断取得胜利。
田穰苴故意把军队司法官叫来,问按军纪规定,迟到者将处以何种刑罚,军正答当斩,这正是田穰苴要的效果。庄贾虽然派人紧急回宫中向齐景公求援,但还没等齐景公反应过来,庄贾的人头已经悬在军门之上。不仅是庄贾因违反军纪被杀,就是齐景公派来捞人的使者,也因为在军营中驰马受到严惩,驾车的仆人被斩,这是田穰苴故意做给军队看的。
庄贾当着齐军将士的面被斩首示众,这对平时军纪散漫的齐军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这等于田穰苴借庄贾的人头告诉军人们:别说庄贾这样有背景的高官我敢杀,就是国君做错了事,我也照样不当个泡踩,何况你们!
田穰苴的强硬,为他赢得了军人对他的忌惮,从此不敢再军纪涣散。立威的目的是达到了,但立威只是将军赢得军队拥戴的鼎足之一,另外两足是立德、打胜仗。田穰苴深知一点,军纪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如果只强调军纪而忽视了人心的团结,是永远别想打胜仗的。
军队是冰冷的国家战争机器,但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田穰苴非常注重与普通军人拉近感情。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主将对下层军人体贴关心的军队,往往都是战无不胜的,比如岳家军、戚家军等。
战国名将吴起之所以百战百胜,原因就在于吴起与下层军人打成一片,不能说吴起的做法是抄袭田穰苴的,但至少田穰苴早在吴起之前就注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一般来说,主帅只要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就可以了,军中后勤自有专人负责,但田穰苴却直接干预后勤工作。比如军队在行进过程中需要修建营舍、寻找水井、架起炉灶,以及军队的饮食、医疗,都由田穰苴亲自安排,尽可能地让军人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这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效保证。
除此之外,主将还不能在军中搞特殊化,否则就不能服众,主将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让普通军人相信你。田穰苴从来没把自己摆在普通士兵的对立面,而是和他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弟兄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田穰苴特别注重对老弱士兵的照顾,这一点赢得了很多人的感动。
赢得人心其实非常简单:你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田穰苴虽然不是从底层中走出来的,但最终回归了底层,而历史反复证明,往下看比往上看更容易得人心。得到人心,往往就意味着胜利。
田穰苴仅用了三天,就彻底征服了底层士兵,这只能说明齐军内部的等级制度森严是长久以来积累的严重问题,受压迫时间越长,受感动的时间就会越短,这是铁律。当田穰苴下达命令开赴前线时,几乎所有的齐国将士都含泪请战,包括老弱残兵,“争奋出为之赴战”。
齐军士气的空前提升,对企图浑水摸鱼的晋、燕两国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两国之所以敢对齐国动手动脚,就是吃准了齐军军纪混乱,战斗力不强,现在田穰苴突然来这么一手,让两国感觉到难以再占到齐国的便宜,只好仓皇撤军。之前被晋、燕两国抢占的齐国地盘,被田穰苴指挥齐军悉数收复。
这是田穰苴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当田穰苴率得胜之师返回临淄时,齐景公率文武百官亲自出城迎接并慰问犒赏为国立功的将士们。至于已经升为齐国第一名将的田穰苴,在职务上也进一步高升,由将军改任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大司马。田穰苴被后世称为司马穰苴,他所著的兵法被称为《司马法》,典故就源于此。
田穰苴凭军功谋取富贵,天经地义,齐景公并没有滥赏,但让齐公景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封赏,却对日后的姜氏被田氏废黜产生了致命的副作用。
在田穰苴出场之前,田氏在齐国的势力就已经尾大不掉,而田穰苴的横空出世,客观上不仅帮助田氏在齐国建立比之前更高的威望,更要命的是田氏在军界树立威信,为日后田氏代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不过田氏代齐是在百年之后,和田穰苴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田穰苴本人是忠于齐国的。而且田穰苴公私分明,眼里从不揉沙子,齐景公只要提出非分要求,田穰苴照样冷面拒绝。
有一天夜里,齐景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突然窜至田穰苴府邸门前,派人传话,说国君驾到,请大司马准备酒宴,陪国君喝酒。齐景公平时胡吃海喝,和佞臣梁丘据等人厮混在一起,他以为田穰苴是他一手提拔的,自然要上杆子拍他马屁,哪知道却撞到了南墙,碰得头破血流。
田穰苴平时和齐景公没有多少私交往来,基本上以国事为主,而且田穰苴对齐景公“老混子”的做派向来比较反感,他更不会自污其名,和齐景公在一起鬼混。听说齐景公要他接客,这事好办,田穰苴很快就准备好了。
齐景公还在门外伸头踮脚等待田穰苴出来迎接的时候,田穰苴已经全身披挂,扛着大戟,在火把的衬映下,站在大门前“欢迎”齐景公。还没等齐景公流着口水问大司马都为寡人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田穰苴就劈头盖脸狠抽了齐景公一顿。
田穰苴问齐景公为什么要来找臣,是因为有强敌侵犯边疆,还是有人企图发动军事叛乱?如果都不是,那么,国君找臣干吗来了?齐景公倒是痛快,直说想和将军饮酒取乐,“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将军乐之”。
已经口水直流的齐景公认为田穰苴怎么着也会卖给自己一个薄面,但让齐景公尴尬的是,连这点他认为不是要求的要求也被拒绝了。田穰苴当头砸了老馋猫一棒,而且语出讽刺,拐弯抹角地骂那些宠臣。“国君喜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自然会有人能满足国君的要求,但臣没这个兴趣,国君请回吧。”
齐景公以国君的身份被大臣弄得如此下不来台,脸上自然挂不住,心里也应该记下了田穰苴的这笔“账”。不过此时齐景公还不敢和田穰苴硬顶,真把田大帅惹毛了,田穰苴手上的大戟可不是吃素的。
齐景公骂骂咧咧地离开田府,去找宠臣梁丘据,在梁丘据的府上胡吃海喝,醉得一塌糊涂。估计在席前,梁丘据也没少说田穰苴的坏话,而且齐景公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田穰苴如此不听话,会不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
要知道在春秋时代,大臣杀国君是家常便饭,何况田穰苴还是手握重兵的大帅。而且对齐景公来说,打倒田穰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解除田氏集团对姜氏公族的威胁。齐景公当初重用田穰苴,更多的是一种应急策略,对付燕晋侵犯。现在齐国基本渡过了危险期,再留下田穰苴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讲,齐景公不算是昏君,但也不是什么明君。他不过是齐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表,他最需要考虑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齐国的利益,更遑论百姓利益。
齐景公曾经立志要做齐桓公第二,而且他手上的牌面也是相当不错的,文有晏婴清吏治,武有田穰苴定天下。齐桓公时也不过只有一个管仲可堪大事,没有一流的武将,这也是齐桓霸业主要靠政治因素维持的重要原因。
齐景公已经在考虑废黜田穰苴的问题了,和他站在一条船上的,还有鲍牧、国惠子、高昭子这些顶级权贵。老话常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田穰苴不与权贵佞臣同流合污,共享富贵,那就必定会站在这些人的对立面。
鲍牧等人和齐景公之间存在着一个权力互不兼容的问题,但他们又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所以当田穰苴成为利益集团的敌人时,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打掉田穰苴。
撤掉田穰苴大司马的职务,是齐景公以官方文件形式下达的,但这同时也代表着利益集团的诉求,不过撤职命令并没有说是以何种名义。而这一命令对性格单纯的田穰苴来说,无疑是意外的打击,他根本没有想到齐景公会突然来这么一手。
田穰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渴望得到更大的舞台,比如帮助齐国二次称霸,而不仅仅是守住齐国的半壁河山。田穰苴生卒年不详,但他被解除职务的这一年,应该是齐景公三十年(前518),田穰苴此时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岁上下,他还有时间,但历史认为田穰苴的表演时间到了。历史,本来就是属于少数人的,任何一个企图闯进宴会分蛋糕的人,都会被愤怒地打倒,无论这个人是否代表更多人的利益。
田穰苴失去了所有权力,被废黜在家,没过多久,郁郁寡欢的司马穰苴含恨离世,一代将星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更耀眼的光芒,就带着遗恨划过天空,堕落在遥远的天际。
齐景公和权贵们以为除掉了田穰苴就能保住权力,可他们却忘记了田穰苴的死,直接导致他们和田氏家族彻底撕破脸皮。田氏家族的旗帜性人物田穰苴被陷害至死,对田家来说,这就是公族和鲍、国、高等族对田家下手的政治信号,他们岂能坐以待毙?
就在田穰苴死后的第三十七年(前481),田氏家族的强人田常通过政变夺得了齐国的最高统治权,并以为田穰苴报仇为名,诛杀田氏认为齐国公族中有能力威胁到田氏的人物,以及鲍、晏等大族,彻底控制了齐国局面,为日后田氏代齐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田氏后人为田穰苴报了一箭之恨,田穰苴可以瞑目于九泉之下。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田穰苴生前所著的兵法,在一百年后,由战国霸主齐威王田因齐派人搜集整理成册,这就是军事史上有名的《司马法》。齐威王靠着一部《司马法》,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围魏救赵”,大破魏军于马陵,成就了一番霸业,可见《司马法》的分量。
讲田穰苴而不讲《司马法》,就如同讲孙子不讲《孙子兵法》一样,田穰苴的一世英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传世的《司马法》带来的,下面用一定篇幅讲一讲《司马法》。
《司马法》,又称为《司马穰苴兵法》或《军礼司马法》,共五篇,是宋朝刊定的《武经七书》之一。这部兵法虽然是齐威王搜集编辑而成的,但田穰苴的遗稿成稿时间至少可以肯定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之前,早于《孙子兵法》的出世,可以说《司马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理论支撑的军事理论著作。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司马法》的篇幅不断缩水,现在流行的通本是五篇,实际上在汉朝时,《司马法》共有一百五十五篇,到了唐朝初年,只剩下“数十篇”,遗失近一半。
而到了北宋末期,“数十篇”都不知去向,仅仅剩下了残存的三卷五篇,遗失数量达到了31:1。不过后人能看到《司马法》原稿的三十分之一,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有些古书连书名也没有留下来,湮没在历史的扑天黄尘之中。
论知名度,《司马法》无法和《孙子兵法》相提并论,但自古以来,许多名将和有志于军事研究的知识分子对《司马法》推崇备至,比如司马迁、唐朝名将李靖、明朝大儒邱濬,都是《司马法》的狂热崇拜者。
李靖曾说《司马法》是兵学之祖,邱睿则认为《司马法》的地位应该排在《孙子兵法》之前,而不是仅排在《武经七书》的第三位。到了清朝,更有一位狂热的学者汪绂干脆从新排定《七书》次序,拿掉《孙子兵法》,将《司马法》排在第一。
《孙子兵法》是一部单纯的军事理论著作,为了打仗而打仗,更多的谈论战术细节,很少涉及政治和思想。《司马法》虽然字数不多,仅有三千四百字,但涉及门类极广,甚至包含了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精髓,其中有很大篇幅是谈论政治之于军事的重要性。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对战争的理解往往是“慎战”,轻易不要开启战争,田穰苴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名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司马法·仁本篇》。
残存的《司马法》共分为五篇,分别是《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不清楚遗失的那些篇幅都是些什么内容,但从残本来看,《司马法》更像是一部政治军事研究,而不是单纯的作战法则。
从某种角度讲,《孙子兵法》讲的是军事战术,而《司马法》讲的则是军事战略。有些学者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其实就是田穰苴《司马法》的现代外国版,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这两部一古一今、一中一外的兵书,都是从宏观战略角度解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战争的最高目的是什么,相信绝大多数军事家会给出一个相同的答案:以战止战。“以战止战”同样是田穰苴首先提出来的军事政治思想,在《司马法》开篇,田穰苴就道出了战争的本质——用战争消灭战争。
春秋时代的兼并战争,是从来不讲什么道义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司马法》的整体军事思想相对有些“守旧”,体现的是西周时期的战争观,特别强调政治范畴的“仁”,即所谓非义兵不战。宋襄公子兹甫就是死守着“非义兵不战”的军事教条,结果兵败身死,为天下笑柄。
实际上,田穰苴是最早提出战争分为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的军事理论家,他所说的义与不义的标准,是根据本方的利益立场,而不像宋襄公那样首先尊重别人的利益立场,这是非常愚蠢的。田穰苴所谓的以仁治军,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不是宋襄公那样眉毛胡子一把抓。
田穰苴对正义之战的理解就是杀少数人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包括对他国人民的保护,但对外作战,首先要符合本国的利益。再进一步延伸田穰苴的军事政治理论,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来代替,就是“人权高于主权”。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也不过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幌子罢了。
《司马法》的原文是:“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基础,早在两千五百多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
作为一部兵法,《司马法》谈论具体的作战战术其实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严位》和《用众》,而前三篇讲的都是政治军事,包括军队的思想建设、军纪完整,以及占领道义高地。
田穰苴特别强调“师出必有名”,在《定爵篇》中,田穰苴提出了作战“七政”,即“人、正、辞、巧、火、水、兵”。其中的“正”是指尊重“普世价值”,师出有名,“辞”是指军事宣传工作,要懂得给自己造势,把敌人抹黑成邪恶的反动派,把自己吹嘘成拯救人类的正义大兵。对于田穰苴的这种军事技巧,现代人并不陌生,比如美国就是这么玩的。
有种观点认为《司马法》和《孙子兵法》相比,弱在战术布置,而强在政治工作,并非没有道理。《司马法》反复强调主将要重视对普通士兵的思想教育,要和士兵打成一片。
《司马法》的思想体系与儒家思想有相当程度上的重合,比如孔子常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田穰苴同样提出了“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
所谓与下畏法,就是包括主将在内的所有人员都要遵守军纪国法,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军纪国法之上。主将要普通士兵遵守军纪,自己首先要做到,起到表率作用。否则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到?
现在我们提到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会想到一句名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其实这种观点也是《司马法》最早提出的。在《严位篇》,田穰苴认为“三军一人,胜”。从将军到士兵,大家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不成功的。
如何才能做到“三军一人”,田穰苴给出了两条妙计:
一是“凡战胜,与众分善”,如果军队取得了胜利,主将不要贪功,要把功劳记在普通士兵头上,让大家都有蛋糕吃。
二是“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如果军队打了败仗,不管是谁的责任,主将都要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功劳是大家的,错误是自己的。
在《严位篇》的最后,田穰苴告诫军队主将:“让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只要主将能做到这两点,人心齐一,将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