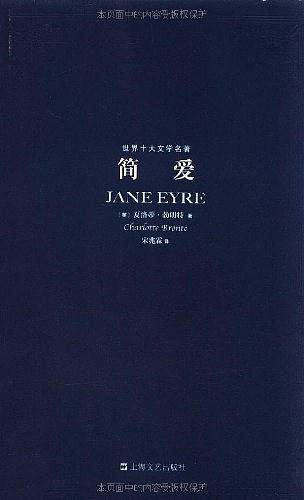第9章
“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话说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家国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16日回省,20日入校,22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祖国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近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祖国,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4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1917年8月23日
8月31日,黎锦熙接到了毛泽东8月23日的信,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趁着周末休息和张昆弟、彭道良结伴外出野游,他们的目的地是昭山。这昭山乃是潇湘8景之一,有“山市晴岚”之称。
张昆弟在他的日记中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这次野游活动的前后状况。这种近百年前的史料,尽管后人读起来有点困难,耐不住性子,但因它极其稀少而珍贵,所以笔者就不忍妄加改写,只好抄录如次了。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日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于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
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边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休息于一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性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
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
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缓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
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
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
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然之。
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张昆弟在这篇日记中所说的“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的话,可能是彭道良一时之戏言耳。后来,彭道良不但没有出家当和尚,他还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多贡献,最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乃后话。
且说9月20日,毛泽东和张昆弟等人一起冒着西北风前往水陆洲游泳。
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不足信哉!”
9月23日,张昆弟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在22日下午及23日的活动: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
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光明思想。余甚然其意。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