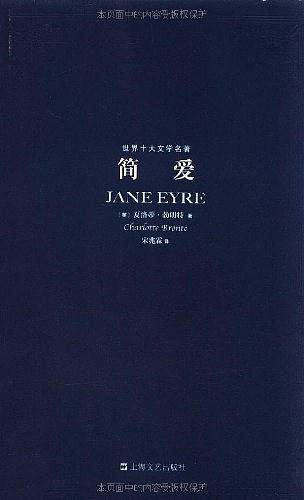第5章
“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话说杨怀中先生逝世后,给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夫人向振熙和儿子、女儿失去了精神支柱及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湖南板仓老家去。蔡元培为使杨怀中先生的灵柩沿途能顺利通过,特地写了一个手札给北大文牍科,要求他们速速办理运送杨怀中灵柩的护照。
1920年2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哥哥杨开智、六舅向明卿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怀中先生的遗体安葬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
杨开慧在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关照下,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李肖聃的女儿李淑一很快就成了杨开慧的好朋友。
湘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她思想守旧,觉得杨开慧这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就说杨开慧“男不男、女不女”,是一个“过激派”。此时所谓的“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贬称。杨开慧轻蔑地笑答:
“剪短发,是我的自由。”
李肖聃先生作为湘福女中的国文教员,自然要保护杨开慧。他向各方面解释说:
“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也是我的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于他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人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由他出面讲情,任是这位洋牧师夫人的校长,自然也不好再难为杨开慧了。
杨开慧后来在湘福女中积极地向同学们宣传民主与科学,号召进步学生冲破礼教的樊篱,走进社会。她还采取各种办法,带头不参加“礼拜”,并向同学们宣传说,宗教迷信是害人的精神鸦片。她把《新青年》、《湘江评论》送给同学们看,还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她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一文,成了师生们议论的焦点。
且说1920年2月19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午后,润之至,谈文化运动方法。”
此时的毛泽东,看到驱张运动遇到了这么大的阻力,知道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取得成功,便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方向及“文化运动方法”这两个方面。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他考虑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如何发展,一是对外如何发展。
在国内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对王光祈在北大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他向王光祈详细了解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他们这一实验极为关心,还亲自到北大参观考察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他受北大工读互助团的启发,也开始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的办学计划。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胡适,想征求一下胡适的意见。他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这个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我们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听了毛泽东的计划,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他说,这样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共产的生活”,则表示反对。他说:
“我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李大钊过从甚密,所以与张国焘也逐渐相识了。他和陈独秀、王光祈、张国焘等人也商讨了工读互助的问题。
在新民学会会员对外发展问题上,毛泽东由于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正思考着出国勤工俭学到底是去法国好,还是到苏维埃俄国好?他在与李大钊商量这件事的时候说:
“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为此,他给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斯咏(即陶毅)的信中,也提出了他所思考的“大留学政策”的“同志的分配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斯咏先生: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地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什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1920年1月成立的进步女学生团体——笔者注)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份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的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指魏璧、周敦祥、劳君展——笔者注)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像你曾说过杨润馀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4人,该团连前共8人,湖南占6人,其余1韩人1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课,不知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民国纪年——笔者注)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通知了在北京的毛泽东。
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王光祈、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出的《上海工读互助简章》、《上海工读互助募捐启》,重申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生活。”
后来,王光祈曾赴德国留学,改学音乐。1936年,王光祈病死于德国波恩。因本传下面很少再提及此人,所以笔者不得不在此做一交代。
且说3月10日,黎锦熙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下午,润之来,久谈解放与改造事。”
3月12日,毛泽东将他所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寄给黎锦熙先生。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驱逐张敬尧后的改良方案。在军政方面,毛泽东提出: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2、军队以一个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他在信中还写道:
“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