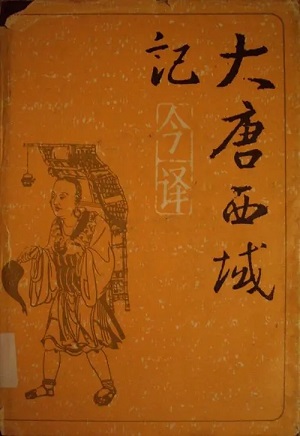再说5月12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戚本禹,通知说:
“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你们,要你和陈伯达、杨成武3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电话就通知了陈伯达,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
“我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你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戚本禹回忆录》记载了他们此次上海之行的整个过程:
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打电话催戚本禹和陈伯达出发。戚本禹、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与杨成武会合。他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戚本禹心里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现在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3小时左右,杨成武一行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泽东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泽东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发给了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要他们先看看这些文件。
毛泽东也是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不久。大概清晨7点左右,陈伯达一行到了毛泽东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但他事先有交代,说陈伯达3人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护士长吴旭君请陈伯达等人在客厅里先坐下,转身去叫毛泽东。
这间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3人沙发,在沙发的两侧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戚本禹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戚本禹想,你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你坐椅子呢?一番推让,最后还是戚本禹坐了椅子。
不一会儿,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了。他通常都是晚上工作,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他和陈伯达3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对戚本禹说:
“好久不见了。”
入座后,毛泽东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戚本禹坐在他身边。此时,江青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戚本禹马上起身让座,请她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以手示意,要戚本禹还坐在他边上。江青在3人沙发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戚本禹叙述至此,在《回忆录》中加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接着,戚本禹记载了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情形和谈话内容: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毛泽东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
“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他问陈伯达等人看了文件有什么意见?陈伯达首先发言说:
“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杨成武说:
“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
杨成武接着说:
“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
毛泽东听了,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杨成武回答说:
“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戚本禹开始发言,他从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说起: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 “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戚本禹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毛泽东插话说:
“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
戚本禹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时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他在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他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他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他复述的战士的话,问道:
“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
戚本禹说,这个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毛泽东说:
“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老残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
“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戚本禹说:
“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这次谈话,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他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毛泽东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这次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让陈伯达3人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毛泽东那儿出来,陈伯达3人就入住到锦江饭店。吃过午饭,他们3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和文件,对毛泽东的批示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5月14日,毛泽东的回批就下来了,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让他们当天上午带回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
戚本禹叙述了这件事后,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就在5月1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林杰撰写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文。文章中写道: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1962年2月22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1962年7月25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作《专治“健忘症”》的杂文。”“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欢喜有人愁。物极必反尔可知?自作孽时祸临头!
欲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情况怎样?请看本传第九卷:玉宇澄清。
东方翁曰:关于党内在文化战线上发生的那些斗争的起因,叶永烈曾经引用过史学家黎澎的一段话。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她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黎澎的这些话,是针对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在文化艺术上的不同立场和观念而说的,无非是要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党内的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永烈似乎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看,如果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话,那么可以说,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颗重要信号弹,而后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则无疑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大决战的宣言书,从而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