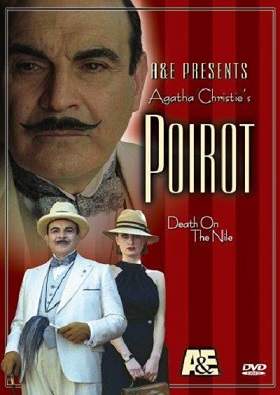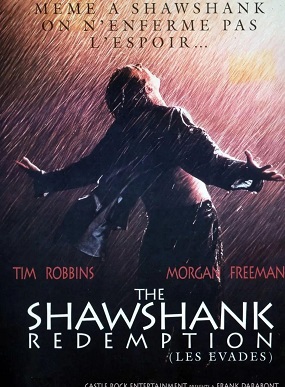河洛要言
包牺氏聪明睿知,见龙马而画河图,则万古文章从此始,千载道德由此兴。中五阐天道之奥,皇极立人道之精,则圣人之功备,而王道之要明。
讲河图,使学者知先后二天,性命二理,阴阳二物,天地二形,男女二精,清浊二分,道以此而显,理以此而明。
河图之数,生于一成于十,而一者数之始,十者数之终,明乎此,则幽明之故,鬼神之理,可得而会心焉。
天一生水,一之为一,起于天地未判之始,清浊未分之前,藏于无极太极之先,太始太素之初,无声无臭,无色无相。
一如鸡卵,清浊具焉,青黄包焉,皆可见者,其中之一气,谁得而见之。可见者,形下之器,不可见者,形上之道,《易》所谓太极也。
一气,道也,即人身一点真性之原,在天谓命,在人谓性,遵行谓道,修道谓教。道谓得其一,万事毕,儒谓一以贯之,释谓守一于中,了性无生。
天,一大包罗也。河图之一,又包罗中之真宰,无上无下,无昼无夜,无四季,其为物不贰,其生物不测,於穆不已,至诚无息。
以形体言之,曰天;以主宰言之,曰帝;以性情言之,曰乾;以功用言之,曰鬼神,其实不过一而已。
一气,道也,一风喻之,风不见,道可见乎?然柳花雪絮,器也,形之下者;舞柳花雪絮,风也,形之上者。身亦器耳,道驭虚实动静,形之上者,悟得虚中实,静中动,则理在是,道亦在是。
太极未分之前,此气蕴于空冥之际、洪蒙之间,一经发动,则阴阳判而刚柔分,动静形而万物化,凡天地间之形形色色,莫不从此而生。
日月气之阴阳,山川气之刚柔,昼夜气之动静,寒暑气之行藏。天地间成形成象,莫非此气变化。
花木未生,一气囫囵,种之于土,受气发生萌芽,而枝、而干、而花、而果,皆一气之精神流露者。
非天之一气,无以成五行,非性之五常,无以显天之一气,知人始可知天,知天必先知人,人与天,一以贯之。
人未生,天主其命。命,一气也。天以一气,而五行生,人得一气,而五常运。识得天之一气,知得人之一理;识得天之五行,知得人之五常,天人之道,何贰之有。
一气,含于胎元,无形无象,直待发动,而后两仪生,四象形,百骸具,五官备。不知天人之原,蔽于六欲七情,则一气竟为形役,无惑乎,明昧而寿夭。
一无形而有形者,为之始一;无象而有象者,为之生一。何先乎生?先生水耳。水为北极之贞,二五之精,乾坤甫辟,而形上者昭其象,形下者露其形。
一气始于北,终于南,所以先生水,由水而递生五行。五行顺布,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水者,从无形而化有形,天道显然,人道易知。人未生时,一气藏于胎元,胎者元之一气耳,气化为神,血化为精,借此一气,混合为形。
形本一气,五行未分,先有一点空虚之气,化为洞彻之形,如银如晶,若蚌珠,若荷露,无形有形,无象有象,先后天之由分。
地二生火,二之为二,形其阴阳。心未动时,犹是一也,心或一动,善恶形焉,理欲分焉,百虑出而情伪见,二之象也。
知二之为二,保一之为一,则可以保其真,而造化莫能拘其数,是以有尽者可固其无尽,有终者善保其无终。
欲求明性至命,先当尽其心以守之,固其精以藏之,养其气以充之,则一气自然凝聚。寸里有主,内念不生,外物不摇。
天一之水,有形之始,地二之火,发情之原,火动也,经云:“火发必克!”人生于寅,木之象也。木以水生,木以火终。水滋则命蒂系焉,火发则寿数定焉。
心原喜静,不静者欲牵之也。欲者,发情之火,火静于一,而动于二,无对为一,有对为二。理与欲对,性与情对,善与恶对,公与私对,有对不一,不一非诚,故曰慎独。
理欲、善恶、公私,不外是非,皆有对者,有对非独,慎独于火发之时,转姤为复,制动为静,则心术可正,大道可企。
天以二运阴阳,地以二成刚柔,人以二发性情。三才之中,以一而始,以二而终,造化之机,生物之理,同归于数。
仁,一也。欲,二也。仁是欲之源,欲是仁之流。先天未杂血气,欲含于仁;后天一杂血气,仁变为欲。仁即欲,欲即仁,第视其杂血气与否,天理人欲所以两歧。
天一之水,未发动则伏于坎,一发动则用于离。离,火也。心,亦火也。火遇火则有动而无静,有生而无藏,是以造化之道,有尽而有终。诚能静而有常,动而有主,则失者复得,去者复来,善明初复,性功自立。
槐,亦植物耳。然发迟收早,是以根坚内实,历千载而不改柯易叶,善藏伏也。使如蒲卢之速,蒹葭之敏,安望其历久远而不朽者乎!藏伏而能长,速敏不能久,是其明验。
初生一阳发动,生于肾而运于心,于是情伪出焉,万绪起焉。好个不识不知,天真变为用巧,用谋机械,昼不伏继以夜,暂不伏至于久。可惜坎中一点真阳,克于离中一点真阴,火气日炎于上,水气日竭于下,无惑乎?气馁神疲,性命不立。
熄火则阳伏于坎,不为离用,此阳在天为命,在人为气、为精、为神,此精气与神,非离中之阴,无以显其浩大,有离中之阴,即以斫其真诚。识得伏之之道,则返二成一,归根复命。
于未发之中,观其如何景况,详审透澈,无喜、怒、哀、乐、忿懥、恐惧,方到无声无臭地位。
人之为人者,理;人之所以不能成人者,欲。知其理而养之,知其欲而克之,自与天地合德。若将天禀之理,杂于地赋之气,则清浊不分,心为形役。
明命於穆之精,纯一之神,在万物譬之。水载舟行,舟不知其为江河湖海,形而下者;操舟者操于水面,知水之为水,形而上者,操则存。
天三生木,天者,一气之总。名三者,在天日月星,在地水火风,在人精气神,莫非此气之运之动之存。
日乃众阳之总,月乃众阴之宗,星乃日月之余辉,分而观其象,合而为一理。故《中庸》曰“为物不贰”,又曰“日月星辰系焉”。
日者,太极黑中之白;月者,太极白中之黑。皆一气也,惟动静不同耳。月映日以生辉,日映月而得魄,冬夏二至所由分,日夜长短所由判,晦朔弦望所由始。
星各守其垣,经纬交错,时序流迁,惟视冬行北陆,夏行南陆,故寒暑不一,春秋不同,皆一气运转。
一气在天地间,无形无象,无声无臭,真精中一点真气,所谓中也。
中者,无天地之前,此中少不得一分,有天地之后,此中停不得一息。此中一停,则日月不明,星辰不运,万物不生,所谓天行健,健,中也。
中在天地间,气息亦归主宰。无中,则天地亦一形壳耳,何其若是之神明广大高明。
天不离乎三,三实出于天,而三又出于一。三有象,一无象;三有形,一无形。
河洛象数之已形者,能于有形上寻无形,则性命之原知,而河洛之真见矣。
河洛之真,大而含天地,小而藏黍米,物物皆有,人人各具。
河洛之真,喻之风,风有声;喻之木,木有形;喻之水月镜花、蜃楼云峰,皆有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果何喻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
“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乡有本乡,乡有故乡。《大学》言独,乡中主人,《中庸》言诚,乡中实际。时习是功夫,仁义是体用。
天之象,日月星;地之象,水火风;人之宝,精气神,三才一贯,天人一理,无二致也。
风不动,则物无以散;火不动,则物无以暄;水不动,则物无以润。分观之,其象各殊;统论之,其妙则一。
风者,无形之火;火者,有形之风。风与火,其象殊,其用一,不离乎天乙之水。水之气发而生火,火之气散而成风。
胎元先禀,一气生水,水生气,气生血,血凝五官百骸,从中发神,神发精,精发气,周而复始,循环无息,造化见焉。知天知地,而后可以知人,不知人不知精从何来,气从何化,神从何生。欲求原始,返终归根,复命能乎!
精气神,身之三宝,是谓大药。大药中之真。人未生时,浑然于天地之内;人既生后,来往于动静之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似气非气,似精非精,神则似之,又非神之可测, 《诗》曰: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精气神,得乎天者言之,不过是日月之精华;得乎地者言之,不过是水火之精气,风化之妙道耳。
精气神,妙感于无极之中,太初之始,成象成形,造化遂显,人事遂兴,是谓无形化有形,无象化有象。
昧其来由,迷其觉路,不从先天寻真机,转向后天从私欲,可惜者正自不少也。
欲求上乘之理,必待上智之姿,明乎阴阳,彻乎造化,认得根由,识得来路,自然外物不摇,内念不起,养到静而极静,安而极安,见无形中之形,无象中之象,则阴阳在抱,造化在手,可得大药。
只凭凡体凡眼凡心,一善不行,一德不积,即欲明其阴阳,夺其造化,而成大丈夫,难矣!
精气神,本于日月星,水火风。水火是精气之母,星辰是元神之母,人乃天地之聚,天乃人之散者也。
太处说,曰天地,小处说,曰人。何以大视天地,而小视其身?故《中庸》首言天终,亦言天正,使人知根由识来路耳。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人生之理,一健一顺。故孔子曰: “吾道一以贯之。”老子曰:“得其一,万事毕。”释迦佛曰:“守一于中,了性无生。”
识得为物不贰之物,则不同者可以同,有异者即无异,彼天赋之良,乃不同中之同,有异中之不异者也。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此物在人,具众理应万事者,乃为气禀拘于有身之初,私欲蔽于有身之后,故诚者不诚,而明者不明。
诚者不诚,明者不明,无惑乎。有物而不格,有止而不知,此物在人身,至虚至灵,毫无渣滓,故往圣俱言明德明命。
明德明命,本是一贯。动而有象,静而无形,有形原根于无形,无象能生乎有象,非有形为有形,无象真无象。一动而见,无形而有形;一静而寂,有象而无象。
神,一物也,未杂气禀曰元神,已杂气禀曰识神。第视其先天后天之不同,非有二也。
欲知先天,先求来去,识得来去,即知先天。既知先天,先保其精,后养其气,精气既固,神而愈神。
精气犹乎日月,而神乃其光也。质不聚,光何生?光欲生,先聚质,此其象也。
精气神三者之中,神为第一。神凝则气固,气固则精足。精气既固,神明不漏,而丹结焉。
聚者气,而所以聚者非气;散者气,而所以散者非气,一言以蔽之曰神。
神无形而有形者,从兹始;神无象而有象者,从兹生。生也,始也,总不离乎神。可坏者识神,不可坏者元神。坏于有形之形,不坏于无象之象。欲无形而见有形,欲无象而见有象,得其无形之形,得其有象之象,斯为上智。
求跻圣域,必先立定脚跟,壹志向上,打破一切幻境,初而勉然,久而自然,渐到返本境界,超乎凡壳,自得真乐。
现在尘寰久已,气拘于前,物夺于后,觉得眼前景况,俱是现成快乐,自家性命,视为渺茫事业,就正嫌苦,修为嫌烦,熟于欲而昧于理,精于此耗,气于此散,神于此荡,不到尽处不止,譬如蛾之赴焰,蝇之赴膻,乐乎!否乎!
性命之道,如剥蕉心,去一层更有一层,非一层而可尽,亦非一层而可止,即河洛之理,正以示人于明处指点耳。
诚字较静字深,以境言之;富贵贫贱非诚,难必其不谄不骄,以心言之;喜怒哀乐非诚,难必其不偏不倚;推之尽性至命非诚,难必其希圣希贤。
《中庸》一部书,教人学一个诚字,乃性中之实际也。天以诚而覆,地以诚而载,圣以诚而治,物以诚而化,心以诚而明,不诚则流于虚寂,成何学问。
一,在天为健,在地为顺,在人为仁。仁者,生人之本也,大而天地莫能载,小而一心所自具,千经万卷,形容不尽。但能体察欲之斯至,先寻天理,得见天理,自知所止。
事事敬循天理,知有所止,自然外物不摇,然后定静安虑,悉见分晓。所以《大学》开章,未传格物,先传知止。
知止即格物。物何以格?非慎独不能格。故曾子以慎独谆谆告诫,使知入学门户。朱子恐人流于虚无寂灭,补出格物一章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知字即物字,知物焉有不止于静养之时,主一无适,久而久之,自有豁然贯通妙境。
经传未尝发明精气神,然精即智也,气即勇也,神即仁也。故道经谓精非交感之精,气非呼吸之气,神非思虑之神。精也,气也,神也,即三达德也,贯于大本之中,太极也。太极即一,太极即中。
抱一,抱其无妄之真,而不为私欲所夺;守中,守其秉懿之性,而不为习俗所牵。圣曰时习,曾曰慎独,颜曰不违,子夏曰无忘,孟子曰有事,程曰静存,朱曰主敬。读书人不知格本身之物,徒于经传寻文意,谬矣!
慎独之功,于机未动时,抱其一,守其中,一诚不动,如月之空,如镜之明,如水之澄,如山之静,无一点渣滓。一发动,自然好恶中节,中和于此而致,万物于此而育,天地于此而位,生生化化,神变莫测,皆一中之所推。
地四生金。地,坤位也。四,先天震也。坤本西南至阴至静之方,养性养到极静之际,如西南得朋之乐,由晦朔而望弦,日新无间,私欲净尽,天德流行,自然如镜之照。瞻若月之当空,何事不知,何物不明,众理贯通,是谓格物。
法象上求至道,文章内求训诂,不知极之地,善之处,心妄动,意妄驰,不求其诚,不求其正,无惑乎!出入无时,操舍无向,人禽之界无从而分,舜跖之品无从而辨。
诚意,越人鬼之关;正心,跻圣贤之域。善由是明,初由是复,自然西南得朋而见月。月者,性之体,命之根。未明性于月,焉能会其明性之功;未立命于月,焉能得其立命之术。上弦下弦,比理欲之消长;一晦一望,喻乾坤之复姤。
得朋之理,何以在西南,为是后天坤位,先天巽位也。巽,风也。《丹经》曰:“鼓巽风,用坤火。”在后天寻有象之风,故用火在坤;在先天寻无象之火,故鼓风在巽。西南月之得魄处,犹人之身心俱禀于天地。循理,则身心可修;味理,则性命安识。天理本是自己故物,同于故友,理明如故友重逢,是谓得朋。
欲修性命,先立大仁大智大勇之心,将气质化尽,天理复明,静极之中,忽有一线之明,从本原中现出,愈进愈明,愈修愈显,修到圆明大觉之时,如月到中天,空空洞洞,澈上澈下,自见性天。到此地步,更进一层,再求向上功夫,不致虚寂无实,安于小成。
艮之止,坤之复,得朋之门径也。曾子闻道之后,夫子授与《大学》,说出知止二字,将《易》理一言道破;颜子得道之后,将“克复归仁”四字许,颜子分明将复字提出,使人知复知止之义。
四勿,使人知耳目口体皆阴,惟仁惟理是阳。却阴返阳,无一毫私欲,无一点妄心,即是返本还元。
经云,若要人不死,须得不死人。天理在人心,无古今,无上下,无老幼,无圣凡,无形象可指,无声臭可寻。得之者,千圣比肩,古今一旦暮耳,又何生死之可言哉!是谓不死之人,至刚之体。
求道之心切,守道之心难;守道之心易,得道之日难。难不难于功之次第,难于路之邪正,得其路方得其门,得其门斯登道岸,静字即门也。
静字,人人皆知,未必真知。欲知静之为静,先求动之为动。静者动之基,动者静之迹。静本无形,而动乃有象。欲知无形之静,先观有形之动。动能制静,岂有不安!
内而目欲色,耳欲声,鼻欲臭,口欲味;外则欲位,欲禄,欲名,欲寿。以百年有尽之身,动千载无穷之想,以致精疲力衰,欲其明善复初能乎?惟静足以收此无穷之想。
去一分欲,静一分心,初而勉强,久而自然,自能知其所止,然后此心不动。
欲求静,先制动,动而动收,来即静。若不能静,将此身藏于先天之内,自然渐渐收敛。
日新日新,久而久之自然认得自己真性。既见真性,方知天地间外物是假,自家性命是真;既见真性,不暇外寻他物,不求静而自静。
先破外物,后虚其身,既虚其身,更守其心,人心一退,道心自生。象外有象,身外有身,视富积万镒,贵登八座,相去天渊。
冥心默坐,非所谓静,私欲不挠,乃所谓静。果一尘不染,非大智大仁大勇而何。
三大德,非静不能入,非净不能守。欲静先净。内净其心,七情不动;外净其身,六欲不挠。内外交养,仁在其中。
内净其心,居仁由义;外净其身,四勿为法。先净其身,后净其心,身心俱净,乐水乐山,乐在其中。
言乃心之文章,字字斟酌,庶无鄙俗,一言可出,择而出之,一训可训,忠以训之。不发人之阴行,不道人之恶迹,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四海之内,谁非兄弟。净其言,言必中,自无口过。
身乃父母遗体,天地所毓,师保所教。不交匪类之友,切磋有功;不践是非之场,牵连无因,而足净矣。不睹非礼之色,不看邪淫之书,心绪不乱,而目净矣。欲净其耳,闻丝竹不如闻嘉言,闻笙簧不如闻圣训。闻其有声,不若以无声之声闻之;闻其无声,须当以有声之声会之。守其天君,除其六欲,一净而无所不净,是谓不净之净,乃为真净,非以洗濯为净。
静净二字,非靖无以致其功,非靖无以致其效。静中不靖,虽静不静,静中不靖,即净非净。静中持一靖字,净中有一靖字,自然心有所主,私欲不生。
内念一起,靖而靖之,外物一逐,净而净之。靖无可靖,净无可净,静字自然发见。
处事,不偏于好则偏于恶,不偏于情之所在,即偏于私之所夺,时时抱定靖字,则七情自正,六欲不生。
胸中抱定靖字,富贵能守礼,贫贱不慑志,甚至患难颠沛,一心有主,何事能迁,所患者无恒耳。
果能静亦靖,动亦靖,养至靖无不靖,自然从容中道。
静净靖,三德之根,九经之本,浅视之,日用之地;深窥之,性命之精。
道曰精气神,就五行上言,犹有渣滓。儒曰智仁勇为五常之德、五行之精,纯而无疵。
三德在五行,智乃水之精,仁乃木之精,勇乃金之精。道云金木间隔性功之中,金木为要。子曰仁义,孟子亦曰仁义。道之炼神归气,炼气归神,金木归一,即儒之仁以义正,义以仁辅。不明于儒性不明,不明于道命不至。性也,命也,相依者也。
尽性而不知至命,非学也;至命而不知尽性,亦非学也。儒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道曰,性体原来如月明。
气之精曰命,理之精曰性,阴阳之本,形气之原。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其中至精至粹,无形无象,流行不息。生化无已者,命也,人得之,曰中,曰仁,曰德,曰诚,皆性也,在天为造化,在心为经纶,谓知觉运动,为性则非也。
知觉生于灵明,运动生于气血,乃后天之渣滓,非先天之本性也。先天本性,五行中之精粹,五德中之纯一,显之于心,藏之于密。其未发也,无声无臭;其既发也,有物有则。 《易》曰: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谓良知良能。
命之理微,有生死之命,寿夭定焉。有气数之命,穷通定焉。气数之命,根于生死之命,生死之命,囿于气数之命,操于天者半,操于人者半。天未与我权,在天;天既与我权,在我。
不知立命之法、修命之功,自失其权。诿命于天,愚命也,求进欲明。柔命也,求进于强,以及躁也而静,质也而文,未始在天者不可化于在人,在人者亦可以回夫天。
生死、寿夭、穷通,得丧其有定耶?其无定耶?不知立命修命,愚者自愚,柔者自柔,躁者自躁,妄者自妄,无惑乎流于污下,而不能上达也。
天五生土,合形与气,贯性与命,合四象而言无形无象,得之者,一中有五,二中有五,三中有五,四中亦有五,而五乃四象中之中气,譬如四时中之土旺,四德中之性诚。故圣训曰: “主忠信。”道经曰:“全凭戊己作根基。”又曰:“要用黄婆作媒翁。”
先天者,后天之母;后天者,先天之子。母生乎子,子食其母,自然之理,诚实之道,即如天五生土。土者,脾土也,属后天,土中真阳由先天。先天者,坎中之一,水中之金,结胎先肾而后脾。肾者,脾之母。脾者,肾之子。肾气旺,脾气亦旺,肾气衰,脾气亦衰。
肾足坎中之精,心运离中之神。有离中之神,始能鼓呼吸之气,气依于神,神依于气,神气交动,而胃中之谷化肾中之水。泻水,谷化而不息,神气运而不休,日复一日,岁复一岁,自得长生。
坎中之火如油,脾中之阳如灯,有油则灯明,无油则灯灭。坎中之阳如火,脾中之火如鼎,火盛则鼎沸,火尽则鼎冷。人知脾之化谷,膀之泻水,而不知所以化谷泻水者,非脾非膀,实根于肾中之火,即坎中之阳。坎阳肾火又何以不息,实根于左肾之气右肾之精,即命门三焦也。左阳长,右阴生,资谷食津液以养其胃,分润五脏百骸,故古书云,有胃则生,无胃则死,脾绝命绝。三焦曰命门。
既发明后天生死之根,而先天性命之原再递及之。先天之性命,在无形无象之前;后天之性命,在有气有血之际。不修先天,则后天无以保;不修后天,则先天何以固。先后二天,相因而不相离者。
人死先散后天,及于先天,先后俱散,气理始尽。何以见后天之散?人生五行具于五脏,目得肝而明,耳得肾而聪,鼻得肺而出纳其气,口得脾而辨别其馨,五行之气聚五官之运灵。
私欲纷起,百虑横呈,以致肝散而目不明,肾散而耳不聪,肺散而毛脱,脾散而食减,此后天之天五散也。
先天乃无声无臭之物,百骸五官依之为主,五行五脏赖之为君,乃生死之根,造化之枢。后天之散,犹可药;先天一散,无可医。
先天者,五行之精,一元之本,人有之,物亦有之。人与物,清浊偏全之别耳。仁主生,义主当,礼主节,智主明,而信贯四端,真实无妄,周流不息,如土旺四季,各得其主,实五常之精,五行之本,五脏之原。此气不散,则物物不散;此气一散,则物物因之而散,较后天为最切。仁气散,则刻薄即生;义气散,则羞恶不起;礼气散,则名分混;智气散,则是非淆。仁无信而不存,义无信而不集,礼无信而不执,智无信而不明,此先天之天五散也。
不修后天,身不固;不修先天,性不明。先后皆修,而始可以闻性命兼修之道。
道无象,在天日月星辰象其象;道无形,在地山川草木形其形。天大而无穷,日月星辰可得而穷之;地廓而无尽,山川草木可得而尽之。欲知道之为道,先求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
道有体有用,道有形有理。知其体,则存养无虚;知其用,则省察有要;知其形,则无物不有;知其理,则事事皆然。一动一静莫非阴阳之理,一呼一吸俱是造化之精。河洛中五之中,体也;一三七九、二四八十,用也;东三南二、北一西四,形也。惟中五之中之理,无形无象,无声无臭,主宰于不见不闻之地,为物不贰,生物不测,易曰黄中,道曰元牝,释曰净土。彼虽无形,而有形者依之生;彼虽无象,而有象者赖之长。寻得此理存而养之、省而察之,经纶参赞,自可推而行之。以呼吸为养气,坐静为养神,绝欲为养精,郛廓也。
道在天地,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平庸则在日用行习之际,广大则在位育参赞之间,圣不离,凡亦不离,草木禽兽皆不离,其形象即河洛之五中已言之。而体在天地曰上天之载,在人曰未发之中,此中具众理、应万事,尧舜揖让、汤武征伐、老子五千、牟尼三藏,一言道得尽,千卷说不了。儒曰性,曰命,曰一,曰中,曰诚,曰敬;道曰元,曰牝,曰戊,曰己,曰黄婆,曰中宫,曰谷神,曰主人;释曰舍利,曰慧光,曰自在,曰净土,曰佛国,曰莲花。
此中未发,无声无臭;此中一发,有象有形。喜怒哀乐中之动,礼乐文章中之著,圣贤执之而顺理,凡人违之而从欲。
凡人违之而从欲者,此中即天赋于人,有善无恶,乃不知保其至性,陷于情欲。目欲色,耳欲声,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久则习为技巧,愈染愈深,总在外面费心思,不在内里修正果,流于污下而不知,入于禽兽而不觉。
圣贤执之而顺理者,有身以来,本性不迷,天真不丧。格物以明其理,致知以养其灵,诚意以严其自欺,正心以端其好恶,甚至克其私欲,复其天理,不到尽性至命,时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及到物格、知至、意诚、心正,参天地,赞化育,自然饭蔬饮水,箪瓢陋巷,有乐无忧,无入而不自得。
人皆境遇所累。贫贱,日营生计;富贵,日纵贪求。少壮以至老死,总觉境遇是真,性命是假,不知生是谁来,死是谁去,境遇可能随来去乎?
无怪乎有眼能视,则色界实;有耳能闻,则声韵实;有口知味,有鼻知臭,则口欲鼻欲,无所不实。外而习之,内而养之,以外诱内,以内随外,以致禀来真气化为后起私心,小体用而大体退矣。
果能穷理尽性,内里养出实际,则外面一切境遇尽如浮云,富贵何加,贫贱何损,仰不愧,俯不怍,无疑惑,无恐惧,当生而生,生无可喜,当死而死,死有何惧,是谓大丈夫。
天地间,暖日多,寒日亦不少。何世之求暖者多,安寒者少?有寒即有暖,有暖即有寒。暖而知寒,寒而不凋,寒而得暖,暖而不热,是为无心,无心即道。
万卉争妍,梅则隐于幽岩,及至霜零雪降,始得天心,显其生意,另有一段真气味、真骨格。凡柳媚花明,归于寂寥,方见花中之魁。物尚如此,人能苦一日,炼一日,受得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否则心智何以明,气节何以坚。
知境遇是假,性命是真,养到明善复初之后,始信圣训有益,真学不诬,自登彼岸。
求道心法,目之所见,见而不见;耳之所闻,闻而不闻,不识不知,何思何虑,其心自与太虚游。
知境遇是定数,道德是天性,不为境遇丧天性。知有小体,更当知有大体,既知大体,则大体不能役其人。理欲之界,小大之体,一致两途。
能将心性认得真、守得固,日新又新,复而更复,明命明德,确有实际,始知境遇何足累。人不入禽兽之境,则登圣贤之途。
至贵,天爵也。功名富贵不过养其小体,安能益其大体?为养小体,致坏大体,愚也。
生前之日月有尽,死后之声名无穷,何必以有用之身堕无涯之欲,凿本真,丧天良,未必即得,即得之,焉能常享!
得一层更求一层,遇一境更望一境,何日是卸心之期?何时是知命之候?醉里生,梦里死,虚天地所生之身,失乾坤所赋之理,活一世不如不活。
古往今来,世事思一番,更体一番,始觉纲常名教是真,身心性命是实,看得开,信得及,守得固,习得熟,觉得理长欲消,德充私退,自破愁城,入乐国矣。
身中尽为私累,心内尽为欲夺,安宅正路,谁居之,谁由之?自暴自弃,朽木粪土之诮,知其难免。
宇宙内以何为要,只是求其无愧于心可耳,境遇听其自然。夫无愧于心,即无愧于天;无愧于天,生死尚然不惧,彼区区之境遇,又何必萦于心介于怀。
体用合一之道,体者,一也。喜怒未发之中,阴阳未判之始,天以一而生物,人以一而立命。
一之为用,阴阳、刚柔、动静,消长也。盈虚进退,无非此一之发动;吉凶悔吝,无非此一之形容。
一无形,而有形者为之始;一无象,而有象者依之生。春夏秋冬,体中之用,生长收藏,化中之成,体不可见。而春夏秋冬于不可见之中,偶一见之,化不可形;而生长收藏于不可形之中,偶一形之,不知者为四序,其知者实一理。
一中,太极未画之前,八卦未书之始,天地间停停当当,有个一在,有个中含。
一,动也,阖辟形而声音出,动静有而造化成。以及象也,而尽于方圆;色也,而尽于形气,则乾坤之成形成象,资生资始,莫非以一而尽,以中而始。
一不可见,而一之发动,未始不可见;中不可知,而中之造化,未始不可知。有形可以会无形之体,有象可以寻无象之原。
无形之体,乾坤之化育;无象之原,圣贤之经纶。不精以察之,故不明;不一以守之,故不行。
此一元,在太素之始,太极之先,不动不知,一动即知,不发不明,一发即明,物物俱有,人人各有,在善悟者会之,善体者行之。
体用之道,天人俱具,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在一身,暂于瞬息,凝于动静,莫不有此,知之则希圣希贤,不知则为愚为蠢。
一是生人生物,真宰作始作终,物事欲求此理,须在无声无臭之间、不睹不闻之地,非静不知,非动不晓,一动一静,真机露焉。
人不知人之为人,是以不保其人之真。欲知人之所以为人,先观古之所以为古,上古之人何以寿而久,当今之人何以夭而札。上古民质风醇,不甚摇精,不多伤神;今人万事劳心,无端凿精,百虑耗神,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天札所以不免也。
抱定真元,守其至诚,扫尽外缘,不涉内念,主一无适闲邪,存诚五事三德,一以贯之,炼有形归无形,炼有象归无象。浑浑噩噩,如太素太初之始,然后有物有则,勿助勿长,养成浩然之气,乾健之体,是谓至命。
血肉躯壳有形有象,天下岂有有形象而能长久不坏乎?惟无形象之物,藏在血肉躯壳之中,如金中之铅,石中之汞,阴阳常姤,坎离时交,犹如结丹一般。不知至命之理,搬运血肉躯壳,是谓抱梁柱、哭日食。
立勇猛之心,定有恒之念,气凝神合,炼归一处,天理同归。一处私欲,看在一边,久而久之,博文约礼,归于一贯,为贤之本,作圣之功,于此可企。
道本不能一蹴而及,譬如登高必自卑,诚能识得及守得定,以有恒之心,求无尽之道,日新又新,毫无间断,自然尽心尽性,则知天矣。
知之明,行之力,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非毁誉,生死患难,临之不动其心,守之不二其念,方为真人品,真气节,谓之不动,真不动矣。
人生天地,原是依此刚大之体、健顺之气,立于宇宙之间、名教之地,何私可挠,何欲可破。乃自嗜欲一开,人心用事,道心退藏,七情频夺,六欲常引,则聚者散而凝者消。诚欲养此刚大之气,先从静字立基。
事来时,应之以精详;事去后,守之以混沌。不识不知,何思何虑。存想无极之始,太初之前。念未动,静观夫未发之体;念一动,精察夫中和之用。果然静存动察,不使私欲微动于隐微,暗长于方寸,久而久之,曰有活泼之机,如泉之达,如火之然,流于心目隐约之间,不可进锐,不可退速,日省又省,日新又新,乃是立命时候。诚身光景至此,再言进境,更上一层,雷复地中之象,可得而会心焉。
人心不动而欲动之,人神不动而私动之者,不迁于心而迁于气,不迁于气而迁于境。
富贵贫贱,原有定数,蔬食饮水,箪瓢陋巷,日不举火,纳履踵绝,世岂少哉!一心求作圣贤,心不苦,识不明,境不苦,力不定,贫是炼心炉,贫是试金石。
厌贫之心,败名丧节之渐相依,日流于贱而不觉也。然人之所欲终不免耳,厌之而能不贫乎!故千古圣贤,造次颠沛,何尝一刻去仁。
贫为美德,守得贫,则忠孝节义之事皆从此中做出;守不得贫,则败名丧节之事亦从此中生出,故贫者天之所以困人,正天之所以成人也。
常观子史,往古世事,龙争虎斗,合纵连横者,谁得实际,今安在乎?还是忠孝节义者本性犹在,不求名而名,与日月争光,不求利而利,与山河并永。
古来大聪明、大智慧、大气力英雄,莫不为小体所累,俱以圣言为迂,故不能下学上达。
道虽至简至易,然亦至精至微,贤如颜、闵,亦有知不及、行不能处,在人所到境界以分道之高卑,然亦道其糟粕耳。其精微者,还当自悟。
言道,如画水者,不能画其声;画月者,不能画其光;画花者,不能画其馨;画果者,不能画其味。道在眼前,人人用之,人人未必知之,知之而未必行之。实在看到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究到原头之地,本来之方,物不离,人不离,彼不离,我不离,天人万物俱不离。天即我,我即天,则天人合德矣。
天人看成一体,自然见其大,不为小累。生死之根明,性命之理得,有求即应,有感斯通,自然心不动,而欲何能牵!
人生于世,无人不在梦中回思未有身之初。混元一气,安有思虑之衷!赤子之心,那有知识之妄!与天合一,与圣同真。毋意必固我,可动可静,可安可止,不惟清者之欲无,而浊者亦无欲矣。
思其所思,思无所思,而犹思其不必思,不能思。思到终老,仅仅一线灵明,尚复惺惺不昧。一思往日所为,俱在梦中,未来时未入梦,既去时始觉梦。
过去是虚,未来何实。虚虚实实,一场大梦。早觉是梦,便不是梦。无梦始可明善,无梦始可复初。不生勇猛心,何以破大梦,不破大梦,不能真静。
谁不欲破此大梦,看不破,故不能破。能知尘世一切幻境,皆是虚中法相,有何实际,曰破此关,得过且过,不存一点尘垢,专保自家灵明。保之又保,见得真,守得定,则外缘不求破,而自不纷扰,何必深山穷谷,徒守孤静。
人心一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情之欲也。有身即有心,有心即有欲,有欲即有情,有情则静者而动,诚者而妄。欲明其道,先化其身,后死其心,将此身心,看作一物,并不是我。神之来,不居于此;神之去,不由于此。昧时惺惺而退藏,动时静静而潜伏,如虫之蛰,若水之谢。外不见物,物不得而引;内不见己,己不得而诱。此身寄在大小之间,此心藏于动静之介,化有形而归无形,化有象而归无象,自此以后,无中生有,乃为真有。庶乎身外有身,天外有天,徒守血气用工,不免随灭随起,随静随动,一念生而众念附,一欲兴而各欲攻,抱薪救火,何济于事。
天乙生水,地六成之。天乙之生,无形无象;地六之成,有物有则。天一之水,充乎宇宙,贯乎古今,无上下,无东西,充仞于太素太初之中,洋溢于在左在右之际,鸢得之而飞,鱼得之而跃,活活泼泼,至神至妙,不贰不息,惟性命源头生化主宰。《书》曰:“顾 天之明命。”已说破真机。真机者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从此无形无象之中化而为有形有象之物。
地六者,有形之形;天一者,无象之象。因无形,故曰生,因有象,故曰成。有生始有成,有成始显生,生成之理,归于一。故《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若无形象,得《易》之道矣。
天生也,地成也,所以生之成之者。譬如春柳夏槐,秋菊冬梅,谁为主宰?若无主宰,梅不可夏,菊不可冬乎,各因其性耳。然物之性,亦天之性。无四序,则生气不显;有四序,则天道始成。无四时之前,性其一也。
人未有身,性无所著,既有其身,性有所役。性贵乎?非性者贵乎?性既贵,何得转为非性者?所役非性,身也。知其性,而不知非性之性;识其命,而不随非命之命。性之性,不识不知;非性之性,欲食欲色。命之命,无人无我;非命之命,有此有彼。得乎性之性、命之命,则一气混化,无我无人,无彼无此,一以贯之。
天下之大,尽于天地二字;古今之富,尽于一六二字。人本天地所生,真一之气,受于胎元,无形无象,圆明一点,孕于黄中,然后血气始凝,借山川之气成形成象,木气成发,土气成肉,石气成骨,水气成血。此后天之成,因于先天之生。非生无以知成,非成无以知生,生成之理,有体有用,有内有外,有大有小,虽在后天,说实乃先天之显相。
天之造化,生物生人;人之造化,为经为纶。乃自有身,累于细微末事,致失刚大本体,甚为可惜!
天一之水,形之于地六之火,水火交而成形,水火离而落魄,聚而散,散而聚,无端倪,无古今,在人之识与不识、修与不修耳。
人生在世,那一件不是散的事,那一息不是散的时,认得六一之理,生成之道,将散者使聚,离者使合,何性不复!何命不立!
内而六欲,外而六贼,伐性之斧,戕性之根,是谓六阴克一阳。外识六贼,内去六欲,自然阴尽阳复,何患性不明,命不至!
小体抱得紧,大体看不着,只去阴上行阴果,不在阳上求至道,浑浑默默,欲上达,难矣!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动物也,在天象日,在人象心。心之为心,无息不动,无处不动,动无休息,不收之以静,非成也。
天七属艮,天乃艮上一阳,藏于心中,原来活活泼泼,无一息之停留,惟有艮以止之,则动者可静,而不息者亦可休。《易》曰“艮其趾”,惟曾子得之象,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黄中至善之处。故曰正位居体,美在其中。
地二之火,非天七之艮无以静之、无以成之。火在心中,忧惧从此出,哀乐自此生,甚至好恶皆由此发,有时宜动,而动固不休;有时不宜动,而动亦不息。火此象而心亦此象,必用天七之艮以止之,则动者静而焰者息。
艮止之法,一心守定黄中,切重四勿,和以处事,求其中节,养到心如明镜、如止水,胸有把握,何欲可挠,何私可动。久之,如山之静,如水之澄,如月在天,如云归岫,圆明洞彻,是何等景况,何等胸怀,岂非不动心之大丈夫哉!
看破已往之境易,看破未来之境难。明眼英雄,谁不知性命为切身之要,其如不知天外之天、身外之身,以富贵、贫贱、毁誉、是非一切尘缘幻境,刻刻挂心,随灭随起,随惺随昧,虽说认得大体,却又不丢小体,何以明善复初,与贤圣比肩哉!
果能正心修身、存诚主静、拔本塞源、喻义成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千载作舟揖,往者可继,来者可开,不是至诚圣人是谁?
圣人者,参天两地,中立而不倚。如河洛之理,贯乎三才,周乎万物,在人为性命之精,在天为造化之本。在天在人,易知易从,平平常常,并无他奇。乃以造化为精微,性命为奥妙,转于高远处求,不从切近处思,愈求愈远,愈怪愈失。
人不能成圣,火而已矣;天不能无憾,亦火而已矣。人之火不息,以艮止之,天之火不息,亦以艮止之。春生夏长,秋为白藏,冬为元英。冬之藏,所以养春之发、夏之长、秋之成。天之元气,非冬之藏,则生机息而造化停,欲其生生化化,无疆无尽能乎?天不静,无以为天;人不静,无以为人。人也,天也,一静而后有主有常。
能静而基立,基立而道生,道生则用妙,用妙则造化可得。空守寂静,无济于事。
邦畿千里,止之所也。缗蛮黄鸟,止之知也。穆穆文王,止之善也。菉竹猗猗,止之功也。《大学》不言格物,先言知止,能知其止,格物即在其中。不能知止,何以格物。
圣贤立言,先言敬,言静,言诚,言德,言仁,言时习,言有事,言无忘,俱教人入门知止处,圣功基此王道始。此体虽一,而用不同,其实一理,化育不离此,参赞亦不离此。
河图中五,心之体也。天七之成,功之基也。万物坏于动而久于静,静者,万物之所成始而成终者也。
静净靖,即是知止紧要功夫,犹如程朱补出格物一章,即是心法。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阳也,三阳属也,阳中之阳也。地,阴也,八阴属也,阴中之阴也。有老阳以生,必有老阴以成,此乃阳中之阳以配阴中之阴。阴阳相配,而造化见。
天德在人,阳中之阳;身体在人,阴中之阴。有此阴中之阴,必有阳中之阳。阳中之阳,飞扬难制,汞象也。故曰,木阴中之阴,铅象也。故曰,八八者坤,属坤者,老阴也。阳非此阴以收之,而胡以得成?坤譬于釜,乾譬于汞,汞在釜中,飞扬难制,必须密封其口,坚固其顶,始可用火炼之,而金丹可结。此天三之木,即人之精气神也。
坤八之数,即人身声心意也。坤则象土,八则象意,土意而知,则三家相见,而三家可制矣。天三,象三家。木象三家之飞扬,有地八之静以制之,则龙降虎伏,自然归于鼎中,用吾之真意以制之,则飞者不妄飞,而扬者不轻扬矣。此时自有一番把握,炼之而久,则聚者常聚而不散,合者常合而不分。虽有七情之感,六欲之挠,亦不害其天真,伤其元气,谁谓三家之不成哉!神仙之术尽于此矣!
此三段,乃道家金丹之理,用真性、真气、真元以炼之,则性明初复,不致惑于旁门。
天三生木之道,地八成之之理,天三象三家,地八象八识,三家与八识,分其体用,连其本末。本非末,无以成其本;体非用,无以见其体。体用本末,一而二,二而一。天象三家前,已发精气神,而地象八识者,一身之中。惟天一之真阳,乃阳中之阳,余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不得谓之纯阳。夫八识乃丧真阳之门户也。坤本象地,地以成形。眼形成而神时露,耳形成而精不凝,口鼻形成而气日耗,此乃外之三家,而引诱内之三家者。以及哀乐恐惧、忿懥好乐,又无形之八识。有形之八识害真犹浅,无形之八识贼性实深。第天三之阳,终于八而其实亦成于八。不睹非礼之色,则眼净而目成;不听非礼之音,则耳净而闻成;不道非礼之言,则舌净而口成,加之手恭、足重、身静、意诚,则阴皆变阳,岂有不成哉!
阴者阳之舍,阳者阴之主,前已发明外成之道矣。而内成之道,不外圣人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甚矣!血气之累人,可不畏哉!
外之八识已发明矣,内之八识,心象离,肾象坎,肝象震,肺象兑,腹象坤,三焦宗气象乾,静意象艮,顺德象巽。心不动,则神识不走;肾不动,则智识不泄;肺之识为魄,魄不移则气固;肝之识为魂,魂不离则精坚;以及三焦总三家,喜怒无伤,哀乐无损,则三家混合而五行周矣。腹之象坤,聚识之所;艮之象静,养识之方,巽以顺之可也。《大学》正心、修身二章已详言之矣。正心言内而不离外,修身言外而不离内,内与外其一贯者也。有忿懥哀乐之四情,足以坏其性;有亲爱贱恶之四情,亦足以倚其心,其所以不得乎!正者无正位耳,一得正位,则贼化为主,主可制贼,又何必强伐其性,使情尽归于无有。夫情与性,不过内外体用之不一耳。情静为性,性动成情,情性归正,体用合一,本末兼修。
不于动中观真静,专向静中死制动,不惟无益而又害之。不知真静,取喻譬之:月到天心处,静也,静何尝不动,静者体而动者用也。风来水面时,何尝不动,动者用而静者体也。若于静时寻得着动,动时寻得着静,是谓动静交养之法。火本动,常使静,水本静,而欲动,动上交静,静下交动,水火济而性命修,仙道之能事毕矣。
夫人之所借以生者,精气神而已。天之生人,先赋其神,神合化精,精凝神充而成形。人能先藏其神,神化为精,精固气凝,自然有一段道不破的光景运于其中。
欲养精气神,将胸中一切私欲除之极尽,自然见得良知良能。用惺惺法时时收敛,敛而敛之,一切恶念从此消,一切善念从兹长,养到神凝气聚时候,再加上达功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元牝之门可得而见。所谓元牝之门者,恍兮惚兮,若忘若存,杳兮冥兮,其中有神,一阖一辟,乾坤在中。问之何似,动静之根,天之太极,人之黄中,无上无下,无涯无垠。识得此理,圣凡何分。
养之之法,不以精养精,而以神养精。欲以神养精,先以气养之,神健气固而精自化,化交媾之精,而成元精。
元精者,天一之水也。养成元精,然后炼精化气。气本呼吸之气,久而久之,真气自现,然后用胎息之法炼之,化呼吸之气而成元气。
元气者,地二之火也。气炼真而化神,神本思虑之神,久而久之,阴尽欲消,阳复理长,化识神而成元神。
元神者,贯乎水火,统乎阴阳。阴阳颠倒,水火既济,久而久之,则水火归原,阴阳一致,是谓三家相见,混沌一气,而妙用出焉。
精进之理,知之者鲜,闻之者稀,即道之金丹,释之了性,儒之神化。
果能明心见性,本来良知良能,一一悉归于心,而神化之道,当更进一解。
神化之道,古圣未传之密,恐人不明一贯之理,执虚守寂,入于异端,无筑基炼己功夫,而即谈元,致使学者不修五伦,不尽五常,将性中之固有职分之当然,一概扫除,妄称了道。假仙释之名,藏无为之拙,孤守空静,坏其真传。将生生不息之理,归于一一执中之权,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敬之道,一律抹煞,抛妻别子,使国无桢干之臣,家无干蛊之子,为世间罪人,安望成仙成佛哉!
仙释与儒,原是一理,果能善明于心,无一毫间隔,无一点偏私,自家念虑与圣贤道理一一浑合,推而行之,家国天下皆我性分所固有、职分所当然,为民为官,顺而行之,无往不利。彼以入山为高、入林为深者,安能成大功,立大业,明大体,入大道哉!
先静其心,后净其身,心身静净,大道可成。
混沌初分,三教无名,三代以下,分门别户,家各异学,人各异教,曰儒,曰道,曰释,犹之花曰莲,叶曰荷,根曰藕,名殊而本则一。
前言八识,统乎本末,贯乎内外。而八识归元之道,人初生时,混混沌沌,无炎凉,无毁誉,无彼此,无贵贱,无贫富,无智愚,无高下,无远近,无亲疏,只是个一元之气,恍兮惚兮,惟知天真自如,何曾有一点渣滓。自知识一开,则万虑起而百事形,真阳日渐磨灭,阴神日渐操权。圣人千言万语,总使复其本性,克其己私,无非除阴复阳而已。
私在人心如火,然燃而不息,志随欲迁,难脱尘缘。
欲求八识归元,先制其外,外不见外,外识自归,内识尚难制伏。将此身立于乾坤之中,此心混在九天之内,明净无碍,自有一段光景现出,不在小体用心,专在大体留神,则三家自然相见,八识自然归元。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之道。地居坤,四居兑,即地四生金之象。坤,老阴也;兑,少女也。老阴生少女,即地四生金。地本至阴,而得乾之二,即变为兑,兑乃阳极,而阴坤乃阴中之阴,以阴中之阴而生阳中之阴,即是生金之象。
金者至坚至刚,光明照彻,尘氛不染。西南是得朋之地,而正西乃炼金之方。坤以象身阴也,兑以象金坚也。志由心生,不坚不成。坚者,兑体也,化坚者阳也,真元之气也。真元者,阳中之阳,天也,九也。欲石成金,必得以气运火,即此上下之谓也。
地四在人身,为心为志,心无志神不灵,志无真丹不凝,志真合一,而大道始成。
羲皇视阴阳、健顺、刚柔之义画为八卦,有对待,有方体,有循环,有端倪,总然将天地中之造化,未必尽泄尽也。
木未出土,两仪具焉,四象合焉。既出土,犹是一元之气,而干立焉,稍长焉,枝分焉,再长而四条出焉。由四而百而千而万,一生而无不生,生而生之,无所不生,则根死而木枯矣。
人以木喻之,当其混沌之时,眼未生视而眼具,耳未生闻而耳具,口未生音而口具,鼻未生臭而鼻具,四者在混沌之时,初非无形,而真元之气不为形役,母生子生,母死子死,疾病夭折与彼无干。
裂胞而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地生而我亦生,天地死而我亦死。何世之人寿夭不齐,此不在天地而在己身修为也。己若长生,天地岂忍使不长生?果能修其身以合三元,凝其神以合三家,则纯阴者倚纯阳而长,纯阴者依纯阳而久,立命之学,可企望焉。
河图中之妙用,只在天人一贯上参之,而天人一贯之理,自始至终,皆不可无,看其功之浅深、识之高下以为心得。故夫子教有四科、言有三雅,非有偏私,因人而教,悟者自悟之。颜子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与礼,人人皆同,何颜子独谓是我,亦不过在己之独得处,以示门人耳。
天下有有形之文字,亦有无形之文字,须借有形之文字以证无形之文字。证明无形之文字,则有形之文字俱为糟粕。无形之文字,智者见其智,仁者见其仁。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惟三圣人,才算得能作书,能读书,不然寻章摘句,于己何涉!
文字原是圣人之心,非精深不能识,非见性不能知,如天机流行,上下昭著,无非此理之运,万物以之而生,百姓以之而行。天之机一息,则万物不得而化;人之机一息,则生化何由而继;地之机一息,则收藏何以而永,此机之所由生,即机之所由息也。人人由之,究竟人人未必真知之。果知其机之所以为机,天之所以为天,则人之所以为人者,可得而会心焉。
天机不必求诸远,只在日用之中,悟之者可以希圣希贤,不悟者即刻为愚为狂。夫子曰明德,曾子曰慎独,子思子曰中庸,孟子曰仁义,千经万卷,无非言良心,良心即天机,天机即良心。
终身讲学,不知真真学问果在何处,或依于性之所近,或流于习之所夺,或限于质。质近者以为可学,或谬于禀,禀来者以为无弊,如此偏倚,何日明道,变化气质,学者要务。
河图天九之数,阳中之阳,阳极而动成姤。天下之数成于九而终于九,故乾卦六爻皆阳,而上九必曰亢龙,用九必曰无首。无首二字,泄尽无限天机。
春而生,夏而长,秋而实,阳气至此而已极。阳极阴生,死之象也,若非硕果不食,则生绝而数终,此物之阳极有悔。
幼而长,长而老,阳极而阴坚。乾元之气散于外,坤阴之气塞于内,纯是阴上用事,不向理上探求,日复一日,理尽气散而数止。圣门功夫,不在功名上较优劣,只在诚笃上论高低。颜子克己复礼,得复字;曾子思不出位,得艮字。知易理之精微,闻性道之一贯。知《易》者二子,学《易》亦只二子,其外或长于《诗》,或长于《礼》,莫不欲求至道甚矣。至道本来难闻,子曰:“信而好古,敏以求之。”犹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学者乎!况下愚乎!
养阳之法,惟在无首。无首者,藏之象也。君子退藏于密,高而不危,常守贵;满而不溢,常守富。富贵且然,况性命之道乎!
一身全是精气神三者运之。眼光不凝,神乃散耳。韵不收,精乃泄,舌神不守,气乃亡。
知识一开,目有见,耳有闻,色色声声,无穷私欲,时散真元之气。以有形之欲推之无穷之识,以分外之极极于分外之求,可思者,思以耗其真;不可思者,妄以摇其精。一点真阳,用于纯阴之地,用之不已,用而复用,以至用无所用,则阳溢于外而不能藏于中,故下学不能上达。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之道。天地皆有五,合之而成十,五者,阳之变化也。十者,数之始终。天有五行,地有五运,人有五常,一而二,二而一也,此处不以五行言,而以变化言。
天之金,地之石,人之勇也;天之木,地之柔,人之仁也;天之水,地之脉,人之智也;天之火,地之刚,人之气也;天之土,地之形,人之信也;此即三才合一之道,五行攒簇之理。
了然天地之道,然后以有恒之心求刚健之德,则欲自消而理自长,自能明善复初,而入于无为之天。
天五,说无形之变化;地十,讲有形之错综,那无形之变化成有形之错综。
春无形,而草木发生形其形。无形者,天之木;有形者,地之成。
夏无形,而云行雨施形其形。无形者,天之火;有形者,地之成。
秋无形,而霜露葭苍形其形。无形者,天之金;有形者,地之成。
冬无形,而梅开雪舞形其形。无形者,天之水;有形者,地之成。
中五属土,贯乎四时,无形无象,健运于四时之内,直贯乎三才之中。《易》所谓“正位居体,健行不息”。一部《易经》,不外此理。
天地之道,公而已矣。公即中也。河图之中五,乃三才之本、万象之根,天无此无以生,地无此无以成,人无此何以真!
天下物物色色,皆从中字化生。邵子曰:“天向一中生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千古圣贤,俱由此成;天下万物,亦从此化。以有形求中不得,而执以无形求中亦不得。而执欲求执中,先从有形之中寻出无形之中,是谓时中。
时无定,中亦无定。一室之中,中即是中,分为三室,三室各中,而一室之中不得为中。推之人事常变、时运推迁、学问高卑、事物大小皆然。
河图之数,错综变化,生于一而终于十。十者,数之终。一者,数之始。天地虽大,莫逃其数;人身虽小,亦莫逃其数。数不尽则生化不休,数一尽则长养何依?
数何以生?何以成?始之则生,资之则成,是谓万化归根之道,一元复始之理。
不能归根复命者,非根之难,归命之难。复不晓其理,故有尽而不能有成。欲成其数,自万而千而百而十而一,即是三教一原,万圣一揆。
得其一,即是天地间明贤,乾坤内豪杰。
心思智虑,憧憧往来,不知几千万亿涉想,几千万亿妄念,昼而思之不已,形于夜而梦之,尽是动中用事,那能一息安静,致将本原一点灵明,悉为私虑所夺。欲求归一,先将此身看破,扫除一切妄想,使耳目口鼻,各各归原自然,有一段真精神、真命脉时时流露,收而养之,自能复命归根,明善复初,何患下学不上达,不成顶天立地奇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