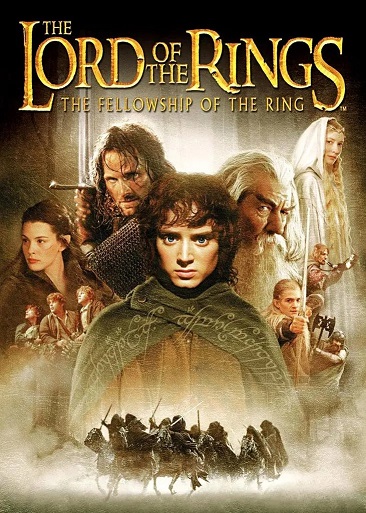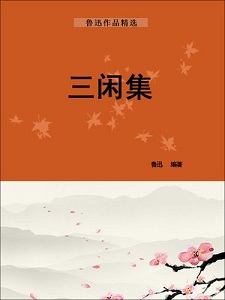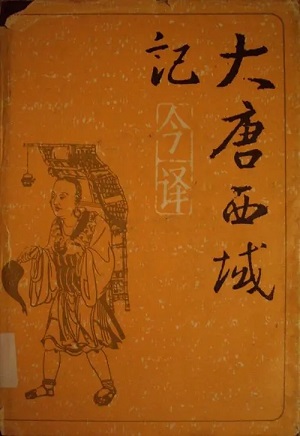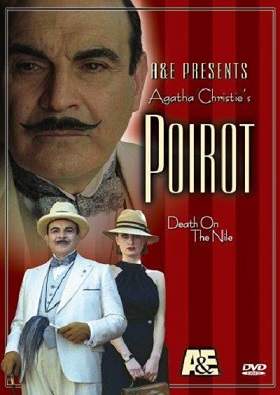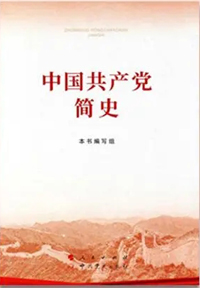惕虑要言
福缘福地,良知良能,即佛即心,应观自在,不役于形,不妄其心,不劳其神,神完而后气充,天地真实无妄。道之极,则冲和洞达,道之光明,八面玲珑,一尘不染。
能尽心地,便能达乎性天。时时守之得其心,逾时放之亦得其心,又阅一时游之而愈得其心,如是则吾心之乐在是也,吾性之根亦在是也,是谓操存,可须臾离哉!
瑞雪甘霖,顺时美应,资万物,养苍生,天心仁爱至矣哉!身得润泽之气,百体俱泰;心得润泽之气,一念不生。
心无着则苦,心有着则苦,心有着而无着则甘,心无着而有着则甘。先由甘苦并进,愤乐相循,久自心定,定则水源清静,有乐无苦。
欲制无根火,先寻活水源。垂帘观自在,处处见先天心。定乃见先天之心。先天之心,一念不杂,纯而又纯,自然阴气尽消,阳气充盈,方成纯阳之体。
守心须由眼门入手,方为切近。守到一念不杂,纯而又纯,即是先天之心。先天之心,即性根也,即净土也,是谓即佛即心,即心即佛,莫不从心上用功。
报功一世,现享厚福;报德三世,世食厚泽。食德者,世其德;报功者,积其功,绵绵之泽,可限量乎!
举动、言语,细微曲折,无往不有利济于人于物之处,不以为德而德之所积者厚,不以为功而功之所及者广。
不诚无物,诚无不通,不必探微说渺,亦不得泥见胶固。立心于笃实之地,则举念罔非,初心行事,共见光明,天真流露,性光发越。
方圆寸地,囫囫囵囵,不动不移,浑如太极,却又变化无拘,如大和尚布袋,其收也毫无作为,其放也何所不至。
后天有意,因意而持之,是谓以后天治后天,意在后天;先意而除之,是谓以先天治后天。先天本无意界,有意即完无意,开朗处便是意界;无意而至有意,知识处则为意累。
意在阴阳两合时便是空明,象便是太极。完无极界,由太极而无极,在有意无意间;由无极而太极,在无意有意间。以意归无意,而密之,而纯之,而化之,得其意旨矣。
漂流欲海,迷而不悟,由于是非乱于中,好恶诱于外。所谓是者,自是其是;所谓非者,自非其非。若知所是之有非而自非其是,知所非之有是而自是其非,则是非好恶归于至公,大同启化,本真可复。
心无所心,体天心为心以达其心。达天心者,自能立命。命禀生初与性交合,尽其性以修命,安其命以全真,方成金刚不坏之体。
天人消息通于呼吸,毋曰不见神其临矣,毋曰不闻神其听矣,以心之神合天之神,此自然之理而不可易也。
神鬼之界,决于阴阳,判于方寸,所行合乎理者,其气全乎阳,违乎理者,其气全乎阴。全乎阳者为神,全乎阴者为鬼。知神之可敬,鬼之可畏,即是把握,空言正心,易流顽空,临事而反,不胜其局蹐矣。
心不了了,何能了事!故以制事者制心,莫若先以制心者应事。事至物来,随时洞彻,融其敬畏之心,而无所容心,此治心之要道。
克己十则,一曰务本,忠孝立基,伦常无憾。二曰安分,穷通得失,不可强求。三曰习劳,士农工商,各尽本业。四曰积功,立德立言,寸阴是惜。五曰明理,圣狂分界,决于几希。六曰择交,贤奸难辨,成败攸关。七曰知人,居家治世,皆宜明察。八曰立主,见危授命,大节不亏。九曰却魔,酒色财气,勿使昏性。十曰怀宝,精充气足,保护元神。
七情,性之作用,非本体也。性之本体,囫囫囵囵,无雕无琢,如三冬草木,内含生气,阳回发越,静极而动,神妙莫测,天人同此一理。
明性急宜活性,性无着便是活。喜、怒、哀、乐、爱、恶、欲,是性之作用,非性之本体,本体无着,故无累,无累故能活。
人心无物不有,可以神,可以鬼。人之为人,谓之神可,谓之鬼亦可,在乎自为神,自为鬼,一心通之而已。试问愿为神乎?愿为鬼乎?
心之所结,谓之缘;机之所凑,谓之缘;神之所合,谓之缘;情之所聚,谓之缘。天缘乎,地缘乎,人缘乎,缺一不可也。
天非人,无以通地气;地非人,无以见天心。一念之动,天地之戾气可以消,天地之和气可以迎。
动时得静,未为真静,定时得静,乃为真静。动时无所谓动,静时无所谓静,乃解脱之妙境也。人之身甚大,不可以自小;人之心最灵,不可以自蔽。自蔽即小,自小即蔽。
离中虚,虚其心,则有意归无意,久自阴净而转乾。坎中满,满其精,则后天还先天,原始而返终,久自决阴而还乾。身心交养,归于纯乾。
乐水乐山,游行自得,居尘出尘,飘然恬淡。若有想,若无想,若有为,若无为,到得性命同归,可证惟精惟一之道。
三才一气也。罡气在先天后天之界,元气在天清地静以前。观心犹为后天之功,裕气乃为先天之诀。五行生则耗气,克则裕气。裕罡气如彼此相敌,立定脚根,竖起脊梁,力大而归一,可以全真养元。气如彼此相爱,一味姑息,无从着力,止于观心,终至不振而后已。大要于养气中立定脚根,与其安而顺,未若猛而提,以养其优柔充足之气使自得之,如圣世宽大之政,贵乎恩威并济,惟在善用其威,以适化于宽大之中,勿猛之一朝,如宋人之助长可耳。竖起脊梁,鼓四端之气用以观心,气自裕而心自定。
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从一事做起,从一念寻起,推而至于事事念念皆善。
善无大小,即片善亦作万善观。万善之始,即以要万善之终;万善之端,即以立万善之极。
诚敬之学,极大极细。能极其大,则诚无不通;能极其细,则敬无不至。诚为积学之验,敬为入手之功。非刻刻临渊履薄,不足以言敬;非时时笃信谨守,不足以言诚。
心为万事宰,性为四德根,纯粹以精,必由气质炼出。金刚百炼,乃成不坏金刚。炼之之法,心不死,则金刚无由而活;性不生,则金刚无由而定。心性源流,何处通寸心,如在白云中,开将云雾留天日,一点光明四望空。
恬然为安身之基,淡然是养身之学。知所安则得所养,得所以安养之法,自有得于学问。
以心见心,以性明性。心之体圆,性之体直。圆则光明,直则正大。光明正大,自明之学。
寅为发念之始,阳光初升,性宜舒畅。午为日中之令,阳神易竭,气宜安恬。戌为火伏之时,阳气易郁,心宜坦适。
自内而外,诚意以正其心;自外而内,绝念以定其心。偈曰:“念念从心起,令心无所止。绝念观自在,菩萨在心里。”
一诚,无事不格上帝,无时不通鬼神。心静而气恬,心动而气舒。动乃虚中之动,静非无为之静,故能恬淡舒畅。
万事有一件看不透,便是不活处,不活即不肯死;万事有一件丢不下,即是不死处,不死终是不活。心死神活如不死,从此死起。
游思妄想,机械变诈,无所不为,是谓心术。有定识,有定力,有定慧,有大德以培其基,是谓心田。天性不坏,耕以仁义,修以伦理,是谓心根。心虽方寸地,性天欲海,由此扩充。
人生所最难得者,刚也。刚气近于阳德,直养无害,不昧本来。稍有私曲,便非正体。守此刚气,济之以柔,归于中和,庶几不流于愎。
无心为善,即使事未推广,功无博施,根本厚实,是为真善。有心为善,即使绝大美事,功及无涯,源头虚浮,事多中变。竖起蓬莱百尺竿,高台一镜试相参。飞云惯作奇峰态,幻出层峦远近看。
孝为百行先,即孝以见性源,方寸时存孝思,不忍拂亲志,不敢违亲德,则念念皆善,事事从善矣。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之推广,何往不是尽性之道!
人生不能无者,情。人情不能已者,欲。至情即是至性,大欲即为无欲,以道运之,则情欲俱不为害。一局棋中包世事,千枝花里见人情。花开花落浑无定,止水从来彻底清。慧眼慧心参造化,阴阳只在一圈中。分明见得刚柔异,合并还看神气通。
或谓后天盛,而先天遂衰,或谓守先天,而使后天不复生。或谓先天即后天,后天即先天,皆非也。由先天生后天,有次第相生之义,因后天溯先天,有返本完元之理。
思虑百出劳脾神,游魂散志耗心神,隐跃欲摇丧肾神。收此三家神,养我一点真。
精气神,以守精为第一。肝心肾,以观心为第一。口闭时舌下泉生,眼闭时胸中露降。忍得定,不要因心动火;丢得开,不要因假损真。坐不定,息心静气,自然耐性;睡不着,纳气收心,可以安神。
气之赋于心者,本自浩然。人之养其气者,须宜渊然。惟此渊渊之中,能容浩浩之体。
冲和雅淡性情和,一曲人间乐意歌。漫说步虚天上有,天公为问乐如何。娱心志,悦耳目,俗情之乐也。所谓真乐者,乐其道,非道不乐,无乐非道。人皆自有其道,何不各从其乐。呵呵一笑乐何穷,天空地阔此心中。满腔活泼无留滞,何论人间塞与通。
心以心看,心以心守。看得心,则水从中来,自下合上也;守得心,则火从中降,自上合下也。心和气自舒,心息气自微。舒则真气日凝,微则真气日和。
形长生非长生,神长生乃长生。有表里精粗之辨,辨在表里。气表而神里,辨在精粗。天精而人粗,人事合乎天缘,人事尽而天心自露。
一了无不了,了了又何了。了却尘俗缘,向道方为了。自不了谁了,自不了了何时了。了了了,了便了,不了便不了。哈哈一笑终身了,哈哈一笑终身了。
佛为不二法门,亦至诚之道。知其不二,而心与佛一;知其不二,而心犹与佛分。必忘其不二,而心始与佛融。林间筛月蟾飞魄,石上横琴山有音。色相浑无真窍奥,时闻天籁即仙神。
性根所结,无不光明。一盏琉璃开世界,从教无地不光明。先生自有莲花座,瓣瓣原知各有因。观心始则模糊逼仄,拘苦久自渊然浩然。不可着迹,不可着急,有此二字,即生魔相。
自有天地以来,弥纶充满流行而不息者,道也。道即性也,古圣贤之得道,尽其性也。尽其性,通其道。须知神者通之基也,神定则基圣。气者通之本也,气清则本立。精者通之源也,精冲则源长。志者通之干也,志专则干实。慧者通之体也,慧沉则体固,皆心为之主。用之修身养性,安知不名入丹台;用之事君泽民,自可见功垂青史。
心如如非,一身之气,与神与心。气乃生天生地之气,神乃通天通地之神,心乃不可思议之心,于不动之中,而有流动充满之义。静极而动,其感应之理无所不包。
我无所有,我无不有,随处有我,我本无我,不离此肉身,那能开慧眼,面面通灵,头头是道。肉身筏也,道岸既登,筏亦可舍。
人事何忙,其心自忙。人心本闲,何不使闲。处忙若闲,无忙非闲。知此真闲,便是真缘。一切烦恼心,皆由心自造。心中诸烦恼,还请心自扫。烦恼真烦恼,烦恼何时了。愿此烦恼心,一了无不了。
心地常使宽厚有余,便能容人,容乃生物之体;起念之间常使通达无碍,便可化人,化乃生物之用。是谓生机。体用分两层,不分两段。分两层,则有人己之界,不分两段,初无人己之私。
凡事多一件不称心,即多一层磨炼,刻刻拿住此心,便是精进。火不能足,惟枯木之火为最足。心如枯木,此间求足,无所不足;此外求足,无一而足。
无事不感于心,心之所通,无所不至,神而明之,其感甚捷,不外一个真字,稍着一假,便不成事,不诚无物之谓。
多学,所以寻道也。圣门端木,子不多学,安得一贯之旨!日日求道,而未见道者,缘未至也。心心求道,而道未见者,无此理也。道不远人,人自离道。求道见道,应在呼吸,神明常在目前,何处何时不可见道。事贵专而有成,在乎自立主张。见其所见,未必真见,求见所见,乃得真见。既得真见,又何所见,所见既别,即是真见。既见真见,可无他见,一见真见,全神活现。
守己贵严,虽幾微而必察;待人以恕,纵怨怒而不迁。始于家庭,和气为致祥之地;推之朝政,秉公为起化之原。祗厥父而恭厥兄,非仅博闾里之声称,实由天性。进思忠而退思过,岂徒效驰驱于王事,遂为贤劳。移孝作忠,求忠于孝,乃臣子之大分,亦儒者之要务也。
夫妇为人伦之始,乖戾实足召殃;朋友有他山之攻,狎比反能致戾。诸父伯叔,亦一体之相关;邻里乡党,系同情而甚迩。怜贫敬老,勿恃势以欺人;悯独恤孤,勿重财而薄谊。
性圆,自见光明台;性和,自得光明镜。有有者非有也,无无者非无也,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始以来,天地亦无,那里是有。本来无一物,须求最上乘。一脚不落空,天梯自我登。
心定则气定,气定则神定,神定则气凝,气凝则心安,周环相见。定字之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一息定,则一息之神光可合;刻刻定,则刻刻之神光若接。神有舍乎,定处即神舍也。心何灵乎,定时即心灵也。以心求定,以定安心。心与神,若有依,若无依,此即定中境界。
拙则忘言,拙则忘机,拙则息虑,拙则省事,拙则保气太和,拙则神归原始。不着中有着处,着中有不着处。
守吾中,固吾宫,妙吾宗,呼吾风。返吾先天一气通,无思无虑豁心胸,无视无闻如瞽聋,世法包含道法崇。
道未有不长生而长生,未便可以言道。圣人言“朝闻道”,“闻”字何等通达,“夕死可矣”,“可”字何等活泼。既得之,则此身乃可有可无之物。
信善二字似浅近,然工夫却实朴朴地,善则着不得一毫私曲,信则着不得一毫虚伪。充满其量,即至诚之道。
少年人未识三宝,先守三关。第一怒气冲天关,第二桃花绝艳关,第三贪宝焚身关。不犯者,千不得一。若不从此立脚,空谈性命何益。
现享之福,受自祖宗,如取火燃灯,愈燃愈干;将来之福,积与子孙,如燃灯添油,愈添愈明。
先立其本,要有根脚,不动浮念,不涉妄想,有事时尽其心,无事时安其志。心肯从我乎?始以心不从,我定以必从之心,继以心渐从,我定以纯全之心,是谓根脚。
心血几何,须时时凝神定气,不使虚火上炎,方可生水以补火。分阴不尽不仙,言后天杂气也;分阳不尽不死,言先天真气也。保后天返先天,当于静中验之。
无过去心,无未来心,无现在心,自然心细,自然心灵,可以察天,可以明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心能空矣,其能神乎!又须着实为之。气化而后能神,能神乃化境也,所谓妙有者,此也。
心定,即从定处用功;心动,即从动处用功。原有活法,妄念如金钟之鸣,声闻千里,摩空而来,其势最远,以慧剑斩之,以金治金;恶念如燎原之火,不绝昼夜,草木俱灰,其来较迟,以猛火攻之,以火治火。金完金,火完火,由动亦能入道。
心气因血,心血因气,常看此心,则一切皆空。由空中一点着实,不空不能实,不空乃遂空,从后天培养,以还先天,常使此心在空阔之地,此神在淡定之中,如此则自有把握。
有事时认真办去,无时不谨慎小心;无事时自我收来,无刻不冲和恬淡,积此心行此事,即为实德实功。
一念之起,人不知而我知之,有我也,实也。一念之起,我知之谓人不知,而我忽之,去我也,不实也。实与不实,善恶攸分,所贵辨之于幾微。日用饮食间,常用此法,放心自收,精神自集。
一动于欲,欲迷则昏;一任乎气,气偏则戾。初起念,即便回心,一想其是非,固自较然,非者去之,是者存之。克己工夫,即从此初念克起;行善工夫,即从此初念行起。
净土净者,净此心而明其性。土者,性根也,从无始来,寻无始去,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即是莲花品,即是金刚诀。
功德皆由心造。古人云,吾一生所为,无不可对人言者。此绝大学问,正绝大功德。
天之言由人而发,圣经贤传,皆天之所欲言,而圣贤代言之。人与圣贤同此心,通其言即通天矣。
外宜刚而内宜柔,至刚之气直养无害,万世不避。粗中加细,细中加察,察中加守,守中加择,择中加密,密中加详,详审周到,则为人处世待人皆合乎宜矣。
运五脏流行之气,统会于丹田,气足神完,却尽外缘,留其本真,斯为极矣。太极本无极,无极本无妄。静极而动生,太极是着手处;动极而静还,无极是收功处。
气以聚神,心以凝气。心定神在舍,心动气浮体。真气日凝,元神日聚,以渐得之。若以为行之无效而舍之,天下无此易事。若以为行之既久,而恐终于无效,天下无此难事。
凝气聚神非难非易,惟在行之坚固、守之笃实,淡定中有真气,渊默中有真神。
观心能见意之所生,观气使知命之所主,观神能知性之所聚,事事念念,常思此从意起,此从气起,此从神起,皆有归宿,可收放心,自无妄念。
气无形其用最大,形无象其累最重。去其累,化煞于实;全其用,炼有于虚。分明是先后天、阴阳界,人皆模模糊糊,寻不着头绪。
一心千魔万怪,莫非一身之精气凝结,以慧眼定业根,转得收其精气化为金刚,不外一个定字。
定心不如死心更着实,能死到千死万死,死无可死,跳出一个生字来,真是生龙活虎,不可端倪。
脾主思虑,故魔不生于心而生于脾。心不死则脾益生脾,魔益生魔。故死心在开垦脾土,方能斩断魔根,何思何虑。
心真则豁然开朗,无纤尘之蔽;气真则浩然流行,无一息之间;神真则湛然常凝,无一念之扰。鸢飞鱼跃,活泼泼地。
垂帘内视,而心必忽出忽入,不可捉摸,及见有腔子,又见腔子内之主宰,看得定,拿得住,靠得牢,便是见心,便是见气。见气为见心之效,见心为见气之效。气非养不充,心非养不定,多一息收敛,见一分内功。
静养要诀,勿着迹,如行云流水,勿着急,得寸斯寸。言到心即有腔子里一点,言到气即有腔子里一圈。见心即有此气,见气即有此心,即真气也,非气有二也。
理境图通,神明光远,天与日月,惟圆故明。理本实境,贵乎变通,变则活泼泼地,变则空明明界。夫子圣之,时变通之义也。不变通则方,而为理癖,其神暗,其情滞,未免太苦。
读书须罗列史传,激发志气,遗臭流芳,有所惩劝,则精神自能郁勃,真气得有端倪。
敬心,善心也。亲爱心,良心也。见父母而敬之爱之,诚于中也,时存此心,即可对神明矣,以之处事,无往不合于理。
神从精出,精从气生,气从心旺。心有主见,不使此身颓然不振,则气盛,气盛则精充,精充则神足。若委靡偷安,则心无主,心无主则气亦溃而不收,则精神无从而生。
工夫无间于须臾,修省不离乎寝食,必身定而后心静,犹其次也。功密而心纯者,虽百忙中如无一事,此真工夫也。
性本乎天,情尽乎人,原是天人合一之处,有一气质之性杂其间,则情失其情,性非其性,究之真情,自在真性难诬。
人心不定如风。然风合乎四时,应时而发,本有定所,偶有不定,气不和也。心体中正,自有定位,有不定者,气不正也。罡风生,不亟避之,则受其暴戾,若避之,而正用之,则又得其鋾熔之力,是在正体而妙于用。
心大一轮月,心重千斤石。大如月,故须收拾于海底;重如石,故须埋定于土中。神舍在何处?黄庭埋得千斤石,神去神来不自知。气海神藏须炼质,相扶相助渐能持。持心要诀也。
观心,观自在也。既得自在,何不刻刻观之。即此“观自在” 三字,扫尽一切浮关,久有许多妙境,原非外铄亦非幻想,所谓真实不空,空即是色,不观不空,不空无色,色即自在者也。
观心,时而见,时而不见,为杂念牵挂,心未定也。扫尽杂念,收拾干净,关好门户,久则自定。
气有通塞,通处欲其迟留,塞处欲其开畅,勿疾勿徐,勿急勿徐。或急或徐,效非速成,功有速应,立中妙境也。
功无速获之理,道无速就之方,刻苦求之,则苦中之甘味无穷也。日积月累,苦情孤诣,积之既久,则日新富有,有口不能言、手不能指、目所未见、耳所未闻之妙。
功非苦到极处,分毫莫能破其道妙,真积日久,一旦贯通,夫然后恍然有悟也。不苦不甘,报应之理,由苦得甘,积渐而来,知此守此,入德无难。
定心之法,刻刻将此心下之,下之既久,深深藏之,如有宝匣洁清无尘秽,将心盛于其中,百变不动,百试不摇,则纷者其绪,而定者其神。
道何在,在心田,种心取心苗,心苗可长年使。既立心,当先采苗。采苗之法并无著迹,只于心上寂然不动,时忽有一点透出,觉耿耿然,安安然,皎皎然,百体舒泰,津液流通,此即心中一叶真苗也,渐滋长而更觉有色有香有味。乐乎!否乎!
闭目而以心下之,心下而以目微启之,心气归于其所。口中津液,具有美味,徐徐咽之,使心气随津液而和,自有泰然之境。早晚静坐,默诵《心经》四十九遍,或圣经六十四遍,再以心气下之、津液应之,便可定心。
口念咒而心可定,目视咒而心可定,耳听咒而心可定。是故不曰诵咒,而曰持咒,借以持其心也。
人情不外好恶两端,立心端好恶,待人同好恶。古圣贤以济世安民为己任,以检身约己为先务,由溺由饥之念,何日忘之。今人亦当如是,果能强恕而行,遇利当兴兴之,遇害当革革之,优容中寓刚毅,坚忍中存和厚,则不失为读书人忠厚之道。
求称心,求如意,恒情也。不必称心,不必如意,定数也。期其必称心如意,而往往拂其心意者,势又然也。即使称其心如其意,头绪愈多而曲折愈多,转闹出许多不称心、不如意者有之,何若寻我本来原,未尝为此有益,彼有损,生心生意,又何尝不称心、不如意乎!
养其体,修其心,调其气,体热若火,心冷如水,气行若泉,则神自定,此乾坤一大转关。
动有则,言有法,束身矩矱,心有范围,加以专一,则不外驰。如考古必究其微,证今必举其要,总使无少间断,虚心自启,身亦自修,沛恩降泽,那能遂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念之公而已,不践生草,不弃虫蚁,一物之细,一念之微,纯任自然,以充其量,仁民爱物之道。
忍得澹泊可养神,忍得饥寒可立品,忍得勤苦有嬴余,忍得荒淫无疾病,忍得骨肉全天伦,忍得口腹保物命,忍得言语免是非,忍得争讼消仇恨,忍得屈辱征气量,忍得诵读增学问,忍得忿戾祖宗安,忍得刻薄儿孙荫。须知忍即性中天,莫言忍是心头刃。
秋云似薄,而清气逼人,却自可爱;冬日可喜,而冷气入骨,却自能消人心。若行云之动静交合,若白日之清光,斯体用得矣。
卓然一丈夫,胸中何所有。飘然一神仙,此身何所有。有心便俗物,无心乃浩浩。有身非金身,无身乃入道。非谓轻此身,实则从所好。
好山好水好明月,谓是人间幽闲客。不知此乐非真乐,别有天机自洋溢。此气常存坚如石,此心空明皎如月。何必日服长生药!何必日服长生药!
行止坐卧,任自然之性,方无碍于气血之流行。气以行心,血以养心,心通百脉,为一身之主宰。心之所化,性为统摄,性之见真,命为良田。性乎!命乎!皆心之用。命乎!性乎!又心之体。体合乎用,在气与血,气血交关,在五行之得其中正和平,自得形长生而神化矣。
性本天成,破空而来,有闻若无闻,不得以无闻而忽之;有见若无见,不得以无见而昧之。天事完天事,人事完人事,天人相与之际,皆自不可闻见处。视思明,听思聪,聪明开辟之由,要从有闻有见处存其心养其性,参进一解,事半功倍。
命之在天,分其气机,入于后天。性之在人,自无始以来,与天地同性,禀于先天。故言性,必求其原于命;言命,必求其原于性,是谓性命双修。始则杳冥昏暗,未见道也,私智穿凿,未见道也。惟有见一步,走一步,进一步,看一步,层累日积,行之既久,豁然开朗,浮云顿卷,丽日当空,诚而明之之学也。
儒之高明,即释之舍利,道之金丹。儒之悠久,即道之金刚不坏之体,禅之定智慧之门。儒言智仁勇,释言戒定慧,道言精气神,三门通乎一气。过去、现在、未来心不可得,即系毋意必固我,不可须臾离,即常清常静之常道,从合参晤,自多取益。
上智炼阴阳之气,凝之为神,聚而不散,加之大功大德,则超乎千劫之中,即至亿万化身,而其本来固凝然不动。其次炼阴就阳,操持性体,而不为形气所役,则一点灵光亦足,久持而主张自在。再其次则养气养体,功力久而勿懈急求,还其原,返其本,虽无显应功德,而神气不至涣散,其灵光可以长留,是谓三乘。
先天气不可见,忘而又忘,存而又存。存而不忘,忘而不存,乃见一点真气,自腔子里现出,化为一点元神,此万劫不坏之本性也。
后天气,存而得之,忘而失之,时时固守中宫,绵绵若存,此为呼吸之根,性命之关,舍此无可把握。此气放之则塞乎四体,敛之则不盈半黍。其性喜恬静无为,又喜坐又喜默,乃一身主宰。但丽于心脾之间,心属思,脾属意,往往为思意所牵动,而不觉致多受病,到得元和用尽,寿数止矣,可不重哉!不重后天,不复先天;不复先天,不能悟道。
亥后子前,天地未分,元黄未判,正是浑沌气象,却有一点先天真阳,微微透出,当于是时,闭关养之。
泰为天道,即为人道,见其大则心泰。天君本泰,不可自扰之,即如守己之时,本寂然不动,而一念之起,旁皇无定,遂至官体若有所失,不泰,孰甚焉?
心本居中,无定者亦神也。而有定者,神之所由,灵也。多一转折,已失本然之体,由是游移无定之神,离其宅而不知所返矣。
性自天生,亦由性染,性爽快者加精细,性执滞者加陶熔,斯成妙品。
曰止曰观,曰静曰明,惟止能静,惟观斯明。进道者贵识止字之义,心如止水,便能洞彻一切。
士能真鲁,惟守本分做起,不知一味求知,不能一心求能,便是鲁字真功夫。鲁字大学问,士农工商,皆当体贴。白昼赖日光,黑夜借火光,照见种种色。其照处,谓自照乎,谓有照之者乎?无照之者,无从自照也。故照者,化机也,照之者,性光也。不内观,如在黑暗中虚度一生,必常常内观。初如白昼无日光,黑夜无火光,止其心以求之,勿杂他念缠扰,久则开开阔阔,闪闪灼灼,微露一隙之明,则性光初生矣。又定其心,静其心,安其心,益求之无虑,其无见也,全光毕见,无所不照,无所不到,所谓到彼岸者非耶?到彼岸则筏可舍。其筏也,其照之者也;其舍也,其自照之处也。知此可以言道,可以言悟道。
道一而已,而心不一,不能见道心。归于一,道即在,是一人一道,千万人一道。一人一心,千万人一心,心即道,道即心。
读书为保身之本,训子为成家之原。性粗率者,宜养之以和平;性鄙吝者,宜养之以宽厚。和平乃成身之学,宽厚是致福之基。
人生百年,倏如瞬息,安忍不及早警勉,时时开方便之门,刻刻存忠恕之念。处丰厚境地,退想贫苦之辈,自不敢骄肆;入圣贤之门,常思理欲分界,自不敢纵逸。
一行一止,神明若鉴。一步一趋,规矩不离,自然处事谨慎,待人谦恭,渐能入道。
天元有始,地元有终,人元善始而成终。始于天元,成于地元。是故人者分天地之中气,而为万物之灵也。
知灵弗灵,神役于形;知灵而灵,神出于形。践形者,神完而形全也。人不见全形之人,以为怪异,岂知形全而神不足以固之,其谓不全形之人也,可谓之不如全形之人也可。
知人之不可自小乃能立志,知学之不可自多乃能进功。有恒者,天地之体;默运者,天地之候。人之秉气亦然,因时消长,固有定候,知其消而避之,知其长而存之,顺天生生之意也。
细其心气则心细,和其肾气则心静。一细一和,道谓龙虎之位成,而婴儿姹女之姤得矣。
用力捏心,心定矣,未必能细;用力定心,心定矣,未必能和。惟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乃细心和心境界。
心定而入定,真空也。心定而仍空,灵空也。空乎?定乎?定乎?空乎?虚实相间,道德之门。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又从空定进一解。
澹泊宁静,四字何味乎?澹泊得味者甘,宁静得味者和,长生药也。然谓非澹泊则不甘,非宁静则不和,是犹以自了结局,不能扩充其量,以四字为把握,行而宜之,神而明之,更进一解。
性为心气交关之物,必守定气、放开心,方能见性。气定而心自活,则放得开,自然境界宽绰,变动不居,是谓灵境。神以灵而精自结,气不定而徒任心,则心放而无所归。归于心则气定,放开心则气舒,此因辅定主之义,义明而性见矣。
气属阳,阳不足,性可以扶阳。扶阳在定心,又在降气。气本上升,升而降之,则得周回之力。一日一升降,而丹田中渐渐阳气填实,填之又填,充满其中。于是乎升降任其自然,断不至升而不能降矣。始由天目中所结,稍为着力纳至丹田,看其徐徐散开,不可使滞,滞则多累,须观其散后乃可任之,必一日一次,寅时为之。取阳之道,心头少一件,肾中滋一分。肾中添一分水,心头制一分火。循环之理,以生为克,以克为生,即生即克,即克即生,生生不已,气定而神集,神贯而精化,化化生生,日见其精。自然之功,候日进之,生机也。
说法并无他法,守心即是清心,道在内而不必旁求也。然正心修身,修身正心,有交关之理。心如滚盘之珠,总无定时。心定于身,定时定之,昼夜偷闲,一时为之定之,久则身动时,心亦常定矣。
天人交感,微在呼吸,显在动作。其机动于无形,无形之感甚速,其用征于有象,有象之应犹迟,故眼前多福,达人自消,见得不敢受,不轻受,则享福之时。即积福之时,积之不已,享之不穷,其道在退一步想。
退一步想,便是进一步观,进一步观,则不惟现在之逆境为难得,即将来之顺境亦无希冀。
涉身处事,全凭一点敬心。神明有功即录,有过即记,心之起念,神明知之。不生秽恶心,不生乖戾心,则心自敬矣。
人心只是放心不下,道心只是撒手得开。撒手即是放心,放心正是收心,放下一切凡心,收成一个道心。寒暑年年催白头,用心何事可寻求。万端憧扰无休息,须向空中认取留。
诚者,诚其所赋之理,因而诚其所禀之气。一切人事,皆不在此理此气之内。惟先天自然之理、自然之气为真理真气,为悠久之道,大要归于撒手两字。鬼神所惧者,撒手两字;天地不能限者,撒手两字。手吾手也,谁使不撒,一撒便撒,何难哉!
内省功深,即见本明之性。性本有光,乃先天之光;目之有光,乃后天之光。然先天之光,未尝不寄于后天之目,故曰慧眼,曰天目,曰佛眼,曰金目。离娄之明,隔一纸而不能洞视者,后天之目也。有慧业,有慧心,乃能有慧眼。磨之又磨,定之又定,然后生内光。
脾胃为后天之本,须知培养,方能保其精气。心脾交关,脾胃相济,常使和合,勿使相克。乙癸同原,天乙之水,仍须从后天寻去。开心足能养胃、和脾、保肺,肺气流旺,而水足木资,火静土安,金之所以重也。
金之母在土,故黄钟为始,即生生之原,脾胃主之。一心培养,使生者得其生,生生者得其所以生。生则克者不克,而克者亦生其不克克者,即其能生生者也。其能生生者,又安往而不化其为克克者乎?
最戒多欲害神,多虑耗神,多食损神,多饮伤神,多走劳神,多睡昏神。守此六戒,可以延年,可以生慧。
毋逐逐,处世须知足。知足便足,足则不辱。毋逐逐,毋鹿鹿,学问忧不足,不足求足,求足方获毋鹿鹿。一心专诚,能勤卷轴,立品安详,躬行自淑。
勿浮其气,勿粗其心,循循规矩,自合准绳。知爱知敬,奉长奉亲,出入必谨,言语有箴,以此蓄德,不愧深沉。
人心各有灵机,而平旦之气甚是几希。此几希者,甚是可贵,知其可贵而贵之,则必守之甚坚,而扩之渐满也。时时有此几希,处处有此几希,则几希者触处皆是,岂非放大光明,存大愿力者,赖有此几希耶!
性无为,命有为。由无为而有为,性之原于命也;由有为而无为,命之统于性也。离性言命则滞,离命言性则虚,必两合而后全美。
由性而入,则寂然不动之时,即有感而遂通之妙;由命而入,则神完气足之时,即在浑沦无际之中。
天有性乎,清者天之性;地有性乎,宁者地之性。一气耳,人禀天地之气,气即命也,而性亦赋之。性即天地之性,原本清宁。性先而命后,性无为而命有为也。
性无为,天地自然之理,澹泊宁静四字该之;命有为,一身之常存常注,精气神三字该之。性虽无为,欲求见性,亦有着己功夫。
常存澹泊宁静四字,从外看入,由两眼看进,两耳听进,一心安然,常定灵机,看出有三关,看入有五脏。通体看来,五官百骸,皆可作恶煞,亦可作用神。心从此炼,神从此固,日日为之,一步还他一步,步步进去,毋中止,毋前却,毋速效,毋助长,日积月累,渐渐有得,无为而有为也。三关者,天目、左目、右目也,为光明聚会之处,心定后看出,到三关静视之,久则妙境自见。
道本平庸,食物器用之间,具见心之流露所为。小无间者,心之无往不可见,即道之无时而或违也。
立心于光明正大之地,即存此心于细微曲折之中。此心何心?敬心也,信心也,即道心也。
归真返朴于淡字中得之,于毅字中守之。惟沉毅者能恬淡,稍一迟回,则不可谓毅,即不可谓淡。
自谓可淡,未尽之词;自谓欲淡,未然之词。故毅字为淡字真种子,从根上一一削去,斩草除根,无一隙余地,可谓毅,可谓淡矣。由此一心持定,涵养纯熟,便是还他真面目。古来谏草频,仍犯颜不惧,皆自绝大文章中做出绝大经济。贵有识量,识量如日月之明而不可掩;贵有气节,气节如金石之坚而不可磨。识量充,气节具,然后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尽是有用之经济,即在家著书立说,有补圣贤之业,岂出而用世,格君爱民,无当于大人天民之学哉!
观心即是用心、看心、去心,三者合参,谓有心可也,谓无心可也。一时有心,一时无心,心所当心,不心所当心,均无不可也,两字诀曰心心。
心有千变万变,炼者不使一变。始则以心炼心,继则以神炼心,其相依之理,有不期然而然者,推之至诚如神,则心神即真神矣。
数与理,二乎?一乎?一而二也,二而一也。何言之?一者囫囵,二者分散。由囫囵而分散,至于虚空粉碎,无非是数,却无非是理。而在数为数,在理为理,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非也。由囫囵而分散之则易,由粉碎而合之则难。有囫囵之心,有囫囵之气,然后容此囫囵之理,先将此心细细收拾过来,归在腔子里,则丝毫不走。所谓心,其心者是也,所谓心,无其心者是也。
总要立心坚,旷日持久而不畏,无所用心而后成,将心上魔端渐渐削去。其道无他,炼心而已。
凡人能于精气神见其会,而不能见其分,见其分而不能见其融。精也,气也,神也,会也。神也,气也,精也,分也。气也,精也,神也,融也。不会不分,不分不融,此理既明,可通三关。三关相通,通自下始,自下上上,自上下下,周而复始,循环无端。结构既密,运转自然,吞吐纳入,必有养基,不疾不徐,天目是依。有光迷见,有影不迷,完全一颗,不实不虚。曰自上下,实自下上,曰自下上,实自上下。此间秘诀,自有真诠,一珠破处求缘。
从实处做去,从空处悟来,虚虚实实,妙合而凝。其丹在分,以气聚之;其丹在虚,以实吸之。其丹在若有若无间,以自然而然者守之。守之既久,而吞吞吐吐,露露藏藏,如蚌含珠,其养之也,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金丹之大要也。日日看丹,一日见丹,日日见丹,一日守丹,其看之而不见也。见有水即以丹目之,则水中有火矣。见有火即以丹目之,则火中有水矣。时时捏一丹字,刻刻见一丹头。丹乎!丹乎!于彼乎!于此乎!其忽忽若来乎,其悠悠若忘乎。其来也非突,其忘也则忽焉。所以贵乎看得紧,见得真,守得定,养得全,而金丹于是乎成矣。
欲识此中诀,逃不出乾坤。认求心地窍,先须问坎离。乾下交乎坤而为坎,坤上交乎乾而为离,坎离成而造化在乎其中。造化虽大,不外乎坎离在众卦之变化不齐,而不出坎离之中爻同游乎六位。盖坎中之一阳,离中之一阴,上下往来六爻之内,固是坤乘乾之一阳以成坎,乾乘坤之一阴而成离。《易》曰:“坎离者,乾坤之继体也。”若能以坎中而用颠倒法,取此一阳以还离中,得成纯乾,便可还丹。坎中之物属金,故曰金丹。坎即身,离即心,取坎中戊土之阳,补离中己土之虚,身心交养,即可炼金丹。
丹者,会乾坤、交坎离,使二者变而为一,至九宫八卦、七政六位、五行四象。三才之生于二者,皆归一致,然后谓之丹。
金者,五行相生至金而极。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最后生,备五行之秀。造化之功用,独全金为之宝,熔之得水,击之得火,其柔象木,其色象土,水火木土,四性俱具,历千年而不朽,经百炼而愈坚,实刚健纯阳之根本,一得纯阳,即成金丹。
呼吸参同,惟人自鉴,须达乎后天太极之理,以善所生。乐山乐水,游行自得,居尘出尘,飘然恬淡,若有想若无想,若有为若无为,到得性命同归之候,斯可立金丹之基,而证古圣惟精惟一之道矣。
道之贵乎恒也,必有振作之气,乃知久而勿懈,日日行功,有把握时亦有无处把握者,须略用内神一提,必到炉火纯青之候,则柴炭无容添入。若才得生炉,炉尚未热,一味用文火而不添柴力,则其光终无发露之时,而其神亦无锻炼之处也。又非加之猛力,须徐徐添入而不觉者,合此两端,乃使真气充满,玉关塞而元神聚矣。若不添功,必有非进即退,势不两立者。
能于天目见之,功进矣。不能于天目收之,尚未合也。自内而形于天目,天目能现而不能藏,自天目而收之于内,则内之所固结者深耳。自内而现于外者,天目中有一丹,其所见,为初得力处,由天目而收拾脐下,其着手为更亲切而有味矣。
人心之灵,易真易假。金丹之道,非假而真。实有是丹,实有是金丹,药之生也不绝,炉之设也常安。采得真,便是妙药;炼得真,便是灵丹。其细也如芥子,其渐长也如弹丸。采之在无心间,却在有意间,是谓采得真;炼之在有心间,却在无意间,是谓炼得真。分明在此,忽然不见,寻得着时,倏已在彼,此恍惚之象,皆非真境也。寻去再寻去,寻之不已,忽然得之,据而有之,如此则真境见矣。
心气何如,中有关元。此气从下而上迎则不隔,从上而下接则易滞。以下气能静,而徐徐上升,其力沉毅,能破关元。上气能动而易浮,降而下之,其力尚薄,未能直破关元。故自下而上迎者,须多一分位置。则自上而下接者,自益一分精神,悟得补偏之弊,而关元无忧隔碍矣。
补一分心气,即从坎中取来,取一分坎气,即从心中用去,用坎补心,竟是用心补坎,此乃交关之处也,非谓偏轻偏重,偏上偏下,补一处即损一处也。两气分看,则有上下两气,合看则有中宫。中宫在丹田上三分,提起下气安之,随即降其上气和之。先提下气,则心气亦着力一分,故下气亦无阻矣。
有有有,藏之深深矣,又须养之沉沉;吐之息息矣,又须浴之耿耿。如此乎,其有之也;如此乎,其不有之也;如此乎,其刻刻有之也;如此乎,其刻刻不能有之也。有之则愈珍之,不能有之则愈寻之矣。所谓深深者,丹之在舍也。所谓沉沉者,丹之自得其所也。所谓息息者,丹之潜滋暗长也。所谓耿耿者,丹之光明流露也。其实丹何在乎有?在即非丹。凡有质之物,可以着实据之,丹之所以贵者,惟其无质也。惟无质,故神妙不可捉摸。然则丹之为言,谓之丹可也,谓之性可也,谓之命可也,谓之神可也,其在自得之乎!其在自得之乎!
精神团结,便能折魔,而即化为护法。心将观乎天目,凝之而含其神;观乎丹舍,养之而聚其精,以合内外。有如此者,弗以易而易之,弗以难而难之,弗以有效而奇之,弗以无效而舍之。弗以时而效时而不效而疑之;弗以时而得时而不得,而不思所以留之。是故寻丹、看丹、守丹、养丹,分为四节,是道也夫。
道从何处着手,从何处收功。着手处即是静极,收功处即是动极;着手处即是太极,收功处即是无极。而所谓极者,何也?乃无妄之谓。太极本无极,无极本无妄。然则空空之说非也,然则空空之说何尝不是。吾心本空,惟空而后以无妄者居之;吾心本实,惟实乃能以无妄者却之。却尽外缘,留其本真,斯为极矣。此中有绝大功力,绝大本领。精义入神,在乎时时看此极字,刻刻听此极字。削去一分妄,便留一分无。妄极固无。妄而不能无,妄又将从何处着手,何处收功乎?是故气有府,神有舍,此二者不可不知。第周流之气藏于五藏,统会之气则在丹田。故曰采药者,采五藏之气也;合丹者,结气于丹田也。气足而神完,斯为无妄。岂不囫囫囵囵,全然成一个极字。
有慧眼自此心生,有慧剑自此气出。出其慧剑,放尔慧眼,而内光达于天目,而内气结于金炉,而真神透于泥丸,此三次有内外上下交合共验之理,守其一处,而上下内外之三处各验,而神而明之化境于焉,得之则非言说所能尽者。
心定,功之基也。然一定字,尚在浅处,须加一个死字。死则无所不死,死到尽头绝处,然后完得一个生字。千死万死中间,跳出一个生字来,真是生龙活虎,不可端倪。若一分不死,则有一分不生。夫人生何物可以断绝?然何物为我所本有?不可断绝之处,皆非我所本有之物,则何不一刀砍尽,一脚踢开,适见我好。好有一件本来金丹,不为水火金木所伤,亦不必借土滋生,其动而能变,变而能化,神妙不测,谓是生之至也。
见丹炉乎?见丹井乎?不见井掘起井来,不见炉设起炉来。无中生有,却是固有之物,所谓观自在者,此也。一刻不自在,炉井之位安在!既得自在,何不刻刻观之乎!即此观自在三字,扫尽一切浮关,却该得许多工夫。不观不知观之久有许多境界,许多因缘,原非外铄,亦非幻想,所谓真实不空,空即是色也。不观不空,不空无色,色即自在者是也,其功效归之于观。
先天一气本无形,中有真人自浑成。凿破元关方许见,龙吟虎啸忽风生。大丹也是无形质,却有工夫在后天。屈舌垂帘身不动,但教养似木鸡眠。不知何物号丹砂,倒转乾坤是我家。莫把葫芦遮蔽住,此中定产美金花。金花恍惚又杳冥,只在阳生一刻寻。亥后子前谁悟得,神仙从此探真神。一先天气,一后天气,皆须熟辨。
调息之功,在养之于丹田之中,而纳之于离宫之下。此地本为神气聚会之所,其根则通乎天目。天目者,两目之间,鼻根之上,人当闭目时,而神气一凝,则天目中若有光明透达者,左顾其目,右盼其目,而神气亦随之而流转矣。呼吸自然,入多出少,则先天之气,转赖后天之气以为增长耳。气是浑全之物,无可名象,及其有出入之候,便自有阴阳之分,呼出为阳,吸入为阴,其功贵乎自然,不可勉强也。
气一而已,先后天亦一而已,分开乃是着手工夫,合并乃是成就工夫。见外丹即见内丹之影,内丹团结而外有此象,此即在心地光明时候,如用水晶器盛一大物在内,其光辉自然发越,即如器外有此一物,其实只在器中。炼丹之法,不过借此以收拾其内,使心气收敛,则其中固结。其中固结,则隐然有一物,隐然有一物,即显然有一物。其在内隐然者,即其在外显然者也。
天有丹乎?曰有。何谓天之丹?日月是也。然则人有二丹乎?曰否。然则丹有异乎?曰否。人之丹与天之丹同,然则何以有二有一乎?曰天之日月合而为丹,人之坎离姤而为丹。曰日月可见其光,而坎离不见其形,何也?曰云埋日,雾藏月。其可得而见乎?曰然。则非风不可乎?曰然。曰人之风何如?曰倐而起,倐而合,是谓风媒。风媒在坎离之间,抑在坎离之外乎?曰不上不下,不内不外,隐隐而起,耿耿而合,是即风也。风无体,故能消云雾而见日月,然则人亦在乎自然起合之间,而巽风以吹之,则其丹可见矣。
聪明内用,便是金仙一粒。灵丹淡然无味,丹宜于淡字得之。淡乎世味,便深于道味,且淡于道味,乃深于正味。正味乃为金丹,若有异味,即非金丹之正道也。炼形乎?采气乎?吸日月之精乎?酿雨露之滋乎?观龙虎之斗乎?排鼎炉之作用乎?种种奇说旁门,不可枚举,若稍犯之,便不可救药。是故丹之为言,淡也。淡而后定其神,淡而后无思无虑,淡而后思无不通、虑无不达,淡而后全神毕露矣。然淡字从何处淡起,从何处淡尽?可淡处先淡,便是淡起;本淡处愈淡,便是淡尽。从口上淡则寡言,从眼上淡则内照,从耳上淡则塞聪。至于一身皆淡,则成一端严相矣。至于一心皆淡,则成一空明镜矣。仙耶?佛耶?人耶?此道合之矣。
功由粗而精,由浅而深。粗而浅者名养身,精而深者名养神。神之养也,在丹田。丹田为真养之宫,其气暖而沉,沉者使之升,则为清轻之气,循转如环,一一收拾个中,不溢不损,忽聚忽散,听其自然,此气一见,则本立而有其基也。为之难者,难在始基耳。既有根本,又何难哉!
养气之法,非静不为功。人生原只是一气,耗之则出多而入少,保之则出少而入多,此自然之理。入之既多,则氤氲充满,所谓成胎者以此,所谓游神者亦以此也。然断断毋求速,毋勉强,循循做去,到一时自有一时见头。耳有闻,目有见,皆自然之气得之,此非外境,乃真境也。
几人之身,总恃气为之主。不炼气不能固形,不固形不能长生,不长生不能悟道。故学道之士,未了性,先了命。命功无他要妙,只在元关一窍。呼吸往来之地,常常守之,时时敛之,如母恋子,如鸡抱卵,如龙护珠,如蜂酿花,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懈怠,无一点之做作。弗忘焉!弗助焉!存存焉!如如焉!自在焉!安止焉!得其一点真气,即可养吾之元神。气为母,神为子也。到充满而极浩乎沛然之候,两大可塞,三千可弥,尚何一身之足言哉!而宁有不能超脱之虑哉!
见贼即破,斩根乃除。斩根与遏欲,其功之深浅,不可一例论。遏欲太猛,魔从中来,何以见之,其根不断而自上遏之,则其机必有发。而难遏之处,惟从根上想去,此从某根起,此从某根起,根根理他清爽,然后见根拔根,而非一时即能拔出,亦非一时即能拔清。自上克下,谓之遏欲;自下制去,谓之除根。脾为后天,意生于脾,其地最下,其根最湿,湿则易于滋生。下则难以开垦,是故必用刚刀斩去,又须用武火烧来,兼此二者,渐可除根。一味看他,打他,制他,终是浮面一层,何如拔他,炼他,化他,乃是归根要诀。知此浅深之别,乃能下手。
有所见否,有所闻否,见不真看进去,闻不真听进去,进而有所见,进而有所闻,便是真面目也。他自他,我自我,如何炼他,我里头有一个他,他外头像一个我。我如何炼不得他,他来靠着我,我要拿住他。看外丹存其表也,守内丹尝其味也。得味者果自结,养果而果大,摧果而果坚,剥果而果成,此又层层进步也,保胎完元此其本。
春者,气之始也。于四时,则以春为首,于十二时,则以寅为首。寅者人事之始,即气之始也。事必从乎其朔,故即以春为始。寅初可为发念之始,子亥为水,而阳光已动;巳午为火,而纯阴已伏。究竟动者,未若寅之能畅伏者,未若寅之尚舒。一日之间,寅为最重,犹岁首之有春也。然非谓在此一时也,午为日中之令,阳易竭,须有以含之。戌为阴,伏火纳之,时其气易郁,宜有以开之,要皆不外乎气之安恬、心之坦适。而其时,则以寅午戌三时为尤重也。
气归于府,神藏于室。返元完朴,黄庭怡悦。奥窍无他,伏寻自得。谷口泥丸,首尾相合。呼应如神,贵保贵纳。纳之深沉,保之活泼。俯见金光,天目出入。各致所知,神明合德。数语关心,守之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