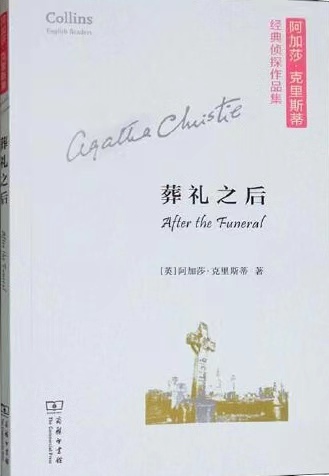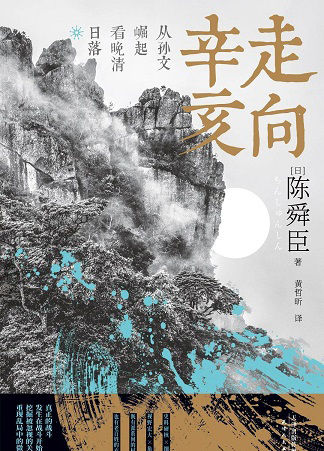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与吕惠卿差不多,《宋史》也将他列入《奸臣传》中。我用他传中的文字来考证,看不出说他是奸臣的 原因。当时的那些新法虽说是由王安石拟定的大纲,而编成条目,形成法典,有一半是出于曾布之手。朝廷中的大臣有非难新法的,曾布都一一为他们解释,《文献 通考》中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那么他文理考察周密的才能,和收放自如、深奥广博的论辩,肯定有非常过人之处。在他的传中记述他第一次被召见时,给神宗上 疏,让神宗拿出真诚果断的行动来,让四方都知道君主不可违抗,新法不可欺侮,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要害之处,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之处。他对新法是很用力 的,只有对吕嘉问办市易不得力的事而狠狠地弹劾了他,说相关的官员自己兼并土地,最终也因此而得罪了吕惠卿而被贬出做饶州知州。所说的和而不同,不是这样 吗?司马光执政,下令增加和减少役法,曾布拒绝说:“免役这件事,法令很详细,都是我写的,现在让我自己来改换,从道义上说是不能做的。”他真是不会变通 而又倔强。之后在崇宁年间因为得罪蔡京,蔡京诬陷他受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了他和他的儿子们,刑讯逼供诱使他说自己的罪名,这也是因为曾布不肯依附蔡京的缘 故(以上所说根据的都是《宋史》曾布的传)。凭《宋史》对曾布诋毁得如此严重,以至列他到奸臣中,而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那么他做的其他好事被删除 不记载的,怎么能数得清。那些被指责为奸臣罪状的,不过绍圣年间、建中靖国年间,两次提倡绍述之论罢了。如果说这是“奸”,那么何不把王安石也列入奸臣之 列?我认为曾布是千古正直之士,而他的学识和才华,都足以配得上。曾巩有这样一个弟弟,而王安石得到这样一个人,就像得到夔一样而满足了。王安石的冤情, 数百年来为他昭雪的,尚且有数十人,而曾布的冤情,真如同万古长夜,我必须要把这些说出来!
章 惇也是《宋史》奸臣传中的一名。王安石才开始起用章 惇的时候,他是编修三司条例官,之后让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避开湖南四府的地域。因为有功而得罪,前面的章 节中已经详细论说过这些。元丰三年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不久因为他父亲冒占民田而被贬出知蔡州。元祐初年驳斥司马光所更改的役法,共有数 千言,司马光的政策施行后,章 惇愤愤地与司马光在门前争辩,史书上称他的言语很混乱,大臣交章 弹劾他,因而被罢免。元祐七、八年间,又多次被谏官所弹劾。哲宗亲政后,起用他为丞相,只以绍述所说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间所更改的法令都恢复了,大兴 党狱,并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死后,皇太后商议要立的国君,章 惇说:“按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各个王都是神宗的妾所生的儿子。”章 惇又说:“按大小则应当立申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够立他。”最后立了端王,这就是宋徽宗。被贬知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又贬到雷州,最后转到 睦州时死去。章 惇不肯用官爵暗地里照顾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 援曾做校书郎,其他三人都在州县里做官,最终也没有做大官的。《宋史》章 惇的传中所讲大概就是这样。以此来看,足可以让他是奸臣吗?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给自己的亲友一件事来说,他洁身自好的品格已经可以影响世俗了。哲宗死后与太 后争论要立的人,最终也因此被贬出以至于死去。即使他主张所立的简王和申王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像徽宗这样荒淫无道的国君,最终使宋灭亡,这是世世代代 人们所共同看到了。 怎么知道不是章 惇平时观察他这个人不适合做国家的君主而故意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不足以加罪给章 惇。如果认为绍述在熙丰年间为奸,那么也是以奸上加奸罢了。他最为世人所诋毁的,莫如驱逐元祐诸大臣和请求废宣仁太后这两件事。请求废除太后确实是有罪, 说到驱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则又是以元祐间的大臣用来对待熙丰的方法来做的。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对,那章 惇做的也对;如果章 惇做的不对,那么元祐间的人所做也不对。议论者人肯定要说: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驱逐小人;章 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驱逐君子。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来区分的。如果按私德来论,章 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间的那些贤人比起来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见来论,我没有听说有用政见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认作小 人,那么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差多少呢?章 惇之所以要报复元祐那些人,而且他的残酷程度确实比元祐那些人更甚。即使这样,也要算一下元祐这些人是怎样报复熙丰年间的大臣的,他们的残酷程度也远远超 过熙丰年间的人?以德报怨,确实是美好的,但这只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怎么能用来要求章 惇呢?再说元祐那些自命为君子的人,他们的品德还达不到这么高,况且是章 惇呢?我认为章 惇有才,只是赌气而已,他是不是奸,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蔡确以《宋史》他的本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考查,他确实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主持国事八年,始终没有派他大用,官职最大做到知制诰罢了。所推行的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说他是被王安石所用的
王韶王韶的功劳都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严重地诋毁了他,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熊本熊本的功绩也列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也对他有微词,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所用的边将,在西夏和安南都立有战功,《宋史》对他们也都有微词。以上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自古以来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成功,这些也不足以当做王安石的错误。
范子渊是王安石起用来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而《河渠志》中讲述他所建设的内容很详细。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 于水利,可算是一名有才的人。史书上对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诋毁的,所以说范子渊“迎合取宠”,又说他“其器不可用”,但今天那些陈迹已经湮没很久了,其 中的是非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唐炯弹劾王安石,说薛向、陈绎、王安石等人颐指气使,与家奴无异。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推举薛向做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公元 1068年)又荐举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荐举他做了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非常深厚。而薛向所到之处,政绩卓著,马政和漕运,经过他治理,大大地 去除了长久积累下的弊端。熙河战役,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理财的功绩,可以与刘晏相当,就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能用人,也就是一个例子。只 是奇怪的是,《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多次举荐他的事,一点儿都没有提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心,是不是不想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唐坰拿他和薛向放在一起说,也应当是王安石极为信任的人。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曾知开封府(就像今天的顺天府,是当时的一个 重要职位)。《宋史》中他的传,寥寥几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是神宗评陈绎的话),当政必定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诉讼经常为人平反”三句话,之外则 诋毁他的私人品德,说“他的儿子和儿媳一天晚上一起死于士兵的手里”。又说:“他伪装成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颜回。”在传的最后说到:“陈 绎迎合人来做事,本来就不值得说。闺门管理不严,丢尽了脸。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么能用他呢?”据此来推断,那么陈绎肯定是一个操守严正,办事聪敏的 人,古代的好官,政绩可观的很多,史书上都去除了,只说他“装作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凭什么说他是伪装的。他儿子和儿媳的事与他有什么关 系,因此而指责他“丢尽了人,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么能用他”,自古至今有这样评说人的方法吗?自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重要的是,凡是经由王安石举 荐的人,善良的也会被认定为盗贼,这是全部《宋史》一贯的宗旨。
邓绾邓绾确实是一个反复小人,王安石所提拔的许多人中,他是最不行的一个了,所以王安石虽举荐了他,之后恨他谄媚自己,就自己弹劾自己举荐不当。王安石不掩饰自己的过失,更可以看出来了。而世人说王安石爱听谄媚之言,为什么他做的正相反呢?
许将他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而熙宁初年被破格录用,不能不说是王安石提拔的他。欧阳修曾称赞他的文章 风格像王沂公,被选中进士外任期满后,不经考试就任了馆职,与王安石一样,他对名利的淡泊可以看得出。王安石欣赏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在做流内铨 的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和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让代州,宋要派使者去,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前往,当面指责辽使 萧禧,完成使命而返回。他在宴席上大获全胜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他做尚书兵部的判官,整理保甲法,取得卓著成绩。在他知郓州时,百姓没有犯法的,老人们 感叹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所列的军事策略很全面。等到对西夏用兵,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数,许将马上写好呈上去。 第二天问那些权重的大臣们,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到绍圣初年扒司马光的墓,许将进谏制止。由此来看,许将的才能谋略,品德度量,都是很优异的,王安石执政 时破格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对他的评论,只说他全力制止扒司马光的墓一件中是可取的,其他的都放在一边,这样判断善恶公平吗?
邓润甫因王安石的举荐而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随即被提拔为知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做到御史中丞。他成为进士后,曾举荐贤良方士之士,召他应试 他不去,王安石是不是欣赏他的淡于名利呢?元丰年末,宋神宗命李宪征西夏,邓润甫进谏,不久就被蔡确所陷害,被贬去知抚州,他也是耿直的人。《宋史》评论 他说:“邓润甫最早称赞绍述的谋略,虽有其他的长处,也不足以看了。”唉!这也和韩绛、元绛、陈绎这些人的传是同一个笔法。 只要一旦奉行新法,有再多的好处也看不到了。王安石所用的人,怎么会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王子韶几乎是一个钻营、追求名利的人,王安石开始任他为制置条例司的属官,后提拔监察御史里行,然而马上被罢免,去知上元县。大概王安石自己感到自己错了。
吴居厚吴居厚虽不是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却是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他开始时做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很出力,调查闲田并给了梅山猺。根 据他的功劳,被授以大理丞的职位,后又补司农属。后又授以提举北常平仓,修改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称赞他精于心计,控制审查,收取盈余的利息钱数百万。又 说他到莱芜和利国这两个地方的官属自己铸钱,一年得到十万缗。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治他的罪。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 年),做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通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靠这得利,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做丞相。史书上称他在政的时间长,没有做过很 大的恶事,一时的聚敛财物,被看做是他最大的污点。现在以《宋史》他的传中所指出的他的罪状来看,他查核闲田给了猺民,是很得招抚之道的;就他冶炼铸钱, 使一国的金融界得利,国和民都得到实惠;他疏通河运,史书上也称赞他。这些都不足以说他“聚敛”。只有他每年收数百万的利息钱,是真的有损于百姓而有利于 政府吗?还是因为他办事适当得法,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呢?现在我们无法去猜测。是功还是过,是不好说清的。然而写史的人这样的痛恨他,还说他“没有做过分 的坏事”,那他的为人处事自尊自爱的程度就可以看出了。 既然他能够自爱,又能够这样地理财,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名小吏提拔上来,也不算是过错了。
张商英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学者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与薛向相比,不知道颜习斋是根据什么书说的。考证《宋史》中张商 英的传,张商英因为当面说服了章 惇而被章 惇所敬重,回来后就把张商英举荐给了王安石(这也是章 惇的人不可及之处),因此而被召,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被贬出朝廷,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大用。他是否真是王安石所倚重的人,不能够更深地考证。哲宗亲政, 张商英上书严厉弹劾元祐时的大臣,因而当时的所谓士君子们,都非常恨他。徽宗崇宁初年,蔡京任丞相,张商英又弹劾蔡京身为丞相,专心于逢迎君王,蔡京怀恨 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代替蔡京为相,说蔡京虽能恢复新法,只不过是借此来节制皇帝,禁锢士大夫罢了。于是大力改革弊端, 改当大钱为平泉货,恢复转般法,废除直达法,推行钞法以利于通商,遏制横征暴敛来使民力宽松,劝徽宗不奢侈浪费,不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皇帝很是怕 他。张商英没有辜负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孙觉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因为新法的争论而被罢官,史家很赏识他。而孙觉与王安石之间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孙觉为王安石写了诔文,其中对王安石极力称赞。
李常王安石推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反对新法而离开,史书上多次称赞他。
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执政后让他做学官,始终能尊敬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不怎么诋毁他,只有些婉转的批评。
李定《宋史》他的传中说他年少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孙觉举荐他,被召到京师。拜见了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江南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 样?”李定说:“百姓因它而方便,没有不喜欢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件事,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说:“我只是根据事实来说的,不知道京师 不让说。”王安石举荐他,让他做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说他的庶母仇氏去世而不穿丧服,皇帝下诏到江东、淮、浙转运使查明情况,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 年老,请求回家侍候养老,并没有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也自己说确实不知自己是仇氏所生,因而不敢服丧,而是因为侍养而离开的官位。不久改任为崇政殿说 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当让不孝的人在这里讲经;并弹劾王安石,奏章 上了六七次。元丰初年,升李定为御史中丞,他弹劾苏轼,将苏轼抓入台狱。哲宗继位,他被贬到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自己家没有余财。得到让 子孙任职的机会,他先让给他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才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因而公论对他都很痛恨,他 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说李定为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大多借李定为题,议论纷纷,实际上是当时的一大公案。因而这里详细列出他本传中的 内容而来分辨。传言李定是孙觉举荐的,孙觉字莘老,因学识品行闻名于当时,与王安石虽是旧交,而因为争论新法意见不合而离开官位,他这人应当是当时的贤人 们所赞许的,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据传言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做官的机会也先要让给他哥哥的孩子而不考虑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孝友之道的一项。 李定友爱至此,而怎么会不孝呢?考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仇氏当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就是佛印,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了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 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仇氏已经嫁过三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是恩断义绝很久了。孔氏不为生母服丧,《礼记》中有记载,何况仇氏是李定的 妾母呢?由此来追究,即使不为她服丧,也不为过。况且仇氏既然死于郜氏,那么李定所说的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而不服丧,确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李定 最终不忍不为母服丧,而托侍养之名离官回家,是行的心丧,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又怎么能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允许他为弃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能说 不孝已经很明显了。就算是李定果真不孝,也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而人们都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地把奏章 上了六七次,这是什么道理呢?人们之所以攻击李定,并不是因为李定不孝,是因为李定说青苗法便民罢了。而又不是攻李定,是攻王安石!是因为他不随着大家一 起破坏新法,竟然不惜编造言辞来污蔑他的名节,实质上是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才算罢休。这些谏官们,如果不用张江陵的方法,一一拉来用杖击打,就不能够警告 那些猖狂的人。而后世的史家,都认为他们这是直谏,真令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争辩,只是看当时那些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无赖竟到了如此的地步。
吕嘉问字望之,是协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他的传极其用力地诋毁他,而王安石有祭他母亲的祭文中说:“所生的才子,是我所叹服和赞誉的。 秉公守法,再困难也不做违法之事。”王安石被罢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他的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最后一段写道:“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 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由此来看,吕嘉问的为人必定有可观的地方。《宋史》的评论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常秩字夷甫,是有道之士,也是王安石的挚友。《宋史》因为他和王安石关系好,就丑化诋毁他。在他的传中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辞谢 不应召,熙宁三年,下诏书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才来到朝廷,奏对后就辞谢回家。皇帝说: 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离开也行。 就拜他为右正言。”又说:“当初常秩隐居不做官,世人都以为他肯定会隐退。后来王安石做丞相变法,天下沸腾,认为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所下的法令,认 为是正确的,一召就来了,在朝廷中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也没有什么建树,名望一天天地衰退,被当时人们所讥笑。常秩长于《春秋》,著有讲解数 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春秋》,就隐讳不再提他的学问了。”看他同一个传中前后距离数行之间,记载的内容竟如此矛盾,以前的史书是没有的。考查宋神宗在治平 四年十月,诏常秩进朝,而常秩多次推辞,直至熙宁四年才进朝,他的传中前面是这样说的。王安石做丞相是在熙宁二年,常秩被召见,是在王安石做丞相的前两 年。常秩到朝中是在王安石做丞相之后的两年,而且还是三次去聘请,以礼恭送,才勉强上了路,怎么能说“一召就来了”呢?怎么诬陷人到了这种程度?又是多么 地不会诬陷人呢?刘敞《杂录》中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颖州人,开始不被人知,欧阳修守颖,让官吏比较郡中的户籍,更正每户的等 级,常秩赀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廉洁贫穷,希望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因为他的礼让而感到奇怪,问他们,都说: 常秀才孝悌且有德,不是庸碌的一般民众。 欧阳修为改他的户籍等级请常秩相见,为他的为人而感到高兴,常秩从此闻名于外。”现在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到熙宁三年(公元 1070年),给常秩写的诗和书牍有十余条。欧阳修比常秩大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希望能包着头巾,拄着杖和先生长者四处走走。”等他去世 后,王安石为他写了墓碑,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人的贤德,而他们向往常秩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常秩的贤德就可想而知 了。而史书上竟这样诋毁他,而且评论他说:“学问不为自己所用,而随世道而行,就像井上的桔槔,让它一天不动,也是不可能的。”唉!只因为他与王安石交好 的原因,而攻击他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想不在这肮脏的史上出名能行吗?至于说常秩避讳讲他的《春秋》之学,则我考查王安石并没有废《春秋》,那么常秩即使对 王安石献媚,怎么又会避讳呢?这种诬蔑就用不着辨析了。(王安石没有废除《春秋》,在第二十章 中另加讨论)
崔公度字伯易,博学而且文章 写得好,当时人称“曲辕先生”,曾经作《感山赋》七千字,欧阳修、韩琦都很看重他。刘沆推荐他为茂才异等,称病不应召。英宗时授予他国子监直讲,因母亲年 老而辞去官职。年轻时与王安石交情很好。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有一篇《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之死而痛惜,说“世上了解王逢原的人再没有像 我们两个人这样了”。王逢原安贫乐道,品德超世绝俗,和王安石正是同一种节操,而崔公度能被这两个人所赞许,则他的清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而《宋史》 在他的传中说:“只知道取媚于王安石,白天晚上去拜访,就是王安石蹲在厕中他也要见。曾从后面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头看,崔公度笑着说: 相公的带子脏了,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 见到的人都笑,他也恬不知耻。”噫!不知道蹲在厕中时怎么会有人在一旁;说见到的人都笑,怎么在厕中会有这么多的人?这真是不近情理的最污秽最卑鄙的话 了,而将这写入正史,是什么用心呢?重要的是凡被王安石稍敬重的人,务必要诋毁他,把他说得不像人才罢休。
王令字逢原,是王安石生平第一个敬畏的朋友。他是刘敞所说的:“处士有道者”三人中的一个。王安石集中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死之后,王安 石为他写了墓志铭,称他为“天民”。《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在王直方的《诗话》中说:“王逢原被王安石所赏识,王安石执政后,一时间来依附的人,每天门外 满满的,一个个恭维奉承有加,王逢原很厌烦这些,于是在他的大门上写到: 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 意思是应该有知耻的人。可是来拜见的人却不见少。”看王安石所写的墓志铭,王逢原应该是死于嘉祐四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那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 呢?可见宋代的人对于王安石,污蔑的方法是没有一种不用到极点的,亲友没有一个幸免的。幸运的是《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了传,那么类似崔公度将 《春秋》的学问藏起来,以及常秩在厕中擦拭衣带的事,就满纸都是了。
这三个君子,常秩和崔公度虽然一度在朝中任职,未曾担任过重要的职位,他们对于新法,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王令则是在新法施行时,他墓中的木头已 经都弯了,而后来写书的人,竭尽全力地污蔑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使我连史书中有关吕、章 这些人的恶行,也不敢全都信了。 并不是我爱屋及乌,实在是因为那些史官们看不惯某个人就要累及他的亲友,所以不足为信了。
王安石所用的人,不止于这些;他所交的朋友,也不止于这些。就拿这四十人来说,其中贤才有一大半,品行不好的不到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品行不好, 他们的罪状还都是没有定论的。以王安石崇高的品德,不肯以品行不端来看待别人,偶尔被别人所出卖,也应该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逢迎,乐于谄媚,王安石肯这 样做吗?凡是曾经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或者与王安石有亲缘关系的,或不肯随声附和诋毁新法的,即使是君子也必定被诬为小人,这样说来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 是合适的。只有一个被极其怨恨的罪魁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有远亲,熊本又曾经以奉行新法聪明机敏多才的原因举荐他(见《宋史》中他的传),而他曲意奉承、 谋求仕进的本领,没有用到王安石身上,而反倒用到了司马光身上,那么王安石即使不善于了解人,也比司马光高出一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