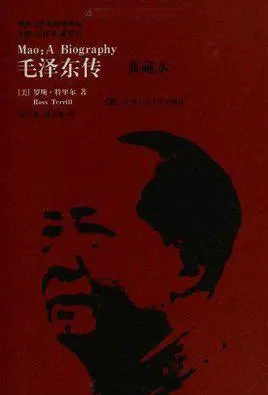柏林禅寺在唐朝出过一个伟大的禅师——赵州从谂禅师,他的舍利塔现在还在这里。赵州禅师有一个话头,成为禅宗修行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叫“无门关”——现在我们的禅堂就叫“无门关”。
这个话头来源于这样一个公案:有人问他:“狗子还有佛性吗?”赵州禅师说“无”。就是赵州禅师的这个“无”,成为一个话头。这个话头,从唐朝到宋朝、乃至到元朝,有很多禅人参究,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无”下明心见性。
“无”是什么?宋朝有一位祖师叫无门慧开,专门讲到无门关这个“无”,如果你在那里参“无”,赵州禅师说“无”、“狗子无佛性”,若是观想什么都没有,观想“虚无”,那就错了,那不是参禅,那是观,有点像天台宗的空观,所以“无”不是虚无的“无”。
“无”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令我们起疑情,疑什么?疑赵州禅师为什么说无?就是疑这个。你也可能猜测,有很多推理,很多经典里面的理解,现在告诉你,所有这些意识活动、猜测、理解、来自于经典里的注解,在这里都用不上,都不算数。你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说无,一二三四……打叉,不对!
告诉你,用意识在这条路上走,不可能找到答案,就算你以为找到了,它也不能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既然解决不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它有什么用呢?所以可以直白地说,你费尽心思猜测、理解,甚至找寻经典里的注解,都白费功夫。
你说我参这个“无”,不知道从何下手,那就对了,参它就是要让你感觉到不知从何下手;有的人参“无”,说心里感到很闷,对了,就是要让你感到闷;有的人说,我参“无”完全用不上功,对了,就是要那种完全用不上功,但又能不放弃,不断地在心里提起话头,提起“无”的话头。
在这种参究里,支持我们不断地提话头的“什么”,实际上是信。这里的信有很多层:首先我们信赵州禅师,他说“无”,绝对不是随便说的;
其次我们信自己的心,除了分别、妄想,除了理论、注解,无量劫以来我们生死轮回就是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佛学里有“识”,“分别心”,我们相信,我们的内心除了这个识以外,还有一条路。当我们不断地提“无”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识的活动,会逐渐地削弱,妄想、分别会越来越少。
关于这个“无”,古人有很多比喻,这个“无”就像铁钉,现在要你用嘴巴去嚼它,后果是什么?后果可能是你的牙齿全部嚼烂掉,如果你坚持嚼的话。“无”就像一个铁钉,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地被咀嚼,就会把我们无量劫以来平时特别活跃的分别心那个牙齿嚼烂掉,让它起不了作用。
它就是要让你无路可走、无理可申、无话可说,把你堵在这里,被堵在这里,你还能不放弃,而且越闷、越堵,你越勇猛,越坚持,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这个锻炼的过程,也许是痛苦的,刚开始也许是烦闷的、茫然无序的,但是就像嚼铁钉,慢慢地你会从茫然无序、烦闷、没有滋味中,嚼出一些滋味来。这个时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一湾水,很浑,有很多泥巴、杂质,这个话头就像是往水里扔一个东西,扔进去以后,在一个阶段这个水会更浑,比以前还浑,比不参禅的时候妄想还要多。
但是越过这个阶段之后,这个浑的东西就会沉淀下去,变清,清归清,浊归浊,清浊就分判了,到这个时候,你才觉得,啊!这里面大有文章啊!你的心就不肯轻易放弃了。所以这个方法很绝,是要逼我们悬崖撒手,头撞南墙,舍身跳黄河,逼拶我们。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有一个习性,就是一定要在理路、意识上得到点什么,所以众生最大的贪在这里。最大的贪不一定是贪吃、贪衣服,不是贪财、色、食、睡,我认为,众生无量劫与生俱来的最大的贪是名。我讲贪名的时候,你们想的是什么?想当住持,大和尚,会长,这是一个很肤浅的理解。
名是名相。所有的名相是怎么建立的?是由分别心建立的。所以众生的分别心就像一个贪婪的野兽,要你不断地给它喂食,喂什么?它吃的那个食料是什么?就是这些名啊!这个好,那个坏,就那些判断。这个野兽在那里张开血盆大口,要你不断地喂这些名言、名相。
其实云水行脚的师父的行脚体验,对修行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能观照心念。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寺院,我们马上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要搞清楚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个人是什么?这个是住持,这个是知客,这些反应来自于不安全感,不安稳,进而产生各种分别——名。
所以众生最大的也是最难断的贪,实际上是这个名,分别心这个野兽,现在我不给它喜欢吃的东西了,它不是喜欢吃山珍海味吗?现在我扔给它砖头瓦块、木头、铁钉。我让你吃!在我们不断地扔砖头、瓦块、木头的情况下,这个分别心野兽的胃口、贪就会歇下来。所以参话头,我觉得是非常猛利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