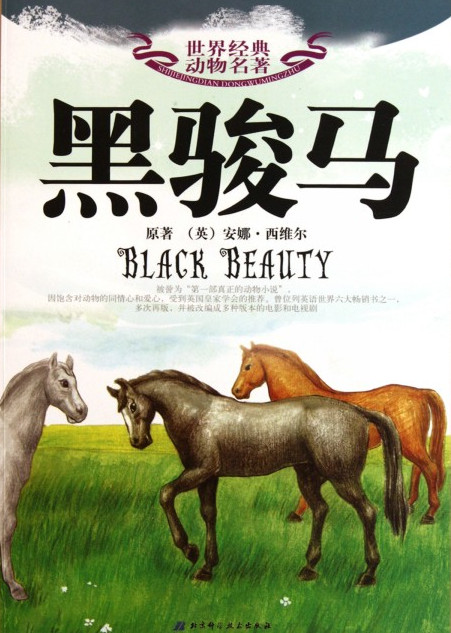九九重阳,起兵之日。
此处的“九九”,自然为农历九九。农历九月九日,为公历10月26日。[此处是指1895年。]
三月初三(上巳)、五月初五(端午)、七月初七(七夕)、九月初九(重阳),这四个奇数日月,并列为传统中国的四大节气。
重阳别名“登高节”,抑或“菊花节”。在这个日子里,人们习惯登高望远,出入佛寺,头饰茱萸以驱邪气。古人迷信时值盛开的菊花亦有驱邪扫浊之效,因此又得名“菊花节”。
孙文之所以将举事之日定在九九重阳,皆因此日人人外出,市井热闹,成群结队不易引人注目。
广州城内暗潮涌动,义军看似活动频繁,实则是随波逐流,对大局模棱两可。这场爆发于1895年、史称“乙未广州之役”的武装起义,由于兴中会内孙、杨两派的分歧,难以在步调上保持一致。
孙派在广州据点受袭的第一时间便急电警告革命军按兵不动,谁知“泰安”号竟然擅自提前起航,以至于打草惊蛇,加之朱淇的背叛,此番起义失败已成定势。
由于西医在当时属稀罕物,孙文在广州医学界内算小有名气。当缉捕委员李家焯将谋反与主犯告知两广(广东、广西)总督谭钟麟时,谭钟麟还兀自不信:“李委员想岔了。这个孙文,本官亦识得。身为郎中,却打出农学会的招牌,确实算是个异类。但你说他造反,本官是万万不信……”
但李家焯态度强硬,谭钟麟不得不勉强妥协道:“依你之言,反贼潜伏在周边海域?本官自会派兵将其一网打尽。另外,此事机密,切勿泄露。”
两广原是由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坐镇,直至同年三月份,李瀚章因病辞官,原闽浙总督谭钟麟才得以接了这肥差。
广东自乾隆以来便垄断着清国的一切对外贸易,此处自然成了官员眼中捞油水的宝地。
新任的总督谭钟麟为湖南茶陵人,在四川等多地官界浸淫多年,算得上是官场老油条。他眉头紧锁,对手下幕僚道:“今日马巡抚病情日益加重,恐大去之期不远。值此非常时期,谁敢轻言谋反之事,休怪本官重罚。”
现任广东巡抚马丕瑶重病卧床,照惯例,巡抚身笃,上级总督必须兼任巡抚之职,直至次任巡抚到任。巡抚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各事务亦是由总督衙门签批。谭钟麟心中早有了计较:“重阳前后,总督公务繁重是众人皆知的。届时再曝光谋反一事,这失职之罪,便加不到我头上。”
座下幕僚自然是对上司的念头心照不宣,当即应道:“是,属下定当守口如瓶。”
两广总督贵为封疆大吏,府中自然聘养着私人的幕僚团队。这些幕僚随着雇主走南闯北,忙碌时则帮忙出谋划策,闲暇时则陪同吟诗对弈。谭钟麟虽是湖南出生,却发迹于闽浙,因此其座下幕僚多为浙江人。
谈起浙江幕僚,其中绍兴师爷声名尤甚。他们大多善于察言观色,且嘴皮子也牢靠。
“谋反之事尚未坐实,切莫声张。”
仅凭谭钟麟这一句话,幕僚便将上司的拖字诀猜出七八分,道:“属下这便去嘱咐底下人注意些。”
身为地方官员,自然巴不得管辖民众能安分守己。但若事端在所难免,市井流氓暴乱,与知识分子运动可完全是两种概念。强盗恶徒无处不在,实非区区地方官吏所能管束得了的。但带有政治性的“造反”可不同,就以“明哲保身”为第一要务的朝廷命官而言,“造反”无异于是对顶戴的最大威胁。
因此,谭总督是不择手段也要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暴乱”的,万不能让朝廷察觉到此事。要知道,觊觎两广总督这一肥差的人,可虎视眈眈地窥伺着他的失足。若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再理想不过。
此时此刻,孙文正强作平静。广东富庶,商界常有持续至深夜的晚宴。为防酒后闹事,此类场合多半少不了政府军队的监视。
此情此景对孙文来说本应习以为常,但此番的阵势却有些许不同。官兵数量多于往常,且神色紧张。
作为圈子里少见的西洋医生,孙文应邀入席。今晚的异常显然不是他的错觉。坐在孙身旁的商人也感觉到了,向他搭话道:“看今晚的架势,衙门是铁了心要与觊觎闱姓饷银的贼人分个高下。”
“哈哈,那倒未必。”孙文唯恐天下不乱似的高声笑道,“怕就怕,他们这趟是冲着我孙某人来的,毕竟我们‘四大寇’凶名在外,早是朝廷的眼中钉了,哈哈……”
虽说“四大寇”一说早在圈内传开,但孙文在公众场合如此大摇大摆地承认,倒还是头一遭。他在高笑的同时,不忘暗中观察听了这席话之后周边人的反应。
“四大寇”诽清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香港崇尚言论自由,孙文等人诽清,可谓一呼百应。这一点,在清廷管辖下的广东是绝不可能实现的。若有人胆敢向官衙告密,难免会被视作众矢之的。毕竟,广州民众多未接触过满人,他们对满人的认识仅局限在一点:“满人真是一群废物,竟被小小日本打得满地找牙。”
另外,在广州的洋车场,车夫之间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那群满大人哪还能打仗?冲锋陷阵,都是咱汉人吧?咱汉人若能打着自己的旗号作战,哪会输得这般惨?”
孙文一向坐不惯洋车,一部分是因为他爱好步行,然而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坚信身为革命家,必须踏遍革命之地的每一寸土地。
在归途中,孙文仍不忘暗中为巷战指挥部选址。在旁人看来,此刻的他形单影只,实际上,有一名同志匿身于隐蔽处,暗中护卫其周全。这名保镖不仅要时刻关注孙文的行踪,还得脚底飘忽,故作醉酒状。装作醉汉,步伐忽快忽慢,或当街叫喊,往往不会太引人注目。
而今晚,这位保镖却走出阴影,攥住孙文衣袖,故作发酒疯道:“老子姓王,是中国的大王,哈哈哈。”
这是事态紧急的暗语。在旁人眼中,这个醉汉缠着绅士继续撒泼道:“你的耳朵是摆设吗?我说了我姓王,不是陈,不是陈!是王!”
孙文自然知晓其中含义,忙回应暗语,表示自己明白了:“臭酒鬼,给我让开!”
事情败露了!——孙文把戏演足,心中却已翻江倒海。他摆脱了醉汉后,立刻转身钻进一旁的暗巷之中。此处地处繁华街,酒楼菜馆林立,人多眼杂,敌人或许就隐藏在人群之中,陡然钻入小巷不免招疑。但有了躲避醉汉的名义,便显得自然得多。
方才同志的醉语中多次出现“陈”字,莫非是暗示让自己求援于陈少白?不对,他嚷嚷着自己不姓陈,又像是在警告自己,万不得前往陈少白处?
陈少白藏身于圣教书楼后院的福音堂,此处藏有大量用作宣传起义的文书,谈得上是起义军位于广州的司令部。照理说,事情败露,应第一时间赶往司令部,与同志商量对策。醉汉同志究竟语出何意?
孙文可不是优柔寡断之人,当即便做出了决断:“去找黄旭初。”
孙文的友人之中,只有这黄旭初在官府眼中算得上是地道的良民。甚至,没多少人知道他与孙文相熟。黄旭初的住所周边地形复杂,作为匿身处再合适不过。由此决断,可见孙文遇事不乱,心思了得。
福音堂,陈少白等人得信后,连忙将起义文书投入井中,彻夜逃亡香港。毕竟香港乃孙派的根据地。他们此时能做的仅有祈祷孙文与陆皓东能免于官府通缉,安然返港。事实是他们刚登船,广州城内便进入戒严,孙文在城内变装潜伏了十日之久,才在当地会党的协助下,偷渡澳门,再转至香港。
孙文的潜逃,宣告着这一场本该轰轰烈烈的起义,就此胎死腹中。
按原计划,河南轮船“泰安”号本应在起义前夕起航,翌日抵达广州后,起义军取出暗藏在水桶中的军火,一举攻下主要政府部门。
起义军人数众多,为防走漏了风声,直到临岸前,数个带头人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并授以红色腕带用作甄别敌友。
可恨出师不利,起义军方才登岸,迎上的便是严阵以待的官兵。
总督谭钟麟上奏于兵部的奏折,将起义军谎报为觊觎闱姓饷银的盗匪,并称匪众虚张声势,扬言五万兵力,实则仅有五百余乌合之众。孙文、杨衢云在内的四十五名主犯已悉数就案,剩余逃匪尚在缉捕中。
“泰安”号原计划九月八日起航,奈何在组织上出了些许问题,只得延期。也正是因此,才让地方政府注意到风吹草动。所幸孙文将将潜逃,但另外四十余名驻广的干部可就没那么走运了。
谭钟麟在奏书上一口咬定这是一起劫掠闱姓饷银的暴乱事件,对“造反”一事缄口不言。这自然是谭总督的明哲保身之策。
清朝十八省,地方政府以官营博彩筹银的只有广东一隅。发起这一制度的是前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他创此制度并非是为了一己私念,纯粹是为了给胞弟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筹集军饷。
在潜逃的小型蒸汽船中,孙文强忍泪水。潜逃之际,盟友陆皓东的死讯传来,他满腔的悲痛只得化作沉默,静静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这一基督教礼仿佛让孙文的思绪回到了十一年前,回到了与陆皓东一同接受洗礼的那一天。时隔十一年,挚友陆皓东的洗礼名,再次在他脑中响起。他注视着远方的波涛,颤抖的双唇微微张开:“中桂啊……”
两人曾一同推开基督教的大门,曾一同将光复中华的志向铭刻在心中。
孙文恍惚地抬起手,试图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浪花。从指缝中掠过的海风,在他心生自责的同时,却也将他内心中那团烈焰煽得愈发炽热。自责愈深,反清的意志也随之愈坚定。
“中桂,我定会把你那一份意志带到清朝覆灭的那一天!”
据传闻,被捕后的陆皓东宁死不招,留下遗书后,慷慨就义。至于遗书的内容,会党同志百般调查,也只获取了一部分而已。其中有这样一句:
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敌人软硬兼施,最后甚至钉其手足、锯其四肢,无所不用其极。他不知被冷水浇醒了多少次,但由始至终只有一句话:“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陆皓东精通洋文,外籍友人众多。美利坚领事曾愿为其保释。但有陆皓东白纸黑字的供词,造反之罪已坐实,领事也无能为力。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
当然,在总督府对外界公开的公文中,这些志士只是一帮见财眼开的强盗而已。
孙文想象着挚友被捕与受刑时的情形,心如刀绞。
逃离广州的孙文,全程变装从顺德逃至新会,在此地搭乘小型汽船前往澳门,再转至香港。一路坎途,听闻情报颇多,却难辨其真伪。直到抵达香港,才得以把握局势动态。
此番起义失败,就义的会党干部除陆皓东外,还有朱贵全、邱四二人。新军首领、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由于是军籍,被关押至营务处,处以六百军棍身死,这算是对军人的死刑。其兄,曾留洋英吉利的海军士官程耀臣也死于狱中。其弟程璧光及时逃往南洋槟榔屿,保全了性命。
统而言之,乙未起义的就义者仅有五人,其中包括陆皓东、朱贵全、邱四三名民间人士,与隶属于军队的程氏兄弟二人。
另外还有受捕者六十余名,均为受煽动的愚民,官府也不欲多做追究,每人赔偿了一元抚慰金,当场给打发了。
谭钟麟那“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当成功,一系列措施下来,孙文等人倒真被归类为了见财起意的匪徒。
数日后,广东按察使发文,在逃人员的通缉令与悬赏金额也一一出炉:
孙文,号逸仙,香山县人。悬赏一千元。
杨衢云,香山县人,祖籍福建。悬赏一千元。
朱浩,清远县人。汤亚才,花县人。悬赏三百元。
其余从犯,皆悬赏一百。
看到这些贴在街头巷尾的告示,陈少白贫嘴道:“啧啧,逸仙一千,陈某一百,同样是人头一颗,差距竟有这般大?”
孙文放声大笑道:“知足吧,少白,你至少榜上有名。你这样都抱怨,士良榜上无名,岂不是要闹将起来?”
“辅仁文社的谢缵泰也未在通缉名单中,可见被捕的同志直至最后一刻也未背叛。”陈少白态度一转,沉痛道。
广东当局的上奏,对陆皓东供词中的民族主义只字未提,并将孙文塑造成了一个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
朝廷回诏指示,福建、广东两省毗邻台湾,对其治安要严加防范,但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此后既无实际剿匪措施,对潜逃香港的主犯孙文也只是要求香港当局将其引渡而已。
数日颠簸,孙文抵港。道别之日,在此处与陆皓东做下的约定,仿佛如发生在昨日一般历历在目:
此番起义若有一方遭遇不测,无须照顾其家小。
陆皓东的父亲早亡,孑然一身的他,将继承的数千元悉数投以革命。
而孙文已把家小安置在夏威夷,托孙眉照顾。他的家室仅有两人,指腹为婚的妻子卢慕贞与数十年后成为政客的小儿子孙科。
在夏威夷与众亲友道别的时侯,其兄孙眉貌似对弟弟入教基督一事仍心存芥蒂,不无苦楚道:“倘若你真遇不测,慕贞母子俩由我照顾,你放宽心。你信耶稣,怕是收不到我们供的香,但孤儿寡母仍旧会为你烧香供养,以表心意。”
“无须烧香,你们若有心,在我灵前放上几束白花便可。”
孙文等人满以为逃至香港便可万事无忧,谁知清国一张引渡令,香港政厅便剥夺了他们长达五年的在港居住权。
孙文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恩师康德黎介绍的律师德尼斯,但仍于事无补。引渡名单上仅有孙文、杨衢云、陈少白三人,但未上榜的郑士良也不欲在此地多做逗留。律师德尼斯无奈下,只能建议道:“你不妨去日本?那儿与香港往返不过数日,剩余的资金应该足够保证你在日本生活无虞。”
日本确实是个理想的安身之处。孙文至此三度往返于中美,皆途经横滨歇息。而最后一次,就是在刚过去的今年1月份。
当初孙文适逢进言受挫,与陆皓东一番旅途下来,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那后便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民族主义革命家。革命团体兴中会应运而生,孙文在夏威夷印刷了一批会党纲领,打算运往香港。
当时,在洋船上讨生计的船小贩基本都是清国广东人。孙文返航途经横滨时,与一位名为陈清的船小贩邂逅。陈清性子豪爽,听了孙文的意向后拍手称快,取走一部分宣传纲领,自愿为孙文向在横滨居住的华侨发放,并放言道:“这热闹我是凑定了!这样吧,暗号是‘送一份五岛明鲍过来’,举事前,你写信或用电报知会我一声!我一定星夜赶赴战场!”
孙文当即对这条好汉心生亲近,用力地拍了一把他的肩膀,笑道:“好,一言为定!以五岛明鲍为号!”
日本五岛特产的明鲍(鲍干),不单是上佳食材,更是治疗眼疾的上好药材,各地药店均有销售。
陈清果不爽约,起义前月,孙文一通电报,他就抵港了。他就是混在泰安号中的一员,因在港是生面孔,又是日本归来,当局也觉得抓错了人,支付了一元的抚慰金,就将他打发走了。
如今,被香港当局下了逐客令的孙文与陈少白打算暂时栖身于日本,郑士良也欲同行。陈清连忙早一步返日,安排准备工作。
这一日,孙文正独自在港口附近的茶馆中暗自神伤,廖大竹带着他的大嗓门儿出现了:“夏老板,别灰心。”
“是大竹兄啊。‘隼’号打算几时离港?”
“船出了些问题,还在修理。”
“早日修好吧,正好捎我们去日本。我、少白、弼臣(郑士良),三张船票,先与你预定了。”
见孙文还有心思开玩笑,大竹也就放心,大笑道:“哈哈哈,得了吧。我家这头‘隼’可上了年纪,再受不起折腾了。当家的正考虑把它卖掉。”
“这么说,大竹兄暂时不上甲板了?”
“是该歇几日了,随时待命吧。下趟出航,打算到台北溜溜,这些年尽在台南转悠了。”
“不赚钱了?就为旅行?”
“哈哈,赚钱、旅行两不误。谁让客人的意思,就是云游四海呢?”
“让我猜猜,你说的客人之中不会就有上回带着郑先生的引荐信前来拜访的台湾举人林小兄吧?”
“还真瞒不住你。孙先生,你欲行大事,得记住,台湾万万不可弃。”
“我此番只是暂寄日本,方便观察大陆局势。他日大事有成,孙某计划以夏威夷为起点,环游世界。台湾是同胞领土,我自然片刻不敢忘怀。少白也打算到了日本后,立马动身去台湾见识一番。他想看看,亚细亚人会怎样殖民亚细亚人。”
“哼,你们可别期望过甚了,日本在殖民方面是个雏儿,只怕会照搬洋人那一套吧?”
“此言在理,我们只能期待能有稍许创新吧……”
攀谈至此,廖大竹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低声道:“香港当局虽不像广东那样恨不得将谋反者就地正法,但仍然对你们没安什么好心思,你看那个人……”
就在远处,一个头戴斗笠的农夫路过。老江湖的大竹自然不难发现这个农夫便是方才摇着蒲扇经过的读书人。
“唉,我早就有所察觉,看来此地已不可久留……”孙文叹息。
距前往日本的航班尚有数日,孙文等人一面谨防港英当局的迫害,一面收拾此次起义的烂摊子。
清廷严厉打击任何反政府活动。国人聚居的“他乡”,才是反清运动的主战场。华人占九成以上的香港自然就成了革命家眼中的乐土。只可惜,孙文等人被港英当局下了逐客令。另外,中英两国乃是友邦,英国人不会坐视反清组织在香港为所欲为。
由此,孙文只得再择新据点,也就是日本。
在日本的华人远不如香港多,甲午战争时更是严重缩减。虽在战后有所回升,但仅局限于横滨、神户、大阪、长崎四地,合计人数不过三千。反观香港,九成居民属华人不说,再加上与之毗邻的南洋,总计华人数量何止千万。与之相较,日本的三千实乃九牛一毛。
但孙文之所以选择此地,有其道理:“日本华人虽少,却直指我国的心脏。北京与上海的局势时刻牵动着全国。香港与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感受得到。”
但郑士良对此表示异议:“我推荐南洋。那儿的唐人远超于日本,最主要的,洪门的力量也散布在那边。”
洪门是当时的主要反清地下组织之一,郑士良同样是其门下中人,称得上是兴中会与社团之间的媒介。
郑士良,字安臣,号弼臣,是圈内有名的“千面人”。初在广州医学校与孙文邂逅时,他自诩医生,同时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反清会党身份就不用说了,更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是个武术高手。此次起义,他是九龙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唐人之多莫过于唐山(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别称),唐人数量未必就是评判标准。此次暂移日本只是权宜之策,有朝一日,孙某定携弼臣一同游遍‘唐山’。”说完,孙文紧紧握住了郑的手,他对这位同志还是非常感激的。孙文与杨衢云被悬赏一千,郑士良连通缉名单都没上。但在清廷眼中,掌控洪门的郑士良,其威胁可远非孙、杨二人可比。
早在策划起义之初,兴中会内早对是否拉拢会社有所争论——会社提供的人力是不可或缺的,怕就怕他们有人嘴不牢靠,走漏风声。
而结果呢?最后走漏了风声,导致功亏一篑的竟是孙派自己人朱淇。新军与会社倒是将秘密保守到了最后一刻。
自那后,孙文独自致力于留美华人的游说工作;陈少白暂居日本,密切关注台湾时局;而郑士良则频繁往返于香港与“唐山”之间。
三人起航日本之日已定下了,搭乘的是日本邮船“广岛丸”号。
当时的外籍船,无论其国籍,皆对中国旅行者来者不拒。那年月,物美价廉的华人劳动力可是抢手货。“广岛丸”号虽是邮船,却满载着前往菲律宾矿山、农场的华工。稍年长的华工被称作“买办”,年轻的华工被唤作“波伊”。幼时初至夏威夷的孙文对“波伊”一词的含义甚是好奇,直至学习了洋文,才得知所谓的“波伊”只不过是英文中的“BOY”(小弟)。顺带一提,船小贩陈清曾几何时就是某条客轮上的“波伊”。
陈清提前返日,做筹备工作。他已与“广岛丸”号上的小弟打过招呼,让他照顾好孙文一行人。“广岛丸”号在香港停泊了整整四日才离港,孙文吩咐小弟道:“能给我弄把剪子来吗?大概这么大的就可以。”
孙文比画了个十厘米的手势。小弟是个性子开朗的青年,说道:“交给我吧!多问一句,客人这是打算到日本开理发店吗?”
孙文揪起自个儿的辫子,在小弟眼前摇了摇,笑答道:“或许吧……但在此之前,我得先把自己的头发给拾掇了。”
“您可考虑清楚了,这一剪子下去,您怕是再不能回‘唐山’。我就怪了,近几年,不留辫子的唐人怎么越发多了?”
孙文抚了抚手中的辫子,笑道:“哈哈,别说不留辫子,我在夏威夷的华人朋友里,有三四人把发色也给染黄了。”
阴阳头、猪尾巴,称得上是清国人的独有标识了,但孙文从未引以为傲。这从一开始,便是满人的风俗,是他们强加给汉人的。
所谓阴阳头,就是剃光前脑的毛发,仅留后脑的头发以便编辫。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翌日就颁布了“薙发令”,强迫所有汉人削发易服,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
自那以后,除天生秃头与佛门中人之外,所有汉人男性均剃发留辫,清廷视其为降服的标志,凡有违令者,一律做反贼处分。但这一法令的有效区域也仅限于清国本土而已了。
香港现属英领,在住华人本无须蓄辫,但考虑到两岸往来频繁,蓄辫之人还是占大头,仅有少部分决心与清国断绝关系之人,能够毫无留念地断辫。就算是远在夏威夷,长年不归的华人,念及故乡,也下不去决心断辫。
“其实也用不着纠结太多,瞧,不知是谁发明了这么方便的法子。”小弟摘掉瓜皮帽,竟连辫子一同摘了下来。
孙文奇道:“假辫子?”说着取过帽子细细端详起来。
小弟顶着个寸板头,并没有蓄辫,一条假辫子拴在帽尾。他见孙文反应,纠正道:“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假发。我在日本时换上身学生制服,再戴个鸭舌帽,活脱脱一个摩登青年。”
“广岛丸”号常停靠于上海与广州,这顶假辫帽可是小弟走南闯北片刻不离身的宝贝。郑士良与陈少白也一同凑过来瞧这稀罕物,两人皆被这玩意儿逗乐了,拍手叫好。自打起义失败后,他们还是第一次笑得如此畅怀。
言及辫子,孙文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对了,我听陈清兄弟说,我们这趟去日本,负责接待我们文具商冯镜如先生,就有个外号叫‘无辫老冯’。此人,一定与我们志同道合。”
今年初,从夏威夷返航香港,途经横滨时,孙文从陈清口中听说了此号人物。只可惜当时旅途匆匆,未能亲身拜访这位奇人,孙文只得托付陈清将革命文书转交给他。
虽未曾谋面,冯镜如在孙文眼中却好似相交莫逆的知己。清国在日本设有领事馆,“无辫老冯”的作为等同于在向清国叫板。
当时,日籍船的船长多为洋人,尤其是国际航线更为如此。此番赴日,说白了就是起义失败后的逃亡,四人沮丧的心境可想而知。如今为了缓和气氛,硬是拉出假辫子这个笑料,四人都从各自的笑声中听出了一丝牵强。
孙文强装笑颜鼓励道:“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做人要向前看。只有好好反省这次的失败,才不会重蹈覆辙。”
对,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广岛丸”号刚出港便遭遇台风,船体剧烈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船去。
陈少白抱着桅杆大声道:“我倒想好好反省,但老天爷好像不大支持!”
“看来这是……”郑士良瞅准摇晃停歇,继续喊道,“老天爷在警告我们,今后命运多舛。”
“我命由我,不由天!”孙文猛地站起身,却差些跌了个踉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