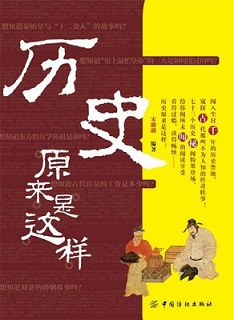滞英期间,孙文是大英博物馆的常客,尤其是那栋圆形的图书阅览室,俨然成了孙文在伦敦城的“第二居所”了。
在国外媒体的大肆渲染下,“Sun Yatsen”之名气一时无两。身处博物馆中,耳边时常能传来陌生中年妇女那语带崇拜的赞叹:“这张椅子,曾是加里波第与马克思的专座。最近又多了个新主人,便是那大名鼎鼎的孙逸仙。”
那年头在英吉利,东洋系的外国人可是奇货可居。照常理,本地人辨别“Chinese”的标准便是那垂在脑后的“猪尾巴”。孙文遇绑前,不止一次被误认为日本人。对方每每得到“No,I am Chinese”的答复,总会狐疑地打量孙文后的脑勺,确知无编辫后,则两手一摊,表示不可理喻。
公使馆迫于压力还孙文自由后,仍继续雇用私家侦探监视其行动。辛亥革命后,侦探社的监视报告被公布于世。冗长的监视记录中,仅罗列着一列列孙文每日出入图书馆的时间,想必那负责盯梢的侦探也后悔接了这份苦差使。唯一算得上文字记录的也只有寥寥数行:
今日未用午餐。
今日携带面包进入图书馆。
探索革命的经历,让孙文认识到自己的才学浅薄,故而每日如饥似渴地阅览群书以汲取知识。孙文拜读过卢梭名著《社会契约论》,心中五味杂陈:欧洲社会早在百年前便浸淫过如此先进的理论,相比我泱泱中华……唉,真是时不我待。
那时,清、英两国间并未建立正式的学术交流,在英的华人学生大部分是自费留学,父母多半为政商界中的豪强。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将区区公使馆放在眼里。然而孙文却从未将这一群体视作招揽对象。他清楚得很,拥有得越多,便越瞻前顾后。此类人,绝不会忠于革命。
在孙文心中,已将此类资本家群体与士大夫画上了等号。
然而常驻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留学生就不同了,至少不会是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他们大多认得这每日现身于阅览室的人便是公使馆囚禁事件的主角——孙逸仙。
每每于阅览室内擦肩而过,他们都会对孙文报以笑颜,这友好的氛围让孙文颇为享受。
这一日,三名结伴的留学生邀请孙文道:“不知学生们是否有幸,能邀Doctor Sun共进午餐?”
这三人也算阅览室的常客了,其中两人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很显然是孙文的同乡。剩余一人时不时以蹩脚的粤语插话,据孙文数日下来的观察,多半为江浙之人。
孙文对这三名好学的年轻人并无恶感,笑答道:“求之不得,孙某这数日独自用餐,正寂寞得很……但是,必须得Dutch Treatment(AA制)。”
“这可折煞晚辈了……我们邀请先生,于情于理也得我们招待。晚辈姓陈,单名闲。如先生所见,人如其名闲人一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后,便欲伸手请孙文。
孙文自个儿起身,笑答道:“劳小兄们前边带路了。久居异乡,与同胞攀谈可是种奢侈。唉,孙某代罪之身,几位小兄邀孙某,就不怕被公使馆那帮人盯上?”
“先生莫要笑话晚辈。若抱有此等顾虑,如何有颜面出现在先生面前。再者,我们三人计划在英吉利求学六年,如今一年未满,离归国之期还远。”
一行人在博物馆附近随意寻了一家餐厅就座。餐厅简陋,所招待的大部分顾客估计都是时常出入博物馆的寒酸学者与穷苦学生。
点过餐,陈闲摆弄着手中的叉子言道:“此间餐厅的掌勺师傅里,有几个在远洋航路上讨生活的BOY。若先生不嫌弃,待会儿不妨去见个面?对他们来说,没有比同胞的探望更振奋人心的了。”
一番攀谈下来,孙文对这三个年轻人有了大致了解。三人所学专业不同,陈闲主攻桥梁建设,而另两人则分别是造船与纺织专业。学校那头假期频繁,三名好友便时常结伴前来图书馆学习。
众人熟络后,陈闲自嘲道:“晚辈在家父眼中已是扶不起的阿斗。家父时常念叨着,要将家业托付于孙辈。可笑可笑,晚辈至今还是单身……哈哈。”
“令尊看得还真是长远。”孙文奉承道。
“非也,家父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他给出的解释是,你们这一辈仍生长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但到你们的子辈,必然已完全脱离清朝之桎梏,因此,我的孙儿定远胜于你。”
孙文的表情陡然严肃,决绝道:“令尊高见!即便只是为了儿孙,我们也必须在这一代与清国有个决断!”
“家父甚至为这影儿都见不着的孙儿准备好了名字。单名甫,诗圣杜甫的甫。先生可知其中奥妙?杜甫的父亲,名作杜闲!如此想来,晚辈这莫名的‘闲’字,多半是家父取来陪衬孙儿的‘甫’字之用?我该向谁喊冤去?”
“有趣,有趣,竟将子孙辈的名讳相关联,令尊的远见果真非常人可及!”孙文由衷感叹道。
“看得是远,但是这种将推翻清王朝与孙辈幸福挂钩的观点,却让人恭维不起。在晚辈看来,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是奄奄一息,只要愿意,随时都能让其土崩瓦解。呵呵,这不就是孙先生毕生所求吗?”陈闲言罢,直勾勾地盯着孙文,待其答复。
孙文直视着对方那强势的眼神,郑重地点头道:“否则,清公使馆为何会煞费苦心地‘邀请’孙某呢?哼,孙某又岂会因此而退缩?在座诸位小兄,也请继续习得才学,以救国之危难!至于公使馆,榨干它的利用价值便是了,同胞的血汗税用于你们这帮有志青年身上,也算用得其所。”
与三位年轻人攀谈,让孙文仿佛回到了久违的书生时代。
对比孙文的故乡广东,香港是个倡导言论自由的社会。曾几何时孙文求学于香港时,同乡杨鹤龄所经营的商号“杨耀记”的二楼空闲处,便成了一众爱国青年畅所欲言的场所。常客除场地主人杨鹤龄外,还有孙文、陈少白、尤列和从上海而来的陆皓东。“四大寇”的“恶名”也是当时传出的。
如今,眼前的三位留学生,比起孙文不过年轻七八岁,却让他不由得感怀过往的种种。与此同时,自然少不得伤怀挚友陆皓东的牺牲。
久违伤感的孙文正欲抹泪,陈闲话锋一转:“恕晚辈三人冒昧了,这数日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孙先生。您……每隔一日才进一次午餐,这样于身体无益。书本中可以汲取知识,却无法汲取营养。至于今日的餐费,方才也说好了,就AA制罢。若先生不嫌弃,今后也愿与先生AA制。只不过,我们不日便要去参加实习,怕是会时常缺席。不妨这样,晚辈三人先将餐费交与孙先生保管,请切勿推辞。”
陈闲言罢,当即便取出一个鼓囊囊的纸袋塞给孙文。孙文再也克制不住,因思念陆皓东而酝酿的泪水夺眶而出,他颤抖着用手帕抹去眼角的泪花。
孙文重新仔细端详眼前这三名未被乱世所染的年轻人。自费留学,家庭必定为富庶的士大夫阶层无疑,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并未受过清廷恩惠。三位年轻人自身,乃至他们身边的环境,在如此时局下,都可称得上清清白白。
与三位留学生的邂逅,让孙文对革命重拾信心。也是在那时,他亲自执笔了论文《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并发表于1897年正月二十八[公历时间为1897年3月1日。]的伦敦《双周论坛》(Fortnightly Review)上。文中,孙文将饥荒、洪涝、瘟疫等天灾的频发,乃至暴乱、匪患等人祸的猖獗,皆归咎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另外,他更是阐述了蕴藏在国殇之下的无限潜能以及自力更生的可能性。
有两位恩师做导游,孙文早早将伦敦的各大景点游览了一通,余下的时日,便整日消磨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之中。他偏爱的席位,被一干同伴称作“Sun Yatsen’Seat”(孙逸仙专座)。阅览室的几个“老面孔”也与孙文混了个面熟,众人都乐得与这位为国操劳,且英文流利的华人医生交流。媒体界更是对孙文推崇备至,某刊物甚至以插图的形式,解释Doctor Sun是如何如何不畏清廷强权,如何如何削辫以明救国之志。一时间,孙文倒成了阅览室中的焦点,尤其是在与他一般黄皮肤的亚洲人眼中。那年月,在欧洲的亚洲人,除却数量稀少的唐人,便是日本人了。脑后的编辫可清楚表明他们的国籍。当然,孙文这个异类除外。
这一日,便有一位亚洲“同胞”与孙文搭话:“你便是那风头正盛的孙逸仙了?本人名作南方熊楠,日本人。我挺中意你,交个朋友吧?”
孙文对这位“自来熟”倒不感到陌生,相反,对方那双犀利的眼眸颇投孙文所好,他一早便想主动结交。孙文紧紧握住对方伸出的手,问道:“阁下是学者?”
熊楠摇摇头,犀利的双眸直勾勾地与孙文对视:“我是学者中的学者。”
对方如此,孙文也不客气:“那孙某便是革命家中的革命家了。”
“哈哈……爽快,你果然配得上做本人的朋友!报纸上说,你是1866年生人?长我一岁,看来我得注意措辞啦,哈哈哈。”熊楠大笑道。
两个男人的对话,用的自然是英语。但即便如此,却无丝毫违和感。这也是两人意气相投的最佳佐证。两句近乎打趣的对话,便让双方在对方心中定下了终身挚友这一位置。两人虽道不同,却仿佛被一根细线隐隐相连。
熊楠的头衔颇多,生物学家、民俗学家,更是菌类植物收藏家。他公开反对“神社合祀”体制,单论这份“反骨”,倒与孙文意气相投。再者,孙文学医,在细菌学上也有所造诣。自那后,孙文每与熊楠再聚,总不忘捎上从各地采集而来的菌类样本。
自邂逅开始,熊楠在孙文面前便从未掩饰自己的“怪人”气质,孙文也是乐在其中。
“孙医生呀,你可知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你倒是声名在外,却累得我也不敢出门。这一出门呀,难免就会被误认为是‘Doctor Sun’。那些庶民可不听解释,见我是亚洲人面孔,又没编辫,便先入为主地咬定我就是那孙逸仙!真是一刻都不给消停呀,哈哈哈。”
“哈哈……孙某知错,孙某知错!出名有时也是种罪孽呀。”两人畅怀大笑。
南方熊楠,1867年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市,与孙文仅有一岁之差。南方熊楠于1883年在和歌山中学毕业后上京,在神田公立学校研习一年英文后,就读大学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也就是如今的第一高等学校。与他同期入学的有夏目漱石、正冈子规、秋山真之等一众其后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熊楠却就读一年便早早辍学,对外公开的理由是因病,实则是代数科目不理想,落榜退学。
熊楠于1886年2月退学,同年12月留学于美利坚密歇根州州立农业大学[即密歇根州州立大学。],却同样未待上些许时日便退学。传闻的理由是他拒绝接受伦理课教学。
“熊楠贤弟,总算是寻到我们俩不同的地方了。”孙文闻知熊楠如此厌恶自己的信仰,也不争辩,仍是一张笑盈盈的脸,他对此早已习惯了。
“逸仙呀,我承认你这个人,可不意味着我承认你信教,还接受了洗礼。”孙文被这样说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言者甚至有自己的至亲。这时,他总是会回答道:“信仰嘛,是个人问题,是天主与我孙某的问题,容不得他人介入。相对的,我也不会对他人的信仰说三道四。”
熊楠听了这番陈述后,赞同道:“对头,对头,逸仙此言甚得我意!那密歇根大学便不懂这理,犯了我的忌讳!你说你好好一个农业大学,乖乖教你的细胞培育不就得了。”
就是这份敢说敢言的豪气,太投孙文的意了。若是再加上一份侠气,便是孙文对终身挚友的标准了。豪气与侠气,这是孙文结交友人的关键词。
这便是两人能要好到食同席、寝同榻的原因了。要形容两人的关系密切到何等地步,甚至有人怀疑熊楠在孙文手下从事着秘密工作。
罗丰禄接任伦敦的清国公使后,对孙文的监视仍未懈怠。据私家侦探统计出的数字,孙文在长达九个月的伦敦生活中,单是与南方熊楠的私会便有四十次之多。
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每日承客约三百余人,于此相知相识的友人不在少数。孙文与南方早先便是点头之交了,要说正式开始交流,还亏得博物馆的东洋典籍部主任道格拉斯的介绍。其后,南方在写给柳田国男的书信中,曾提及如下一个片段。
在某次攀谈中,孙文问及熊楠:
——熊楠兄今生有何目标?
——但愿能盼来我等东洋人将西洋人驱逐出境之日。
熊楠反问,孙文答曰“革命”。“革命”一词英译“Revolution”,但孙文好用“Reform”。前者指纯粹的武装变革,后者却蕴含“改良”之意,换言之,便是“改革”。在《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一文中,孙文亦自称“改革党”(The Reform Parry),望英政府持友好中立态度。
一同用餐,一同游玩,意气相投的两人要好到形影不离。每每有人表示好奇,南方总是答道:“能与我南方熊楠论菌者,问世间只有孙逸仙一人尔。”
这倒真不是捧孙文,想当年在西医书院时,孙文的细菌学成绩可是首屈一指。
孙文将满腔热血化作革命激情,对同怀热血之人本能地亲近。
将洋人皆驱逐出境!——如此的豪言壮语,绝非南方一时口快。出于谨慎,孙文面无表情地瞟了眼周边。南方见孙文此举,压低声音道:“孙医生亦有所察觉了?自昨儿起,便有个华人男子三番五次地出现在我们周边。”
孙文不露痕迹地点头,答道:“孙某也是刚察觉不久。昨日他也跟踪我们了吗?”
孙文如何会认不得此人,密探周榕是也。
周榕当时表示要在美利坚多滞留一段时日,他很有可能是囚禁事件结束后,才抵达的伦敦。
南方费解道:“奇了,我从这条‘尾巴’身上并未感到杀气。他不是来加害于你的?莫非,是在防着我?”
“多半是了,此人大概与我有私密话要说,能否请熊楠兄……”
“哼,那我便先回图书馆了。你自个儿小心,别又着了道。”
周榕与离去的南方擦肩而过,不露声色地走到孙文身边,如释重负道:“总算盼到你一个人了,让我好等。”
“嗯,是我让他先走开的。”
“其实倒也不妨事,咱说中文,那日本人也听不懂……您与那家伙很熟识?他倒不算坏人,但性子堪称古怪,能避便避吧,还是少牵扯为妙。”
“哈哈,感谢忠告了。”孙文煞介有事地行了个压帽礼。
“不忙谢,待我说完……清公使馆此番虽崴了脚,可不意味着他们便死心了。您仍要尽力避免只身一人,与南方形影不离便是良策。瞧那日本人的言行,怕是早已对此心知肚明,有意要保护您……”
“笑话了,那家伙也会有如此细腻的一面?对了,周兄何时来得伦敦?”
“你获救前两日便到了。”
“便是说,你那两日在使馆内眼巴巴地瞧着我在小黑屋里受难了?”
周榕被孙文那没好气的模样逗乐了,笑道:“哈哈,我如何忍心……咱绝不会轻易进出公共场所,除非是任务需要。咱的差使,便是如此见不得光。我自登陆以来,便一直住在使馆周边的小旅社,不曾挪过窝。”
“那么,请问你此趟大驾伦敦的差使是?”
“‘护送’您上轮船,然后,全程‘看护’。”
“哈哈哈,身兼数职呀,辛苦辛苦。”
周榕却笑不出来,缓缓摇头道:“非也,我的差使仅是监视您的行踪,负责确保您不会逃跑的另有其他密探。至于这密探的底细,我便不得而知了。”
典型的“左右制衡”之策。清廷特色,一个任务,两个执行者。执行机密任务时,则要求两个执行者互不知晓底细,由此可见清廷对下边人的戒心。此次任务,需要其中一名执行者全程死守在目标周边。孙文受囚于公使馆期间,周榕刻意却与公使馆保持距离。可见,与其说周榕的任务是监视孙文,不如说是在监视另一个执行者的举动。
“好吧。恕我多问,你有打算在护送途中偷偷放我逃走吗?”
“何必多此一问!我周榕最重一个‘义’字。即便是你已被吓软了腿,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背你走!”周榕拍着胸脯道。
“感激。再多问一句,茫茫大海,周兄打算背着孙某往哪儿跑?”
“唔,这确实伤脑筋……原计划在轮船抵港前,经停休整时动手……事到如今,何苦再自寻烦恼,难道您还想再到公使馆‘做客’?”
“好意心领,我可不愿‘二进宫’。但周兄的恩义,孙某此生无以为报。”
“公使馆又何尝能容忍自己重蹈覆辙?对南方那怪胎,也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儿。”
“嗯,我晓得进退分寸。”
这是孙文与周榕在伦敦城唯一的一次碰面。1897年6月末,孙文在离英之际,与南方依依惜别,赠予对方两册书籍,并题告别之词于封面上:
海外逢知音
南方学长属书 香山孙文拜言
孙文敬称南方为学长,视对方为学问上的前辈。
说个有趣的题外话,孙文离英的同年11月,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内,这位学长在大庭广众之下,咬伤了英籍馆员的鼻子,而被拒之馆外长达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