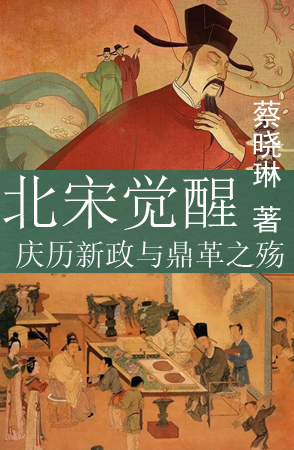中国大陆以“淮河”为界,分作南方、北方。清末两大事件——“戊戌变法”(1898年)与“庚子事变”(1900年)均以北方为舞台。“戊戌六君子”就义不过两年,西太后一行便仓皇弃京西逃。
乱世无史,时任侍读之职的叶昌炽所留日记便成了重要历史依据,日记中有如下一段:
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杨深秀)外,皆南人也,今(义和团起义)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赵舒翘)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反手复手,顷刻间耳。今日之祸,非“党祸”。
戊戌党人杨深秀祖籍山西,为“北人”,赵舒翘是陕西人,为“汉人”,因此不可以“党祸”论之。
纵观中国历史,前有汉末朝臣结党对抗宦官与外戚,反致山河破碎。后有宋时“新旧法”党政,消耗国力。因此,各朝统治者皆视“结党”为洪水猛兽。
但恰恰是在国家危亡之际,志士为救亡图存,“党派”应运而生。救国之道有几条,“党派”便有几个,“党争”在所难免。
第二次武装起义,在孙文的主导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1900年6月11日,他于横滨搭上客船,重返香港。同一日,日本公使馆杉山彬于北京永定门遇害。
在客轮上,孙文偶遇台湾举人林炳文,林炳文也常驻横滨,两人时常能在街头巷尾碰上,孙文也不惊讶。
与孙文同行的,除宫崎滔天、平山周等熟面孔外,还有前番广州起义的组织者、辅仁文社会长杨衢云。林炳文表情玩味,神秘道:“此阵容聚首,怕是又要在大陆那边掀起一阵波澜了吧?正好又碰上京师局势不稳……”
众人所乘“Indus”号为法兰西船只,乘客多为日本人,林炳文眼下也是西装革履,一副日本人行头。
去年11月,香港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三派联合。当时,孙文因“禁留港令”没能出席联合大会,却依旧被推举为总会长。
自此,兴中会干部毕永年游说于长江流域,郑士良开始在华南方面走动,与另外两会的联系愈发紧密。三派联盟暂名为“兴汉会”。联合大会当天,兴中会派代表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三人出席。香港方面制作“兴汉会总会长之印”,由宫崎滔天带回日本,呈交孙文。
孙文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口袋,里头正塞着印章,叹道:“这年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稀奇了。”
林炳文眺望着海平线:“据说,清廷终于向李鸿章服软了……”
“所以才说,谁都可能突然改变立场,不稀奇了。”
大陆政局晦暗不明,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卜。就连那占尽主动的列强,既不能与清廷翻脸,还得在反清组织面前赔着小心。搞不好过了今晌,这紫禁城就会易了主。林炳文调侃道:“所以说,孙先生也顺应时代,与阿尔曼密会了?”
孙文苦笑道:“若是密会,你又怎会得知?我们兴中会不行那偷偷摸摸之举。”
林炳文口中的阿尔曼是法国驻日公使。孙文原一厢情愿地认为经历过二月革命的法兰西会站在己方阵营,曾请求公使馆提供起义所需军火以及军事顾问。谁想阿尔曼竟一口拒绝,给出的理由是本国政府的对清政策趋于维稳,无法向革命方提供支援。
庚子事变,让法兰西政府愈发瞧不清当前局势。阿尔曼也不愿就此斩断与孙文一派的联系,欲从另一方面提供帮助道:“若尊驾革命成功,法国政府愿与新政权友好建交。届时,法领印度尼西亚总督将成为尊驾一大助力,还望尊驾重视。”
说完,还不忘亲自为孙文作引荐信一封。
孙文此番游历众国,首要目的便是携手各国华侨。其中,夏威夷与美利坚的华侨力量,尤为受孙文重视。至于华侨最为势大的东南亚,则全权托付给辅仁文社。有引荐信在手,孙文向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扩张便更有底气一些,目的自然是凑齐军资。
“瞧那大块头的兴奋劲儿……”林炳文一向爱调侃宫崎滔天的体形,“看来,是对新加坡颇为期待呀,倒是逸仙先生您,依然是愁眉不展。”
“期待越高,若落了空,摔得更惨。香港如此,新加坡也差不远。”
孙文是打算听天由命了,毕竟新加坡有保皇会会长康有为坐镇,而香港则是李鸿章的新据点。
清国中枢面临八国联军的来势汹汹,苦于无谈判人才。唯一能与西洋掰掰手腕的李鸿章,却被左迁至广东。西太后屈尊一连几通电报,也召他不回。
“Indus”号自出航后,先后途经了神户、长崎,下一站便是香港了。林炳文笑道:“香港的局势可耐人寻味得很。可惜,李鸿章也是弥留之际,若再早个十年,还真掐不准了。”
“李中堂不复当年,新加坡那帮人可个个不好相与。比起他们,我更好看华侨中的年轻一辈。”
海风袭来,孙文赶忙摁住要被掀翻的帽檐。林炳文问道:“在下此番在香港登岸,逸仙先生呢?”
“五年之期,再有几个月就到头了。香港,孙某迟早会卷土重来,此番便先去见识见识那印度尼西亚。”
“香港事宜便交给迪之先生去操办。若有在下力所能及之处,请尽管吩咐。”
孙文有些吃惊:“你认得迪之先生?看来,我也有必要喊你一声‘同志’了?”
何启,字迪之,别名沃生,是当时享誉中外的著名医学家、法学家。何启任职于香港议政局,曾进言时任香港总督布雷克,协助李中堂与孙文建立南方联合政权,以稳定大陆局势。
孙、李二人一向亲英,布雷克自然乐意见到南方由友好的和平政权统治。得总督应允,何启随之将此构想经由陈少白传达给孙文。
也难怪孙文惊讶,此事甚是机密,知情者只有寥寥数人同志而已。至于赞同与否,孙文一时踟蹰不定,但下次抵港时,是务必要给出明确答复的。孙文暂且态度暧昧——兴中会愿做尝试,但一旦建立新政权,为顾全大局,便只有革命一途;李中堂是否有此魄力,孙某深表怀疑。数日后,孙文收到了来自李鸿章帐下幕僚刘学询的邀请函:请速至广东,协商合作事宜。
“Indus”号抵港,林炳文扫了眼港口,蔑笑道:“怕是鸿门宴,不赴也罢。”
“孙某哪有魄力效仿关二爷单刀赴会,早已安排代表去赴宴了。”
港口停泊着一艘清国军舰,明眼人一眼便可瞧出,这是李中堂旗下的“安澜”号。与孙文同行的宫崎滔天在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中,对当情景有如下记载:船抵香港,一艘支那军舰为迎接孙文,待机于码头。
“硬石”“吞宇”分别为内山良平与青藤幸七郎名号,两人均是支持孙文革命的日本志士。于是乎,三个日本人代表孙文,换乘至“安澜”号,转航到广州。他们被领到当地某位大户的宅邸中,与李鸿章方面进行会谈。
会谈内容与某大户的身份,宫崎滔天在作品中并未提及。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三十三年之梦》初版发行。此作品也流传到中国大陆,但那时距清朝覆灭(1912年)还有十年,暂未正式出版。
据相关史料记载,“某大户”不是别人,正是出函邀请的刘学询。此人在广州垄断了国营博彩“闱姓”的庄家位置,身家以数亿计。前番广州起义前,孙文一众曾意欲拉拢他。奈何此人自小受儒家君臣教育浸淫,思想泥古不化。孙文只得作罢。打那儿以后,更是对他敬而远之。
然而士别三日,当年的“顽固派”,如今竟全权代表李鸿章,与“革命派”谋划建立民主政权。
“保障孙文人身安全”自然是双方合作的第一前提。在此基础上,孙文方要求李鸿章方提供六万元借款,做革命资金。谈及金钱,刘学询很是爽快,当场应允,并预支了三万元。此事项为机密,宫崎滔天自然不会写在作品中。
广州密谈当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西太后仓皇失措,连发电报,催促李鸿章“上京入卫”。李鸿章却从容得很,也不着急动身,反倒先安排幕僚刘学询会见孙文一派,也算是为自己,为中国加了层保险。坊间倒心急了,一部分人盼着李中堂能在京师失陷前独立两广。
孙文对刘学询这位香山老乡可算知根知底。此人因君临两广的财力,受李鸿章青睐而收入帐下,专门负责见不得光的活动。
此时此刻,真正被李鸿章视为后盾的是香港总督布雷克。相较之下,交好孙文只不过是其中一条“后路”罢了。布雷克也有自己的考虑,大陆政局不稳,大英帝国在江南乃至华南的利益难免受损。届时,两广若能独立,好歹也多个保障。
然而时任英吉利首相索尔兹伯里却视“大英帝国孤立政策”为信条,尤其忌讳与他国野党政权交往过甚,认为此举有失荣耀。李、孙两家合作,注定要以夭折告终。
宫崎滔天三人将三万巨款笑纳,意气风发地返程香港。孙文不得登港岸,只得留在“Indus”号船舱中,随之同赴下一站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宫崎等人也不理孙文了,径直就要赶往新加坡。孙文从一开始便表明态度:“孙某就不去新加坡了,建议各位也别去浪费时间了。”
没办法,毕竟新加坡现在是保皇会康有为的地盘。宫崎等人是一心期盼兴中会与保皇会能握手言和,两股势力若能携手,一加一将远超于二。
两会有共同的敌人——顽固派。宫崎滔天与梁启超坚信,两派绝对有理由站在一条战线上。先携手铲除顽固派,再和平讨论接下来是改良还是革命。但两派领袖,孙文与康有为似乎对两派合作很是悲观。
在东京,康有为始终不愿意会面孙文。孙文也是硬脾气,不愿做那热脸贴冷屁股之事。康有为说话丝毫不留情面——吾乃天子直臣,如何能与革命党那帮乱臣贼子往来。
孙文也死心了——对方就差没有拿棍子撵自己,这新加坡还有必要去吗?但宫崎滔天却认死理,满心以为自己能打动康有为。
两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狼狈逃亡香港。坊间误传光绪帝遇害,康有为心如死灰,一时间欲自尽殉主。若无英吉利友人劝阻,如今还哪里来得保皇会?
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门下四十弟子,听从日语老师田野橘次的建议,赴香港求援于宫崎滔天。十日后,康有为也现身香港。说来,也难怪宫崎有此等自信。要知晓,康有为与四十弟子危亡之际,他宫崎滔天作为局外人却犯险相助。康有为欲逃亡日本,为其周旋奔走于外务省与公使馆之间的也是宫崎滔天。如此恩德,康有为如何能拒绝自己这个大恩人的建议?
此时,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作客于富商丘菽园的宅邸。远在异国,他身边依然是众星拱月,一大帮崇拜者为他出生入死。甚至连新加坡第一拳师,也愿意屈身做他的贴身保镖。
康有为很是慎重,就连出门买瓶醋,也得计划再三。他时刻不敢忘记自己是清廷要犯,顽固派为取自己性命,派遣刺客也在所不惜。
孙文当初亡命至日本时,第一个目的地便是当地警署,得让日政府明白,清国刺客随时会潜入日本,得多加防范才是。
这一日,康有为派去的探子带回一条重要情报——数名日本人在广州密会清朝高官后,赴新加坡而来。宫崎寅蔵便在其中,有必要予以注意。康有为闻讯,不免惊疑:“要说宫崎,我认得,他一向与孙文走得很近。你说,他与清廷高官密会?可疑,很是可疑……广州高官,莫非是李鸿章?”
“听说,高官还专程派炮舰到香港去迎接。”
“那便是李鸿章无疑了……我听闻西太后正传唤他回京?李鸿章回京便要带着‘孝敬’。西太后此时最想要的不就是我康有为的项上人头吗?”康有为考量再三,踌躇道,“让他们登陆新加坡,怕日后会成为隐患。”
探子得令,立马展开行动。要知道,在新加坡保皇会成员中,不乏在警界吃得很开的人物。康有为在广州与香港知己众多,单是万木草堂的学子便有数百人。他们便在圈子里奔走相告——更生先生有危险了!
解释一下,康有为字“祖诒”或“广夏”,号“长素”。变法失败后,改字为“更生”,算是寄托一个浴火重生的愿望吧。信奉者们的“护主”之心,连康有为本人也大感招架不住。以讹传讹,宫崎一行人倒真成了欲谋害康先生的奸徒。康有为忙做出解释:“说来,若非那男人仗义相助,我还真无法从清国全身而退。”
然而,信奉者不仅不感恩,反倒挑起这帮“恩人”的不是——协助康先生逃亡的那帮日本人多为崇洋媚外的草莽之士,更可恶的是,他们历来抬高孙文,贬低康先生。他们选择性地无视康有为那似有似无的辩解,同仇敌忾道:“与这帮草莽谈何恩义?”
于是,宫崎一行人刚下船,正打探康有为住处时,便让个混血巡警喊住了:“喂,那边那伙日本人,站住!”
警察也不提有人告发,正主就在眼前,要揪他个小辫子还不容易?他劈头就是个下马威,指了指宫崎腰间的佩刀,明知故问道:“这是什么?”
宫崎不想生事端,老实道:“您说这口刀?世间凶险,带把武器,方便护身。平时,也就当手杖用。这有何不妥,英吉利人不也随身配枪?”
警察随之将宫崎行囊中的那摞钞票甩在桌上,厉声道:“那这又做何解释”
这笔巨款可得稍作隐瞒了,说是刘学询赠予的,就相当于承认自己与李鸿章暗中有经济往来。宫崎义正词严道:“我等来贵国做生意,又不是来游玩,带些钱财有何不妥?还是说,你嫌钱财少了?”
警察冷笑道:“真是巧了,前些天有人报案说被盗了三万元。若确证这笔钱真是您的,自当全数奉还。还请阁下少安毋躁,到牢房里稍歇片刻。请宽心,咱新加坡的牢房可舒适得很。”
宫崎滔天这才瞧出来者不善,也不发作,冷静道:“好说,但还烦请帮忙联系一下贵地的日领事。”
宫崎众人无端遭受牢狱之灾的同时,孙文已与西贡的华侨接上了头。乍闻友人落狱,孙文也料想不到康有为竟如此决绝,叹道:“瞧见了吧,瞧见了吧……清国的忠臣,便是如此报答恩德的。我早已提醒,不要对他们抱有期望……”。
虽心中埋怨友人不听奉劝,但孙文还是担忧友人安危,连夜赶赴新加坡相救。宫崎吃了整整六日牢饭,钱财所属虽被证实,但仍被安上了一条欲加之罪的“妨碍治安”,经审判,五年内不得入境新加坡。宫崎心如死灰,愤恨道:“若当初听逸仙之言,何至于落得如今田地?正如你所言……食清禄者,不净也,不净也!”
若非孙文从中周旋,宫崎怕是难以全身而退。要知道,英国人原本是打算向康有为一派卖好,重判这伙日本人的。在英国人眼中,无论是受清廷缉捕的保皇会人士,还是被左迁的李鸿章,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棋子。偶尔施些小恩惠,对自己有利无弊。
宫崎就想不通了,即便谋害自己的是保皇派那帮盲目分子,并非康有为本人之意,但自己早已报上名号,请求出面相见,康有为缘何默不作声?他便是这般报答两年前的救命之恩的?
在返程客轮上,宫崎滔天奋笔疾书,作绝交信一封:
弟与先生在国难之际结义旧事,今日何必多言!但处此时局,弟今怀有一片深忧与满腔热血,不远千里来访知己。焉知昨日之知己,今日已非知己,竟以最大耻辱之名相加!世事表里,人情反复,如梦如幻,实令人惊骇不已。日南同志亦将来此谒见先生,已由香港出发,正在航中。倘彼抵此,闻知此事,不知亦将作何感想?呜呼已矣!吾辈将与谁共议兴亚之大事!
谨具手书,致于感泣皇帝之知遇,却不解朋友大义之人,以表诀别之意。幸加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