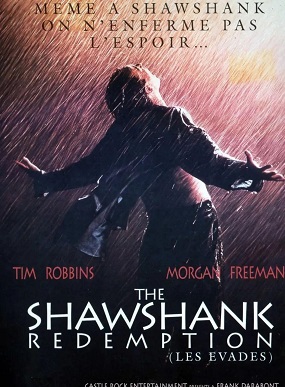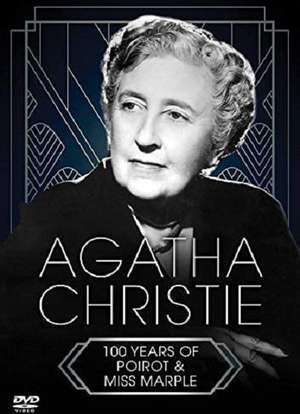重阳起义翌年3月4日,港英当局针对孙文颁布了长达五年的入港禁令,孙文不待禁令实施,便早早逃亡至日本。1900年7月,孙文自新加坡乘“佐渡丸”号返航香港。入境禁令尚未期满,港英当局得知孙文行踪,客轮刚靠岸,便下令提醒孙文不得上岸。
在坐落于伦敦城的英吉利国家文献局中,保存有当时香港总督布雷克与首相索尔兹伯里的电报记录。该记录早过了保密期限,现已向世间公开。据电报内容,当时布雷克曾有打算破例放孙文上岸。那一日,孙文所乘“佐渡丸”号,凑巧与李鸿章所乘招商局“平安”号同时抵港。若准许孙文上岸,则可促成孙、李会面。布雷克拿不定主意,电报至伦敦请示首相。电报注明日期为7月12日,正是“佐渡丸”号从新加坡起航当日。
电报发出两日后,7月14日,索尔兹伯里首相回电,答复很简单:不可。于是,孙文便与李鸿章失之交臂。
日本外务省历史文献中也保存着一份很是耐人寻味的报告。此报告出自兵库县知事之手,7月25日发出,标题为“兵法秘字四一〇号”。里头记载了一日前(7月24日),“佐渡丸”号抵神户时,孙文与友人的对话。
据孙文所知,香港总督曾怂恿李鸿章,如今时局正是独立两广之良机,大可雇孙文为幕僚,自立门户。对此,李鸿章的答复是“静观局势,后徐图之”。孙文看得真切,香港总督是盘算着要将两广纳入英吉利势力范围。然而,李鸿章仅在香港滞留了一晚,便起程北上,想必香港那帮洋人是空欢喜一场。
照理,视“孤立主义”为荣誉的索尔兹伯里首相,是铁定不会支援李、孙联盟。直至两年后日、英联盟,兰斯唐伯爵跻身外相,李、孙联盟才有一线生机。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平安”号赴香港,于翌日18日再转航至上海。“平安”号抵港时,仪仗队沿岸列阵,行“十七发礼炮”国宾礼,甚至连香港总督布雷克也亲身相迎。如此豪华的阵仗,仍无法拴住李中堂。
7月16日,孙文一行人所乘“佐渡丸”号抵港,20日才扬帆日本,凑巧与李鸿章留港之日撞在一块。可惜,入境禁令仍有效,两人终究还是没会上面。孙文一行人,在“佐渡丸”号船舱中召开了秘密集会。孙文调兵遣将,一一分配任务:“眼下形势有利于我方,起义地暂定惠州。弼臣对惠州了如指掌,联络会党事宜可全权托付于他。史坚如与邓荫南则坐镇广州,等待呼应。至于民政,便委托毕永年处理。”
讨论到起义日,宫崎坚持“宜早不宜迟”:“既然迟早要见刀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孙文却有多方顾虑,指了指停泊在岸边的清国炮舰,用英文问道:“你打算如何瞒天过海?”
荷枪实弹的清国炮舰固然可怕,躲在暗处的间谍更是令人防不胜防。宫崎懊恼道:“唉,看来还得从长计议。”
孙文便真沉得住气?那真是笑话了……他一早便吩咐惠州郑士良,在三洲田建立了秘密据点。三洲田毗邻香港,距臭名昭著的海贼窝“大鹏湾”不过几海里。六百会党成员早已驻扎据点,严阵以待。但孙文着实性急,六百人渐渐粮草不济。最后,只得将驻扎人数削减至八十人,其余人遣散至周边村落潜伏。
为避免走漏消息,郑士良还将路过的樵夫、渔民强行纳入队伍中。坊间甚至有传闻,起义队伍一时间达到千万规模。三洲田早已摩拳擦掌,孙文更是按捺不住,但还是捺着性子,回日本隐忍了月余。
8月22日,孙文终究是坐不住了,暗中在横滨踏上了发往上海的客轮。9月1日,他便被迫匆匆返程。孙文从横滨起程当日,自立军起义被镇压,翌日,唐才常等十一人起义军头目于武昌受刑。与此同时,西太后领光绪帝与一行清廷要员,正在逃亡西安途中。湖广总督张之洞恐事态恶化,先斩后奏,将与自立军的同党一并处死。孙文被上海的戒严杀了个措手不及,仓皇折返。
起义迟迟不见进展。宫崎来信,简简单单两个字冲破了僵局——台湾。革命党人皆深晓当今局势,不用多加提点,便可知宫崎心意。众干部早在方针上达成一致——独立南方六省,坐等全国呼应。五年前,广州那点儿星火未能燎原,从中教训发人深省。
孙文也未必执迷于起兵广东。没错,那儿是他的故乡,人脉广布,但也有其弊端。宫崎便一语中的——离中原太远。
只要火势能蔓延,在哪儿点火便没那么多讲究了,重点是此地能否备齐足够薪火,是否能避开清廷耳目。香港会党广布,“薪火”不成问题,却谍报猖獗,不做考虑。台湾兼具两个条件,最重要的是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等一众高官对孙文的起义颇是支持。当然,这也是考虑到日本的利益。
清朝遭甲午战败与义和团运动重创,已是满目疮痍,其统治力再难稳定南方。坐镇福建的闽浙总督许应骙为典型的守旧派,早在百日维新时,就由于匿下礼部尚书王照的奏折,一时被光绪帝罢免,既无才学又无实干,充其量就是个挂名等死的老政客。与之相较,儿玉等人自然是愿意与孙文这样的进步人士打交道。
孙文此时已有了初步的战略构想——惠州若生事变,清廷必然如五年前一般增兵广州。而起义军大可趁此良机,暗中进军闽地,叫清军首尾不能相顾。史坚如便负责将广州捅出个天大窟窿,很简单——炸死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为此变卖家产,购得两百磅炸药。
德寿原为广州巡抚,皆因李鸿章北上,两广无主,才得以兼任总督位置。史坚如一深入调查,得知德寿仍旧起居办公于巡抚衙门,他便在衙门后门租了座宅子,连夜挖掘隧道,将塞满炸药的铁桶运至衙门正下方,逃出隧道,点燃导火索,只待惊雷一响,便动身香港。
这里还有段小插曲——史坚如在隧道外迟迟不见动静,壮着胆子原路折返,才得知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了。他再引燃导火索,谨慎确认无误后,才逃至西关教会处等待。顺带一提,他信奉基督教,等待时也不忘一个劲儿地祈祷。
有了上帝保佑,不多时,巡抚衙门那头便传来惊天巨响。足足两百磅炸药,照理说,将巡抚衙门掀个底朝天也是绰绰有余,但事后坊间谣传,目标德寿竟逃过一劫,反倒是害了二十余名无辜官民性命。伤及无辜,令史坚如心如刀绞,得信后,不顾同志阻拦,他起身便要赶赴现场:“二十余条无辜性命呀,叫我如何置身事外!”
事后,他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火药未完全引爆,不气馁道:“我再坐尝试便是。”经同志力劝,好说歹说,才将他拉上返程香港的客轮,但赴港中途,还是未逃过清兵堵截,受囚于南海县监狱。
直至十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南海县衙忘记销毁相关记录,清廷密探的身份被公布于世——原来,清廷密探郭尧阶从一开始便盯上了史坚如。
史坚如被捕当年,刚满二十一岁,传言是位貌比潘安的美男子。有趣的是,他少年时代体弱多病,独爱丹青笔墨这一特征,竟与他的“前辈”陆皓东不谋而合。据记录,负责审问的清官曾罗列四十余人的“黑名单”,逼迫史坚如佐证其“犯罪事实”。史坚如自然是宁死不出卖同志,有记录曰“受严刑拷问,仍傲睨自若”。
因其教徒身份,美利坚牧师曾在美公使馆协助下开展游说,要求南海衙门从轻发落。然而当局声称物证确凿,绝不姑息。原来,衙门从史坚如身上搜出了用德文书写的火药配方,估计他是打算再做尝试,便未及时处理。
10月28日,广州爆炸案起。11月9日,主犯史坚如于海南县受刑。此后,同志们称牺牲的史坚如为“共和殉国第二健将”,这“第一”毋庸置疑是陆皓东。
事后,宫崎滔天于东京不忍池畔的宅邸疗养时,孙文来访,才得知史坚如的噩耗。对此,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有如下记载:
呜呼,胡为至是?彼十八岁之少年,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暗通惠州革命军,只身潜入广东省城以放火,又投爆裂弹于大官邸内毙二十余人,以大寒官人之心胆,窃为惠州军尽力牵制,事觉而遭捕缚,卒处断头之极刑。
但凡乱世,世间情报多有误传。史坚如时年二十一岁,宫崎却称之“十八岁”。史坚如是掘地道埋炸药,宫崎却误以为是“投爆裂弹”。宫崎言史坚如“只身潜入”,却不知邓荫南与黎礼也参与其中。
史坚如本名“文纬”,他却不喜爱名中的“讳”字,特意改名作“坚如”——“纬”为横,少了纵“经”加以固定,难谈牢固。坚如,坚如,我很好奇,自己的意志能坚毅到何种地步?
史坚如身体孱弱,可论行动力,却丝毫不含糊。广州“东亚同文会”会长高桥谦便曾怂恿他赴日游历一番,他早有耳闻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坐镇日本,便心生向往。他专程拜访了潜伏在香港的革命党干部陈少白,随后又远渡上海,结识了毕永年和一干湖南会党同志。
几番周折,他终于踏上了心心念念的日本,并在陈少白与杨衢云的极力引荐下,成为兴中会一员。孙文也对这位年少有为的同志早有耳闻。
史坚如籍贯广东番禺县。番禺与南海并列为“广州二县”,也算小有名气。史坚如虽生在广州,却是外来户。史氏一门祖籍浙江,史坚如的曾祖父便是闻名天下的绍兴师爷。
常言道“天下师爷出绍兴”,浙江绍兴有两大名产:一是绍兴酒;二是绍兴师爷。此地文教繁荣,中举学子不胜枚举,但头顶顶戴者却是寥寥。绍兴学子早已看透官场——入仕或许能出将入相,留名丹青,却同样要忍受官场之混浊,伴君如伴虎之危险。于是乎,他们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幕僚,也就是高官的“秘书官”。比如不善理财的官员,大可将经济、民生交于帐下师爷打理。即便这位师爷凑巧也不懂经济,但其所在的师爷圈子里,势必有精于此道的同僚帮忙出谋划策。久而久之,绍兴师爷便成为众高官眼中的“抢手货”。
清廷权力中枢,由数位军机大臣坐镇,其地位凌驾六部堂官。但论影响力,终究还是逊色于手握兵权的各地总督、巡抚一筹。这样的“地方霸权”帐下,无一例外地供养着数名甚至数十名绍兴师爷。他们负责收集整理当下情报,包装以自己的才学见识,“上达”给雇主。绍兴师爷多出自名门,虽寄人屋下,却不受管制。高官们多少对其身后势力有所顾忌,对“绍兴”二字,既是青睐,又是戒备。
史氏一族至史坚如祖父一辈,便移籍广东。那年月,因结婚等诸多缘由背井离乡、移籍他乡也不算是稀罕事。
终于,史坚如在东京见到了憧憬已久的孙文,两人促膝谈天下局势。年轻的史坚如,不禁为这位革命领袖所倾倒。
其实,“广州爆炸案”尚有一个未解谜团——先前也提过,此次事件目的不在暗杀清官员,而是为孙文一众的战略转移打掩护。但事实上,酝酿已久的“惠州兵变”临时取消。革命党上层给出的解释是弹药不足。其实,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原因——日本拒绝施援。儿玉先前向孙文许下的支援,却因京师政变(一说因伊藤访京)而临时变卦。
“外援难盼……”10月22日,郑士良得信后扼腕叹息,不得已将起义军遣散。事后,他自然不忘将消息告知广州同志,那时距“广州爆炸案”还有六天之多。这便叫人费解了——史坚如明知形势有变,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实行原计划呢?
这位年轻人的心思不难猜——花了好些工夫才挖通地道,炸死个狗官,就当给清廷一个教训也好……确实,这一声惊雷让清廷一时间人人自危。
史坚如献身革命,被称作“第二健将”。其实,还有一人也担得起这名头,此人便是先前提过的唐才常。
唐才常籍贯湖南,与长他两岁的谭嗣同是打小的挚友。谭嗣同受康有为之邀赴京,见变法派式微,便一通电报到长沙,唤唐才常上京增援。唐才常知发小有难,连夜便收拾细软,赶赴京师。然而他才抵达汉口,便传来变法夭折,挚友遇害的消息。唐才常悲愤交加,作诗道:“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
挚友已故,他立马返回湖南,妥善安置了家人,由上海登船,先后途经香港、东南亚,最终抵达日本。在那儿,他结识了犬养毅等一众日本志士,进而又返程东南亚,拜访了挚友的恩师康有为。
此番拜访,唐才常也谈及了“两派联盟”之事:“兴中会日渐势大,康先生可有与孙会长合作之意?”
康有为倨傲道:“建议本人同那帮草莽之徒携手者甚多,吾之答复,想汝必有所耳闻,何必多此一问?”
唐才常共鸣于孙文的革命思想,却也不忍见曾经的变法派领袖故步自封。倒是孙文,听说康有为仍然执迷不悟,摇头苦笑道:“莫非他还自恃那‘帝傅’的身份?士大夫呀士大夫,将虚名看得比性命还重。”
“帝傅”也就是俗称的帝师。康有为平日里谈不到两句,便会捧出这两个字来卖弄。在他眼中,“帝傅”可算是皇帝的“监护人”,其分量远远凌驾六部堂官、封疆总督。
唐才常与谭嗣同交好。由于这层关系,世间多误解唐才常为保皇派,还称他为保皇会中唯一的武装起义分子,其实不然。
唐才常赴火奴鲁鲁前,康有为曾设宴为他饯行,同时还邀请孙文、陈少白、宫崎滔天等一众革命分子。席上,孙文热情地向唐才常介绍了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兴中会成员。
唐才常旗下有属于自己的组织。他曾在上海成立名为“东文译社”的日文学校,实则是作为起义据点。学校的幌子里,潜伏着名为“自立会”的起义组织。会章很“中庸”,主张在贯彻君臣之仪的前提下,废满立汉。“勤王”口号是万万丢不得,除非是不想要康有为的经济援助。“废满”也得喊着,得保持在地下组织中的话语权。
单单是围绕这章程,“机会主义者”唐才常便与“教条主义者”毕永年通宵争辩了一通。唐才常很懂变通:“当务之急是什么?兵马!粮草!没人,没钱,谈何制敌?忍一忍,待进了那金銮殿,再做争论不迟。”
毕永年是死脑筋,油盐不进,气急败坏道:“我管你今后如何,总之有‘勤王’,就是不行!”
“永年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你又不是不懂。”
“忍,忍,忍!你们就晓得忍!再这么忍着,还不如一刀抹了脖子来得痛快!”
唐才常笑骂道:“你要抹便抹去,别拉我整晚在这儿浪费唇舌!榆木脑袋!你以为‘勤王’这口号能喊多久?”
“此话怎讲?”
“有王,则勤之,若王‘没’了呢?”唐才常的笑容别有意味。
“不谈了,不谈了!我还是先让自己没了吧!”毕永年说完,甩门而去,留下唐才常一人摇头苦笑。
当时,另有一个名为“中国国会”的进步组织也如日中天。其会长由人称“留美学生第一人”的容闳(chuǎng)担任。副会长之职责请到了《天演论》译者、名声在外的翻译家严复。唐才常也受邀担任总干部一职。维新破产后,地处租界的“中国国会”倒是成了变法派的避难所。
唐才常所主导的自立军起义因粮草供给迟迟不到位,一拖再拖,终究是露出了破绽,遭清廷一网打尽,唐才常也未能幸免。湖广总督张之洞当即将一众起义军就地处决,受牵连者逾千人。
严格来说,将自立军归属于保皇会门下是有些勉强了。保皇会的“首席掌柜”梁启超早先曾担任长沙实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转战上海后,唐才常接任这位置,此前,唐才常甚至未见过康有为。如此说来,保皇会为康有为“私党”,而唐才常仅仅是一名无归属的“变法志士”罢了。事实上,当时敢于高调宣扬变法的,放眼全国也只有湖南一省而已。
唐才常之所以甘愿屈居康有为门下,缘由很简单——军资。但直至起义失败,康有为也未资助过自立军毫厘,即便是有,那也仅仅是毫厘。大陆军情火急,面对一封封求援信,远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却紧攥腰包:“‘勤王’?笑话……打着‘勤王’的名头,打的无非是我腰包的主意,怎能让你们这帮‘伪勤王’抢了风头!”
一场万事俱备的起义,便是这般让康有为硬生生地拖垮。
这还真不是康有为小肚鸡肠,就拿隶属自立军的秦力山来说吧,他曾赴天津劝说义和团领袖在口号“扶清灭洋”中删去“扶清”。不料义和团闻此请求,竟认定秦力山等人为“二毛子”(指的是西化中国人),欲行加害。秦力山才连夜潜逃回汉口,为保命,这才不得已投了自立军。康有为也放出话:“天下‘伪勤王’者听好了,莫要再自讨没趣。我康某人也是九死一生之身,不是你们能骗得的!”
保皇会的“秘密金库”一向不设明账。据朱和中所著《欧洲同盟会纪实》记载,新加坡富商丘菽园曾以资助起义为名,豪捐三十万两,然而,唐才常实际收到的资助不过两万两。坊间谣传,康有为从中昧下了不少好处。
谣言不无道理——家产早被清廷查抄,赞助者丘菽园也在数年后破产,康有为却仍锦衣玉食,生活阔绰,这也怨不得世间会质疑。
1900年8月22日,唐才常在汉口受刑。同日,孙文在横滨港登上了远赴上海的客轮。六天后,客轮抵岸,但港口戒严,此时登岸无异于羊入虎口。孙文只得原路折返,白跑了这一趟。
国内形势愈发严峻,革命派把视线放在了台湾,毕竟那地界眼下由日本管辖,清廷也是鞭长莫及。9月28日,孙文登陆基隆。
早先,台湾总督儿玉与民政长官后藤便承诺会施以援手,但天不遂人愿,就在两天前,日本山县有朋原内阁集体下台,以伊藤博文为主的新内阁改变了对清方略。
纵观时局,眼下摆在日本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条,清朝廷积重难返,不再指望。当下应促使中国南方数省独立,扶持以孙文为主的新政权,这是儿玉首推的方略。
第二条,守旧派虽落马,但只要有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支撑,清朝政权便一息尚存。比起新生政权,老朽政权更易掌控。此为伊藤博文的见解。
要知道,眼下的话语权由伊藤把持。他复任首相不久,便禁止与反清组织接触,更别说派遣军事顾问。
孙文算是醒悟了——求人不如求己。前番起义所准备的军火武器,一枪未发便借给了菲律宾用作独立运动。反倒是日军参谋部资助的那批军火,起义失败后,便暂搁在三井物产旗下的“布引丸”号上。谁承想,这艘货船年久失修,尽葬身于宁波潮。
菲律宾方面多番向日求援,中村弥六议员继而资助了六万五千日元。只怪菲律宾独立势力不成气候,只局限于小打小闹,现成的军火也只得扔在仓库里吃灰。
菲独立运动领袖阿奎纳多是重义之人,听闻孙文需要这批军火,便悉数偿还了。可悲的是,吃了几年的灰,这批枪支弹药大多成了无用的废铁。想要“求己不求人”谈何容易。
所幸,“惠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还算有所进展。
此次起义的“总掌舵”郑士良,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学院求学时的校友。孙文逃离香港,郑士良独自回到故乡惠州淡水镇,创办“同生药房”,专用作与三合会碰头的地下据点。他深谙武艺,除出售药材外,还兼着处理一些简单的跌打损伤。
郑士良与孙文同是天主教徒,升学入博济医学院前,曾求学于广州“礼贤学校”,这是一所德意志教会创办的教会学校。郑氏一族与三合会颇有渊源,在广州经营多家武馆。郑士良自记事起便混迹于帮派之间。
起义的第一站暂定三洲田,三合会人员陆续在周边聚集。起初还能掩人耳目,但人数增加至五六百,难免会走漏风声。清廷得知乱党聚集于此,却难以明确人数多少,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在数里外埋伏。
儿玉的支援是盼不上了,阿奎纳多馈赠的武器弹药又是一堆破铜烂铁,三洲田方面起义军只能先行解散,再等上头命令。惠州无电报设备。郑士良只得将军队托付黄福指挥,独自赴港与孙文联系。
孙文得信后,怕用电报交代不清,还专门派遣日本同志山田良政赴港稳定局势。山田良政时年三十二岁,籍贯青森县弘前市,其父为津轻藩贵族。山田早年毕业于青森师范,随之求学于东京水产讲习所。离开校园后,他入职北海道昆布公司,并被外派至中国。日清战争时,他应召从军做翻译,愈发精通中文。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藏身日本公使馆,掩护其安全抵达军舰“大岛”号的一众日本志士中,便有山田良政。
惠州起义夭折,山田甚感内疚。儿玉与孙文先前的合作协议是山田一手促成。如今因祖国政局变更,导致协议夭折,山田自认为有责任亲自将这“噩耗”传达给三洲田的同志。最失望者莫过孙文,摩拳擦掌,眼瞅着就要回国冲锋陷阵,却突生变故。即便如此,他仍强忍不甘,鼓励同志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点挫折算什么!”
面对美利坚记者的询问,孙文极力维护日政府颜面,将此次起义胎死腹中的缘由归结于弹药匮乏,甚至放下豪言:明治维新三十载之成就,中国不过十五载可成!
如此一来,黑锅自然便转嫁到了以“废铁”报答恩德的菲律宾头上。这批老旧的军火,原本是美国政府援助菲独立组织,做对抗殖民宗主西班牙之用。然而,美西战争以美利坚完胜告终,巴黎会议上,美方竟要求以两千万美元向西班牙购买菲律宾殖民权。可笑阿奎纳多还率独立军协助美军攻打马尼拉,典型的“被卖了还帮着数钱”。阿奎纳多从此一蹶不振,索性将库存军火一股脑儿丢给孙文,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话说当年,中村弥六向上头申请了六万五千日元军资,通过小仓商会采购这批军火只用了五万日元,这余下的一万五千日元,从此不了了之。对此中饱私囊之举动,宫崎滔天是最为不耻:“余实食背山(中村弥六的别号)之肉而啜其血,犹且不慊。”
三洲田易攻难守,但所提供的装备,东拼西凑也仅有短枪三百支、弹药一万余发而已,驻扎于此绝非长久之地。眼下只有六百余人规模,但只需揭竿而起,定会一呼百应。尤其在广东沿海,仇视清廷的走私者众多,且与起义组织同气连枝。这些后备人马,招之整装而来,挥之即潜伏坊间,很是方便。若非粮草供给堪忧,召集两万人不成问题。
两广总督德寿预感到事态不妙,火速调派水师提督何长清领军四千进驻深圳,再命令陆军提督邓万林埋伏于惠州以南,严阵以待。
郑士良赴港联络期间,副司令黄福率八十人敢死队突袭清营。清军一触即溃,敢死队活捉俘虏三十人,念及是同胞,不愿伤其性命,只削去了他们的编辫。
初战告捷,“初战”却也是“终战”。虽然小规模的游击战也时有发生,但郑士良仍忍痛遣散了队伍。起义军多为本地人,卸下武装,重拾农具,任谁也瞧不出破绽。唯独替孙文传话的山田良政,自队伍解散起便下落不明。山田初来乍到,怕是在混乱之下迷了路。他虽精通中文,却仅限于北方官话,在这广东地域,怕是连问个路都成问题。一说是他不幸被清军逮捕并处死,另有一说,他或是牺牲于两军交战的枪炮之下。两年后,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有云:
革命军之迫惠州城,日本同志山田君来投助之。及军返三洲田,失其踪迹。实堪忧虑,尔来二星霜,杳无音信。
彼逍遥于如何之天地?愿其健在。
孙文手无兵权,难成气候。山田最愿意看到的局面便是“孙、李结盟,儿玉协助”。孙文对他的信赖不亚于对宫崎滔天。
孙文隐瞒起义破产事实,始终维护日政府颜面,此亲日之举已让周边同志颇有微词。即便真是如孙文所言,起义失败归咎于弹药匮乏,负责采购调拨的日本政商界仍是难辞其咎。就连身为日本人的宫崎滔天,也怒言要将那中村弥六“食肉啜血”。
贪污罪行败露,宪政本党也只是将“罪魁”中村弥六革职劝退,草草了事。可笑的是那中村竟然拒不认罪,本党也黑了脸,直接将其撤职查办。
史坚如被誉为“共和殉难第二健将”,撇开派别,只谈理念立场,于情于理,此称谓应属于谭嗣同挚友、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另外,再抛开国籍,山田良政也堪称“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都是名留中国革命史的健将。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年头(1913年),大总统孙文赴日视察铁路发展,专程于东京谷中“全生庵”立“山田良政君碑”,墓志铭如下:
山田良政先生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先生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陨灭,其志不朽矣!
碑末署名“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孙文 谨撰并书”。“撰”为创作,“书”为挥毫,“撰并书”也就是孙文创作,并亲自书写。短短五十一字的墓志铭也被公认为孙文一生最佳之撰文。
所谓“庚子又八月”,照旧历,庚子为闰,八月有两回。“又八月”指的便是第二个八月。革命爆发于辛亥年,次年——1912年被定为民国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