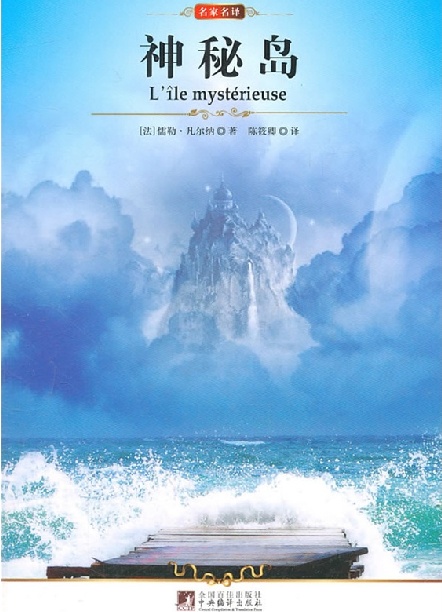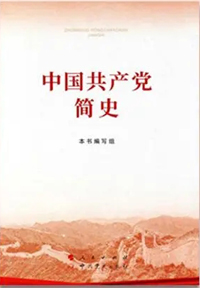只要南方六省宣布独立,为保命不惜弃京而逃的清廷中枢定然不战自溃,届时,全国各地的反清组织再争相呼应,清朝灭亡便在顷刻间。如此想来,能否点燃惠州的这第一把火,便显得尤为重要。
孙文原计划坐镇上海,运筹起义军作战。8月22日,他在横滨登上了回国的客轮,奈何同日,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就地处决。六日后,客轮抵达上海,但全城戒严,孙文只得在船舱里躲藏了三日,随客轮原路折返日本。
革命进展踟蹰不前,宫崎滔天与山田良政等一众日本志士提出了“转战台湾”的战略构想。尤其是山田,他在日清战争时曾担任随军翻译,与现任台湾总督儿玉交好,对此方略推崇非常。
儿玉总督也对清国局势尤为关注。于是乎,孙文化名作“吴仲”,于9月28日乘“台南丸”号抵基隆。日清双方白纸黑字的协议书摆在那儿,日本人可不敢大张旗鼓地迎接这位清国的“乱党头子”。儿玉总督以视察军营为名,只带着副官小泽与旅团长土屋两位亲信随行,秘密会见孙文。虽不及“列阵鸣炮”来得热闹,但儿玉亲临也算是颇高规格的礼遇了。但孙文有所不知,就在两天前,山县有朋首相刚向内阁提出辞呈。
双方谈妥,孙文于台北新起町(后改名长沙街)设革命司令部,用作秘密联系日本政府与惠州三洲田郑士良。常驻台湾的林炳文闻信也赶来新起町拜访,劈头便调侃道:“哎,我该喊您吴先生还是孙先生呢?”
“林兄,你倒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不怕让朝廷盯上了?”
“如今大陆局势晦暗不明,晚生便不去搅那浑水了,也省得坏了孙先生的大计。倒是孙先生这儿,有用得上晚生的地方,尽管吩咐便是。”
孙文问道:“且不论大陆形势,如今台湾形势如何?日据台湾,与先前有什么变化?”
“还能有什么变化?从前是听满人的,如今是听日本人的,仅此而已。倒是有一点,不知谈不谈得上变化。”
“不妨说说看。”
“台湾属清时,旗人在岛上是奇货可居。如今日本当家,假洋鬼子倒是烂大街了。还有呢,从前管事的是巡抚吧?底盘是满洲的,两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和邵友谦却都是汉人。再看看如今,且不说几个总督了,桦山、桂、乃木、儿玉,无一例外全是日本人。甚至连民政长官、州知事、郡守,只要有实权在手,便是一水儿的日本人。您说说,这是不是有些歧视汉人的意思?”
林秀才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多年后,儿玉在帝国会议上汇报在台工作——自颁布“匪徒刑罚令”起(1898年),处决台湾住民达5330余人,其中经审判处决者3480余人。颁布法令前,剿灭“土匪”万余。日方水土不服病亡者统计为4640人。有议员当场就抗议了——小小台湾,资源匮乏,却如此耗费物力、财力,还不如以一亿日元的价格将其殖民权转让给英吉利来得划算。
孙文将台北新起町的临时居所设为“革命总司令部指挥所”。照原计划,惠州前线指挥全权托付郑士良,香港方面增援工作由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三人打理,自己则伺机赶赴大陆。儿玉临阵变卦,对摩拳擦掌的孙文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
从林炳文那儿大致把握了台湾近况,孙文想起了处于半停工状态的兴中会台湾分会,继而拜访了数名分会骨干。
要说众干部之中,谁是顶梁柱,当举“良德茶行”东家吴文秀了。吴家祖籍福建泉州,如今置产于台湾大稻埕,茶叶远销欧洲,可谓是富甲一方。兴中会元老杨鹤龄的族人杨心如眼下便藏身于“良德茶行”内。
孙文颇具语言天赋,各地方话均能领悟个七八分,唯独闽南语是他的软肋。台湾人大多只懂闽南语,孙文在台湾的生活可谓不便。
吴文秀祖籍泉州,更是视闽南语如“母语”一般。所幸吴家做的是洋人的买卖,吴文秀身为少东家,自然精通英文,在交流上并无障碍。
托这位吴少东家的福,林炳文也跟着学了几句洋文。吴文秀健谈好客,时常邀孙文到其在德贵街的宅子里做客。林炳文与他相处也没什么顾忌,曾调侃道:“吴少东家,我前阵子听说,日本人还给您颁发了一枚‘绅士勋章’?怎么也不拿出来让我俩开开眼?”
“哈哈,林兄,您还真别瞧不起这块铁疙瘩。即便是抽了大烟,摆出这玩意儿,警备队也不敢动你。”
林炳文皮笑肉不笑道:“这叫什么?收买人心?”
“林兄鄙视,在情理之中。我们出卖‘人心’,不过是为给子孙换一个周全罢了。”吴文秀不愿多提这茬儿,摆出严师的架子,伸出三根手指,“今日英文对话,林兄犯有三处语法错误。”
吴少爷讲起课来可没完,孙文忙转移话题道:“听说,巴黎前些日子建了第一条地铁?吴少爷能否给我们说道说道?”
前不久,吴文秀应邀出席了“巴黎世博会”,法政府为迎接世界来宾,斥资在巴黎搭建了一条地铁,这也是法国的第一条地铁。
三人正闲谈,一名军装笔挺的日本军官进屋,行了个端正的军礼,用生硬的中文道:“吴仲先生,打扰了,总督阁下来信,请查收。”
日本军官说完,径直走到孙文跟前,恭敬地交给他一个白色的信封。显然,孙文的身份在总督府那头不是机密。日本军官继而说道:“总督阁下说,吴先生过目便好,不必回信。卑职先行告退……”日本军官行礼离去。
林炳文见孙文皱眉,会错了意:“事关机密,外人在场多有不便,我等也先行告退了。”
“二位请留步!”孙文制止欲起身的两人,“这是哪般话?我孙某人对友人一向坦荡,绝无保留。再者,眼下也正需要两位帮忙出谋划策,莫非二位要弃孙某于不顾?”
两位友人坐定,孙文却一时间没勇气看信上内容,自嘲道:“若未猜错,伊藤首相的方针与儿玉总督相悖矣。”
很不幸,孙文果真未猜错。信中内容,正是关于日本对清方针的变化。
儿玉一心要力排众议——至今与清国的交涉,多踟蹰不前,全因清廷政权腐朽,与当今国际形势格格不入。与其相较,孙文领导下的革命派明事理,至少,会按国际常识出牌。
他的方针无非是“扶孙灭清”,扶植一个新政权来统治中国。但伊藤博文曾担任日清议和代表,又亲身经历戊戌变法,有另一番见解:“观如今形势,妄谈清国覆灭者,浅见尔。所谓‘义和团义士’与自诩‘以身殉国’者,在我看来才是清国‘毒瘤’。为清国铲除‘毒瘤’,是维护正义之举。若无‘毒瘤’作祟,再加以扶持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徐世昌等能人志士,清政权至少还能维持二十年!”
面对这套言论,儿玉终究是独木难支:“二十年?在本督看不出十年,清国必亡……哼,本督人微言轻,方针如何,还不是听他伊藤首相一人之言?”
伊藤特别“点名”了儿玉——台湾总督府不得收留清国叛党,一经发现,应即刻驱逐出境。
9月26日,山县内阁全体辞职。10月7日,伊藤博文着手重组内阁,短短十二日,第四次伊藤内阁正式成立。内阁重组当天,儿玉写信便将“噩耗”告知孙文,并恳求孙文谅解。总督毕竟是拧不过首相。
时隔多年,再一次当头棒喝……孙文不认命,开始紧攥住任何可以扭转乾坤的机会,甚至有些病急乱投医。
他第一个想到的救命稻草,是在夏威夷教会相识的日本友人菅原传。这菅原时常在众人面前吹嘘自己与伊藤博文首相如何如何交好。孙文眼下也不顾真伪,直接修书一封至菅原,恳请其劝说伊藤首相支持中国革命。
这日,林炳文见孙文又在伏案修书,苦笑道:“这几日,您修书没上数十,也有十几了。如何,可有回应?”
孙文头也未抬:“垂死挣扎罢了,总好过坐以待毙。”眼下未完成的一封信,是寄给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的。
孙文之烦恼,无外乎为军资供给。如今他是走投无路,否则放在从前,他是一万个不愿意向刘学询这位“红顶商人”求援。追究其缘由,刘学询资助宫崎滔天三万元时,曾半开玩笑似的说了这样一句话:“三万元就可以组织一次革命,您说说,坐上那龙椅,得花多少钱财?”
刘学询的态度半真半假。宫崎不得不上心,忠告孙文小心此人。照理说,这刘老板若真能斥资百万援助革命,扶持其称帝倒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称帝”一词显然与“民主共和”水火不容。众人商议下,专程为刘学询量身定做了“主政”一职。
孙文甚至拟定了建国第一届领导班子:“主政”刘学询,“主兵”孙文,杨衢云分管财政,内外政分别由李纪堂、盛宣怀掌管。李纪堂算是“会中元老”,前不久刚继承了巨额遗产,眼下长居香港,做日本邮船“买办”。盛宣怀为李鸿章财务幕僚,与刘学询一样,要接触到这两人,得先过去李鸿章那一关。
林炳文瞅见信封上的收件人,警告道:“您确定要将这封信寄出去?前番在广州,这刘老板是不确定他家主人的态度,才暂且给革命党摆了张白脸。眼下,他追随李鸿章去了上海,算不算站明了立场?万一……”
孙文打断林炳文,还是那句话:“总好过坐以待毙。”
7月21日,李鸿章抵上海,身体抱恙不得不安歇数日。翌日,其子李经述发来电报: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老宰相也是无奈:“现今局势,身不由己也。”
8月15日,京师沦陷,西太后等一干清廷中枢弃京逃往西安。9月8日,澳门《知新报》曝光了两封康有为寄给李鸿章的信件:第一封意图说服李鸿章勿要逮捕新党(维新党),作为报答,保皇会愿与其协力讨贼(革命党);第二封则恳请李鸿章对义和团网开一面,并领导其镇压内贼(革命派),修改外交方略以救圣主(光绪帝)。
9月14日,李鸿章在多方面重压之下,带病赴京。
伊藤内阁对台湾总督府下达了驱逐孙文的死命令,儿玉却不肯买账,迟迟不采取措施。这一日,先前送信的日本军官再次拜访孙文宅邸:“请吴先生借一步说话。”
终于,要下逐客令了。孙文心中犯苦,强装笑颜道:“吴某已整顿妥当,随时可以动身。”
日本军官今儿穿着便装,笑着解释道:“吴先生您是否误会了?在下此行绝非是来催促。您看卑职的眼神,便像是在看一个间谍。”
孙文苦笑道:“吴某草木皆兵了,若误会,还请见谅。”
“在下此番拜访仅为私事。吴先生……哦不,私底下,我可否唤您本名?自我介绍一下,在下服部,为陆军中尉。”
“在下孙文,同志多唤我别名孙逸仙。您姓服部?我有一同志也叫服部。”
“您说的这位同志,一定是陈少白先生了。”
陈少白的日文名叫“服部次郎”,这是鲜有人知的机密。眼前的日本军官,恐怕与日谍报机构难脱关系。见孙文目露狐疑,服部坦白道:“我早年在参谋总部做情报工作,日清战争时从军,我这一口中文便在那时学得。”
孙文对服部的身份虽尚有疑虑,却仍随其来到城郊。
重峦叠嶂的观音山脚下,水流湍急的淡水河,摇摇晃晃的老帆船,汇聚为“宝岛”河港的自然景致。曾几何时,发往“唐山”的商船多由淡水、艋舴、新庄三港。然而,由于常年河沙堆积,加之船舶规模渐增,传统河港已力不从心。日本占领后,三个传统河港逐渐呈衰败之势。但小商船受不住海港的风浪,离不开原始林的“庇护”,仍是河港的常客。当时,那片原始林便是两岸船商的“市场”。服部在前边带路,还不忘给孙文介绍此地:“想当年,这片原始林,延绵至新庄还不见尽头。如今河沙堆积,原始林毁了大半,勉强只能覆盖到万华周边了。您可别小看那一艘艘破船,那是出了名的富商‘摇篮’。您在唐山,可否听说过一种药酒,叫作‘五加皮’。不瞒您说,普通‘五加皮’贴上‘天津’二字,在台湾能卖到原价的两倍。”
“冒牌货?台湾同胞端的是淳朴,如此轻易就让大陆商贩给坑蒙了。”
“孙先生谬矣,这作假的商贩也是台湾人。台湾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他们自家的事。”
“保皇派与革命派也同是汉人,争到你死我活,也都是汉人窝里斗,谁又能怨得了谁呢?”
“成王败寇,全凭手段……”服部感慨道,“商贩的手段也是着实高明,先将在上游酿成的假酒发往海外走个过场,再原封不动地运回。一个转手的工夫,小作坊酿出的杂牌酒,就成了刚出炉的‘天津五加皮’。”
“这般伎俩,在大陆也屡见不鲜了。”孙文道。
“确实,这算入门级的伎俩了,更为高深莫测的伎俩也是层出不穷的。”
“世情如此,弄虚作假,诈些钱财,终究也就是吃个官司,落个坏名声罢了。可恶的是,某些人对国事也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可悲还有一帮愚民,对他的谬论推崇备至,国将不国矣……”
孙文话音刚落,服部突然驻足,恳切道:“孙先生,服部有一事相求。”
“哦?愿闻其详。”孙文诧异于对方态度转变之快,也随之驻足,注视着对方的神情。服部面相稚气,乍看下像是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但他声称自己曾在日清战争时从军,满打满算,如今至少也已过而立之年。少年的稚气,杂糅着军人的刚毅,这与众不同的气质,倒让孙文颇有好感。
“在下原是奉儿玉总督之命,赴台专门协助孙先生。此次政局更替,我等怕是再不能插手贵国之事。照理说,在下是军人,奉上级命令办事,从不问缘由。但唯独这一回……这段时日,我研究观察了贵国之形势,明知不可,但仍不由得要对新内阁的对清政策存疑……”
孙文如何感觉不到其中蹊跷……新内阁究竟对儿玉施加了何等压力,竟令其顶着“背信”的骂名,也要收回承诺?其中,会不会另外有隐情?孙文答道:“孙某亦深感疑惑。”
“同是疑惑,在下之疑惑,为站在日本国民立场对新内阁的怀疑。而孙先生的疑惑,却未必是站在清国国民立场的吧?在下好奇于孙先生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理念。在下并非要求教孙先生,只愿效劳于先生鞍前马后,亲身去体验,去理解。不知孙先生是否愿收下在下这个马前卒?”不知从何时起,服部保持着岿然不动的军姿。
孙文也不是第一次应付这样的场景,严肃道:“孙某周边的日本同志,支援我中华革命皆不图回报。服部中尉可有此觉悟?”
“我服部又怎是唯利之徒?为先生效劳,解开困扰我已久的疑惑,这便是最好的回报。”
服部言罢,再次挪开脚步,孙文与其并肩而行。孙文对这位日本军人的话不敢尽信,毕竟还未查清对方的底细,只知道他是儿玉总督从参谋总部中选拔而出的精英。
两人一时无话,孙文心中便开始计较了:日政坛“改朝换代”,儿玉源太郎的对清政策算是死于襁褓。但依儿玉的性格,怕不会轻易缴械投降。如今,儿玉自己不方便出面,便交于眼前的服部全权代理。
儿玉的目的自不必多言,为日本谋求利益尔。他身为总督,一举一动自然以国家利益优先。在儿玉来看,革命党完全能成为日本的“双赢”伙伴,但显然,新首相伊藤不这样认为。儿玉不愿逆流而上,只能寄希望于历史能为自己的方略正名。
如此想来,服部便是儿玉精心挑选的分身,代其行动。自己的“一意孤行”,便由服部去贯彻落实……
孙文起先不敢妄作臆断,行至万华龙山寺时,才勉强说服自己。他一度一厢情愿地猜想,会不会是服部仰慕自己,不满日方侵略暴行,意欲归顺?这念头刚冒出头,孙文便暗自扇了自己一耳光。到头来,孙文决定暂且相信服部,但有所保留。
“来者不拒”为孙文座右铭,即便疑点尚存,革命阵营的大门也依旧为任何人敞开。
事已至此,台湾是不可久留了,孙文决定暂退日本。这时,服部又向他透露了一个内情:儿玉总督原计划将存在厦门“台湾银行”支行的三百万日元赠予孙文,充作两个师团的军资补寄。起程前夜,儿玉亲自前往为孙文饯行,他愧疚道:“万事俱备,却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是本督有负于孙先生……”
“宝岛”是一块造梦之地,它给予孙文太多的希冀。儿玉亦有自己的鸿鹄之志,奈何他是体系中人,难免会身不由己,只能将自己的梦想,托付于服部去一一践行。
起程前的某日,林炳文将两个男人领到孙文居所。他们正是重阳起义前搜集溃败的清军遗弃在岛上的军火,再出售给起义军的廖大竹与李小军。孙文问两人道:“前番军火的账,可与你们结清了?”
“若未还清,趁咱的大财主在场,赶紧开口。”林炳文三句不忘调侃,“不怀好意”地朝在一旁饮茶的吴文秀扬了扬下巴。
茶行少东家仍是一副标志性的憨厚笑颜,对林秀才的调侃不置可否。孙文对这位赞助者却很是尊敬,诚恳道:“台湾兴中会,便有劳少东家多照应了。”
吴文秀反倒过意不去,挠了挠后脑勺儿,苦笑道:“不提了,不提了,会上好些时日未整出动静,吴某人已打算到少白先生那儿去‘负荆请罪’了。”兴中会台湾分会乃陈少白一手创办,但成立没多久便哑了火,如今正处于“半闭会”状态。
孙文先后与廖、李二人握手致意。吴文秀见状,下决心道:“不能再这般浑浑噩噩了,不能让台湾分会衰败在我手上。今后,还要麻烦两位义士。”
11月初,孙文化名“吴仲”,从基隆起程至横滨。当初抵台,虽无列阵鸣炮,但好歹有总督屈尊相迎,也算是国宾待遇。然而此番离去,哪还能奢望总督亲临。为避嫌,甚至连众同志亦未前来送行。只有廖大竹、李小军替孙文将行囊捎到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