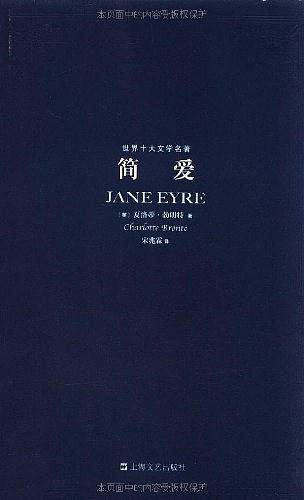1900年11月16日,孙文抵达横滨,尤列已提前为其准备了落脚的公寓。
香港“四大寇”之中,单论行动力,属尤列首屈一指。同为“四大寇”一员,孙文与他自然是莫逆之交。
惠州起义时,尤列曾协助郑士良与长江流域的地下组织接头。可笑的是起义失败后,一份湖广总督署名的公文,竟宣称“乱党尤列已于武昌伏诛”。圈子里也开起了尤列的玩笑:“悲乎哀哉,革命尚未成功,少纨(尤列字)升天不能。”
一纸公文也令尤列身价倍增。不知何时起,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仰慕其名望的留学生。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日中国留学生呈几何数目增长。1900年,中国留学生不过堪堪百人,短短两年,便增长至六百余人。到1905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一度达八千人之多。
事到如今,孙文再不能忽视这一群体。中国留学生无论“公派”还是“私费”,在当今时代都是人中龙凤,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子弟”。同时,他们亦是孙文最不愿拉拢的人群。须知,孙文欲行之革命,追本溯源,便是要“瓜分”士大夫手中利益。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加速了清廷守旧派的倒台。科举制度也难以为继。随着1904年最后一场“会试”结束,持续千年的科举制落下了帷幕。逐渐地,学校取代科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留学生激增也是意料中事。
驻日公使裕庚公派的十三名留学生,堪称“中华留洋先驱”。按理说,对“食公粮”的留学生,革命派是无从下手的。但公派留学生中,也不乏戢翼翚这样死忠革命的热血汉子。说起这戢翼翚,他在自立军起义时曾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后随秦力山等人赴东京,创《国民报》,可称革命一健将。
1895年革命火种初燃,孙文领导下的革命党,携手辅仁文社,共同成立兴中会。辅仁文社是个极端的反清组织,与革命党的理念从开始便相悖。孙文让出会长一职,退居副会长,才勉强将矛盾最小化。
然而孙文因“伦敦使馆绑架案”而“一炮走红”,加之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等一众革命派骨干的行动受世人瞩目,1899年“三会联盟”(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组建兴汉会,孙文被推举为总会长,迫使杨衢云也不得不让出兴中会会长之位。
清朝当局知晓革命派中山头林立,便从未停歇过策反工作。惠州兵变名为起义,战死者却只有寥寥四人,算上下落不明的山田良政,也不过五人而已。清廷欲从中挑拨,也无从下手。就在清廷一筹莫展之时,兴中会叛徒陈廷威主动请缨,说是要策反杨衢云。说来,他还是杨衢云的远亲。
杨衢云出生福建澄海(现漳州),福建人在香港的圈子很窄,消息闭塞,策反工作的保密性足以保证。杨衢云对自己这位不成器的远亲是深恶痛绝,索性就来了一手将计就计,将清廷的劝降条件透露给了孙文——革命党高层若受招安,则封道府副将,配给五千人队伍,数万两军资。这泼天的好处,到真让杨衢云颇为动心——军队暂且不提,有了这笔军资,可解革命党燃眉之急。
孙文是坚决不赞同杨衢云的这“诈降之计”,并吩咐陈少白警惕其行踪。这也不怪孙文多疑。乱世之下,“招安”的事例屡见不鲜,如今为清廷效力的重臣中,便有几位出身草莽之人。原太平天国旧部刘永福自不必说,就是那曾出兵剿刘永福的冯子材,曾经也是草寇出身,让清军吃过不少苦头。
孙文打心底不愿怀疑同志,他还有另一番考量——清廷若策反失败,极有可能会恼羞成怒,从而加害杨衢云。
果不其然,清廷的“策反计”破产,索性出重金三万两悬赏杨衢云首级。孙文苦劝杨衢云赴日本避难。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三万两重赏之下,只怕觊觎杨衢云性命的不仅是区区职业杀手那般简单了。周边友人也开始苦劝杨衢云:“香港的治安差,也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了。身负几条人命债的恶徒也能招摇过市,警察哪里肯管。肇春兄,还是尽快到日本避避风头才好呀。”
杨衢云对友人们的忠告嗤之以鼻:“哼,日本……”说来,他倒未必反感日本,还记得,当年众同志准备从日本回国迎战惠州时,犬养毅与头山满等日本志士,还专程举办了一场“杨衢云、孙文、郑少白归国壮行会”。只不过,就是那一趟日本之行,让杨衢云不得不将会长之位“让贤”于孙文。对这点,他至今仍如鲠在喉。
孙文力劝杨衢云赴日避难,并经会上商议,愿负担这位前会长赴日的全额差旅费。然而好心办坏事,这一举措倒让杨衢云争起了一时意气:“投身革命,一死又有何惧?我在香港开洋文学堂,再不济也能蓄妻养子,如何能动用革命资金到海外逍遥快活?”
杨衢云出生于越南,十六岁才重归故乡福建,补习了整整五年的汉语言后移居香港,就职于当地造船所。后因事故被削去三根手指,再不能从事技术工作,开始苦学英文,投身英文教育,并先后辗转于招商局与外资商社。
在港谋生期间,杨衢云亲身体验了洋人对同胞的欺辱与压迫,即与友人共创辅仁文社,宣扬“种族思想”,后融入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铸就了如今的兴中会。两派之所以能融合,杨衢云挚友、位列“四大寇”的尤列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英领香港警察庇护,香港成为“反清分子”的避难所。郑士良与杨衢云的“反清罪行”已路人皆知,又这般肆无忌惮地在眼皮子底下晃悠,清廷怕是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
两人自知为“国家公敌”,自然谨慎小心,但仍然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刺客陈林也不磨叽,直截了当,一招得手。
这一日,杨衢云像往常一般在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谁能料想刺客陈林不躲藏、不埋伏,在众目睽睽之下踹开教室门便是一枪,正中杨衢云要害。估计他在先前仔细踩过点。待众人反应过来时,他已没了踪影,当日便逃至广州。
行刺后,友人劝陈林三思而后行:“你苦兮兮地为清廷卖命,就不怕清廷为撇清干系,卸磨杀驴!”
陈林冷笑道:“富贵险中求嘛。干咱这行,不把脑袋系裤腰带上,哪盼得上飞黄腾达呀……我可是忍痛将一半赏钱赠予某位大人物打点关系,有了这层保险,我可高枕无忧……”
清廷承诺“取杨衢云首级者,赏银三万两,封千总”。这“千总”并非虚职,可是正儿八经的南石头炮台编制。
杨衢云挣扎了一夜,翌日早间才咽气。暗杀当日为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901年1月10日)。事后,清廷如实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还不到一个月,陈林的宅子久遭查抄,并被“搜出”谋反物证。后得知,是清廷派遣在刑窃贼暗中将谋反信件藏入了陈宅之中。可怜陈林,终究难逃“走狗烹”的命运,被射杀于任职的炮台之下。
远在东京的孙文得知杨衢云遇害,特赴横滨举办追悼会,并筹集一千两百元义捐,以赡养杨家遗族。
兴中会有两座山头,分别为旨在革命的“孙派”与原辅仁文社成员组成的“杨派”。孙、杨二人的会长之争,自合并起便未停歇过。孙文起初为缓解两派矛盾,主动将会长一席让给年长自己五岁的杨衢云。照理说,这杨衢云仗义豪爽、为人坦荡,虽身无大志,却也配得上会长一职,然而三会合并(三合会、天地会、兴中会)之时,众人一致推举孙文为总会长,且革命派活动频繁,这逼得杨衢云只得退位让贤。他退居二线后,仍默默为兴中会奔走操劳,甚至愿意涉险诈降。孙文对这样一位同志的牺牲倍感惋惜。
谁能料想,七个月后,孙文更是痛失一视若臂膀的同志——郑士良。
惠州一役,郑士良统筹前线大局,已然心力交瘁。为随时可以与孙文取得联络,他先后几番往返清廷控制地带,战战兢兢数十日,撤回香港时,其肉体与精神已濒临崩溃边缘。
某日,郑士良与《中国日报》记者在琼林酒楼畅饮后,一同返回位于永乐街的报社。记者们开了门,回头招呼郑士良,却发现其瘫倒在黄包车上,已然咽了气。警方未在尸首上发现外伤,便将死因判定为“脑溢血发作而亡”。然而,坊间有谣传说,某友人在赠予郑士良的食物中下了毒。这位友人的姓名甚至也被挖出,叫郑梦唐。
《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为革命派在香港之阵地,陈少白担任主编。其“敌阵”为保皇会操办的《商报》。海外华人误以为两派是一家,同时加入两派者不在少数。就连孙文的兄长孙眉,也是那保皇会的挂名干部。直到1900年,两派再容不得“劈腿会员”,这一态势才稍稍得缓。
郑士良尸骨未寒,1901年9月,清廷签署《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处死“战犯”数百名,且赔款八国总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要知道,当年清廷的一年岁入,上亿都成问题,如何能一次偿清?八国也不强人所难——既然无法一次付清,便分期三十九年,利息按年利率四分计算。这算盘打得响,四亿五千万两,四分息,三十九年,连本带息至少九亿八千万两。
十年后清朝覆灭,新上台的民国政府仍得继续填这个无底洞。有关税作保,八国可不愁拿不到赔款。一直到1940年(昭和十五年),这个无底洞才被填满。
赔款还不算完,《辛丑条约》还要求清廷进行改革。“改革”不就是“变法”换了个说法?清廷刚处决了变法先锋“戊戌六君子”,却得去继承他们的“遗业”。
那如何处置变法领袖康有为?是否为其平反?——答案是否定的。清廷仍唤康有为做“康逆”。清廷在西安颁布《辛丑变法诏书》以自圆其说: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清廷中枢的官老爷们,竟连区区义和团也掌控不得,可谓颜面扫地。自此,清朝之实权,逐渐转移至汉人出身的各位封疆大吏手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呈奏变法事宜,因湖广自古有“楚地”之称,此奏疏又被称作“江楚会奏”。第一封奏疏呈奏于1901年7月12日,大概内容有以下三条:废科举,设学校,派留洋。
孙文看到《江楚会奏》的报道时,尚未听闻郑士良猝死的噩耗,还暗自思量道:“学校,留学生的时代终于到来……距下次起义尚有时日,学生那头便暂时交予弼臣(郑士良字)负责。”
1901年,新世纪开端,孙文是没闲情感受那新气象了。正月,杨衢云遇害,仅仅是革命大业受挫的开始。
这一日,孙文在横滨的“监护者”温炳臣邀孙文道:“南方先生邀我们至和歌山一游,孙先生意下如何?”
温炳臣为多德韦尔商会买办。买办一职,非洋商绝对信赖者不能担任。就说前番在香港对革命派慷慨解囊的李纪堂,便是日本邮船之买办。洋商欲在中国开展贸易,出于对华商信誉的质疑,只愿对接买办。买办便在中、外商人之中协调周旋,收取些中介费。
温炳臣这是在邀孙文一块去拜访南方熊楠。其实早在去年,南方熊楠自伦敦回国后,便联系了孙文。说来也好笑,南方自欧洲回国,却赶上家业破产,自此后便倚仗其弟常楠的接济过活,没有闲钱去横滨拜访孙文。
南方熊楠可是孙文在英期间难得的挚友。孙文忙应允道:“要去,要去,还请温兄为孙某打点出行事宜。”
温炳臣点头:“要不要跟警署那边打声招呼?”
“其实不用我们去求援,他们也会暗中护孙某周全……但如今非常时期,还是与他们招呼一声吧。”
何谓“非常时期”?杨衢云惨遭横祸,孙文首级的赏金更胜于其数倍,即便是身边贩夫走卒,为求财,难保不会铤而走险。如今,孙文的一言一行,尽在日本政府的监控之下。此次拜访南方之行的始末,日外务省自有详细记载。
孙文迟迟未从杨衢云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此番与南方久别重逢,对消沉的他来说,无异于“强心剂”。两人依旧以英文交流,仿佛回到当年的大英图书馆。同行的温炳臣身为买办,自然精通洋文,也时不时插上两句。
熊楠自伦敦与孙文一别,好久未像这般相谈甚欢。毕竟,愿意与他探讨菌类的友人,怕只有孙文独一份。两人一聊起菌类,在一旁的温炳臣便识相地闭上嘴,笑眯眯地旁听。
南方熊楠的好记性仅用在感兴趣的事物上,至于让他兴致缺缺的人与事,哪怕是一丝心思也不愿往上花。就拿温炳臣的名字来说,熊楠唤错不是一次两次了,要么是Mr.陈,要么是Mr.翼,也不知将温炳臣错认为是谁了。再来,他时常会哭穷:吾辈不名一文。孙文拆台道:“整日哭穷,何不外出工作赚钱?”
熊楠没心没肺地笑答道:“能寄人篱下,何尝不是件快事?就我这荒唐性子,怕难求雇主。”
想想也是,就他这烈性子,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研究机构都容不得他,遑论区区的私营企业了。孙文笑道:“天下之大,能容你南方熊楠者寥寥。”
孙文嘴上调侃,实则对友人的就业问题颇为上心。事后,还专程至信犬养毅,希望这位内阁重臣能帮衬友人一把。
南方落得如今田地,哪还能行那地主之谊。唯一的一次招待,还是在和歌浦的“芦边屋”,这是他的发小友小笠原誉至夫经营的餐厅,说白了,他没花一个子儿。
一个月的和歌山之旅见尾,孙文想顺路跑一趟自己的“治愈之地”,第二故乡夏威夷。临行席上,孙文将跟随自己多年的巴拿马帽赠予南方:“经此一别,万水千山。南方兄且收下这顶帽子,权作纪念。”
南方珍惜地收下,举杯道:“愿我与孙逸仙之友谊万古长青。”
孙文在夏威夷修养两月余,于6月中旬返程横滨,他特意还带回了夏威夷特产的植物标本,期待有朝一日赠予南方。一个月后,也就是1901年7月,《江楚会奏》问世。
《江楚会奏》主张废科举,兴留洋,尤其推崇留学日本,并指出赴日留学的几大好处:文字相近易学,留学费用不过欧美三分之一,且为邻邦往返方便。
孙文闻消息后叹道:“留学生之时代终究还是到来了……不假时日,必定有大量留学生涌入日本,任公(梁启超)盼此日久矣。可惜,我方阵营中还未有在此方面可与其匹敌之人物。”
温炳臣不服道:“孙先生这般说,怕是少白要伤心了。”
“孙某绝无贬低少白之意……据我对两人之了解,要说为人处世,少白与任公可称伯仲,但少白输在太过耿直。你想想,任公一手妙手文章令人趋之若鹜。然少白为人率直,不善婉转。如此比来,单论虏获人心,确实是任公棋高一着。”
“我们唐人圈子里怕也寻不着与之匹敌的人物……但是要比生意手段,可就另说了。”
“炳臣兄这话可说得太满了……若真让任公端起算盘,你们怕有一半人要丢了饭碗。”若无法将梁启超收为己用,则他必会成为革命道路上的一大阻碍。
眼下,梁启超正着力巩固保皇会在夏威夷与澳大利亚的势力。他处事圆滑,常故作神秘地向周围人道:“我对外声称是保皇派,这只是幌子,方便我暗地里进行革命而已。”
孙文不责备梁启超“欺世盗名”,他坚信梁启超素有“反骨”,只不过是碍于与康有为的师徒情谊,不敢公开倒戈罢了。孙文看得通透,不由得感叹:“梁启超呀梁启超,何其狡猾……”
观如今局势,朝廷为“康逆”平反不是不可能,届时“勤王”旗帜重振,梁启超作为保皇会第二把交椅,注定会位高权重。反方向想来,若有朝一日革命成功,即便是孙文也只能向世人承认:“其实,梁启超是革命派安插在敌营中的卧底。”不论鹿死谁手,他都是名利双收。
清廷废科举,以留洋代之,也就是说,留学群体大多是走不得仕途,才无奈选择留洋的士大夫子弟。先前也提过,孙文一直对其敬而远之。在拉拢留学生方面,梁启超可以说是占尽了主动。
1901年,赴日留学生尚不足百名,其身份可一一追溯——除却驻日公使馆招募的十三名“先驱”,另有浙江省公派八名,湖广总督派遣二十四名,北洋大臣派遣二十名。甲午惨败令清廷看清了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所派遣的新晋留学生中,“武备学生”占了大半。
留学生设立同乡组织“励志会”,成员四十余人。成员中既有后战死汉口的自立军骨干黎科,又有清朝宗室良弼,可见“励志会”仅是纯粹的老乡会,政治立场很是模糊。
1902年,会中出现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激进分子,并另创“青年会”,这迫使稳健派相继离会。同时,一起惊天革命事件正在酝酿——留学生谋划于1902年4月26日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事件的总策划人为国学大家章炳麟。
1644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1661年(辛丑年),吴三桂擒拿住永历帝,距今整好二百四十二年[参考一些历史文献,此纪念会名称是以“南明”政权崩溃推算,日期则选为崇祯帝殉国之日。]。明眼人瞧得出,章炳麟这是在含沙射影追思亡明。
章炳麟年少孙文三岁,却年纪轻轻便被推崇为“国学大师”。章炳麟致力钻研国粹,曾参与《时务报》主编工作,却因理念与“公羊学派”梁启超相悖,离开报社,一度成为张之洞帐下幕僚。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避难台湾,后流亡至日本。
时任驻日公使蔡均闻知此事,要求日外务省即刻叫停这场不知所云的“亡国”纪念会。即便公使不开口,日本政府也不会由着异国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神乐坂警署先后传唤了十名集会组织者。发起人之一冯自由,有幸旁听并记录下了章炳麟与警署长之间的问答:
署长:你是清国人?
章:清国为何物?余等为支那人!
署长:可有官职?士族?庶民?
章:遗民尔。
日方高层都勒令解散了,人在屋檐下,组织者也只得收手。但消息已放出,集会当天,在计划用于会场的上野精养轩附近有数百名留学生滞留,警方驱散还费了好大工夫。
孙文自然不愿错过这场好戏,连夜赶至上野会场,哪承想白跑了一趟。他索性就近在精养轩就了餐,折返横滨,联系众同志,在横滨永乐楼“补办”纪念会。第一发起者章炳麟自然出席了此次补办集会。除此,会议还邀请了自立军幸存者秦力山等人。
章炳麟在策划集会前,不忘征得孙文与梁启超两位华人代表的应允。事后,梁启超曾至信章炳麟,嘱咐其切勿对外宣扬自己的名字。
“清”这一国号逐渐遭抱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所唾弃,被取自佛典的“支那”取而代之。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印度王曾询问三藏法师,支那国若何?其后,随中日关系遇冷,“支那”一词才带有了歧视意味。
遥想盛唐时代,日本“遣唐使”千里迢迢赴唐求教,如今风水轮流转,留学生们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但甲午惨败摆在案前,泱泱中华不敌这蕞尔小邦已成事实。
我大清仅在军事上略输一筹尔——“武备学生”们带着这般自我麻痹的想法,不情不愿地涌入了日本。
日陆军省暂将留学生们安排于“东京成城学校”,接受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教育。这所五年制学校特意增设了留学生部。并于1903年更名为“振武学校”。自此,学校再不受文部省管辖,而是直属参谋总部。因横穿西伯利亚闻名的福岛安正少将上任首任校长。学校创始之初,学业仅十九个月,后改为三年。毕业生被分配至各联队实习后,方有资格升入士官学校。
早在1898年,北洋大臣裕禄便计划派遣六名海军学生赴日留学,但日本海军兵学校却不愿录取外国人。一番交涉下来,日方放宽政策,同意让清国学生在日本商船学校接受普通教育后,安排其到各海军校实习。然而,申请者还不到三人。赴日留学遇冷,不完全归咎于日方的排华态度。早在1875年,福州船政学校便与英吉利海军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英吉利才是留学生心目中的首选。
日本方面,留学预备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专门为留学生提供日语教育的宏文学院。后世文豪鲁迅便是经由此校升学入仙台医专(现东北大学医学部)。高楠顺次郎创立之日华学堂秉持少数精锐主义,曾将三名被海军兵学校拒之门外的留学生成功送往东京帝大。另有明治大学旗下之经纬学堂、东斌学堂等知名预备学校。除此,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实践女子大学等名校也纷纷创立清国留学生部。
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自1902年起,赴日留学生数量呈几何式增长,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再不能无视这股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