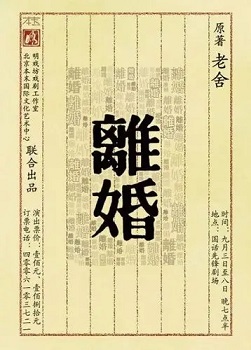孙文常把一句抱怨挂在嘴边,叫“任公一过,寸草不生”。也难怪,他费尽唇舌招揽来的寥寥几位同志,竟相继倒戈,进了保皇会,甚至还反过来劝说孙文:“逸仙先生宽心,我等生为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加入保皇会,仅是一时从权,为保家人不受牵连罢了。先生家中亦有妻小,不妨也……”殊不知,孙文远在夏威夷的家人孙眉,早已是保皇会干部。
加之,保皇会主刊《新民业报》以及其前身《清议报》不时发表激进的革命言论,导致日本兴中会成员锐减,转阵营至保皇会。梁启超手段之高明可见一斑。倔强如孙文也不得不服输:“孙某甘拜任公下风,只恨曹营无卧龙。”然而这份挫败感不一阵儿便烟消云散,随着留日热潮逐渐升温,思想先进的留学生纷纷投向兴中会阵营。
清廷苦心培养出国的留学生,竟成为乱党阵营的“储备人才”,尤其陆军学生群体是重灾区。清廷只得规定留学者必须有公使馆出面担保。
留学生群体的“扛把子”吴敬恒自身并非是留学生。吴敬恒为江苏无锡人,却带领着数十名广东籍留学生,以“成城学院拒绝录取”为名,至公使馆示威抗议。公使馆没法子,只得允许日方警察进馆拿人。于是吴敬恒被捕,并被遣送回国。说来也凑巧,被日本政府遣返的吴敬恒在法国客轮上,偶遇视察归国的蔡元培(后北大校长),两人曾在南洋公学(后交通大学)共执教鞭。
吴敬恒若随客轮直接回天津,怕是羊入虎口。所幸,客船停靠了上海,两人登岸便藏身租界内,清廷也是鞭长莫及。
追溯孙文的1902年,除却年头与年尾的小段时间,其余时日都是在日本岛内度过。1月28日,孙文乘“八幡丸”号至香港,“五年入港禁令”已到期,但香港仍非久留之地,他流连六日便匆匆返日了。4月忙于操办“亡国纪念会”,7月随宫崎滔天出游冈山后乐园。
12月,孙文受法领印尼总督杜美相邀,赴越南参观河内世博会。法国政府刻意交好中国次代政权候补,可见清朝政权时日无多已是国际共识。
香港陈少白与孙文会合,同往河内。陈少白临行前,收下了同志李纪堂赠予的两千元做饯别。李父于去年辞世,李纪堂可名正言顺地自由支配家中财产。
辅仁系骨干谢缵泰素来与孙文不对付,杨衢云遇害后,他极力推举年长孙文三十八岁的容闳接任会长。
容闳现年七十有三,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先后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顾问”,现居美利坚养老。谢缵泰曾至信委托容闳争取美国政府的同情与支援,在落款于9月22日的回信中,容闳表示自己将竭尽所能。
谢缵泰出生华侨家庭,其父谢日昌为三合会骨干。谢父与洪秀全之族侄洪全福交好。有谣传说洪全福乃洪秀全的三弟。如今距太平天国覆灭已有四十载,天京沦陷后,洪全福流亡至外国客轮上做伙夫,躲过了清廷的屠刀。
孙文在停泊于香港的客轮上,等待与陈少白碰头之时,李纪堂携两千元现金前来送行。他是日本邮船买办,进出外国船舶自然是畅通无阻。背着孙文,谢缵泰将李纪堂拉到一旁,嘱咐道:“切勿说多余之事。”谢缵泰刻意要对孙文隐瞒这“多余之事”,陈少白作为孙文的左膀右臂,更不可能得知。
还有片刻便要起航,李纪堂在甲板上与孙、陈两人话别……
信奉基督教的陈少白无力地感慨道:“唉,这一晃,明天又是一个平安夜了。”陈少白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一直以来都是亲自执笔,与保皇会针锋相对,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孙文见状,责备道:“我们这趟去河内,只为放松。暂时将任公与保皇会抛诸脑后罢了,不要自寻烦恼。”
李纪堂忙接茬儿道:“逸仙兄所言极是,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说了,不说了,孙先生难得来香港,在下未尽地主之谊,着实有愧。”
孙文暗觉李纪堂话中有话,但汽笛声响,不待他追问,李纪堂便匆匆下了船去,辞别时的笑容,越看越觉得怪异。
待李纪堂离船后,陈少白疑惑道:“阿柏的态度,不对劲儿呀。”“阿柏”为李纪堂的小名。
“少白兄也有所察觉?今日的李掌柜,确与往常不同。”
客轮驶往河内,两人心中之疑窦也就不了了之。
孙文有所不知,香港谢缵泰暗中联合太平天国残党洪全福,正在密谋策划一次新的武装革命。
与已故的原会长杨衢云不同,谢缵泰一向瞧不上孙文——孙文之辈,屡战屡败。即便无他领导,吾等亦能举大事。
举兵之日初定为1903年1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凑巧撞上了壬寅年最后一日——“除夕日”。与九九重阳一样,除夕之日市井喧闹,便于起义军暗中行动。
谢缵泰幼年成长于澳洲悉尼,精通英文。这段经历,赋予其异于普通人的国际思维。他看得通透,重阳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未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他在港期间,广交海外人士,并积极接触海外新闻工作者,尤其与《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莫里森、《香港日报》记者坎宁安二人交往甚密。外国记者为掌握第一手情报,自然争先恐后地讨好谢缵泰。谢缵泰向同志孙文隐瞒起义一事,却对此二人和盘托出。坎宁安协助起草了“对外宣言”,莫里森则为此番起义争取到了《泰晤士报》的言论支持,而谢礼,自然是“除夕起义”这一大头条。
起义军由洪全福统辖,商人出身的梁慕光负责坐镇前线,头衔更是气派非常——“南粤兴汉大将军府军总司令”。参谋长则由在德国教堂做汉文总教习的李植生担任。起义军甚至提前拟定了新国名——“大明顺天国”,高呼“排满兴汉”口号,公开向民众承诺:天下太平后,即订立年限,由人民公举总统。
谢缵泰称新国体为“君民共主之制”。顾名思义,由民众推举而出的总统,其本质依旧为“君”,扎根在谢缵泰骨子里的“帝王思想”可见一斑。起义成功后,则立即从美利坚迎回七十三岁的容闳,奉其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如此仓促,说到底,只是为了及早将孙文一派扫地出局。
李纪堂在香港出资建立商铺“和记栈”,暗中进行军备的采购、调配与储藏。为采配这批军火,李纪堂不得不变卖家产,接受广州沙面租界“曹法洋行”的坐地起价。
距起义仅余三日(1月25日),全军统辖洪全福暗中潜入广州。谁承想他前脚刚踏出香港,在港各据点便遭警方突击检查。短短两天后(27日),广州的据点也被清廷一一查处。一批起义分子锒铛入狱,洪全福乔装潜逃。
因告密而胎死腹中——此番起义,竟重蹈了“重阳起义”之覆辙。
告密者是一个周姓男子。这周某先是领香港警察查抄了“和记栈”,又将查抄所得的“谋反”文献誊写了一份,呈给两广总督。起义军恨不能将奸细挫骨扬灰,却不知早在奸细告密前,“曹法洋行”便玩了手“黑吃黑”,为了昧下那笔巨额订金,早就将消息卖给了官府。
后人将这场死于襁褓中的起义,称作“壬寅义举”。这是一场刻意将孙文排除在外的起义,有关首谋者的身份,史书也未有明确记载。起义军计划在起义成功后,迎容老先生归国任临时总统。单就这点,孙文对谢缵泰等人的擅作主张,也难生责备之意。
由于首谋者未明确,这场起义的名称也有数个版本。其中,“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最被世人接受,另外还有强调赞助者的“洪全福?李纪堂举义”(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突出革命派的“谢缵泰广州之役”(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
前有“曹法洋行”告密,后有细作周某提供谋反物证,清军“捷字营”逮捕起义人士十人。经论罪,七人被处以极刑,三人则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其中,一人不待过堂便卒于牢中,一人重金行贿官衙,免于牢狱。
两广总督遣“使节”杨枢赴港,要求香港政府遣返其余乱党。但自事发起,谢缵泰之好友莫里森与坎宁安便不断组织游行活动,向港英当局施压。最终,港督只得以“他国人犯不予关押”为由,将起义分子悉数释放。
时任两广总督德寿为旗人,加之前番险些丧命于史坚如之手,对革命党可谓是深恶痛绝,当即拿出了屡试不爽的“悬赏作战”——活捉匪首洪全福者,赏两万元,封守备(正五品武官)。取其首级者,赏一千元,封千总(正六品武官)。
曾在广州衙门任杂役的张佐庭瞅准了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衙门发了悬赏,却没人见过洪全福容貌。也难怪了,太平天国覆灭后,洪全福便做伙夫,随外国船队走南闯北,如今已是古稀老人。太平天国得势时,他还一度被册封为“瑛王”,被称作“三千岁”。顺道一提,“万岁”自然是“天王”洪秀全。另外,“东王”杨秀清为“九千岁”,以此类推,“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分别为“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以及“北王”韦昌辉。如此可见,“三千岁”在天平政权中的地位。
然而当下距“天京沦陷”已历四十年,太平天国之兴衰也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剿灭太平军的曾国藩与左宗棠早已辞世,“淮军”创立者李鸿章也在平定义和团之后,于1901年辞世。
话归原题,张佐庭吃准清廷官吏未见过洪全福,便在香港杀害了一位名叫吴六的七旬老人,将尸体塞入箱中,运至两广总督府——我已手刃了洪全福。两广总督德寿兑现承诺,当即支付给他赏金一万元。但纸包不住火,事情很快便败露,事实甚是残酷——这位冒牌洪福全,竟是张佐庭之养父。
清廷官员满腹冤屈无处诉。港英当局不明就里,一口咬定其派刺客越境暗杀起义分子。而此时,德寿已被调任为漕运总督(未起程赴任,于翌年病卒),岑春煊续任两广总督。
说起这岑春煊,昔日西太后避难西安时,他是时任陕西巡抚,多少与列强掰过手腕。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效力新政权,致力于南北统一事业,这都是后话。
岑春煊刚上任,便下令处决张佐庭。由于冒牌洪全福的尸骸是经由水师的船舶上岸,岑春煊还不忘罢免了水师提督。港英当局见广东当局诚意如此,也不再作追究。而正牌洪全福趁这当口儿,乔装潜逃新加坡,风声过后重返香港,于1910年病故,也算寿终正寝。
“壬寅义举”失败于1903年1月28日,旧历整好是正月除夕。
同一天,在彼岸的日本国,留学生群体已初成规模,数千人汇聚在年前方才落成于神田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举办“春节团拜”。集会上,学生代表马君武、刘成禺抨击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海外这般肆无忌惮还则罢了,毕竟天高皇帝远。然而就在清廷眼皮子底下的上海租界内,竟也传出了公开反清之声。
由于当时的留学生多出自上海“南洋公学”,时任“中国教育会”(负责废科举后的新教材编写)会长蔡元培为整合这股新兴力量,特成立“爱国学社”,其会旨言明: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显然,蔡元培主张中国切忌照搬当强盛之日本。1903年,“爱国学社”收购《苏报》做主阵地。章士钊、吴敬恒担任主笔,专门刊登章炳麟、雏容等激进分子之文章。
邹容未及弱冠,却已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在此前,他便坚定“排满”。邹容出生四川巴县,1902年留日,曾做出削断留学监官姚甲辫发,公示于宿舍之壮举。
清廷设留学监管一职,为的便是监管留学生。如今,留学监管竟辫发落地,这对留学生们来说是大快人心了。一入夜,宿舍走廊时常会响起幸灾乐祸的“痛哭”声:“呜呼哀哉,吾之辫发,汝何在。”每每悲鸣声起,总会引起一阵哄笑。
要知道,公然成笑柄者并非姚甲这个小吏,而是堂堂清廷之权威。留学生之嘲笑,正是清廷权威日落西山之佐证。虽清廷时日无多已是不争事实,但在留学生群体中仍有奉劝同伴收敛的声音。其中一位留学生代表曾告诫周围:“姚甲咎由自取,诸君哄笑,图一快活便是了。但谨记,此处若是清国,后果又如何?”
此言论受理性者赞同:“甚是,太过招摇,于革命大业有害无益。”
果不其然,邹容作为辫发事件的始作俑者,不久后便被遣返回国。风华正茂的邹容是政论界中的后起之秀。他仰慕谭嗣同之殉国壮举,偶像的遗像片刻不离身。
邹容在留日期间著名文《革命军》,却一直拖到1903年其归国后,才由上海大同书局公开出版。章炳麟阅读后惊叹不已,为之代序后,转载译文于日本《苏报》。《革命军》总字数逾两万,折合当时的印刷用纸,不过四五十页。日文不比中文精练,译文字数超原文三倍有余。文章开头便脍炙人口: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当初在东京,拜读过这第一段话的留学生,无一不咋舌:“威丹兄真乃三国之陈琳再世。”
众所周知,陈琳为建安年间(?-217年)文人,名列“建安七子”,以檄文见长。邹容是受宠若惊:“区区邹某怎敢与三国名家相提并论。”
这倒不是邹容谦逊,只不过据《三国志》所记载,这陈琳起初侍奉袁绍,官渡兵败后,即转仕曹操。所谓“忠臣不事二主”,邹容是真看不上这陈孔璋。
顺道一提,在官渡之役前,陈琳曾代袁绍作檄文,斥骂曹贼“宦官之后”“五毒备至”,又指责其“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滔滔罪行,天理不容。
官渡之役后翼州沦陷,陈琳自以为必死无疑,谁想曹孟德却只是气哼哼地埋怨了一句:“你骂我曹孟德便是了,为何要拖上我祖宗三代?”便不再追责。
章炳麟时常调侃邹容:“威丹兄尽管将清廷骂个狗血喷头。汝不见陈琳骂尽曹孟德祖上三代,却换来高官厚禄?”
“邹某可不愿做满贼灵丹妙药。”陈琳一纸檄文,反倒治好了曹操的头风顽疾。
《革命军》结尾道:
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在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 岁次癸卯三月日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明崇祯帝自缢煤山距今整好二百六十载。
然而当代国学泰斗章炳麟在代序的署名中,却用了另一个时间点——“共和两千七百四十四年余杭(现浙江杭州,章炳麟的故乡)章炳麟序”。
照理说,章炳麟虽反清,却与宣扬“民主共和”的孙文等革命分子不属一路人。他笔下的“共和”,并非革命党口中的新政体。“共和”一词,在国学家眼中可有些年头了。
西周后期,周厉王出奔(逃亡),因后主宣王年幼,周公与召公共同主政。《史记》将周、召共政的这十四年,称作“共和”时期。而据野史记载,厉王出奔后,一名为“和”的共国诸侯被扶持为王,故称“共和”。即便说法众说纷纭,但就周厉王出奔的时期,还是很统一的——春秋一百十九年前的庚申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距今正好两千七百四十四年。
上海租界不受清廷管束,清廷若欲缉捕租界内嫌犯,必要先经“工部局”(租界行政机关)的“照会”。但只要事关政治犯,这“照会”多半要被驳回。
清廷恨不得将章炳麟、邹容二人活剐,奈何租界领事有意袒护,三番五次拒绝“照会”。无可奈何的清廷只得求助于洋人律师,欲起诉那二人“辱骂君主”“教唆行凶”之罪。甚至贿赂主审法官十万两之巨,工部局那头更是用黄金开路打点。
也难怪清廷如此痛下血本,瞧瞧《苏报》上的头条是如何“大不敬”:
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以为不明事理)。
杀满杀满之声,已腾众口。
汝,辫发左衽(衣襟向左)丑类。
杀尽胡儿方罢手。
另外,描述清军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清朝禁本之选节,更是明目张胆地登载在报刊上。在清国,藏有此等禁本便是罪无可赦的极刑。然而在邻邦日本,此禁本却广为流传,甚至公开发行,在留学生群体中更是争相传阅。
颇有争议的是,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抨击镇压太平天国的三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称三人为“奴隶根性”之典型。
租界当局是猜不透清廷的做法——堪堪言论,何以致死?而在清国的大众观念中,“诋毁朝廷”之罪被凌迟处死也不足为奇。如此一来,工部局之态度更是强硬了:
既已知贵国之手段,此番清当局之“照会”,似另有图谋。
“中国教育会”公然在张园与王之春叫板。传闻王这回是真恼了,正在煽动恩寿,企图将反对者一网打尽。
“张园”位于租界内,“中华教育会”常在此处集会演讲。王之春时任江西巡抚,他谏言朝廷“借款予法兰西,借法之兵力,以平匪乱”。此谏言一出,自然在革命派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张园内“倒王”之声不绝于耳。
王之春勃然大怒,要求江苏巡抚恩寿照会上海租界,缉捕“乱党”。照理说,“缉捕乱党”的照会,以往也有过先例。但唯独这回,清廷的态度异常强硬。工部局权衡厉害,还是决定先拿人。于是乎,章炳麟被捕,邹容自首。清廷随之要求引渡罪犯,而工部局却再没有动作。
几番交涉下来,章、邹二人免于被引渡。租界方为顾全清廷颜面,重判两人终身监禁,但后有英吉利公使求情,又分别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与两年,这都是后话。
清廷为取这两人性命,称得上无所不用其极,许诺只要外方引渡此二人,便将目前在押革命分子一律无罪释放,甚至强行撤回已下达的判决,免去二人死罪。这可谓是有损国体的让步了,但领事方仍不为所动。
有趣的是,清廷频频让步,让时任美利坚驻上海总领事的态度有所松动。但他刚向白宫请愿,便当即被调任回国。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维持“治外法权”之强硬态度。
1903年7月中旬,孙文自越南返回日本。当时的日本,汇聚着一批留学生仰慕、清政府憎恨的“反动分子”。开学季在9月。7月和8月,新一批留学生纷纷涌入日本。
在清廷愈发猛烈的攻势之下,同年7月7日上海《苏报》停刊,中国教育会领袖蔡元培赴德避难,会长由黄宗仰接任。然而黄宗仰未坚持多久,也潜逃日本而去。
孙文归日后专程拜访了黄宗仰。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巧合的是,孙文在西医书院的同窗廖翼明赴日经商,与黄宗仰在横滨山下町本牧桥周边,合租了一栋小洋楼。于是乎,廖、黄二人僦居一楼,将二楼让予孙文落脚。
有孙文这顶金色招牌坐镇,这栋小洋楼可谓门庭若市。因反清演讲而“一炮走红”的马君武、刘成禺二人时常登门请教不说,后国民党领袖廖仲恺也曾携妻慕名而来。廖仲恺是旧金山华侨子弟,其妻何香凝当时正就读于“女子美”(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小洋楼时常至夜半三更,仍灯火通明。
这一日,众人谈及前阵子风头正盛的《苏报》事件,孙文当时正赴越南公办,听闻事件始末,分析道:“观此形势,清廷是谋划着趁此机会向租界法庭施压,阻止反清组织‘攻陷’租界。”
黄宗仰也愤慨不已:“清廷也端的是好手段了……不仅害得章炳麟与邹容两位国学泰斗锒铛入狱,就连贫僧这般遵纪守法的出家人,也被逼得退守日本。”
黄宗仰年长孙文一岁,年轻时曾一度皈依佛门,自称乌目山僧。这乌目山,坐落于黄宗仰的家乡江苏常熟。
“未必未必。据线报,清廷是拉下颜面,破天荒地求助于洋律师,一心要取两位大师首级。结果又如何?还不是落得个自掘坟墓的下场?”
众人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1903年1月至7月,也就是孙文赴越公办的半年间,留日学生操办的刊物。其中有湖北籍学生在孙文南下后合力创办之杂志《湖北学生界》,由于刊名过于地域化,后更名作《汉声》。还有浙江籍学生于1903年2月17日创办之报刊《浙江潮》,直隶籍学生于同月创办之报刊《直说》,江苏籍学生于同年4月创办之杂志《江苏》。
黄宗仰对桌面上的刊物如数家珍,感叹道:“真可谓百花缭乱。”创刊热潮时,他身在上海,并未亲身参与。
“这帮江南才子也甚是狂妄,公然整出如此大的阵仗,竟也不与乌目山僧言语一声。”廖翼明调侃。
“乌目山僧”黄宗仰连忙摆手,谦逊道:“江苏有铁云先生,鄙人学识浅薄,如何敢越俎代庖。”
铁云为江苏籍文人刘鹗的别号。同年,其著作《老残游记》方才登刊连载。刘鹗早年便被同乡文人们奉为楷模,他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小说之先驱,后世常将他比喻为中国的二叶亭四迷(日本近代作家)。
孙文将眼前的“新潮”刊物一一翻阅,细细去体会那论述中满溢的激进与愤慨。黄宗仰见孙文沉默,还以为他有所不满,笑道:“毕竟是出自学生之手,热情之余,难免有幼稚之处。”
孙文苦笑摇头道:“非也,论幼稚,我等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反倒是他们的热情,确实令人折服。”
黄宗仰不置可否,换话题道:“逸仙兄此趟越南之行可有收获?下一步如何走,心中可有打算?”
孙文沉吟片刻,徐徐答道:“纵观形势,摆在我等面前的道路不过两条,且都是必经之路,孰先孰后尔。”
“容我猜猜看……梁启超在日本地盘上‘呼风唤雨’。逸仙作为兴中会魁首,怎能任其嚣张若斯?两条道路之一,便是争回地盘吧?”
孙文忍俊不禁:“浩瞬兄只说中一半。你方才仅言道‘日本的地盘’,纠正一下,我孙逸仙之地盘,除日本外,还有夏威夷。”
“如此说来,其中一条道路,便是夺回日本与夏威夷的势力。请教这另一条道路是?”
黄宗仰是聪明人,一点就透。日本方面,留学热潮未退,而留日的清国学生多偏向革命,谅保皇派也兴不起多大风浪。问题出在夏威夷,当年孙文一封引荐信寄予胞兄孙眉等夏威夷同志,愣是将梁启超夸为万众挑一的人中龙凤。此举,倒为梁启超蚕食夏威夷势力扫清了障碍。
孙文也有苦难言,继而补充道:“另一条道路便是培养新兴革命力量。最近,孙某大量参阅了布尔之役的相关资料,发现布尔人民在战争中后期的反抗方式,可为我中华之革命的参考。”
布尔人,乃是荷兰祖籍的南非人。布尔之役随着《弗里尼欣和平条约》的签署,于去年(1902年)方才落下帷幕。布尔方虽战败,但因游击战术而大伤元气的英吉利则恼羞成怒,在战后对布尔民众进行了疯狂的打击报复。现今,英吉利已为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
“怪不得见你最近总是三天两头地就往日野熊蔵少佐那儿跑,敢情是去请教军事学。看来,你还是将日本摆在了第一位。”
孙文苦笑道:“孙某倒想跑一趟夏威夷,奈何囊中羞涩呀,不得不延期再议。”
同年9月26日,孙文凑齐旅费,自横滨赴夏威夷。他7月中旬才抵日,这趟日本之行,待了不到三个月。而就在这短短数十日内,他手把手成立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储备力量的学校。因事出隐秘,这所学校甚至没有名号,地点在青山县,圈内人含糊地唤之为“军事学校”。首届学生不过十四人,且入学者需直接向孙文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学校的执教人员为日野熊蔵少佐、小室健次郎中尉等数名日军军官。他们之所以愿意出山相助,在台湾效忠于孙文的服部登中尉功不可没。服部虽是退伍军人,但显然仍栖身于儿玉源太郎帐下。顺道一提,就对孙政策问题,与伊藤内阁政见相悖的儿玉总督竟然晋升入阁,任陆军大臣。
这一日,服部奉劝孙文道:“孙先生,依在下拙见,您与其把心血投入在这所不成气候的‘军事学校’上,还不如去精心经营现成的夏威夷势力。”
孙文心存感激地拍拍服部的肩膀,笑道:“服部兄谬矣……别看眼下学生只有寥寥十数人,十人中只要有一人成材,就不枉我孙某苦心。只不过,学生中多是心浮气躁之辈,我自然不会抱有太多期盼。”
孙文滞日期间,访遍日本政坛名士。其中,“平民社”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的实践,给孙文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欲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必先贯彻中国民族主义。
他提醒孙文,学宣誓文中“驱除鞑虏”一句,应在清王朝倒塌后即刻删去;参与宣誓者,必须明确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