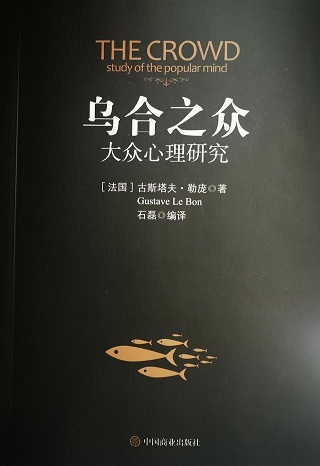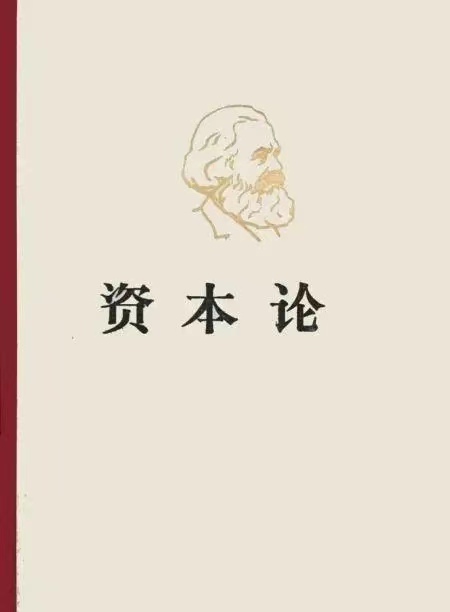孙文辗转于夏威夷、美利坚、欧洲三地期间,日俄战争爆发,一度发展到不可收拾,最终却草草收场。八年前,李鸿章赴俄出席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与俄方缔结联盟密约。密约开篇白纸黑字所写的第一条:
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中国东三省,日政府口中之“满洲”。清王朝自入关后分别在盛京(沈阳)、吉林、黑龙江三地设“将军”一职,总领本地军政。义和团运动初始,三名将军便联名要求俄方让渡“东清铁路”的经营权。俄方自然是一口回绝。
《中俄密约》的俄方签署代表维特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如下一段与陆军大臣克洛巴托金的对话:
这义和团来得恰是时候,我等正为染指满洲的名义发愁。
满洲势必会成为我国的第二个“布哈拉”。
布哈拉汗国位处中东,眼下是沙俄唯一一块殖民地。
义和团的排外举动,让外驻于东清铁路的俄籍员工纷纷逃难至俄领地、租界,乃至朝鲜。1985年,清国正苦于太平之乱,沙俄乘人之危,威逼清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条约将额尔古纳河至黑龙江东岸地域划为俄领,后世将这片区域唤作“江东六十四屯”。
六十四屯的原住清民纷纷西渡黑龙江以避难,然而同年7月15日,俄军封锁渡口,对无路可逃的民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潜伏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日本间谍石光真清,亲身经历了这起惨案。据其所言,遇害民众逾三千之众,其中包括老幼妇孺。
沙俄一时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1902年2月,俄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将主要罪行归咎于阿姆鲁地区司令戈里普斯基中将,却草草以免除其以往功勋而了事。具体负责实施屠杀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部队长被判处三个月囚禁,并免职。至于其余战犯,再严厉也不过三个月的囚禁。
义和团运动前夕,沙俄驻扎在清国东三省的东清铁路警备队就多达一万一千人。然而不过数月光景,其驻扎部队竟转眼间暴涨至二十万之众。
沙俄政府对外声称,此次增兵“满洲”只是事急从权,局势一旦得缓,则即刻撤兵。结果不言自明,直到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俄方也丝毫没有要撤兵的意思。
维特伯爵自知本国得寸进尺在先,清廷失约也是情理之中,所以也不敢觍着脸要求清国出兵支援了。
沙俄背信弃义,清国上下卷起一阵反俄浪潮。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组织“拒俄义勇队”。这也便是先前提到的“爱国学社”之前身。
然后,随着1902年1月日英结盟,俄方迫于压力,只得签署《满洲归还条约》(清称《交收东三省条约》)。此次条约的签署,也令清国东三省结束了持续两百余年的将军管辖,正式与山海关以西一般,被列入行省。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被日本统称为“满洲”。中国人也偶尔仿此称呼,但更普遍地称呼其为“东三省”。
实际上,“满洲”二字绝非地名,而是关外旗人之族名。女真人早在12世纪曾终结汉人王朝北宋,占据宋国北方半壁,建国“大金”。这还不算完,金军甚至生擒北宋徽、钦二帝与数千廷臣至北地,施以凌虐。因此,后世汉人视“金”乃至女真人为不共戴天之敌。
努尔哈赤起兵时,宣称本族既非女真,亦非大金后裔,还称自己是“文殊菩萨之弟子”。其部族信奉“曼殊室利大教王”,故取名为“满洲”。然而,东三省的原住民中汉族占据大半,接下来才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所以“满洲”这个地名还是颇有争议的。
俄方承诺分三个六月,将“满洲”驻军撤离。首先是在六个月内调回奉天西南部驻军,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再分批撤离奉天剩余驻军与吉林驻军。其余驻军,在最后的六个月内悉数撤回。
俄方在勉强履行第一次撤兵后,便再无动作,对外声称是正在检讨前番撤兵的结果,很显然是有意拖延。然而,单是拖延还则罢了,俄方非但不撤兵,还有意无意地将剩余兵力集中在了铁道沿线。
日本媒体尤为关注“满洲”局势,尤其是沙俄在清国的举动几乎关乎本国国运,报道称俄方之行为是在“公然挑衅日英同盟”。
俄军阿列克谢耶夫总督高调与“满洲”各部队辞行,做足了撤兵的表面工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反之,仍继续向“满洲”输送兵力,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在奉天举行了一次军演。据日媒的解读,俄方此次武力示威,是意欲胁迫清廷,以促成某项不可告人的协议。
日本的新闻工作者也是“神通广大”,竟事先便挖出了清俄之间的“约法七章”,其中第一条也在意料之中——归还东三省,永世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
除此之外的数条,更是让沙俄殖民清国之野心昭然若揭:
东三省只准营口通商,清方不得为他国开设通商口岸。
清东三省之行政、军事,不得受他国干涉。
营口之关税长官,永世只得认命俄方人员担任……
七条密约之中,清方拒绝任一条,则撤兵之事免谈。
此密约一经曝光,立刻在留日学生中激起轩然大波。学生们群情激奋,聚集神田锦辉馆,开展誓师大会,组建“拒俄义勇军”。在义勇军请愿书上署名者达三百余人,愿支援后勤军队后勤者逾五十余人。清驻日公使蔡钧见状不妙,连忙发电至两江总督:留学生结义勇军,计有两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各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日本有句古话“敌在本能寺”。蔡均猜得不错,学生们只是打着反俄的旗号,行的却是革命之事。他以“有碍国际和平”为由,要求日警方对此新兴组织进行取缔。
日警方卖了清公使一个面子,对义勇军发出警告。义勇军“老老实实”地就地解散,却又重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对外声称是体育同好组织。好笑的是,摘下了“拒俄”的旗号,组织的革命气息不减反增。
“拒俄义勇军”重组后的第二个月,孙文自越南返日。此时,日本的革命氛围颇为乐观,尤其是广东籍为主的唐人也呈现出团结之势。这对孙文来说,无异于一针强心剂。
犹记得,牺牲于自立军之乱的志士唐才常曾有诗云“枉说长沙是萨摩”。他将故乡湖南长沙比喻为日本之萨摩——萨摩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发源地,而我长沙亦是中国革命之根据地。
唐才常做此佳句时,心中定会联想到自己亦兄亦友的同乡前辈——“去留肝胆两昆仑”之戊戌志士谭嗣同。
湖南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海国图志》作者魏源、“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以及后世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说此地简直是革命者之摇篮亦不为过。当然,提起湖南籍豪杰,自然也漏不得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位晚清名臣。
“拒俄义勇军”分为甲、乙、丙三区队,各区队再细分为四个小分队。区队队长皆由留日见习士官担任。这支“学生军”的名单,至今仍有史可考。乙区队第三分队的名单中可以看见“黄轸”这个名字。这黄轸便是革命志士黄兴之化名。黄兴出生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是相当于孙文左膀右臂一般的人物。他毕业于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作为湖北公派生赴日留学。当时,他已经年近而立,体格也壮硕,在一众弱冠年华的留学生中显得尤为扎眼。
众留学生身处安全的国外,却有恃无恐地对祖国革命纸上谈兵。黄兴对此等行为很是不齿,便在圈子里发起“归乡实践运动”。他本身也于1903年6月4日赴革命前线上海,亲身参与革命宣传、武装起义,甚至暗杀行动。黄兴前脚刚离开东京,孙文后脚便自越南返日,两人失之交臂。
其后,黄兴与“军国民教育会”同僚——直隶人氏张继一同返回故乡长沙,出任“明德学堂”的教员。他所发起的“归乡实践活动”很见成效,陈天华、杨守仁、刘揆一、姚宏业等湖南籍留学生陆陆续续聚集长沙。宋教仁、柳杨谷、周震麟等非留学群体的湖南人也深受感召,前来助阵。
时任《苏报》主笔章士钊,也频繁奔走于上海与故乡长沙之间。众人在长沙碰头后,组建“华兴会”,会长自然由黄兴担任,但组建始末已无史可考,毕竟是见不得光的地下组织。
“华兴会”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预定在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十日,也就是西太后慈禧的寿诞之日。每年的这一天,长沙“皇殿”会举办贺寿典礼,湖南各地大小官员必须到场。只要在“皇殿”中埋下炸药,一声爆炸,便可将湖南官员一举消灭。届时,长沙就是起义军的囊中之物。
起义军纠集了众多长沙武备学堂(士官学校)的学生,并与当地会党“哥老会”取得了联系。因担心在校学生与市井侠客之间会心生间隙,还特意为二者新建了一个临时组织,名为“同仇会”。黄兴一身绿林气质,处事豪爽,是与哥老会那一帮市井之徒打交道的不二人选。
长沙西北十五里,海潭矿山的某个矿坑内,黄兴与哥老会领袖——“昆仑山忠义堂”之“大龙头”马福益会晤。两人彻夜不眠,把酒言欢。喝到兴头上,黄兴还赋诗一首,赠予马龙头。
有幸见证此次结盟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生出一种感觉——在座的两人,究竟谁才是哥老会的“大龙头”?
也是,就黄兴这一身江湖气,哪像是个留过洋的学生?马福益自称坐拥属下十万,黄兴与他侃侃而谈,竟不弱半点儿风头。两人相逢恨晚,其后,也时常相聚,重缅结盟之谊。
结盟的酒席上,马福益扼腕自责道:“说来,也不怕克强先生你笑话……若没有结识唐才常老弟,我老妈混了大半辈子,竟还不知道这天下是清廷从我汉人这儿抢去的!四年前,我眼睁睁地瞅着唐老弟让清廷害了性命。如今若再让你有半分闪失,叫我如何面对关二爷。”
这一席话让黄兴颇感动,他同样愤慨道:“唉,福一(马福益本名)是只知其一啊……当年自立军之所以兵败,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所托非人!那康有为揣着革命资金,在美利坚、加拿大逍遥快活,约好的军资粮草却是一拖再拖……但如今不同了,我起义军会力保福一与会里的弟兄无虞。”
“这就不劳克强先生操心了,我手底下那十万弟兄可不是什么善茬儿。”
黄兴字克强,别名黄轸。他参与革命活动时,惯用别名示人,如他参加“拒俄义勇军”时用的就是黄轸。然而,此次与哥老会结盟,他堂堂正正地用了本名黄兴。
黄兴归乡后,便典当了年收三百石的祖产农田,悉数捐予革命事业。之后回到明德学堂,以教授美术与博物为生计。
归国后,他用了一年半的光景酝酿此次起义。期间,他创立矿务公司“华兴矿业”,以暗中安置革命军。至于为何偏偏要选择矿务公司——矿务公司高层勘察矿坑,谁人会生疑?豪迈的矿工汉子,收工后躲在矿坑里喝酒划拳,也是合情合理。
都说湖南人是典型的“一头热”。对革命“一头热”的,是他们湖南的革命家;对镇压革命“一头热”的,是湖南籍官员。偏激地反对革命的学者与当权者,也是湖南出身的居多。
当年,梁启超受邀赴长沙“时务学堂”施教,谁知刚迈入学堂门槛,便让本地学者叶德辉与王先谦给打了出来。保皇的革命派尚且如此,革命派会受到何等待遇也可想而知了。
告密,又是万恶的告密!
先前提到的叶德辉与王先谦二人,皆为进士出身,乃是当世闻名的保守派学者。其中,年近花甲的王先谦曾主张变法派康有为其罪当诛。而叶德辉虽及第进士,却无心仕途,作为长沙首屈的豪绅,他在湖南文教界颇具号召力。
两人作为学者,不满足于一心搞学问,对政治却尤为上心。两人为对付宿敌革命派,甚至还培养起了职业间谍,安插在敌营之中。两人将手下间谍所提供的情报告知湖南巡抚,直接导致华兴会的长沙起义计划胎死腹中。
湘潭的革命据点最先暴露,此地距离革命中心长沙有四十余里。当地官府立刻罗列出乱党名单,眼瞅着便要通知长沙方加以逮捕。要知道,华兴会与会党的高层此时都聚集在长沙。所幸,湘潭会党中有一名外号“飞毛腿”的同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星月兼程,凭双脚赶赴长沙告急。
这是一场电讯与脚力的赛跑。按理说,必然是以电讯完胜而告终。然而,湘潭此地设备落后,必须将汉字内容译作“电码”,才能发送。例如,“逮捕某某”的电码为“49?2198”。这可不是暗号,而是国际通用的“电码文字”。但凡是大都市,都不缺从事“电码”翻译的专家,但可惜那个时代的湘潭可连都市都算不上。
千钧一发,“飞毛腿”险胜电讯。长沙华兴会得到消息,即刻原地解散。“万一”情况下的藏身处,事先便已安排妥当。黄兴藏身于教堂之中,伺机逃离长沙。其余同志多是长沙人,对本地熟门熟路,更是不愁会让清廷揪出来。
黄兴之前在上海时,便时常造访基督教堂。他与孙文素未谋面,却一早便听闻对方是个基督教徒。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信仰基督,黄兴觉得有必要对这舶来宗教稍作了解。
《辛丑条约》第十条有明文规定:清方应严禁任何排外、反天主教运动。一旦发现,应立即逮捕并处决牵涉人员。
没错,是“死罪”。公开反感外国,排斥舶来宗教,便要掉脑袋。此法令一出,各地官员都惧“基督教”三个字如鬼神,避之不及。
如此看来,黄兴还真是挑对了避难所。但他之所以藏身于教堂,还是有自己的“私心”……要知道,他们这帮革命分子整日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总得找些心灵依托,宗教便是最方便的选择。
于是乎,长沙“华兴会”一众安全转移上海,暂时落脚于租界中的“启华译书局”。这家机构为湖南籍革命派的上海据点,其主事人正是先前提到的《苏报》主笔章士钊。众人满心以为逃过一劫。谁承想,这才没几天,租界巡捕便撞开译书局大门,带走了章士钊、黄兴等十人。
这可真是无妄之灾了……就在前不久,无党派爱国志士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租界巡捕逮捕。章士钊看在湖南同乡的情分上,前往探监。警方单纯为深究暗杀案件的始末,于是到探监人住处搜索情报。谁想情报没搜出来,反倒搜出了若干军火与假币,便顺势将在住人员一并逮捕了去。
被带走的十人中,只有黄兴的友人郭人漳一人未用化名。这郭人漳乃是清廷大员,官至山西道台。他今早途经上海时,凑巧听闻友人黄兴在租界,便前来造访,哪承想就碰上了这样的倒霉事。
郭人漳刚入狱,便至信上海道员袁树助求援。袁树助得信,连忙亲自赶赴英领事馆要求放人。清朝的行政区划按级别排列,分别为“省、道、州、府、县”。举例。台湾原为“台湾道”,升格后才叫“台湾省”,一“道”之长,便是道员:这位上海道员袁树助,其后又被提拔为山东巡抚,最后爬上两广总督的位置,是叱咤清末政坛的大人物。
租界巡捕得知自己摊上大事了,哪还敢怠慢,毕恭毕敬地将郭人漳请出了牢房。郭人漳也不追究,只是不紧不慢地道,我还有两名随从。
于是乎,黄兴与张继这两名“随从”也于四日后重获自由。郭人漳打通了关系,其余被捕人员也相继被释放。至于行刺未遂者万福华,他是个我行我素的无党派人士,不愿受革命派恩惠,仍被关押狱中。
远在日本的同志闻知黄兴等人被捕,连忙差人为其雇用律师。已然出狱的黄兴建议道:“这笔打官司的资金,不如使在万福华身上如何?他确实是一条好汉。”
众人一致赞同,于是,在其后的“公审法庭”上(中外法官共同裁决),万福华仅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纸包不住火,黄兴以化名潜藏租界内的消息,终究还是传到了清廷的耳朵里。清廷要求租界工部局立刻移交乱党。上海也待不得了,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四人仓皇逃往日本。这也是宋教仁首次赴日。
赴日的客轮中,四人检讨了此次起义失败的原因。罪魁祸首自不必说,无非是叶德辉、王先谦那两个腐儒。陈天华反省道:“果然,会党之中三教九流,玉石混淆,不得不防呀。”
黄兴却不以为然:“会党虽龙蛇混杂,却贵在一呼百应,且市井多豪杰……我与那‘大龙头’马福益有过接触,他确实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
张继换了个话题,调侃黄兴道:“话说回来了,克强今年的诞辰宴可泡了汤,要不要明年办上两回?”
10月24日,长沙官衙一收到密报,便立即派兵查封了黄兴的宅邸。次日便是农历九月十六日,黄兴的三十岁诞辰。当时,他正藏身于教堂,命悬一线,哪还有心思为自己过生日?
黄兴干笑了两声,心中暗忖:“不知何时能有缘与兴中会孙会长相见……他亲身领导过广州、惠州两次革命,可谓经验丰富了。”
此时,孙文正以纽约“一碗面”为据点,奔走于波士顿、华盛顿等美国东部城市,拉拢各地华侨。
黄兴早先不愿邀请同乡好友蔡锷入伙,仅因对方眼瞅着便要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稍有不慎,就是前程尽毁。这蔡锷为士官学校第三届毕业学生,前两届毕业留学生合计不过六十人,第三届单届便猛增至九十五人。
越来越多的留学士官自愿在毕业后投身革命队伍,这也是孙文长久以来致力的局面。然而在黄兴看来,玉石混淆的会党之重要性,可比肩于革命军队。要建国立制,接地气的民间豪杰也是不可或缺的。
直隶出身的张继总结得妙:“敢情,这好人、恶人都让你们湖南人给占了。”
反观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长沙起义毁于两名湖南进士之手,湖南好汉万福华刺杀湖南籍巡抚王之春……细想来,还真是湖南同乡在窝里斗。
宋教仁摇头惋惜道:“容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我反倒挺庆幸事情败露得早,若是临了才败露,我们的损失可远不止牺牲两名同志那般简单了……当然了,萧桂生与尤游胜两名同志的牺牲,还是很令人惋惜的。”
消息败露于10月23日,距11月16日起义,隔了大约二十余天。只有萧桂生与尤游胜两人因藏身不力,被捕牺牲。
孙文远在美利坚也不忘通过日本的同志掌握各地革命派动向。早先在夏威夷时,他便闻知黄兴组建了个闽南籍革命组织,取名“华兴会”。赴英前夕,又有线报传华兴会骨干暗中集合于长沙。
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浙江籍革命组织落“光复会”成立,章炳麟、陶成章两人分别出任正、副会长。紧接着,是长沙起义败露,会长黄兴逃亡日本。
1905年,孙文远渡欧洲,先后造访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游说各国留学生加入革命组织。这时,清国那边传来了黄兴暗中回国的消息。
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不甘落败,重整队伍,密谋一场新的武装起义。华兴会未参与其中,但黄兴割舍不下当日洞中誓言,不顾同志反对,决定只身返回湖南洪江,为起义军送去军火。
他在汉阳购置了军火,打算走水路运往洪江。谁知船只刚出码头,便让“麓卡”(海关机构)给拦了下来,说是要例行盘查。情急之下,黄兴只得将数名差人推入河中,强行冲过关卡。然而还未等到军火送达,起义便被镇压,马福益被捕身死。黄兴得了兵败的确切消息,丢下军火,又连夜潜逃回了日本。
上述事件发生在1905年二三月间。期间,新加坡华侨许雪秋也于广东潮州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但同样以失败而告终。许雪秋也是嚣张,仗着自己与潮州道员相熟,竟独闯官府为自己申冤,甚至还要求官府释放被捕的同伴。那世道,人脉高过天,竟还真如他所愿,除去已被处决的同志,其余被捕同志被先后无罪释放。许雪秋生怕官府反悔,连夜逃回新加坡,等待东山再起之日。
与此同时,日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旅顺攻防战告一段落,在奉天的最后决战蓄势待发。上海租界那头,同年4月3日,邹容猝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