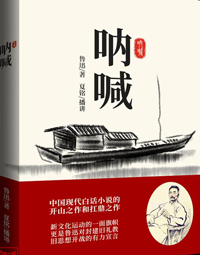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辛丑条约》落地,国门洞开,清廷派遣五名“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出使海外。五名大臣皆为二品以上官职,此行名为“考察外国政治”,实则是行屈服示弱之事。
1905年9月24日,距中国同盟会成立不过月余光景,五位大臣计划乘坐火车至天津,从天津登船,开始此次“考察”之旅。
当时,北京火车站位于正阳门(俗称前门)附近,按理说,必定是戒备森严之地,谁承想车轮还未转动,一声巨响,车厢里便发生了爆炸。“考察团”中四个随从当场被炸死,两名大臣负伤。
两个月后,作案团伙被缉拿归案。清当局这才知晓,主谋便是案发当日一同被炸死在车厢之中的吴樾。
要说这吴樾,他最初是站在梁启超的“立宪”阵营,后转而仰慕赵吉、杨守仁等革命志士,加入了革命派。他很清楚,中国若实行“立宪制度”,无异于是在为清廷续命。
吴樾出生于安徽桐城,早先是保皇派专刊《清议报》的忠实读者,后偶然拜读邹容的《革命军》,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并主笔《直隶白话报》。刺杀“出洋五大臣”,是为了掐灭任何立宪的可能性。
五大臣出行各带有数个随从,随从各不相识。吴樾换上了提前准备的官帽与布鞋。按清官制,有品级之官员,帽顶上会镶有“顶戴”。二品以上“顶戴”为红珊瑚,以下为蓝宝石、青水晶、砗磲、素金,以此类推。有官帽却无“顶戴”,外加一双布鞋,为标准的“皂隶”(随从)打扮。吴樾换上这身行头,趁乱混入车厢之中。
吴樾藏于怀中的炸弹,是他照着书籍,一步步手工制作而成,自然不配备有定时装置那样精密的玩意儿。那年代,火车在出发前,要进行车厢与车头的连接,连接瞬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会让车厢倒退数米;乘客若未及时入座,会被掀翻在地。
说来,也是造化弄人。吴樾进入车厢后,坐在随从的座位上,离五大臣还有些距离。他刚起身,正欲将炸弹掷向五大臣,谁承想刚巧碰上车厢连接,冲击力直接让吴樾跌倒在地,引爆了怀中的炸弹……
吴樾与身旁的四名随从当场死亡,五大臣受了些皮外伤,车厢之外,前来话别的大臣伍廷芳被震伤了耳朵。因此事,清廷不得不将“考察”推迟了三个月,但终究还是顺利将五大臣送出了国。翌年8月,五大臣回国,主张清国最快五年,最迟十年间,必须实行立宪政体。
吴樾自知凶多吉少,留下了遗言。在遗言中,他认为当今并非革命时代,而是“暗杀时代”,而自己愿效仿荆轲之举。都提到刺客鼻祖“荆轲”了,由此可见,吴樾不愿为自己开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此举为暴恐行动:
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
革命派与此次暗杀无丝毫瓜葛。孙文为吴樾的牺牲仰天长叹:取一名清朝巡抚之性命,则要牺牲一名同志为代价。然一同志死,则革命折损一将,一巡抚死,却有千万巡抚代之。我等同志之性命,绝不可如此贱卖。
所谓的“两会一心,其利断金”,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场面话罢了。黄兴尽力从中撮合,好歹让湖南(华兴会)、广东(兴中会)联盟成为现实。然而刘揆一一句反对,便将华兴会部分派系独立了出去。
至于浙江系组织“光复会”,那是革命组织里的“独行客”,估计也是会长章炳麟那独来独往的个性使然吧,孙文根本无从下手。
最负盛名的革命女志士,浙江绍兴出身的秋瑾,便是“光复会”一员。那年月,女学生本来就是稀罕货,女留学生更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然而秋瑾却毅然抛夫弃子,赴日留学。“孙黄结盟”时,部分光复会成员“跳槽”至同盟会,秋瑾便是其中之一,其后还被推举为浙江主盟人。
“管束令”事件中,秋瑾也响应号召愤然退学回国。骚乱平息后,归国的学生陆续返校,但同时也有部分学生不愿再寄人篱下,秋瑾也在其中。
其后,秋瑾与一众不愿返日的同志合作,于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但不久后便与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创办的“大通体育学堂”合并。“大通体育学堂”的前身是一所坐落于绍兴的军事学院,专为革命输送战士。后为混淆视听,才摇身一变,成为一所“体育学堂”。
反观迄今为止的数次武装起义,领导者总是寄希望于“星火燎原”,徐锡麟对此无法苟同。在他来看,分散革命力量,无异于自寻死路。
徐锡麟不同于其他留学生,他可是正儿八经朝廷钦点的举人,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是他的表叔。在俞廉三的引荐下,徐锡麟从安徽巡抚恩铭那儿捞了个“巡警学堂”堂长的缺。然而,徐锡麟放着大好前途不要,竟密谋在毕业之日发动起义,还想杀几个地方大员来祭旗。
起义前线暂定在安徽省会安庆与浙江绍兴两处。徐锡麟并非同盟会中人。也就是说,这次起义同样与革命派无关,论性质,倒颇像是“吴樾爆炸案”那样的独立行动。
有一次,安徽巡抚恩铭将徐锡麟传来,交给其一份名单:“革命党近来会有大动作,就怕这次会冲着我等朝廷命官而来……这是从牢里的叛贼嘴里抠出来的革命党名单,本官命你速速将名单上的人捉拿归案!”
名单上皆是化名,徐锡麟在其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化名,他坐不住了——照这个势头,官府迟早会查到自己头上,时不我待……说来,他之所以不愿与孙文为伍,也恰恰是因为看不惯其不紧不慢的作风。
7月6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观礼台上,徐锡麟着警服,穿长靴,向巡抚恭敬地行了个军礼,取出毕业学生名单,朝台下说出了行动开始的暗号:“今日,革命党将生事端。”
潜伏在台下的同志陈伯平得到暗号,当即朝观礼台上投掷了一枚炸弹……说来也是命,这颗炸弹哑了火。徐锡麟当机立断道:“大师(巡抚尊称),且让属下取下这乱党首级,呈献于你。”
“何方贼人!”
恩铭还在云里雾里,只见徐锡麟弯下腰,抽出藏于长靴中的手枪,对准身旁的上司扣动了扳机……
收拾了恩铭,徐锡麟将目标转向台下的官员,然而他“怯远”,用现在话讲就是高度近视,一连几发打偏,台下的官员们早就逃得不见了人影。
徐锡麟这些年来没少抓对学生的革命教育,在此危急时刻,他满心以为在场的两百名毕业生,至少有半成会随自己倒戈,谁料到这枪声一响,大部分学生逃得比官员还慌张,仅剩下三十余人。
徐锡麟将宝押在这帮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军”身上,但他忽略了一点——这支新兴势力根本就得不到清廷的信任,身上甚至没有一支配枪。徐锡麟率这三十余人的起义队伍突破重围,一路杀进军械库,却发现弹药库的铁门紧锁,一时间打开不得。
所幸,西侧的仓库未上锁,里头有五门火炮。陈伯平正欲准备炮击,徐锡麟制止了他——如今大势已去,无谓挣扎,只会波及无辜群众。既然恩铭已伏诛,夙愿已了,愿玉石俱焚。
陈伯平不愿坐以待毙,出击迎敌,遂战死。徐锡麟则只身静坐于军火库中,听天由命。毕业典礼始于早上八点,起义军于正午时分闯入军火库,负隅顽抗至下午四点。
徐锡麟不甘,不甘就这样兵败身死,更是不甘只有三十名学生愿意追随自己。这时,有左右建议引爆军火库,拉外头的清兵陪葬。徐锡麟摇头道:“取巡抚一人性命足矣,切莫再同胞相残。”
包围库房的“同胞”也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几百人的队伍,愣是没人愿意第一个突进。上头只得给徐锡麟的脑袋悬赏,赏钱从三千、五千、七千,最后跳到天价一万,才见底下人有所动作。
恩铭中弹后,且一息尚存。布政使兼任代理巡抚冯煦假传恩铭遗言:行刺本官者,仅徐锡麟一人,与他人无尤。
显然,安徽当局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让参与起义的三十名学生逃过一劫。事后统计,共有三名清兵和一名学生死于此次武装冲突。两江总督端方闻知此事,即刻下令处死乱党。
被捕的徐锡麟自称是革命党领袖,当被问及此次起义是否与孙文有关时,他傲然否认——孙文“鲰鱼”(杂鱼),哗众取宠之辈,怎能与我徐某人相提并论!
按原计划,此番起义的地点有安庆、绍兴两处。如今,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已然破产,而秋瑾领导的绍兴起义尚未有确切消息。徐锡麟在临死前,定然是做梦也盼着绍兴方面大捷。
然而事与愿违,绍兴起义一拖再拖。先前,安徽巡抚恩铭因私事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推迟了两日,绍兴方面起义也不得不随之延期。终于盼到典礼举行,徐锡麟却连一日都未撑过,便被捕身死。在绍兴方面,徐锡麟名下的“大通体育学堂”自然随之被列入重点监视名单。
秋瑾危矣!
周围人苦劝秋瑾尽早避难。不用旁人提醒,秋瑾又如何不晓得自己的处境呢?然而,她已然萌生死志。
提起秋瑾,她爱好穿男靴,这件事最为世人津津乐道,但谁又明白其中辛苦……秋瑾幼时同其他清朝女性一样,被迫缠足。几年缠足下来,她的脚趾早已扭曲变得畸形,只有大拇趾幸存。所以,她不得不在长靴中塞入一块填充物,骑马、练剑更是奢望。秋瑾有诗云:
放足湔除千载毒,热心唤起百花魂。
7月14日,也就是徐锡麟被处死的一周后(也有说法,是处刑翌日),绍兴“大通体育学堂”被清军包围。秋瑾对此也早有觉悟,所幸时值暑假,留校学生不多。她不愿连累学生,领他们从后门撤离。临别时,学生们苦劝秋瑾:“师母何不一同逃难?”
秋瑾欣慰一笑,摇头道:“快跑吧,就凭师母这双脚,定会成为你们的累赘。”
其实,昨晚便有同志王金发造访,说是大势已去,劝秋瑾尽早撤离。秋瑾在那时,已毅然拒绝。
就在数日前,她专程重返湖南湘潭夫家,见了十一岁的儿子沅德与七岁的女儿灿芝最后一面,可惜前夫王廷钧赴京公干,未能相见。但见到自己的两个孩子暖衣饱食,她在这世间已了无牵挂,大可就义而去。
“大通体育学堂”受困当日,秋瑾被捕,被关押在卧龙山女子监狱。与徐锡麟一样,翌日一早,便被处刑于轩亭口。
绍兴之所以败露得这般快,皆因本地乡绅胡道南告发。绍兴知府贵福接到告发后,曾亲赴杭州,请示浙江巡抚张曾扬。张曾扬采纳了幕僚与乡绅之建议,命贵福即刻将主犯秋瑾逮捕处死。
时任浙江道员的陈翼栋得知绍兴事件始末,严厉训斥地方官府处置有欠考虑——安庆徐锡麟谋杀巡抚恩铭,并重伤一名巡捕,且强闯军火库与官兵对峙,其罪自然当诛。然而,绍兴秋瑾无犯罪事实不说,还提前遣散学生,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即便从她身上搜出一把手枪,却一弹未发,再如何也罪不至死。
任凭你如何严刑拷问,秋瑾就是“百问不答”。按照大清律例,无人犯供述则不可处刑,知府贵福无可奈何下,命幕僚伪造了一份供词,其大致内容如下:我持枪行凶,我宣传革命言论,造反日记也是出自我之手……万般罪责在我一人,与革命党无关,莫要再逼问我革命党之事。
审讯人员攥住秋瑾的手指,逼其在自供书上画了押。秋瑾自知难逃一死,要来纸笔,留下七字遗言——秋雨秋风愁煞人。
赴死前夕,秋瑾向掌刑的知县提出了三个请求:其一,请作书别亲朋;其二,行刑时不得脱衣带;其三,行刑后不得枭首示众。
掌刑知县心怀恻隐,准许了后两个请求。至于第一个请求,处刑在即,是当真没时间兑现了。
秋瑾枉死,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震动。“激进的女诗人”“才貌双全的女革命家”这两个头衔,足以为她争得世间同情:按清律,女犯当以用绞刑处决,为何偏偏秋瑾一人遭枭首之刑?秋瑾未伤得一人性命,且未留下一字供词。现草率施以处决,视清律为何物?为何逮捕翌日便处刑?莫不是朝廷做贼心虚?
也应了那句“善恶到头终有报”——直接导致秋瑾被捕的元凶胡道南死于义士枪下,负责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愧疚自杀,就连那围攻大通体育学堂的巡防营统领李益智,也被活活烧死在广州大沙头的画舫之中。
另外,构陷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后申请调任安徽省宁国府,却被当地百姓拒之门外,正如他在自传的那句话——遂不知何处以终。
浙江省巡抚张曾扬不堪浙江省百万群众口诛笔伐,于同年9月5日申请调任江苏。然苏沪民众亦视他为仇寇,以至于赴任不过两个月,他不得不主动要求“左迁”至山西。张曾扬在山西担任过两年巡抚,满以为在自己的老地盘上,便可以相安无事,哪承想山西民众也丝毫不卖自己面子。最终,张曾扬走投无路,只得辞官回乡。他在自传中描写过这段经历——国人责骂之声难平,忧惧成疾,辞官回籍。
朝廷的人事调配,受民间舆论左右到这般地步,倒是清朝入主中原以来的头一遭。别的先不说,“舆论”这种新玩意儿,本身便为专制政体所不容。由此也可见,清朝之体制,今时今日已然积弱不堪。
当年叱咤中原的清朝,如今也落得惧怕“众怒”。秋瑾赴死后,其结拜姐妹徐自华、吴芝瑛千里迢迢赶来,兑现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誓约,将秋瑾的遗体安葬于西湖畔。
据清律,谋反者之尸骸不得下葬,应受“弃市”之刑。清廷御史常徽上疏,奏请朝廷夷平秋瑾坟墓。然而,如今的清廷哪还敢再犯众怒,当即驳了折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区区一个叛贼的坟墓也不敢碰,堂堂清王朝真是晚景凄凉。下葬当日,徐自华还在坟前吟诵了已故姐妹赠予自己的诗作:
莽莽河山破碎时,天涯回首岂堪思。
填胸万斛汪洋泪,不到伤心总不垂。
秋瑾笔下的“伤心”,便是赴死之意……只有在赴死之日,才有资格垂下那“填胸万斛”的“汪洋泪”。
秋瑾牺牲当日,远在彼岸的东京,保皇会的新载体“政闻社”于神田区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犬养毅、尾崎行雄等一众日本政治家前来捧场。梁启超在会上发言道:“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亦欢喜踊跃。”
梁启超话音刚落,同盟会的张继率会中四百余人闯入会场(政闻社在场成员才二十余人)。张继劈头便质问在场的犬养毅:“晚生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犬养先生……犬养先生前日在早稻田演讲,明言现今中国正是革命时机,而今日却前来出席反革命组织之集会,这又是何意?”
犬养毅没有回避,登上讲台直接回应道:“我能有何意?你支那是革命还是立宪,与我有何相干?”
如今,清廷将“立宪”立为国策,但康、梁二人仍是罪无可赦的朝廷钦犯。要知道,即便撇去政治立场不谈,这师徒俩当年可是密谋要暗杀西太后的主。
这不,清廷查到这新兴政治组织“政闻社”与康、梁两人关系匪浅,立刻要严加取缔。听说,这还是袁世凯告的状。好端端的政治组织开张没几日,便被“贬”为见不得光的地下组织。这让康、梁阵营元气大伤。
然而,革命派也没闲心瞧对手的笑话……清廷捎带着把同盟会主刊《民报》也给取缔了。先前也有提及,《民报》之前身为创刊于日本东京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办人宋教仁邀请出狱后的章炳麟(因《苏报》事件入租界监狱)赴日担任报刊主笔。
章炳麟乃是当代国学泰斗,文笔自然深奥晦涩。孙文却希望机关报能“亲民”,也就是简明易懂。然而孙文几次提醒,章炳麟却只当耳旁风;孙文恼了,明言若机关报再如此下去,别怪孙某分道扬镳。
恰巧在同时期,江西文人汤增璧之论作《革命之心理》被推到风口浪尖。在其影响下,同盟会还邀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衫荣等日本共产主义学者,举办了一场“社会主义讲习会”。
然而该论作中有少量赞美暴恐、鼓励暗杀之言辞,并被引用进《民报》。当时外交家唐绍仪在赴美途中停靠日本时,还专程拜访报社,指出报刊中数点不妥之处,加以提醒。
可惜了,报社还未来得及做出调整,清廷便要求日政府驱逐孙文出境。日政府不愿意得罪邻国下一任首相或者总理的最有力候选人,但眼下还是清朝,有些面子还是不得不卖的。伊藤博文为自己的弟子——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出谋划策道:“孙文对我政府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良驹。此事,若由我政府方出面,不免要顾首失尾……不妨委托黑龙会去办。”
“委托黑龙会”,也就等于全权由内田良平做主了。
日方向清廷许诺,会在约定时日让孙文离开日本,但在那之前日方会继续礼遇孙文。此承诺一下,孙文离日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作为对孙文的补偿,内山打算在饯礼上下足功夫:“现今,同盟会之中,孙文与章炳麟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他现在最急需的不是人才,也不是支持,而是钱!”
正在日本政府一筹莫展之时,日本股票大亨铃木久五郎挺身而出,自愿承担部分饯礼。
村松梢风著作《近世名胜负物语》中的角色“铃久”,便是以铃木久五郎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中,铃久仰慕孙文,甚至将女儿取名为“文子”,后其女儿文子在宝冢舞台上大放异彩。
内田良平的情报网广布世界,堪称日本第一“地狱耳”(同中国的“顺风耳”)。他知道,由于夏威夷近期政策巨变,加之一些许摆不上台面的原因,孙文胞兄孙眉在毛伊岛的牧场与农田被尽数充公。他还知道,孙氏一族已陆续撤出夏威夷,只剩下数人一时脱身不得,其中就包括孙文那尚在学龄的独子孙科。兄长落魄,这一家的吃穿用度,自然便压在了孙文的肩头上。就在前些日子,孙文刚耗尽钱财,在毛伊岛为兄长购置了一套宅子。内田闻知,不免感叹:“为大国,为小家,孙逸仙已尽心竭力。”
徐锡麟、秋瑾起义爆发时,孙文已被“请”出日本,颠沛流离,哪还有闲心率领同盟会参与那次起义。同盟会成立至今,仅在1906年组织过一次大规模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虽然起义军最终因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但也逼得清廷调动四省约三万大军,使得清廷一时半会儿都恢复不了元气。
起义军方面自然也损兵折将,华兴会刘揆一之胞弟刘道一便战死于此次起义。1907年2月3日,同盟会在东京为刘道一举行追悼会。孙文当时还在日本,他在死者灵位前吟诗道: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孙文不善诗词,这首《无题》可称为他一生中难得的佳句。另有传言说,孙文流传于世的作品,多是托黄兴代笔而成。
同年2月25日,内田良平在赤坂“三河屋”为临行的孙文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欢送队伍中自然少不了宫崎滔天等日本志士。让人意外的是,素与孙文不和的章炳麟也前来赴席。
十日后,3月4日,孙文乘德籍客轮“Prince Alice”从横滨离港。起程前,孙文一股脑儿收下了一万七千日元的饯礼。其中的一万日元属于铃木久私人馈赠,落不着话柄。而日政府集资的那七千日元却给孙文带来不少烦恼。
与孙文同行的还有同盟会同志黄兴、汪兆铭、胡汉民,以及萱野长知、池享吉等数个日本同志。黄兴在香港便与众人分道扬镳。
孙文前脚刚走,日本国内舆论就为那七千日元饯礼炸开了锅。这笔钱出自国库,究竟是单纯的饯礼,还是另有意思,日本国民有权知晓。至于同盟会那头,说来也倒霉,凑巧撞上《民报》停刊。章炳麟如何会放过此等良机,便带头大做文章:孙文见财忘义,竟将我《民报》贱卖于日政府!
宋教仁、张继等骨干被谣言所蒙蔽,提议要罢免孙文总理之职,由黄兴接任。令人吃惊的是,刘揆一竟破天荒地站在孙文这一边。会中一时人心涣散。
远在香港的黄兴自然知晓真相,至信一封给东京同盟会总部,为孙文辩解: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孙文则当即贡献两千日元用以重建《民报》,剩余五千日元充作起义军资,好歹将这次“倒孙风波”平息了下去。
不待日政府下逐客令,孙文便自觉离开了日本。乍看还以为孙文“识相”,其实不然,他早就计划跑一趟越南了。
如今,起义什么都不缺,就缺“人”。以往的起义军队,都是由会党与新军组成。会党方好说,全凭头目一呼百应。所谓“号召易,统领难”,会党中玉石混淆,前几次起义的破产,会党都难辞其咎。
再看新军——新军虽统一指挥,统一训练,战斗力远强于会党,但毕竟是政府军,对革命派而言,妥妥的“敌军”。“化敌为友”可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大工程。
也就是前阵子,在广西钦州,数名大乡绅代表当地农民,联名请求官府减轻对甘蔗与砂糖的重税,官府非但不允,还将这数名乡绅给扣了。钦州上下群情激奋,民间自发组织武装力量——“乡团”,杀进官衙救出了被扣人员。钦州知府赶忙上报广州上级,称之为“匪乱暴动”。凑巧的是,在钦州东南不远的廉州(现合浦),民间正游行示威,抗议大地主垄断米市,坐地起价。
朝廷为平定上述两股叛乱,向钦、廉两州分别调遣了一支新军。也是凑巧,这两支队伍的长官都是革命派多年以来的拉拢对象,倒戈夺取钦、廉两州也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然而,两名长官见革命军残兵弱马,当即便收起了响应的念头。
——起义军前线告急,急需军备支持!
——武器弹药是现成的,从清兵那儿抢来就是了!
——边界要塞储藏有大批军火,如今已无后路,突袭镇南关!
1907年12月2日,壮族革命家黄明堂率领突袭部队,成功占领镇南关炮台(现友谊关)。4日,孙文、黄兴、胡汉民等人也绕经越南,自南边进入镇南关。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关隘中的武器库竟空空如也!
攻打钦、廉两州的前线部队尚有弹药,却被困在十万大山(广西南部山脉),一时半会儿支援不得。怕什么来什么,关内起义军弹尽粮绝时,三千清兵包围镇南关!黄明堂果断兵退越南,孙文等人也只得逃回越南,尽量筹集军火。“钦州、廉州起义”就此落幕。
1908年8月3日,法领越南总督府应清廷要求,将孙文驱逐出境。走投无路的孙文,只得再次奔赴新加坡。
起义爆发前,坐镇东京的宋教仁盘算着要趁孙文、黄兴在西南边陲举事,自己号召东三省“马贼”(相当于会党)来一场“南北呼应,包夹黄龙”。他率领数名同志奔走于门司(九州东北端)与安东(现辽宁丹东)之间。然而清廷对自己的“老家”东三省也是极为看重的。宋教仁等人刚入境,便被密探给盯上。最终,随着一名同志被捕入狱,宋教仁也断了“南北呼应”的念想,草草设立了大连分社,便仓皇躲回日本去了。
有逸闻,镇南关一役中,孙文也在前线“亲发数炮”。事后,他感慨道:“可笑,可笑,孙某反清二十余载,今日这般炮击清朝,却是头一遭。”
翻遍关内,却寻不着一枪一弹,众人扼腕,孙文却莫名雀跃,激励同志道:“瞧瞧,这便是吾等之敌人。重要如边境竟也疏漏到此等地步,何愁不可战胜清朝?”
黄兴一听,立马一扫阴郁,拍膝大笑道:“孙逸仙呀孙逸仙,百折不挠也。屡战屡败,竟还有心思谈笑……不得不佩服呀,受教了。”
法领越南总督府应清廷要求,将孙文、黄明堂军六百余人驱逐出境……或许,将“驱逐”改为“请”更贴切。毕竟,法国政府不仅倒贴了一行人的旅费盘缠,更是派军队一路护送他们至新加坡。
法国政府承认孙文“革命军”的身份,英国政府却未必。最初,英领新加坡总督府视孙文等人为“乱民”,不允其登岸。然而,先前在伦敦,英政府曾以“保护国事犯”为由,拒绝引渡孙文,若如今又咬定其为“乱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权衡利弊,总督府最终还是妥协了。
孙文登岸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求援于新加坡同志,成立“中兴石山厂”,好歹解决了六百余名弟兄的生计问题。
孙文称此次兵败为“革命第八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