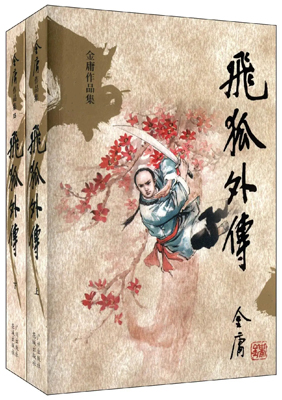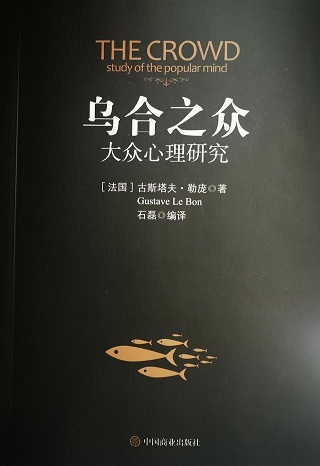孙文奔波东南亚期间,千里之外的京师,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驾崩,举国动荡。说来也蹊跷,光绪帝驾崩于1908年11月14日酉时(下午六点),相隔不到一日,西太后便于翌日未刻(下午两点)咽了气。
光绪帝之夭折并非毫无征兆——自从同年二月上戊(3月4日),他亲自主持了“太社太稷”典礼,便再未现身于其后的祀典。想必,那时就已经卧病不起了。
如此想来,西太后那头也一样——原定于十月壬戌(11月3日)的“圣寿宴”突然临时取消,便是西太后病危的最好佐证。要知道,即便是当年甲午战事告急,西太后的生日宴也丝毫不含糊。更何况,这次“圣寿宴”还撞上日本的“天长节”,兆头非同一般。传言,达赖喇嘛还专程进京,贡上“方物”(土特产),听说,是能愈百病的秘药。
光绪帝弥留之际,西太后下懿旨,召醇亲王领其三岁长子溥仪进宫抚养。光绪帝膝下无子,西太后一早便做好了这手准备。
要说这醇亲王载沣,他是光绪帝胞弟,单论辈分,他得喊西太后宠臣荣禄一声岳丈。然而最关键的,他是西太后的亲侄子。后宫派人上门来接人时,西太后胞妹婉贞嫡福晋紧紧抱住小溥仪不愿松手,悲愤道:“慈禧,你好狠的心!害了我亲生孩儿(光绪帝)还不够,如今又要害我小孙儿!这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谁爱做,给谁做去!”
孙文身处南洋,却心系京师局势,竭尽所能地搜罗相关情报。放眼望去,只有《东京日日新闻》上,犬养毅的一篇对清时评,最能让孙文共鸣:西太后驾崩,对清权力中枢影响甚微,绝非革命派乘虚而入之时机。亲王派与庆、袁(庆亲王与袁世凯)势力争权属于内部党争,并无诸国涉足之余地。
1901年,清国政坛“第一人”李鸿章辞世,他在遗书中写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有老宰相保荐,身无功名的袁世凯一路官运亨通,年近不惑便接了李鸿章的班,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如此破格提拔,可谓史无前例了。
话又说回来,当年就是袁世凯告密,害得光绪帝心心念念的“维新”功亏一篑。西太后避过暗杀,光绪帝惨遭囚禁,“戊戌六君子”身首异处……这一桩桩、一件件,袁世凯难辞其咎。
试想一下,若光绪帝熬到西太后驾崩,别说是袁世凯一人,整个“后党”都会被连根拔起。精明如西太后怎能容忍自己数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坊间不免臆想——莫非,西太后为绝后患,将皇上他……
一时间谣言四起……日本《报知新闻》猜测,是大内总管李莲英遣小太监王某弑君。李莲英为西太后鹰犬,光绪帝恨不能将其食肉啖骨。说他密谋弑君,倒有几分道理。天津某法文报刊更是言无所忌,公然枪指袁世凯,称其下毒弑君。
若小溥仪顺利即位,其父醇亲王载沣当入朝摄政。届时,摄政王若追究起“弑兄之仇”,袁世凯可无法全身而退。
孙文对清朝皇胄之评论一向不留情面,这次也不例外:“爱新觉罗?载沣,年少寡能之辈……自恃有出洋经验,学得西洋制度皮毛,便归国现学现卖。甚好,他日清朝覆灭,算他一份‘功劳’。”
当年庚子事变,德意志驻华公使遇袭身亡,清廷连忙遣使赴德谢罪,而载沣便是“谢罪使”代表。那时,他才刚满十八岁。
迄今为止,他的脑子里烙着一个概念——《宪法》限制皇权。归国后的某次朝议,他发问道:“德意志既已立宪,德皇为何会持有无上权威?”
某皇族答道:“皇室手握兵权尔。”
载沣深以为然,即便“立宪”被定为国策,他仍然强硬主张“皇族掌兵”这套理念。据“既定国是”(计划书),清廷计划在宣统八年(1916年)前,完成一切“立宪”准备工作。留给载沣的时间无多了,必须赶在此前,尽快掌控兵权。
于是乎,西太后临终要求的“服丧二十七日”还未结束,载沣便迫不及待地下谕旨,解任袁世凯一切官职,命其“回籍养疴”。谕旨中,声称袁大人“身患足疾”。袁世凯也是哭笑不得,自己健步如飞,哪来的“足疾”。
载沣恨不得将袁世凯千刀万剐,以报兄仇,但眼下杀他,势必会引来北洋新军暴乱。如今的朝廷,再也经不住这般折腾。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清廷的军备,孙文自然做过深入研究。现今,清军正处于改制阶段,全国军队将逐渐改为配备新式装备的“新军”。
按最新军制,全国军队共分作三十六镇,迄今,北洋六镇已成功过渡为“新军”,且受袁世凯管辖。新军一镇之兵力组成如下:步兵二协(旅)、骑兵一标(连)、炮兵一标、工兵一营(队)、辎重一营。
一镇统共有将士一万两千五百余人,北洋六镇便是七万五千余人。袁世凯曾经手握六镇数万精兵,难怪会被“清朝亲贵”敌视。袁世凯也怕树大招风,便主动让出了四镇的兵权。
20世纪初,清国人口突破四亿,而属统治阶级的旗人只有区区三百多万,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中,直系的“皇亲”被称为“觉罗”,与皇室有渊源者,也就是“国戚”,则被归类为“宗室”。清末,三百万旗人中,单是“国戚”就多达两万人,远超过邻邦日本“华族”(明治贵族)的数量。
想当年,“八旗”横扫中原,睥睨亚洲大陆。然而,百余年的太平岁月,让八旗兵养尊处优,再也不复当年之勇。后成立汉人“绿营”也难挽其颓势。其不堪一击,在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
八旗不堪一战,“绿营”独木难支。镇压太平天国,全仰仗曾国藩与李鸿章统率的乡勇——“湘军”与“淮军”。募集乡勇的士绅,大多是志在救国家危亡的读书人。强调一句,他们之所以投笔从戎,不为“卫国”,只为“保家”。
如今,“新军”之主力仍是汉人,倒也不是因为旗人无能,毕竟相差上百倍的人口差距摆在那儿。当然,军队统帅是绝对没有汉人的份儿。
日本曾经有贵族专属学校“学习院”,相对,清国也设有“贵胄学堂”。醇亲王摄政后,将贵胄学堂改组为士官学校,只招收旗人子弟,只有毕业生才有资格担任新军将领。对这一系列决策,孙文嗤笑道:“载沣如此自毁长城,可笑他还自以为良策……清军,步‘牧野殷军’后尘之日不远矣。”
那段时期,孙文时常出口便是历史典故,多少有些与国学泰斗章炳麟较劲儿的意思。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50年,周武王攻打殷国牧野,殷纣王以七十五万雄师迎战,却落得个“纣师皆倒兵以战(倒戈相向)”……同族兵将尚且如此,各何况如今的清军是“旗人将领,汉人兵”。
新帝溥仪尚幼,摄政王独揽大权,专设“军咨处”代行三军统帅权责。二十七岁的载沣自任“临时大元帅”,并任命其两名胞弟为“军咨大臣”与海军大臣。
闻此消息,孙文笑得直打跌:“哈哈,恭喜、贺喜载沣元帅重掌兵权!”
说实在的,此时的孙文哪有心思围观清廷的“自娱自乐”,革命派这头还有一大烂摊子不晓得该如何收拾。
那七千日元饯礼,果真是烫手山芋……如今,在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宣传册,题为《孙文之罪行》。孙文闻之,拍案而起道:“那七千日元早已尽数用于革命,有账簿为证!你们为何就是要揪住孙某不放?”
这宣传册若是出自坊间闲汉之手,孙文倒也不计较,但执笔人偏偏是章炳麟、陶成章两位名家。章、陶二人属“光复会”,与同盟会同为革命阵营,于情于理也应当和睦相处才对。然而,出自莫名小作坊的宣传册更是满坑满谷,有些甚至恣意编派孙文的私生活。例如说吧,某无良小报就曝光了“四姑”一事。这“四姑”本名陈粹芬,负责照顾孙文起居。会中同志考虑到孙文身份特殊,也怕闹出什么误会,都尽量对这个“四姑”避之不谈。孙文愤愤道:“孙某从未刻意遮掩粹芬之事。此前接受采访时,孙某便公开对四姑与发妻表达过谢意。如今,这无良报刊趁此时机,又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其心可诛!”
如今,在自家的《民报》上发文澄清,难免有自脱罪责之嫌。于是乎,孙文至求援信给伦敦的吴敬恒,请其在杂志《新世纪》上为自己澄清谣言:任公为人磊落,量也不会行此卑鄙龌龊之事。至于南海先生……也不知保皇会自身对这位领袖是何看法?
但凡扯上革命资金,孙文便容不得旁人半句闲话。其兄孙眉之所以破产,与孙文无止境的索捐不无干系。
相较之下,保皇会之筹款可算是手到擒来。想想也是,康有为是西太后眼中钉、光绪帝宠臣,名正言顺不说,在学界也颇有地位,自然是金口一开,金山银山就会来。反观孙文,真是不知从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卒。
康有为初抵新加坡时,当地富豪丘菽园豪赠其三十万两。然“自立军起义”时,唐才常费尽功夫才从康有为腰包里抠出区区两万两。后丘菽园破产,康有为却仍锦衣玉食,直至寿终。那就不免令人疑惑了,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孙文就纳闷儿了——你们光复会对康有为那几十万巨款的来路置若罔闻,却抓着我这区区几千日元不放,究竟是什么居心?
宣统二年,1909年年末,孙文自伦敦赴美。
也就在这期间,同盟会中有同志公然挑战孙文权威,批判其太过倚重会党。在他们看来,如今对新军的革命渗透工作颇具成效,大可将重心转向新军,而非那帮市井之徒。安徽籍成员倪映典向胡汉民谏此策略,并自告奋勇潜入新军内部。
孙文外出时,会中事务由黄兴、胡汉民两人共同操持。倪映典趁孙文未归,便赴香港劝说胡汉民尽早起事——清廷对新军异动已有所察觉,如今事态,拖则生变。
1910年除夕夜,广州数名新军兵士在买书时,因价格谈不拢,与书商起了争执。随着警方介入,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演变为一场“军警群殴”。倪映典闻知此事,当即赴港,趁势高呼“革命”。
然而此次起义本身便为时过早,加之爆发仓促,准备不足,其结果可想而知。倪映典亲率一千三百余名倒戈的新军血战牛王庙,百名新军战死,倪映典牺牲。
同盟会一时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更有甚者抨击其“草菅人命”。光复会所作《孙文之罪行》中的第一条罪状,便有“视同志性命如草芥”一说。
这可真是冤枉孙文了。“倪映典起义”时,已是孙文被驱逐出日本的第三个年头。确实,漂泊在外的孙文一直与东京本部保持着联系,八千美元的起义资金也是由他一手筹措。然而会上的大小事宜可是由胡汉民全权操持,这锅再如何也轮不到孙文来背。
保皇会更是得势不饶人,大肆抨击某些革命党人踩着同志的尸骸上位,自己却食得玉盘珍馐,住得琼楼玉宇。孙文之侧近汪兆铭(汪精卫)闻之愤慨,为正名于世,组织七人暗杀团,赴京刺杀皇族要人。
暗杀团在事先查知摄政王每日上朝必经甘水桥,决定在此处埋设炸弹,以电线远程引爆之。负责炸药的制作和埋设的黄树中,曾在横滨研习化学,深谙爆破之道。他趁夜深人静埋下了塞满炸药的铁桶,接上电线,正欲遁走,谁承想,被一个外出寻妻子的车夫撞了个正着,黄树中赶忙抽掉电线,落荒而逃。
那车夫果然去报了官。警察不敢妄挖炸药,还请了个日本技师前来相助。传言说,铁桶中的炸药、雷管足以将方圆一里夷为平地。
汪兆铭七人在京城租了个门面,开了家照相馆,用以暗中调配炸药。计划败露后,七人不思撤退,留在原地密谋新的计划。直至官兵找上门来,他们才后悔低估了清廷的办案能力。
爆炸物本体除了铁桶之外,其余部分皆为外国产。警察沿着线索,找到了“宏泰永”铁匠铺。老板一眼便认出了自家生产的铁桶:“哎呀,这不是琉璃厂照相馆的东家要的那批货吗?”
证据确凿,汪兆铭、黄树中两名主犯当即被逮捕。警察还照相馆搜出了几把手枪和用于引爆的电线,可见七人真把警察当怯懦之人了。即便刺杀未遂,企图谋害摄政王,罪及“凌迟”也不为过。
清国警察属民政部管辖,肃亲王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汪兆铭在狱中写下数千字供词,善耆过目后,深有感触,遂有了不杀之意。最后,汪兆铭被降罪一级,改判为无期徒刑。
善耆乃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十世孙,在一众皇亲国戚中,那也是一等一的地位。当年,皇太极驾崩,本该由嫡长子豪格继承大统,然豪格不知何种缘由,自愿将大位拱手让给六岁的皇弟福临,其后的清君皆为福临一脉。豪格一族,因先祖有“禅让之德”,代代受封“肃亲王”,这也是贯穿清朝历史最为位高权重的铁帽子王。
善耆膝下有子女数十个。他为经营与日关系,将其中一个女儿过继给日籍结拜兄弟川岛速浪为养女,这就是川岛芳子。善耆素有“侠王”美称,此番义助革命人士,更是让他在民间名声大噪。
顺道一提,七人暗杀团中还有一位女同志,便是那日后嫁给汪兆铭为妻的陈璧君。
同年3月28日,孙文自美利坚抵夏威夷,4月4日夏威夷同志为其举办欢迎会。仅一晚,便为同盟会添员百余名,不愧是孙文的第二故乡、作战主场。演讲台上,孙文感慨万千道:“看见了,终于看见了!”
台下便有听众问:“敢问先生见到了何物?”
孙文心系革命,所看见之物无非是革命曙光。第二故乡之行凯歌高奏,孙文随即转战日本。三年前,1907年的2月,日本政府受清政府重压,被迫驱逐孙文。然名为“驱逐”,实则赠予巨额盘缠,并于私底下许下“三年驱逐”之约。如今,三年之约已至。
三年过去了,清廷对革命党人的敌意不降反增。黑龙会的干部便借宫崎滔天之口提醒孙文道:“孙先生寻求日方庇护终非长久之计,清国外交‘一把手’胡惟德对沙俄尚且不落下风。对我日本,他如今睁一眼、闭一眼则两相无事,一旦发起难来,日本政府怕也招架不住。”
眼下,孙文正寄身在位于小石川区原町的宫崎滔天宅邸。孙文抵日时,化身为夏威夷绅士“Mr.Araha”,这对于在夏威夷长大的他来说,那是驾轻就熟。宫崎滔天乍听闻新来了个夏威夷人,当即便猜到是孙逸仙。除宫崎以外,接替杨枢的新任驻日公使胡惟德始终掌握着孙文行踪,自然也不会被蒙骗过去。后来,胡惟德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再度任驻日大使,可谓是当时的对日外交“第一人”。
果如黑龙会所料,孙文抵日才两周不到,清公使馆便将他赶了出去。但这趟短暂的日本之行,让孙文真切感受到“曙光将至”。
在日本期间,孙文会见服部登,两人久违地聊及儿玉源太郎。儿玉主张扶孙方略,却遭伊藤内阁反对,未能付诸实践。他时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犹记得曾经年少气盛,一言不合便是拳脚相向,但身居高位后,不免要自矜自持,将过去的自己舍弃。若能一分为二,其一理智自制,其一肆意而为,岂不快哉?
孙文笑问服部道:“服部兄莫不就是儿玉总督舍弃的‘另一面’?”
服部叹道:“或许吧,只可惜弃者已去。而孙先生便是儿玉总督未了之‘肆意’。”儿玉太郎在日俄战争期间殚精竭虑,虽为日军争得凯旋,却于战争翌年(1906年)病卒。
离日前夕,孙文会面黄兴、赵声二人,共商今后大计。赵声为江苏籍人,任新军将校,先前提到的倪映典便是其属下。
三人之意见达成一致——既是革命,则重在“一举成功”。先前数次“不成熟”的失败之例,于革命大业有害无利,应当终止。韬光养晦,蓄势待发,方为上策。
6月25日,孙文赴新加坡途中,船经香港,香港当局当即下令将孙文拒之门外。那时,孙文之母杨夫人正卧病于香港,由孙眉照顾。孙文思母心切,却登岸不得,只得在甲板上翻开日记本,写道:“今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是新历七月的……十九日……唉,母亲的八十三岁寿辰,儿子又要缺席了。”
然而杨夫人正是7月19日,也就是其八十三岁寿辰那日撒手人寰。孙文闻知噩耗时,心中之悔恨可想而知。
此次日方“驱逐”孙文的手段,更是客气非常。先是横滨警察署长亲自“劝退”,孙文赴东京登船时,不仅享受正常出国待遇,更得陆军大臣批准,在东京休整了数日才出发。孙文不免受宠若惊——看来,日方政要也看到清廷气数已尽。
反观拒孙文于香港门外的港英当局,其对清政策不免太过于保守。
同年11月,孙文于越南秘密召开革命会议。会议上,他再度强调革命切勿要意气用事,无论是暗杀摄政王,还是营救汪兆铭,都是不智之举。
“也亏得有人懂得审时度势,放汪兆铭一条活路,同时也为自己铺得一条后路。”
“您说的可是那肃亲王?”黄兴问道。
孙文摇头:“若无摄政王本人授意,肃亲王如何敢擅做决断?”
眼下的越南也非久留之地。不仅是法领越南,英吉利所辖东南亚殖民地,乃至澳大利亚,都以“妨害地方治安”为由,严禁孙文入境。
孙文对此不怒反笑,各殖民地政府虽听从清廷的意思,将自己驱逐出境,但纯粹是不想与清廷撕破脸皮,实属无奈之举。
——万事俱备,只欠时机。
——如今之革命环境,与孙某最初举事时相比,何止友善百倍。
在越期间,孙文将下一次起义提上纲程,初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力,赵声、黄兴各率一军,分别自江西、湖南,向南京、湖北进发,途中与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军会合,一举北伐。
孙文乃是流民身份,再不能在东南亚公开开展革命活动,只能躲在幕后,将募集军资的工作委托黄兴、胡汉民、邓泽如三人,与新军的联络事宜则交由赵声去办。
同年12月初,孙文自越南起程赴欧洲,由巴黎中转,于次年1月19日抵达纽约。
欧美诸国的募捐形势一片大好,尤其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当地华侨筹得三万港币资金,悉数捐给香港同盟会。同样在多伦多与蒙特利尔,变卖家产捐款的华侨不在少数。不仅是少数华侨资本家,在外打工的唐人也感于孙文的演讲,纷纷捐出数月的工钱。
自旧金山至温哥华,一路上孜孜不倦地募捐、演讲。场场座无虚席,无论刮风下雨。孙文行事低调,出门在外不爱带秘书、保镖,走南闯北,通常只有几本爱书相陪。保皇会就不同了,但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没有一次不是众星捧月。
最难得的是,孙文虽身在海外,却每时每刻都心系祖国形势,收集情报,并加以分析。孙文的情报源,是他最为信赖的“China Watcher”——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里森。
莫里森早年行医,多少与孙文有些“同行之谊”。后转行做《伦敦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其笔下的时评文章,是孙文旅行中的爱读之物。尤其是他在1909年9月7日刊载的时评Atonishing Weakness,让当时在伦敦的孙文不忍卒读。文中分析道:袁世凯失势后,再无与其比肩人物为清国挽回颓势。
这句话正挠中孙文心中痒处,让他通体畅快——如今清廷羸弱如此,革命派对新军的渗入又日见成效,如此以往,何愁革命不成功?
入主中原之初,清政权之支柱为十余万“八旗”。而入关之时,满人总人口不过几十万。为应对兵力不足的问题,清廷不断将降服的汉人编入“八旗”,加之已在旗下的蒙古人,“八旗”规模不断扩大。
然而“八旗”承平已久,耽于享乐,眨眼间便沦落为了徒有其表的“仪仗兵”。清军入关第三十个年头的“三藩之乱”便没有“八旗”什么事了,平定叛乱全仰仗汉人“绿营”。强调一下,这“绿营”可与“八旗”汉军八竿子打不着边。
制度使然,久而久之,“绿营”也难堪其用,在“白莲教之乱”(1795—1804年)与鸦片战争(1840—1842年)时,便已初现衰弱。直至“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年),其完全被湘勇、淮勇所取代。如今,“清军”早已是名存实亡,汉人将士绝不会同族操戈。
时不我待!然而,如今之阻碍,恰恰是在革命阵营内部……
从表面上看,同盟会之成立,将中国之革命势力拧成了一股麻绳,然散布《孙文之罪行》的章炳麟势力,对孙文一派的敌意那是再明显不过了。湖南革命势力的带头人黄兴,虽甘任副会长辅佐孙文,但因为意见不合所引发的矛盾还是时有发生。
例如,早在同盟会尚未确定会徽时,某日,孙文将挚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悬挂于大堂之上,黄兴见后勃然大怒:“我大中华竟要效仿日本以太阳为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黄兴倾心于廖仲恺设计的“井字旗”,这还得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实行“井田制”,具体说来,便是将九百亩的田地按照“井”字九等分,外围八块农田各分给八家耕种,中间部分划作“公田”,由外围八家共同负责耕种。
说起来,这倒与“平均地权”这一会章交相呼应,但孙文唯独这次是坚决不妥协:“换下‘青天白日’?可以!先踩过孙某尸首,再问问迄今为止,为这面旗帜抛头颅洒热血的数万同志!”
黄兴亦拍案而起:“这‘井’字,难道不是那数万已故同志之心愿,难道不是我中华数千年以来追求之夙愿?……道不同,不相与谋,黄某薄才,便不给这同盟会添累赘了!”
黄兴留下这句话,便拂袖而去。众人晓得黄兴就是这暴脾气,也不追赶。果不其然,翌早,黄兴又同没事人似的出席了晨会。然而章炳麟全程在一旁看孙、黄二人闹笑话,后再《自订年谱》中暗讽: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遂,复还。
如上所述,同盟会自成立起,便呈现出广东香山孙文、湖南长沙黄兴、浙江余杭章太炎三足鼎立之势。然好在黄兴识大局,会隐忍,与孙文算是一对“冤家挚友”。尤其是在孙文受多国驱逐,再不能领导革命大局时,黄兴站了出来,自愿接过孙文肩上的担子。孙文虽心存感激,却不敢苟同黄兴的行事方法:克强操之过急了,观如今形势,何须再动刀兵?坐观清廷自生自灭便是了。
清廷病急乱投医,一连几剂猛药下肚,却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原先,“六部”各由一满一汉两名尚书坐镇。然而摄政王大手一挥,另外增设七部,且各部堂官减为一人。最关键的是,十三名堂官中,只有四名是汉臣,其余九人均为满臣。
按理说,清政权的当务之急是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才对,这节骨眼儿上的一条“抑汉”措施,当真是匪夷所思。顺带一提,这九名满臣之中,竟有六名是皇族宗室,历称“皇族内阁”或者“亲贵内阁”。
孙文的募捐之旅行至纽约,难免要光顾黄二嫂的“一碗面”,说白了,他就好这一口路边摊儿。若换做是康有为,高档餐厅,美酒佳肴,作陪的弟子,挡酒的秘书,那是缺一不可的。
一碗热乎的汤面刚下肚,孙文还在回味,一男子看似随意地走到他身边。孙文也不抬头看对方是谁,放下筷子,悠声道:“有何消息?”
男子慢悠悠答道:“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倒有一条……黄兴按捺不住举事了,却大败而终。”
男人便是那似敌非友的掮客周榕,他沉着脸,将一份报纸扔在孙文桌前。报上的头条被打了个记号——中国革命党之起义再遭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