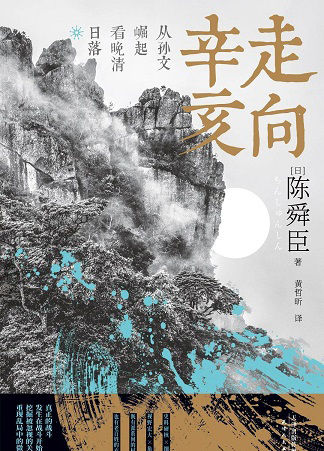1
几天以后,格温达顶着凛冽的风走在滨海大道上。突然,她在一个玻璃顶棚旁边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家体贴周到的公司为访客准备的。
“马普尔小姐?”她诧异地叫了一声。
的确是马普尔小姐,她裹着一件厚毛呢外套,头巾包得严严实实。
“发现我在这儿,很惊讶吧。”马普尔小姐愉快地说,“我的医生嘱咐我去海边换换环境,你对迪尔茅斯的描述又太吸引人了,所以我就决定到这儿来了——尤其是,我一个朋友的厨娘跟管家还在这边开了家庭旅馆。”
“可你怎么不来看我们呢?”格温达问。
“老年人可是容易讨人嫌的呀,亲爱的。新婚小夫妻就该享受二人世界才对。”她对格温达的抗议报以微笑,“我相信你们会让我宾至如归的。你们俩挺好吧?你们的秘密调查进展如何?”
“我们抓住了一条线索。”格温达说着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她把他们目前进行的各种调查仔仔细细地跟马普尔小姐说了。
“现在,”最后,她说,“我们在很多很多报纸上都登了广告——地方报纸、《泰晤士报》还有其他大型日报。我们只是说,关于海伦•施彭洛夫•哈利迪,娘家姓肯尼迪,如果有人了解任何情况,请联系某人什么的。我可以认为我们肯定能得到一些回音的,不是吗?”
“我觉得可以,亲爱的⋯⋯是啊,我也觉得可以。”马普尔小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自若,但她的眼中已经有了困扰的神色。她飞快地打量了一下坐在身边的女孩。女孩的声音貌似坚定不移,但实则听起来有些发虚。马普尔小姐觉得,格温达似乎很焦虑。海多克医生所说的,这件事背后“意味着”的那些事,也许已经在她身上初露端倪了。是的,然而现在回头已经太晚了⋯⋯
马普尔小姐柔声表达着歉意:“我对这一切真是太感兴趣了。你知道,我的生活中极少有刺激的事发生。所以我想请你多跟我说说你们的进展,希望你不会嫌我太问东问西了。”
“当然,我们会让你知道的。”格温达热情地说。“你可以参与每一件事。嘿,要不是你,我准得让医生把我关到疯人院里去。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地址吧,以后你可得过来喝一杯——我是说,跟我们喝喝茶,看看我们的房子。你得到犯罪现场来看看,是不是?”
她大笑起来,笑声中却藏着隐隐的紧张不安。
格温达离开以后,马普尔小姐皱起了眉头,极为轻微地摇了摇头。
贾尔斯和格温达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查看信件。一开始,希望落空了,他们只收到了两封信,都是私家侦探发来的,声称自己有意愿且有能力为他们承担调查工作。
“先不用看这些,”贾尔斯说,“要是咱们非得委托私家侦探去查,也得找一流的公司才行,不能用这种发邮件招揽客源的。不过,我真不觉得有什么他们能做到的事是咱们自己做不到的。”
几天之后,他的乐观(也许是自满)就被证明了并非盲目自大。有一封信寄到了,信上是那种字迹清晰但稍难辨认的手写体,可见写信者是一位职业人士。
---高尔斯山别墅
---伍德雷波尔顿
亲爱的先生,
为你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广告做一答覆。海伦•施彭洛夫•肯尼迪是我的妹妹。我与她失去联系多年,非常希望得知她的近况。
---你忠实的,
---詹姆斯•肯尼迪,医学博士
“伍德雷波尔顿,”贾尔斯说,“不是很远。伍德雷营地是大家常去野餐的地方,一直延伸到高沼地那边,离这儿大概有三十英里。咱们给他写信问问吧,看是要咱们登门拜访,还是他愿意来找咱们。”
肯尼迪医生答复说,他准备在下星期三接待他们。到了那天,贾尔斯和格温达动身了。
伍德雷波尔顿是一座村庄,散布在山的一侧。高尔斯山别墅建在隆起的山巅上,是最高处的房子,可以俯视伍德雷营地和延伸至大海的旷野。
“这地方真冷啊。”格温达说着打了个寒战。
房子里很冷,显然,肯尼迪医生对于中央供暖这类现代新事物持排斥态度。来开门的女人肤色黝黑、面容冷峻。她带着他们穿过空荡荡的大厅,步入书房,肯尼迪医生就在这里接待他们。书房呈长条状,挑高也相当高,陈列着一列一列堆得满满的书架。
肯尼迪医生是一位灰头发的老人,眉毛浓密,眼神锐利。他那锐利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贾尔斯,又打量了一下格温达。
“里德先生和夫人吗?坐这里,里德夫人,这把椅子应该是最舒服的。现在,说说吧,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贾尔斯流利地讲起了他们预先商量好的故事。
他和他妻子是最近在新西兰结的婚,后来到了英国,他的妻子童年时曾在这里小住过。现在,她想找找家族的老朋友和老熟人。
肯尼迪医生的态度僵硬冷漠。他维持着表面的礼貌,但很明显,从殖民地来的人非要跟他攀什么莫名其妙的亲戚关系,让他颇为恼怒。
“所以你认为我妹妹——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可能还包括我自己,是你们的熟人?”他这么问格温达,虽然彬彬有礼,但略带敌意。
“她是我的继母,”格温达说,“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当然,我对她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了,那时候我太小了。我娘家姓哈利迪。”
他盯着她看——然后,一抹微笑点亮了他的面容。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一点儿也不冷漠了。
“天哪!”他说,“别跟我说你是格温妮!”
格温达急切地点头,她的小名,已经淡忘了许久,此刻重新在耳边响起,让人感觉既安心,又亲切。
“是呀,”她说,“我是格温妮。”
“上帝保佑!你都长大成家了。时光飞逝!这得有⋯⋯怎么着⋯⋯十五年⋯⋯不对,当然,还要久得多了。你可不记得我了吧,我猜?”
格温达摇了摇头。
“连我父亲都记不得了。我是说,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
“当然⋯⋯哈利迪的第一任妻子是新西兰人⋯⋯我记得他是这么告诉我的。那是个不错的国家,我觉得是。”
“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国家——不过我也非常喜欢英国。”
“你们是过来旅游,还是定居?”他边说边按响了铃,“咱们一定得喝杯茶。”
那个高个子女人进来以后,他说:“请端茶过来⋯⋯还有⋯⋯呃⋯⋯热黄油吐司,或者⋯⋯或者蛋糕,别的也行。”
一本正经的女管家虽然看起来有点儿刻薄,不过,她说了声“是,先生”便出去了。
“我平时不爱喝茶,”肯尼迪医生含含糊糊地说,“不过我得为你们接风。”
“你太客气了,”格温达说,“不用麻烦了,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旅游,我们已经买好了房子。”她顿了顿,补充道,“山腰别墅。”
肯尼迪医生的声音还是很含糊:“哦,是啊,在迪尔茅斯,你们的信就是从那边寄来的。”
“这真是最不可思议的巧合,”格温达说,“不是吗,贾尔斯?”
“是可以这么说,”贾尔斯说,“的确相当出人意料。”
“你看,当时那幢房子正在出售。”格温达说道,见肯尼迪医生面上露出不知所云的表情,她补充了一句,“就是很久以前我住过的房子。”
肯尼迪医生皱起了眉头:“山腰别墅?可是确实⋯⋯哦,对了,我听说他们给改过名字。以前是叫圣什么的⋯⋯如果我想得没错的话⋯⋯在利翰普顿路的右手边,往南走可以进城?”
“没错。”
“那就是了。真有意思,名字就是容易忘。等等,圣凯瑟琳别墅——它以前的名字就是这个。”
“我确实在那里住过,是吗?”格温达说。
“是的,你当然住过。”他看着格温达,笑了,“你为什么要回到那里去?你对那里并没有太多记忆了,是吧?”
“是啊,可不知怎么的⋯⋯就觉得它是家。”
“觉得它是家。”医生重复了一遍。他说话时语气平静,但贾尔斯偏偏觉得他是想到了什么。
“所以,你看,”格温达说,“我希望你能把一切都告诉我⋯⋯关于我父亲和海伦的事,以及⋯⋯”她说得犹犹豫豫的,“以及每一件事⋯⋯”
他看着她,思虑重重。
“我猜他们之间并不怎么熟悉⋯⋯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没理由会特别熟悉吧?哦,其实也没太多可说的。海伦——我妹妹——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和你父亲坐的是同一艘船。他当时是个带着小女孩的单亲爸爸,海伦也许是可怜他,也许是爱上了他。而他孤身一人,也许就爱上了她。很难说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俩一到伦敦就结婚了,并且到迪尔茅斯来找我。我当时在那里行医。凯尔文•哈利迪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但很是焦虑颓唐,不过看起来他们在一起生活得挺幸福的——在那个时候。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然而,不到一年以后,她就和别人私奔了。你大概知道这件事吧?”
“她是和谁私奔的?”格温达问。
他用锐利如刀的目光盯住她。
“她没告诉我。”他说,“她并不信任我。我看到过——无意中看到过——她和凯尔文发生过矛盾。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是那种古板保守的人,我认为夫妻之间必须忠诚。海伦不会希望我知道她在做什么。我听到过一些传闻——就一个——不过没说到具体人名。经常会有从伦敦或外地来的客人住在他们家。我想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个人。”
“那么,他们俩没离婚吗?”
“海伦不想离婚。凯尔文跟我说过。所以我猜,也不一定正确,对方可能是个有妇之夫,也许那人的妻子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
“那我父亲呢?”
“他也不想离婚。”肯尼迪医生的回答非常简洁。
“跟我谈谈我父亲吧,”格温达问,“他怎么就突然决定要把我送去新西兰呢?”
肯尼迪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我猜是你母亲在那边的亲人向他施压了。第二次婚姻破裂之后,也许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那他为什么不亲自送我过去呢?”
肯尼迪医生在壁炉架上看来看去,踅摸着烟斗通条,表情晦暗不明。
“唉,我也说不上来⋯⋯他的身体非常不好。”
“他的身体是怎么回事?他是得什么病去世的?”
门开了,女管家冷着脸走进来,手里端着重重的托盘,上面摆着奶油吐司和果酱,没有蛋糕。肯尼迪医生冲格温达略微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倒茶。她照办了。她把茶杯都倒满了,每个人一杯,然后给自己拿了一片奶油吐司。肯尼迪医生强打精神,笑着说:“跟我说说吧,你的房子装修得怎么样了?我猜我现在肯定都认不出来了——等你们装修完以后。”
“我们对浴室做了点儿小改动。”贾尔斯说。
格温达盯着医生问:“我父亲是得什么病去世的?”
“我确实不知道,亲爱的。我说过,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非常不好,最后住进了一家疗养院——在东海岸。两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那家疗养院具体在哪儿?”
“对不起,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说过,我的印象里是在东海岸。”
这会儿,他明显是在回避什么,贾尔斯和格温达对视一眼。
贾尔斯说:“最起码,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们他葬在哪里吧?格温达——自然是——非常急切地想去扫墓。”
肯尼迪医生在壁炉前弯着腰,用削笔刀挖着烟斗锅子。
“你明白吗,”他含含糊糊地说,“我真的认为不应该过份沉溺于过去的事。这种祖先祭拜⋯⋯是个错误。未来才是最重要的。看看你们俩,年纪轻轻、健健康康的,你们面前有整个世界。多向前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某个你们都不太认识的人的墓前放上一束花,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格温达激烈反对:“我就是要看看我父亲的墓!”
“那我恐怕就帮不上你的忙了。”肯尼迪医生说话的语气轻松而冷淡,“时间太长了,我的记忆力也不比从前。你父亲离开迪尔茅斯以后,我们就没再联系过。我记得他在疗养院的时候给我写过一次信。我说过,我有印象那是在东海岸——不过即使是这一点我也不是十分确定。而且,我完全不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
“真奇怪。”贾尔斯说。
“有什么可奇怪的,你要明白,我们之间的纽带只有海伦。我一直特别喜爱海伦。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比我小很多,但我竭尽全力抚养她长大,送她上好学校,给她应有的一切。但无法否认,海伦⋯⋯嗯,她的性格太不庄重了。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曾经跟一个不良青年发生过纠葛。我帮她摆脱了这场麻烦。然后她就决定去印度,跟沃尔特•费恩结婚。哦,这桩婚事还行,那孩子不错,他父亲是迪尔茅斯最好的律师,但说实话,他这个人特别单调乏味。他很爱慕她,可是她一点儿都看不上他。不过,她改变了主意,去了印度打算跟他结婚。然而,他们俩再次见面以后,这桩婚事还是告吹了。她拍电报给我,跟我要回家的路费,我就给她寄了钱。她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凯尔文,没等我知道,就嫁给了他。我替我妹妹感到——可以说是——愧疚。所以,她走了以后,我和凯尔文就没再维持这种亲属关系。”他突然补充了一句,“海伦现在在哪儿?你们能告诉我吗?我希望能联系上她。”
“我们不知道,”格温达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哦,看了你们的广告我想⋯⋯”他看着他们,眼神里突然有了好奇,“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登广告?”
格温达说:“我们想联系⋯⋯”她住了嘴。
“联系一个你几乎不记得的人?”肯尼迪医生质疑。
格温达赶紧说:“我是想⋯⋯如果我能联系上她⋯⋯也许她会告诉我⋯⋯我父亲的事。”
“是的⋯⋯是的⋯⋯我明白。抱歉我帮不上什么忙。记忆力大不如前,而且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
“可至少,”贾尔斯说,“你知道那是家什么疗养院吧?结核病疗养院?”
肯尼迪医生突然又板起了脸:“是⋯⋯是的,我很确定。”
“这么一来,我们的调查应该就容易得多了。”贾尔斯说,“非常感谢,先生,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切。”
他站起身来,格温达也跟着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她说,“一定要来山腰别墅看我们。”
他们走出书房,格温达回头看了一眼,肯尼迪医生站在壁炉架旁边,揪扯着花白的八字胡,面色凝重。
“他知道些什么,可他不告诉咱们,”他们坐进汽车时,格温达说了一句,“这里面的事⋯⋯哦,贾尔斯!我希望⋯⋯我现在希望咱们从来没有开始调查这件事⋯⋯”
他们对视一眼,彼此并不知道,各自的脑海里已经涌起了同样的恐惧。
“马普尔小姐是对的,”格温达说,“我们应该离这些过去的事远远的。”
“我们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贾尔斯犹犹豫豫地说,“我想,也许,格温达,亲爱的,我们最好停手。”
格温达摇了摇头。
“不,贾尔斯,我们现在不能停手。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不,就得继续下去⋯⋯肯尼迪医生不告诉我们,是出于一片好意——可这样的好意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必须继续追查,找出真相。即使⋯⋯即使⋯⋯我父亲就是那个⋯⋯”她说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