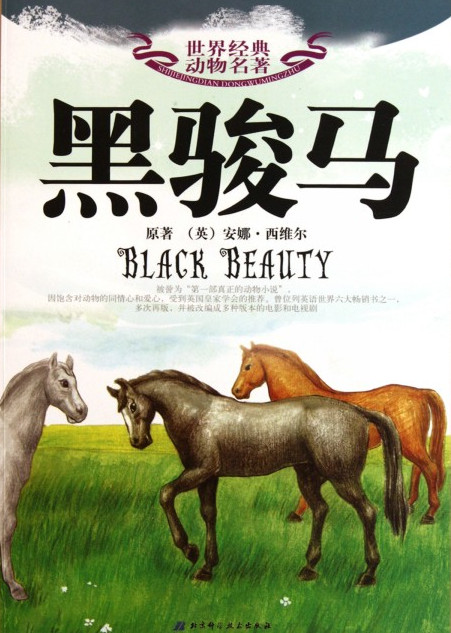有段时间,我痴迷京戏。吃饭走路,全是《春闺梦》《捉放曹》《洪洋洞》。一有空就看戏吊嗓子,结交的朋友全是戏迷。连闲空时聊天吹牛都是这风格的:“等你结婚,我们唱《狮吼记·跪池》,送上最诚挚的祝福——让你的老公像陈季常一样惧怕你。”“那还是杜月笙风光,以后我发达了给我家修个祠堂,把全国名角儿请来弄个粉戏大联欢。”
凡此种种,纯属白日做梦,一说出口,就遭到朋友们的吐槽。但有一个愿望,已经忘了是谁最先提起了,反正一说出来,大家都大为击节,深以为然:“如果找到一个也爱唱戏的爱人,结婚时唱一回《得意缘》。”
《得意缘》说的是书生卢昆杰娶了活泼可爱的云鸾,却在无意中得知岳丈全家都是强盗,吓得想要逃跑,云鸾最终选择爱情随丈夫一起下山的故事。这出戏唱的很少,几乎全是对话,两个人在舞台上还可以加词儿,我曾经听过荀慧生和叶盛兰的版本,荀慧生曾经唱过梆子,叶盛兰现抓词儿说:“还是你去说,你那小嘴跟梆子似的。”荀慧生一点不含糊,没多久来了一句:“哟,我还以为你没看见呢。”(嘲讽叶盛兰是近视眼。)
提议唱《得意缘》,并不全因为这出戏活泼热闹,更多地,是我们每个人都仰慕也唱过这出戏的朱家溍先生和他的夫人赵仲巽。
1982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写了一篇题为《咸福宫的使用》的文章,这篇文章旨在证明咸福宫并非大家从前认为的“嫔妃居住之所”,而是清朝中后期皇帝守孝居住之所。在写这篇文章时,朱家溍先生有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同道堂原存物品中,有一紫檀匣,匣内有咸丰元年、三年、七年等不同年月的朱批奏折,都是当时“留中不发”之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左都御史朱凤标参劾琦善的奏折,列举了琦善的罪恶,建议不应再起用。还有朱凤标、许乃普等主战派为抵抗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时列举的各项切实可行之办法。这些意见都未被采纳。
弹劾琦善的朱凤标,是朱先生的曾祖父。在无意中,朱先生见到了他的祖先一辈子求而不得的答案。
萧山朱家,是朱熹的后代。从朱凤标力主对外用兵之后,朱家的子孙们似乎就失去了皇帝的欢心,但他们依旧勤勤恳恳做官,欢欢喜喜做学问。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留学英法,当时,中国的年轻人正为前一年清政府拖延立宪的决定而大失所望,清王朝失去了一个可以转型的机会。那道拖延的懿旨,草拟人叫荣庆,清末军机大臣。
赵仲巽是荣庆的孙女。赵小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最严重的一次,家里人都觉得活不了了,就让保姆把她抱到马号。保姆老王妈不忍心,在马号守了她三日,竟然醒了,老王妈赶紧给喂米汤,这才活了过来。赵小姐的母亲给老王妈打了一对金镯子,说:“这孩子一条命是你捡的,以后这是你的闺女。”
因为这个原因,赵小姐的童年非常幸福,她获得母亲的特批,放风筝划船爬山,样样精通。除了宠爱她的母亲,还有更宠爱她的“五老爷”——五老爷是外祖父终身未嫁的妹妹。五老爷擅长种葫芦,有次种出一个三分长的小葫芦“草里金”,五老爷用心爱护,终于成形。她对赵小姐说:“可惜配不上对,要再有一个一般大的,给妞镶一对耳坠子多好。”赵小姐出了个主意,借用东坡的诗“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叫玉作坊用碧玉给琢一根竹杖形的戳枝,叫三阳金店用足赤打一个绦带结子把葫芦镶上,岂不是一件有诗意的首饰。”五老爷照办,并把这玉钗送给了赵仲巽。这件玉钗后来在“文革”中被抄没了。
朱先生和赵小姐是世家的情谊,没结婚之前两个人就认识了,她唤他朱四哥,他呼之以二妹。两人的婚事是上一辈的老人介绍的,但并不算盲婚哑嫁。在决定结婚之前,赵小姐去看了一场堂会。
那是1934年,这一年,朱家溍二十岁。训诂学家陆宗达的祖母八十寿诞。韩世昌、陶显庭、侯益隆等在福寿堂饭庄唱堂会戏。这也是朱家溍首次登台,演了三出:《邯郸梦·扫花》中的吕洞宾,《芦花荡》中的周瑜,为谭其骧的《闻铃》配演陈元礼。
朱家溍却不知道,他演的这三出戏如同月老的红绳,拴住了自己一辈子的姻缘。观众席上,赵小姐的嫂嫂陪着赵小姐看戏。一到朱家溍出来,嫂嫂就问:“你觉得朱四的戏怎么样?”赵小姐回答:“朱四的《扫花》演得真好,《闻铃》的陈元礼也不错,有点杨派武生的意思,《芦花荡》的周瑜不怎么样。还是吕洞宾的扮相最漂亮,总而言之是戴黑胡子比不戴更好。”
赵小姐也不知道,便是这几句话,定了她的终身。
这段“戏评”很快传到了“朱四”本人耳朵里,他大为惊喜赵小姐的点评如此精到,亲友之间见面,总拿“戴黑胡子比不戴更好”开朱家溍的玩笑,但他并不生气,且颇为得意。很多年之后,朱先生仍旧对这场堂会记忆犹新:
没有多大时间她说的话就已经传到我耳朵里,大概对于我们后来的结婚有些促进作用,因此我也对于这场堂会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我们结婚了。从此听戏的时候,我们也是伴侣。
——朱家溍《中国文博名家画传·朱家溍》
结婚之后,朱家溍的十姨妈生日唱堂会,家里不少亲戚都加入演出,小两口演了一出《得意缘》。在后台,朱家溍给妻子拍了不少照片,女儿朱传荣说:“可以想见,父亲真是得意呢。”
结了婚,就不能做娇小姐了。
仲巽成了朱夫人,她成了一家子的女主人,操持家务。偶尔地,她仍有一些做小姐时的天真烂漫。在北平时,朱夫人曾带着孩子们上房放风筝(北平的屋檐是可以放风筝的!),结果公公回家,大儿子眼尖,先“飞快地下了房,还把梯子挪开”,等到仲巽发现,已经下不了房,索性坦然地站在房上叫了公公。幸好,留过洋的公公并不是封建家长,不仅没生气,还觉得“挺有意思”。
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里,这个小时候差点活不了的蒙古贵小姐,跟着丈夫从沦陷的北平一路到重庆,搭顺风车时,司机因为疲劳驾驶把车开下了山,幸而落在江边软沙滩里,才幸免于难。路况差的时候不能通车,人跟着人力架子车一起走。她告诉女儿:“如果太阳出来上路,日落之前住宿,一天走六十里。如果天未明就走,走到天黑再住,差不多可以走一百里。”一路没有掉队,全凭仲巽少年时代爱爬山练出的脚力。
到了重庆,朱家溍周末才能回家,仲巽负责所有的家务活儿。屋里进了蛇,她见之大惊,飞跑去叫人,渐渐也学会“用根竹竿挑到远处去就是了”。警报一响,她能最短时间内收拾好一切,带着孩子和必需品钻防空洞。
周末,朱家三兄弟回家吃饭,仲巽负责做饭。猪肉价贵,就买来猪肺,用清水多次灌入,以手击打,排出血水,加了杏仁川贝,做一道银肺汤。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但并不少情趣:
过年时候,山上到处有梅树,折一大枝在草屋里,油灯把梅花的影子照在蚊帐上,一幅天然墨梅。
——朱传荣《父亲的声音》
1951年11月,故宫博物院停止工作,进入全院学习阶段,“三反”运动开始。朱家溍因为在重庆期间曾经加入国民党的经历,在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对象。有关朱先生“三反”中的遭遇,我曾经听刘曾复先生和吴小如先生讲过,但奇怪的是,两位老先生最爱讲的两段,却并不悲伤,像是动荡中的传奇。
第一段是朱先生被捕,我来引用一下王世襄先生的描述:
季黄此时问我:“你从东岳庙回家后,是怎样被抓送公安局看守所的?”我说:“回家后两天,派出所通知前往问话,进门早有两人等候,把我铐上手铐,雇了三辆三轮,押送前门内路东朱红大门的公安局。”季黄兄大笑道:“抓送我的规格可比抓送你大得多了。”这时四嫂等都笑了,知道将有精彩表演可看了。
季黄接着说:“拘捕我可是二三十人编了队,开了三辆吉普来的。特工人员从炒豆胡同大门进入,每进一道门就留两个人把守。越过两层院子,进入中院,正房和两厢房顶上早有人持枪守候。”这时我插话:“看这个阵势,知道的是拘捕朱家溍,不知道的以为是准备拍摄捉拿飞贼燕子李三的电视剧呢。”一下子又引起一阵笑声。
季黄说:“那天傍晚,我刚洗完澡,坐在床上,尚未穿好衣服,两脚也未伸入鞋中。忽听见院中有人声,破门冲进两人,立刻把我铐上手铐,并叫我跟他们走。我因两手不能下伸,提不了鞋,忽然想起林冲在某出戏中(戏名可惜我忘记了)的两个动作,可以采用。我立在床前,像踢毽子似的,先抬右腿,以鞋帮就手,伸指把鞋提上。再抬左腿,重复上述动作,把左脚的鞋提上。做两个动作时,口中发出‘答、答’两声,是用舌抵上膛绷出来的,代替文场的家伙点,缺了似乎就不够味儿。”两个动作做完后,季黄问大家:“你看帅不帅?边式(指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身段漂亮,动作干净利落。)不边式?”一时大家笑得前俯后仰,说不出话来。
——王世襄《锦灰不成堆》
朱先生和王世襄一起先被关在白云观,后来移送到东岳庙,之后又进看守所。拘留时的编号,王世襄是三十八,朱家溍是五十六。关押中的审查重点是贪污,要交代从故宫偷了什么。朱家溍说自己没偷,结果被定性为“拒不交代”。有一位古物馆的冯华先生曾经给美国收藏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编过收藏目录,为了过关,就写了一份名单,说让福开森带到美国去了。结果没通过,理由是嫌弃名头太小。冯先生被逼无奈,加上唐宋元明清的,不仅故宫藏的,凡是知道的都写上,俨然“一部中国美术史”。
1954年4月1日,朱家溍被释放回家,到家已是半夜。下面的这个故事,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但还是决定引用朱传荣阿姨在《父亲的声音》里的讲述,还原一下这个精彩不过的场景:
父亲下车按门铃,就是母亲来开门,隔着门问了一声,谁呀。父亲说,我,我回来了。母亲却突然用戏里念白的口气说了一句——你要后退一步。
《武家坡》中,薛平贵一路追赶王宝钏来到寒窑之外,叫门,说,是你的丈夫回来了。王宝钏说,既是儿夫回来,你要退后一步。这话的意思是,退一步,可以隔着门缝看清楚来人。
父亲也就接了薛平贵的对白:
——哦,退一步。
——再退后一步。
——再退一步。
——再要退后一步!
第三次之后,
——哎呀,无有路了啊!
母亲在门洞里说了最后一句,这一句更响亮一点:
——有路,你还不回来呢。
这才开开门,给了车钱。
好几十年之后,父亲每提起这一晚,都对母亲开门时候的玩笑佩服得不得了,一句话,你娘,伟大。就那时候,还开呢。(这个“开”是开心,开玩笑,开涮的简略语,综合了三者,似乎又高于三者。)
“三反”不过是一个开始,不久,朱家溍又带着夫人仲巽和小女儿传荣下放到五七干校。在那里,六十五岁的朱先生要一天给厨房挑二十多担水,打满十二个水缸。还要去咸宁火车站卸煤,去嘉鱼潘家湾运砖,有时候还要拉着板车去县里拖大缸咸菜,来回几十里路,朱先生觉得这是“锻炼身体”。
朱家养了一条无名的草狗,全家人都很喜欢它。据说,平时家里来人,如果态度和善,小狗就不声不响;若来的是造反派,气势汹汹上来就“朱家开会去”,它就会“嗖”的一下猛扑过去。来人吓坏,躲得老远,连声说:“请你快点去,我就不过来了。”
“文革”期间,朱先生的戏瘾依旧很大,他唱了一回《沙家浜》里的郭建光,洋洋得意和朋友们说:“我这几个亮相,还是杨(小楼)派的!”
无论到什么时候,他都这样乐观豁达,一如他著名的大嗓门,如洪钟大吕。
去过朱先生家里的人,都会对墙上那幅“蜗居”记忆犹新。这两个字来自启功先生。住在“蜗居”里的朱先生,却为国家捐献了价值过亿的文物。1953年,应母亲的要求,朱家四兄弟把家传的七百余种碑帖无偿捐赠给了文物局。1976年,由朱家溍提议,经过两位哥哥同意,将家藏家具和多种古器物无偿捐赠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其中包括黄花梨、紫檀、楠木等大型多宝槅、条案、几案、宝座及床等各类一级文物。
然而,这批文物没有得到当时相关人员的重视和保护,很多家具被毁坏,王世襄先生专门撰文表示了痛惜。后来,故宫工作人员修复了部分捐赠家具,邀请朱先生去看一看,朱先生答应了,然而没有去。再问的时候,他说:“我就不去了,看了难过。”
一说起故宫捐宝人,大家容易想到的名字是张伯驹,朱先生和张伯驹第一次碰面,是在琉璃厂的古董店里。尽管掌柜两边传话,两个翩翩公子都有些傲娇,始终没有过多的交流。
直到解放后,朱先生演了一回《长坂坡》的赵云,演出结束,远远看见张伯驹先生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兴奋地说:“真正杨(小楼)派的《长坂坡》!”
张伯驹先生和朱先生这一辈人,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战流离、内战动荡(张先生还经历了跟军阀抢老婆),他们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在任何时候,面对钱财和权势,他们总是风轻云淡。这种风轻云淡,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正如朱传荣阿姨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家从来都认为自己只是文物的保管者,从来没有认为是私有财产,父亲把它们捐出去,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而他们的夫人,也像极了古代仕女图中的女子,娴静却又不失性格。我们那位提议唱《得意缘》的朋友,每次都要感叹,要找个这么得意的媳妇太难了——我知道他的标准,当然,这世界上有几个赵仲巽呢?
1993年1月9日,朱先生正在香港办事,忽然接到仲巽因肺心病昏迷抢救的电话,紧赶慢赶,赶上最后一班飞机回到北京,朱先生看到的是“插着各种管子,口中有呼吸机”的夫人。仲巽不能讲话,拿笔在纸上写着,朱先生看着,泪已经滚下来。纸上只有三个字:“不要急”。
五十天之后,仲巽走了,捐出几亿文物的朱先生为了给夫人看病办后事,欠了四万多元的债。他写了一首不算悼亡的悼亡诗,都是日常,瓶子里的花朵,盆景上的假山石,读书唱戏鉴古,他的生活里已经充满了妻子的影子:
登台粉墨悲欢意,
恍似神游伴玉颜。
很久之后,他对小女儿说:“我们想共同庆祝结婚六十年,本是可以指望的,没想到她竟自去了。”
2003年,有记者到朱先生家采访,临走时打算给朱先生拍张照,朱先生忽然叫停。他回身走到墙上那张“泰岱晴岚”照片前,这是朱先生八十五岁登泰山拍摄的作品。在这幅摄影作品下方,端立着一方精致的小画框,内有仲巽的小照。朱先生在相框上摆了两朵红绢花,然后转过身来说:
“照吧。”
参考文献:
朱传荣:《父亲的声音》,中华书局2018-10
王世襄:《锦灰不成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