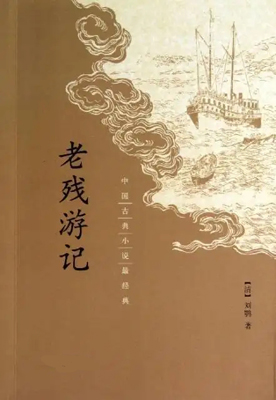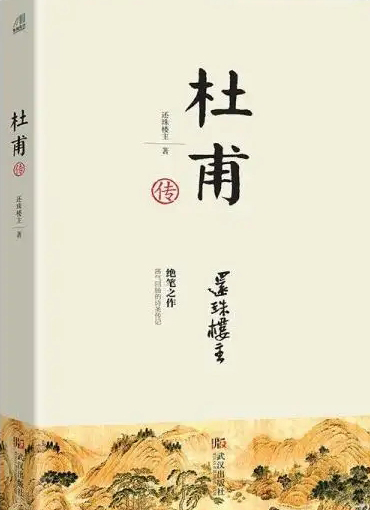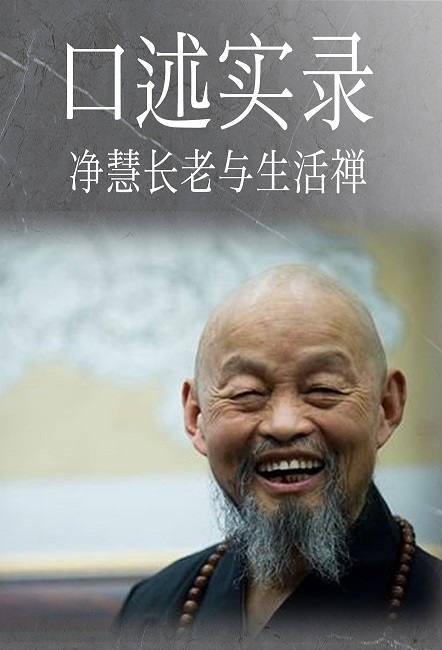最近这半年,大概算是我的至暗时刻。辗转京沪两地,一半给公司,一半给医院。日程表里画了细细密密的红线,提醒我化疗时间到了,提醒我要申请外科会诊了,提醒我交稿时间到了,提醒我开会时间到了,唯独没有停一停的时间。好像一头蒙着眼的驴,看不到未来,只能闷头拉磨。
那些细细密密的红线终于有一日成了梦魇,梦里的我被它们缠绕捆绑,勒得喘不过气,然后落入碧潭深渊。我那残存的幽默感在梦的结尾灵光一现,隐约感觉抛下去的瞬间看见了东方明珠,醒过来第一句对自己说,啊,这就是旧社会被扔进黄浦江的感觉。
旧上海当然没有东方明珠,一如真的生活并不是被扔进黄浦江这么一了百了,醒过来你还得继续闷头拉磨,看那些你看不懂的肿瘤数据,一趟趟跑医院,然后在医院住院部外的楼梯间打工作电话。连这篇文章,也是我在胸外科外因为疫情临时搭建的医生谈话处的桌子上写成的,小护士打开门探了探头看看我,叹了口气讲,那个桌子后面,有一个隐秘插孔,你别告诉别人。
一位师长对我说,历经了这些事,你才能真的长大了。嗨,原来长大是这样地不好玩,早知道逃去忘忧岛,和彼得·潘做伴,永远做小孩。
至暗时刻的光在哪里呢?你是如何熬过自己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呢?买买买已经不管用了,我最近买过的最贵的东西是我爸的免疫药,一针3w+。吃到好吃的也没办法安慰到自己了,我最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我妈的炸猪排,但她已经很久没有时间做一块炸猪排了。至于旅行?看看行程卡上的星标号,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给自己熬一剂浓浓的心灵鸡汤——这一招老前辈们用过,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每次想到她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的至暗时刻——也就还好。
一
我喜欢她的名字,尽管一开始我只认识她姓赵,另外两个字连音都读不出来。
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
——李白《古风》
萝与蕤,是香草,是藤蔓,是繁茂而坚强的生命。赋予这名字的是她的父亲,赵紫宸,这位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大概永远想不到,这个名字将预示着这女子的未来,看上去脆弱不堪,实则坚韧不拔。
赵萝蕤,在燕京大学的绰号是“林黛玉”。我喜欢她一张弹钢琴的背影,时间在那一瞬间凝滞,仿佛留下的只有音符和属于她的优雅。香草美人,自然追求者甚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钱锺书,世间传说《围城》里的唐晓芙正是以赵萝蕤为原型: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据说当年电视剧《围城》选史兰芽做唐晓芙,杨绛先生很欢喜,理由是觉得史兰芽像自己。她呐喊若干次,讲自己就是唐晓芙,无奈吃瓜群众不响,更要命的是钱锺书也不响,“李唐赵宋”“牵芙连蕤”的隐语,实在有点昭然若揭。
杨绛和赵萝蕤是好朋友,或者说,曾经是。
她们的友谊始于清华,赵萝蕤小杨绛一岁,两人都是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所不同的是,杨绛由东吴大学而来,为的是圆梦(她之前梦想读清华);赵萝蕤燕大英语系毕业,读书是因为年纪还小,“不知道做什么”。
在宿舍,阿季还是和赵萝蕤交往较多。她们还一起学昆曲……赵萝蕤当时正在恋爱,追她的男生很多。一次曾问阿季:“一个女的被一个男的爱,够吗?”她的追求者之一、燕京同学吴世昌,从报上读了阿季的《收脚印》后,对她说:“杨季康,你可以与她做朋友。”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这段话有些女生之间的“不怀好意”,至少透露了两点消息:
一、赵萝蕤男朋友很多。
二、吴世昌曾经追过赵萝蕤。
只字不提钱锺书,或者用这个方式否定了钱锺书曾经追求过赵萝蕤。在这段描述里,赵萝蕤似乎离唐晓芙很远,离鲍小姐有点接近。
有趣的是,看过《围城》的赵萝蕤表示自己对于书里面的细节并不熟悉。谈及钱锺书时,她只说是“同学”,而杨绛则是“挺熟”。和扬之水的谈话里,有一段话显然可以看出说的是钱锺书:
又说起近来对某某的宣传大令人反感,“我只读了他的两本书,我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从骨子里渗透的都是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十七世纪如莎士比亚那样的博大精深他没有,十九世纪如拜伦雪莱那样的浪漫,那样的放浪无羁,他也没有,那种搞冷门也令人讨厌,小家子气。以前我总对我爱人说,看书就要看伟大的书,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耍小聪明,最没意思。”
——扬之水《〈读书〉十年》
我爱人,是她的丈夫陈梦家。
尽管有那么多人追求赵萝蕤,这个爱人,却是她自己主动追求的。
二
“是不是喜欢他的诗?”
“不不不,我最讨厌他的诗。”
“那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长得漂亮。”
——扬之水《〈读书〉十年》
不独赵萝蕤,谁见了陈梦家,不会夸一句“美哉少年”?
干干净净的模样,盈盈秋水,雕像一般的五官,带着温柔笑意的少年,我见了陈梦家的照片,只觉得词穷,想了半日,觉得“光风霁月”这四个字,并不唐突了他。
但我还是比赵萝蕤矫情,人家落落大方,只说他“长得漂亮”。
梦家这个名字,源自母亲怀孕时的一个梦,梦里遇见了一头猪。当然不可叫陈梦猪,“猪”字的甲骨文写法为“豕”,加一个宝盖头,便成了“家”。这个名字,大约算是陈梦家和甲骨文考证结下天定缘分的开始。
梦家中学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考进中山大学法律系,认识了闻一多,开始写新诗。作为新月派最年轻的成员,陈梦家在很早是以诗闻名的。俞大纲说他如王勃,“特具中国人的蕴藉风度”,而钱穆则说他“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我喜欢梦家的诗:
不祈祷风,
不祈祷山灵。
风吹时我动,
风停,我停。
这首《铁马的歌》写于1931年11月18日,那天白天,梦家和徐志摩在鸡鸣寺聊天,志摩说自己要过一种新的生活,梦家写了这首《铁马的歌》。第二天,徐志摩飞机失事。梦家的诗,竟然一语成谶了。
赵萝蕤说讨厌梦家的诗,理由是她反“新月派”,宣称自己要做一个理性的诗人。我见过她写的诗《游戒坛寺》:
山里颠了个把钟头,
清晨的风吹冰脸庞,
和车上那班旅行人,
同看龙烟厂的烟囱。
渡过永定河的泥水,
小驴也得得的过来,
十五里无理的尘土,
爬苍茫红叶的大海。
她爱他,似乎是有理由的。在遇到赵萝蕤之前,梦家有过轰轰烈烈的恋爱,对象是孙多慈,为了这个差点和好基友闹僵,然而最终两人都失败了,是《围城》里的“同情兄”。
1932年,二十一岁的梦家认识了二十岁的赵萝蕤。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了甲骨文的研究。普通人谈恋爱轧马路吃饭看电影,这对恋人谈恋爱的成果是1933年10月1日《文艺月刊》上刊登的《白雷客诗选译》,署名齁甜:萝蕤·梦家。
恋爱谈了三年,要结婚时却遭遇了不小的挫折,理由只有一个,梦家穷。赵萝蕤的母亲明确表示反对,她甚至停了赵萝蕤的经济供给。赵萝蕤一度要靠和杨绛借钱度日,每月借十元,等奖学金到了还,还了再借。最后,赵紫宸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的态度:
萝蕤:
你的信,我能了解。我心中亦能体谅。前日摄影,我本向你母说,请梦家在内,他犹豫,我便不再问。我们都是神经过敏的。我爱梦家,并无一丝恶意。我从去年到现在,竭力将你撇开去,像心底里拔出肉来一样,所以我非冷淡不可。你有你的生命,我绝对不阻挡,因我到底相信你。现在只有二件事:
(一)不要将孩子们的话,认真看。也不必向谁作解释
(二)不必重看母亲之举动。
信中之言,关系伦的事,我皆未知。我爱你们是赤诚。我冷淡,请你们撇开我如我撇开你们一般。
我认识梦家是一个大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我不怕人言。你们要文定,就自己去办;我觉得仪式并不能加增什么。
你们经济上我本想稍微补助些。但我目下尚不能,因我支票底根上只有三十一元了。除去新市立刻须寄廿元,尚有十一元,又不肯向徐刘李陆等开口借!以后你有需用,可以写个字来,我可以帮忙。看你认识我几分;我是没有人认识的!
---父宸
---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九日
1935年5月5日,陈梦家和赵萝蕤在燕大甘德阁订婚,订婚仪式是简单的,茶和点心。他们在七月参加了钱锺书和杨绛在苏州的婚礼,这两个女孩子在结婚仪式之后渐行渐远,尽管她们明明有着众多交集。就像赵萝蕤后来回忆的那样:“以后的几十年,我们几乎再没有来往,形同路人。”
三
倘若林黛玉结了婚,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怪兽:家务。这是所有知识女性在进入婚姻生活之后最大的挫折,在传统观念面前,女人天生是操持家庭的,哪怕她有那么多理想和事业心。很多女人败给了现实,连林徽因也不例外。只要看看她写给朋友们的信便可以知道。
1937年10月致沈从文:
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五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中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
1937年11月致沈从文:
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向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致费慰梅:
我继续扮演“魔术师”来玩耍经济杂技,努力使每位家人、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得到一些照顾。我需要不断地为思成和两个孩子缝补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有时我们实在补不过来时,连小弟在周日下午也得帮忙。这比撰写一整章的宋、辽、金的建筑发展和绘制宋朝首都的图像都要工程浩大。上面两项工作我很有兴趣也很自觉地替思成做过,在他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宝宝成绩很好,难为她每天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学校,而且中午她总是吃不饱。
赵萝蕤没有孩子,在家庭负担上比林徽因轻一些,她说自己“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她的牺牲不小,1938年,新组建的西南联大拒绝了赵萝蕤,理由是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而陈梦家已经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员。赵萝蕤选择了回归家庭,从做饭开始。她曾经发表过一篇《一锅焦饭 一锅焦肉》的小文,初到昆明的下马威,狼狈不堪的“林黛玉”。但她确实没有林徽因那么多哀伤,《一个忙人》和《厨房怨》中,把“灵魂交了出去”的日子充满了幽默感:
一早起来蓬头散发就得上厨房。
没有一本书不在最要紧处被打断,没有一段话不在半中腰就告辞。偶有所思则头无暇及绪,有所感须顿时移向锅火。写信时每一句话都为沸水的支察所惊破,缝补时每一针裁都要留下重拾的记认。
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柴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她渐渐学会了许多家务,后来连种菜也学:“菜园的总顾问当然是老朋友张发留君了,我从他学会了如何点刀豆,两颗一堂。”她说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悲观没用:“我觉得一切悲伤事结果都是最大的喜事,一切泪珠恨海在世界的喜剧场中都是些美丽的点缀,珍贵的纪念,活泼的教训,经验的演进……所以我对于悲观者永远怀着疑惧。”
也是在婚后,赵萝蕤翻译出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
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
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
……
我读了艾略特那晦涩的原文之后,才意识到赵萝蕤的翻译是多么精妙和准确。她的翻译甚至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证。1946年7月,艾略特曾经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夫妇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诗人在赵萝蕤带去的《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二书上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下“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题词。有趣的是,赵萝蕤出版《荒原》时,请叶公超写序(因艾略特是由叶公超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叶公超问:“要不要提你几句?”赵萝蕤清高地回答:“那就不必了。”
赵萝蕤靠译名摆脱了“燕京校花”(钱穆评价)称号,成为了实力派翻译家。这当然离不开她的努力,不过,作为丈夫的梦家,确实也和其他的丈夫都不一样。
他时刻照顾赵萝蕤的情绪,比如有段时间朱自清经常去陈家吃饭聊天,陈梦家代替赵萝蕤待客,甚至引起了朱自清的不快,回家在日记里写下“陈太太始终在厨房里吃面包黄油”。他时常鼓励赵萝蕤,希望她不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当陈梦家在金岳霖的推荐下获得芝加哥大学的讲学机会时,他拿出自己一部分奖学金,鼓励赵萝蕤读博士:
维尔特教授问我有多少时间学习,打算学三年还是四年?他说若是你跳过硕士学位这一关,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学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这时我想起了十岁时祖父和我的一段对话。祖父曾问我:“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我夸口说:“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我犹疑了。梦家此时却竭力说服我:“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我对维尔特教授说,那还是四年吧,我想多学一点……
——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
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奢侈的事,当然,现在也是。
1947年,陈梦家决定先行回国,赵萝蕤留在美国继续写她的博士论文。回到北平的梦家心里装着赵萝蕤,鱼雁往来之间,细细密密是他的温情:
小妹:
闻你欲作衣,在其店中挑一件古铜色的缎子并里子……
在东单小市买了小古董,银碟子陶镜子红木文具架子,一一写信和夫人汇报:
此等东西,别人未必懂得它的妙处,而我们将来万一有窘迫,可换大价钱也。……你看了必高兴,稍等拍照给你。
他断定赵萝蕤看了会高兴,因为他们的三观审美都很一致,从读书到欣赏艺术。陈梦家离开美国之前,赵萝蕤鼓励他在行李中塞满书籍和唱片,陈梦家“身上只剩十元,还要借垫付税”,因为“我和梦家商量,必须尽我们所能,享受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和个人文化教养有关的一切机会”。
但他们并不是贪恋美国的生活。1948年年末,当赵萝蕤听说平津战役打响,北平即将解放时,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她放弃了来年六月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的机会,搭乘第一条运兵船“美格斯将军号”离开美国,前往上海——很多年之后,当我们赞誉着钱学森等烽火中回国的赤子时,赵萝蕤的事迹被湮灭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她,沧海横流,这一刻,那个在无数人眼中瘦瘦弱弱的女子尽显英雄本色。
到上海,哥哥全家去了香港,去北京的火车和海轮都已经停运,赵萝蕤最终托查阜西帮忙,搭乘傅作义运粮食的飞机前往北京,至天津上空,她听到了解放军的炮声。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而陈梦家则用最浪漫的方式去迎接他的挚爱——他和朋友们骑着自行车,把赵萝蕤接回了清华。
四
博士赵萝蕤意气风发,她兴奋地发现新中国的旗帜下男女平等,女教授也能施展拳脚,她再也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因为丈夫的出色而不得不蜗居灶台,燕京大学外文系等着她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奋斗。
她邀请了仍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巫宁坤回国教书,当巫宁坤辗转到达北京时,他敏锐地发现,原本爱穿西装的赵老师换上了皱皱巴巴的灰布毛服。但不久之后的院系调整给了赵萝蕤一记闷棍。作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被解散,赵萝蕤被转去北京大学西语系,巫宁坤则前往天津。从来都在困境中颇具幽默感的赵萝蕤第一次放声大哭,为了巫宁坤,也为了她的壮志未酬。
这对天真的夫妇退回了书斋,退回那些明式家具之中,退回赵萝蕤心爱的斯坦威钢琴之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们以为书中自有岁月静好,可惜,只是一厢情愿。
我不想,亦不忍,把那些细细碎碎的折磨一一展现给读者。我宁可讲述在那些沧桑巨变之中,这一男一女的相互扶持。当陈梦家被诬陷贪污清华大学文物馆文物时,一向优雅的赵萝蕤用最通俗的话劝慰丈夫:
我告以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
陈梦家调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之后,夫妻分居城内城外,陈梦家给妻子写信,时常末尾一句是“你放心吧”。想起《红楼梦》里宝玉对黛玉语,他只要她放心:
今日因不放心你,心中不知何故非常难过。……现在但求一个“安”字。
压垮赵萝蕤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陈梦家在“鸣放”时对于简体字的批评,她精神受到严重影响以致失常。协和医院要把赵萝蕤送到疯人院,陈梦家求他的同事夏鼐去说情,最终出院。然而回家二十天,再次爆发,在给王献唐的信里,梦家吐露了心声:
我与她共甘苦已廿五载,昨日重送入院,抱头痛哭而别,才真正尝到了这种滋味。……
小小庭园中,太太心爱的月季业已含苞待放,令箭荷花射出了血红的几箭,最可痛心者是一群黄颜色的美人蕉全开了。美人蕉啊,何以名之为蕉?憔悴乎?心焦乎?
他想把赵萝蕤的工作从北大调到文学研究所来,这样自己可以照顾她,最终也失败了。他下放去居庸关劳动,几乎每天给赵萝蕤写信,写的都是细节,有点啰嗦,但是可爱的:
你的健康是我唯一挂心的事;但其实,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我的床上放的是你的黑大衣……
我买了几卷柠檬糖,居然想吃几颗了。
我理发一次后,并未剃胡子,棉衣很脏了,见到时不要怕。
……
他最想说的,其实还是这一句:
我们必须活下去,然必得把心放宽一些。
他这样劝她,他自己却未必做得到。
1956年,陈梦家写了《殷虚卜辞综述》,用这笔稿费买了钱粮胡同三十四号的四合院,十八间房屋组成凹字形,中间是小院。小院里有一棵小树,没有名,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我们只知道,十年后,1966年9月3日,梦家在这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五
我从前写过梦家的故事,这故事和梦家的骨灰一样不知所踪了,偶尔有人发给我看,署着别人的名字,我并不以为意,这是我对于梦家的祭奠,只要大家知道了他,于我便是值得。我仍旧想要在赵萝蕤的故事里写一写梦家,因为梦家是萝蕤的一部分,是她灵魂里最温柔、最有灵性的一部分。
梦家喜欢研究吃,再简单的食材,他也能欣赏出味之道。大白菜切成条,加胡萝卜丝和生姜丝,拌了白糖,他吃了一盘又一盘下酒,“中国菜肴举世无双,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梦家喜欢干净,“反右”之后家里不再有条件请用人了,但学生上门,发现他一个人做饭洗衣,家中依旧整洁如初。
梦家喜欢买家具,这些故事都被王世襄先生记录下来,往事历历在目,是活泼甚至有些欢快的,只在最后露出一点悲伤的余味,久久荡漾在我们心里:
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我以廉值买到一对铁力木官帽椅,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拿走。我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被他迎门拦住……
——王世襄《怀念梦家》
梦家喜欢晚上工作。赵萝蕤永远记得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梦家天天看到十点钟,太太去睡了觉,他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淡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如今,这足以令她心安睡去的声音,再也不存在了。
赵萝蕤的精神分裂症在最惨痛的那一天“拯救”了她,她没有见到丈夫最后一面,上天似乎用一种残忍的方式挽救了她,让她得以幸免于他最为凄惶的生命终点。我猜,那么光风霁月如梦家,也许也不愿意她见到这样的自己。
梦家用稿费购买的房子,她上交给了国家,象征性地拿了点钱,她去欧洲旅行了一次。这是赵萝蕤的作派。1981年,她重又访美,兴致勃勃地喝了百事可乐,收到朋友送的“当地视为稀罕的松子糖,其实哪比得过苏州的产品呢”。在西班牙风味的饭馆吃了奶酪塞辣椒、肉糜塞玉米饼蘸辣酱、油炸馅饼,她评价道:“口味都失之浓浊,我不能欣赏。”——在吃这件事上,她也和梦家一样,喜欢清淡。
她仍旧喜欢看书,并且如梦家希望的那样,一直在勤奋翻译。1991年她翻译了惠特曼的《草叶集》。1994年她发表的《读书笔记》上说,自己“这个八十出头的老妪”仍然“必须每天抽出两小时来阅读我刚刚收到的精装的1984年纽约大学版的惠特曼《笔记与尚未出版的手稿》(Notebooks and Unpublished Prose Manuscripts),共六大卷……我的职责不是研究原稿原样而是熟读正文,增加我对诗人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理解,正文当然是最宝贵的部分”。
在很久很久之后,她仍旧避免提起有关梦家的一切往事。巫宁坤在宾馆里询问梦家的最后,她忽然正色道:“你要让我发病吗?”她说的是实话。1991年,赵萝蕤参加芝加哥大学校友会活动。在芝加哥美术馆,工作人员向她出示梦家编著的《白金汉宫所藏中国铜器图录》时,赵萝蕤再一次恸哭失声,泪如雨下。她没有忘记,一天也没有,一小时也没有,一分钟也没有。
1998年元旦,赵萝蕤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她去世两个月之后,潘家园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保姆模样的人”,用麻袋装着赵萝蕤的日记、与梦家的书信,甚至她的家用本,开价达数十万元。幸好,这些书信被收藏家方继孝买下,刊登在他的《碎锦零笺》里。
我们难以评价赵萝蕤的一生,我只能说,如她的名字一般,赵萝蕤坚强地攀爬过那些苦难,蜿蜒曲折地绕过那些千疮百孔,一株女萝,一直到最后,仍旧带着芬芳,迎霜傲立。我们难以评价赵萝蕤的苦难,尤其当这些苦难最终只能被付之以“时代”两个字时,我们便更难以启齿。我坚信那个时代将永远翻篇,将永远不再回来。
如何度过生命的至暗时刻?赵萝蕤的答案是“不吃屎,不骑马”,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洋洋得意,不落井下石,不胡乱攀附。在黑夜里静静地等待,像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里写的那样:
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这篇文章写了大半个月,搁笔之际,忽然发现已是9月3日——梦家的忌日,冥冥之中皆有注定。谨以此文献给萝蕤·梦家,献给黑暗中的我,也献给所有感知生活不易的人们,让我们用梦家的话作为结语吧:
我们必须活下去,然必得把心放宽一些。
参考文献:
赵萝蕤:《读书生活散札》,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
方继孝:《碎锦零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4
子仪:《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