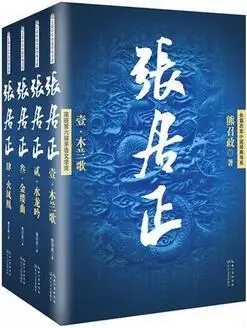波洛用一种审慎的腔调开始阐述自己对案情的解释。
“我的朋友,一个人居然策划自己的死亡,这种奇怪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吧?正因为此事太过蹊跷,所以你把事实当作妄想,反而宁可发明一个在实际中根本无法实现的故事。是的,雷诺先生策划了自己的死亡,但有一点你没有考虑到——他并没有打算去死。”
听罢他的话,我摇着头表示困惑不解。
“事情实际上很简单,”波洛和颜悦色地说,“在雷诺先生所犯的罪行中,正如我强调的,凶手并非此案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尸体才是。换言之,雷诺先生需要的是一具尸体,而非凶手。我们重新来梳理一下案情,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乔治·科诺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逃到了加拿大。在那里,他用化名生活并结婚,还在南美继承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但是他的乡愁始终挥之不去。二十年的光阴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相貌,再加上他地位显赫,没人会把这位成功人士和许多年前的逃犯联系起来,因此他认为回来了也没什么大问题。他把家安在英国,但他更愿意在法国避暑。或许是他运气不好,也可能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则引他走上末路,他来到了梅林维尔。全法国唯一能认出他的人就在此地。这对多布罗尔夫人来说无疑是个发财的好机会,面对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她肯定毫不犹豫。在多布罗尔夫人的操控下,乔治·科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她狠敲了他一笔。
“紧接着,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杰克·雷诺爱上了和他朝夕相处的女孩,并想和她结婚。这激怒了他的父亲,他会不顾一切阻止杰克和这样一个恶妇的女儿结合。杰克·雷诺对父亲的往事一无所知,但雷诺夫人却了如指掌。雷诺夫人是个具有巨大人格魅力的人,她愿意为自己的丈夫奉献一切。雷诺夫妇在一起商量的结果是:面对当下的局面,除了死别无他途。他必须假装亡故,然后逃到国外用化名开始新生活,而雷诺夫人也要扮演寡妇的角色,然后伺机和他团聚。若要如此行事,雷诺夫人必须掌握家里的财权不可。他们此前打算如何一步步从无到有地制造一具尸体的细节我并不清楚——或许一个艺术系学生学习用的骷髅和一把火足矣——或者是其他东西,可是这一计划成型之前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这倒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当时一个粗暴凶恶的流浪汉进了他家,发生了打斗。雷诺与他冲突之际,这名流浪汉突然癫痫发作倒地而亡。雷诺叫来妻子,两人一起将尸体拖进了小棚屋内——正如我们所知,这件事刚好发生在棚屋外。他们俩突然发现这是个上天赏赐的好机会。死去的流浪汉在相貌上没有任何与雷诺相似的地方,除了他是个普通的法国中年男子之外,但这点就已足够。
“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当时他们俩坐在那边的长椅上谈论事情,而屋里的人是无法听到他们谈话内容的。他们很快定下了计策:能够认出尸体的人必须只有雷诺夫人才行,杰克·雷诺和司机(他已经跟着主人两年了)必须不在场。家里的法国女仆似乎也不太可能接近尸体,无论如何,雷诺都要采取措施骗过任何可能探究这件事细节的人。于是马斯特斯被支开了,雷诺发电报给杰克,还选择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让整个故事听起来没有破绽。听说我是个高龄的隐居侦探,他便写了一封求救信,他知道当我到这里并掏出这封信时,这里的法官一定会大受影响——事实的确如此。
“他们给流浪汉的尸体换上雷诺的衣服,将流浪汉的破衣烂衫丢在小棚屋的门前,并未将这些衣物带进屋里。接着,为了给雷诺夫人将要编造的故事增加可信度,他们将那种用飞机金属部件制成的裁纸刀捅进了流浪汉的心脏。那一夜,雷诺将妻子绑起来并塞住嘴,然后用铁锹挖一个墓穴,他知道那地方准备挖成一个——你管那叫什么,沙坑?必须让多布罗尔夫人不产生怀疑,同时尸体也要尽快让人发现。隔些时日,死者被人认出身份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然后,雷诺会穿上流浪汉的衣衫逃至车站,接着不为人知地乘火车离开。因为案件原本应该在两小时后发生,所以没人会怀疑他。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当这个名叫贝拉的女孩突然到访时他会生气了吧?任何拖延对他们的计划都是致命的。因此他需要尽快摆脱这女孩,然后开始行动。他让前门半掩,给人造成凶手离开的假象。他将雷诺夫人绑住并塞上嘴,并纠正了自己二十二年前犯下的错误,不会绑得太松而导致自己被怀疑。这次他让妻子准备好的说辞和从前他编造的也差不多,可见这是下意识的反应,而非什么处心积虑的创意。当晚很冷,他在内衣外面套了件外套,打算把它扔到盛着死人的坟墓中去。他从窗户爬出去,将花坛上的脚印小心地整理好,掩埋掉了对自己最不利的证据。他走到空无一人的高尔夫球场,开始挖了,然后……”
“然后怎样?”
“然后,”波洛神色严峻地说,“他已逃避多年的应得惩罚突然降临,一只无名的手从他背后一刀刺入。现在,黑斯廷斯,你懂我谈的‘两起案件’是什么意思了吧?第一起案件,雷诺先生傲慢地要求我们去调查的,已经结案。但是它背后藏着一个更深的谜团,要解开这个谜团则更难——因为凶手十分狡诈,他充分利用了雷诺安排好的那些材料。直到现在这都是个迷惑难解的问题。”
“波洛先生,你真是太棒了!”我崇拜地惊呼,“绝对厉害!除了你,别人真做不到这些!”
我想我的赞扬令他愉悦。他几乎表现出了几分尴尬,这在他人生中还是头一回。
波洛想表现得谦虚一点,却并不太成功。他说:“毫无疑问那个可怜的吉劳德并不完全是个糊涂虫。他偶尔也背运,比如缠在那把裁纸刀上的黑色头发。不用说,那些都是误导信息,能让人误入歧途。”
“跟您说实话吧,波洛,”我缓缓说道,“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那是谁的头发呢?”
“那必定是雷诺夫人的,那就是所谓‘背运’的地方。雷诺夫人本来黑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几乎全白了,但是要找到一根灰黑色的头发也不难。只是吉劳德不假思索地认定那是杰克·雷诺的头发!事情就这么简单,人有的时候为了自圆其说,难免会去歪曲事实。
“毫无疑问,当雷诺夫人恢复过来时,她会把问题交代清楚的。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儿子会被指控为凶手,这怎么可能呢?当时她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正在安茱拉号的甲板上安然无恙地航行啊!这就是女人,黑斯廷斯!多么强大,多么有自制力!她只犯了一个小错误。在杰克·雷诺出人意料地回来时她说了一句:‘现在这都已不再重要了。’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些话的重要性。这个女人承担了一个多么可怕的角色。想象一下当她发现尸体时遭受的打击吧!难怪她晕过去了。但从那时起,虽然绝望悲伤,可她多么彻底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她又被痛苦折磨到多么严重的地步啊!凡是会让我们追查到真凶线索的话,她一句也不能说;因为她儿子的缘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保罗·雷诺就是杀人犯乔治·科诺。最终也是最沉重的一击,便是她要公开承认多布罗尔夫人是她丈夫的情人——但凡透露一点点被勒索的暗示,她的秘密都会公开。当地方预审法官问她关于她的丈夫过去的生活中可曾有过什么疑团的时候,她的应对是多么的聪明啊!‘我确信没什么浪漫的事,先生。’这样的回答很完美,那种任性的口吻,些许忧伤嘲讽的意味,一下子让阿尔特先生感到了自己的愚蠢和夸张。是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就算她爱上的是一个罪犯,她的爱也是庄严崇高的。”
波洛陷入深深的沉思当中。
“还有件事,波洛——那段铅管是怎么回事儿呢?”
“你还不明白吗?那是为了让受害人的脸彻底被毁,这样就无法辨认了。这是让我走上分析案情正轨的一点,可是吉劳德这个愚蠢的家伙可能还在满地爬着找火柴头儿呢!难道我没告诉过你一个两英尺长的线索和一个两英寸长的线索一样管用吗?要知道,黑斯廷斯,我们必须从头梳理一下。谁杀了雷诺先生?那个凶手当晚十二点前在别墅附近——这个人一定可以从雷诺的死当中获得好处——这样的描述跟杰克·雷诺太符合了。这宗谋杀不需要预先设计。对了,还有那把裁纸刀!”
我猛然一惊。我没有意识到这点。
“当然了,”我说,“插在流浪汉身上的刀子实际上是雷诺夫人的,也就是第二把刀。那么一共有两把裁纸刀了?”
“没错,而且这两把裁纸刀一模一样,这点完全说明了杰克·雷诺是裁纸刀的主人。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困扰我。实际上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对他最糟糕的控告其实还是心理层面的——遗传,我的朋友,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杰克·雷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乔治·科诺的儿子。”
他的语气严肃认真,我不知不觉深受感染。
我问他:“你刚刚提到你有些想法,那是什么呢?”
波洛看看他的大怀表,反问我:“下午从加来开来的船几点钟到港?”
“我记得是五点。”
“那很好,我们还有时间。”
“你要去英国?”
“是的,我的朋友。”
“为什么?”
“去找可能的证人。”
“谁?”
波洛的脸上浮现出一缕诡异的笑容,他回答道:“贝拉·杜维恩小姐。”
“但是你怎么找她呢?关于她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对她一无所知——但是我觉得我能猜出不少内容。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她的名字就是贝拉·杜维恩,虽然斯托纳先生隐约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但明显和雷诺家族没关系,她可能只是个演员。杰克·雷诺才二十岁,年少多金,舞台必定是他初恋的归宿。这从雷诺先生试图用支票安抚她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我觉得我会顺利地找到她——尤其是我找到了这个东西。”
他拿出一张照片,我曾亲眼看到他从杰克·雷诺的抽屉里拿走的。照片的角落潦草地写着“爱你的贝拉”,但这些字并没有吸引我的目光。并不是非常像——但对我来说一定错不了。我感到阵阵寒意在沉积,仿佛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沉重一击。
那是灰姑娘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