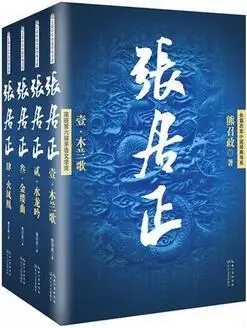北宋年间,闽海都巡检林惟悫重病在身,每日进食不过一盅,进药却满满三碗,病还是一时时往膏盲里去了。
他的发妻王氏,已先他撒手西行,唯一的爱子林洪毅,也早年葬身海腹。五个女儿出嫁在外,膝下只有最小的女儿默娘和一个婢女小眉。
“小眉,阿默到哪里去了?”垂危的老人从昏睡中醒来,不见女儿,声音颤抖地急急问道。
“小姐正在向菩萨进香,她发愿欲减自己三十年阳龄,求能添您十年寿数。”
几滴巨大而沉重的泪珠,沿着老人瘦削的脸庞滚落下来。林惟悫已无力转头,泪水便象一只透明的小虫,流进他的耳朵里,先热而后凉。
女儿,你好傻呀!
默娘早已长大成人了,她知天文水象,会行医治病,俨然一方灵女。附近渔船去海捕捞以至蕃舶远涉重洋,无不向她打探海情,但在父亲眼里,她却永是那个生后一月还不知啼哭的婴孩。林惟悫知道,自己的病对女儿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现在,他不再忧愁自己的生命,而在思虑没有了自己,女儿将如何生活下去。
也许不该为她起名“默娘”。女儿内心秀慧,外表却极庄重。她的几个姐姐,都已儿女成群,唯有阿默,矢志不嫁。以前她母亲在世,没有少劝过女儿,默娘总是安安静静地听着,侍到母亲再也没有什么要嘱托的话了,才低着头,顺从地说一句:“阿妈,我知道了。”之后便绝无下文。她知道了什么?知道了这是天伦之常,还是知道了这是父母的一片苦心?林惟悫不知道。这是一个大题目,老父亲知道自己是无力说服女儿的。
那么,从此她就要孑然一身了……
“阿爸,您今天看起来,气色要好得多了!”林默娘推开房门,放进灿烂的阳光,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她身穿一袭素雅的衣裙,脸色十分苍白。因为有了做作出来的惊喜,面容才有了一层轻淡的红晕。
“阿默,我也觉得好多了。”
林惟悫尽量将所有的气力都集聚到咽喉,那声音便真的显出清朗与平稳。
接着,便是静默。长久得令人感觉到压抑的静默。远处,传来涛声。无边的海浪象一曲低吟的悲歌,徐缓而滞重地拍打着沙滩。
讲完了久已想好的第一句话,下一句该说什么?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又都怕对方识破自己的假话。在生与死的藩篱面前,最亲近的人也变得如此陌生。
忽然,一团嘈杂的人声由远而近。
林默娘焦虑地蹙紧眉头。父亲病重,气息已若游丝,任何一种紊乱的声响,在他都如斧砍刀劈。她低声唤过小眉:“你去对外面的孩童们讲,请稍静息些。就说我阿爸倦了要睡,求他们到远处去玩吧。”
小眉点头应着,象一片轻灵的落叶,无声退去。
默娘绞了一方丝帕,轻柔地拂去父亲额上的水迹。林惟悫昏然睡去,冷汗如油。她心中不由得痛苦地一悸:这是恶兆。老父虚阳外越,性命已危在旦夕了!
无论林默娘怎样命令自己,万不可在父亲面前哭泣,泪水还是难以抑制地往下流淌。
门外的嘈杂错乱之声,不但没有熄灭,反而象涨潮一样,越来赵暄嚣了。
林惟悫终于被惊醒了。这一次,他真的感觉清爽多了。
“阿默,你哭了?”他亲切地问女儿。
“没有,阿爸。不过是刚才进香时灰刮进了眼睛。”林默娘连忙拢拢头发,将泪水擦干。
惟悫悠长的叹了一口气。从小看大的女儿,瞒得过旁人,你还瞒得过阿爸么?
“默娘,听阿爸问你一句话。”林惟悫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需要赶紧作。
“阿爸,我听您说。”林默娘端来一把小竹椅,偎在阿爸的病榻前。一刹时,光阴仿佛迅速地倒流回去,满头青丝的林惟悫正在给咿呀学语的女儿,讲着古老的故事。
“默娘,你说这天下之大,莫过于哪里?”林惟悫虽然喘息不止,双目却依然闪着睿智的光芒。
“天下之大,莫过于沧海了。”林默娘略一沉吟,随即答道。
林惟悫微微颔首。默娘是他最疼爱的女儿,也是他最聪明的女儿。八岁时同哥哥一起入私塾读书,先生只教了一遍,一向号称聪颖的洪毅尚未听懂,默娘已耳熟能详了。
“阿爸再问你,这天下之险,莫过于哪里?”
“这天下之险么”,林默娘稍费思忖,“闽距京城万里,重山叠蟑,这大约就是天下至险的路了。”
“不对。默娘,再好好想一想。”林惟悫困难地皱了皱眉头。
林默娘开始只当父亲不过随便说说,见老人真的动了神恩,也就仔细琢磨起来:“阿爸,我晓得了。小时候读过李白的诗《蜀道难》,‘噫吁唉,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这天下之险,该是指蜀道了。”
林惟悫已无力用手去抚摸女儿的青发,他慈爱的目光温暖地注视着默娘:“阿默,你还是没有说对。这天下至险,并非蜀道。”
“这……”聪慧的林默娘难得地语塞了,她秀美的双目从父亲脸上移到挂满字画的墙壁,又从墙上窗口游到广袤的天空……蓦的,她感悟到什么,刚要张口,又灵巧地将话语象青橄榄一样含在舌下,换了一句:“阿爸,我真是猜不出来。您告诉我吧!”
面对着女儿小小的娇憨,林惟悫苍老的面颊浮现出生动的微笑:“你眼睛怎么光望着天外,竟忘了自家脚下。这天下至险者,莫过如海道。”
一阵庄严而可怖的惊涛声拍岸而来,单凭那宛若千百面战鼓声的巨大轰鸣,就可以想见那壁立的波峰浪谷是怎样陡峭而狰狞。
林默娘没有答话。她是海的女儿。对于海的威严,海的暴烈,她比别人有着更深切的体会。父亲的一生,都是在海上渡过的,父亲对海,了若指掌。只是这个时候谈论海,对于一个垂垂老矣的病人来说,是太不相宜了。
“默娘,你知道天下至不仁者,是哪个么?”林惟悫自己转换了一个话题。
“天下至不仁者,莫过于盗贼了,阿爸。”这一次,林默娘不假思索地答谊。她知道父亲一生缉盗,最痛恨杀人越货的剪匪了。
“阿默,你说得极是。”林惟悫嘉许地点点头。这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出于对自己一生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林惟悫的脸上焕发出光彩。
窗外人声鼎沸,一时间竟压过了汹涌的涛声。小眉匆匆赶了进来:“老爷,小姐,门外聚了许多等待出港的渔船,想向小姐打探一下天气海情。不然,大家都胸中无数,不敢扬帆远航。”
林默娘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天被赫色花岗岩的窗榻子囚禁着,分割为破碎的残片,半朵白云窗花似地缀在窗洞边,看不出是想飘过来还是要散了去。林默娘又轻轻搭起父亲的脉息,极细极软,似有似无,有边无中,起落模糊、如扪及一截的熟的葱管,已是极重危之象了。
“小眉,你去告诉乡亲们,父亲今日……病体欠安……”无论默娘怎么克制,话语中也带出呜咽之声。她调起全身精气,以让自己不要过分失态:“请乡亲们多多见谅。这看天观海,原需极沉稳的心境,默娘今日实难安心。待父亲病体稍稍见好,默娘一定登门将海象告知大家,望乡亲们请回吧!”
林惟悫听言,刚要说什么,一股浓痰翻涌而上,哮喘不止,话终于没有说出来。
小眉走出去了。嘈杂之声象被一床棉絮罩住,渐稀渐薄渐远,终于寂静如轻烟般飘散了。
“默娘,你告诉阿爸,阿爸的病,究竟怎样了?”待喘息稍定,林惟悫虚弱地问女儿。
“阿爸的病正一天天好起来。”林默娘直视着父亲的眼睛,毫不迟疑地说。她一点也不感到自己在撤谎。尽管父亲的脉象气色和心中的预感,都恰恰与之相反。但此时此刻,她完完全全明明白白地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
“默娘,休要瞒阿爸了。你从小就能预知吉凶祸福,还记得你十六岁那年的事吗?”
“不……不……阿爸,我不记得那些事了。小眉,你快把我炖的参汤端来吧。”林默娘实在不愿父亲在此时回忆如此悲的往事。
林默娘的苦心没有效果。林惟悫以老年人的执拗,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痛苦和欢乐,象一尾尾鲜活的鱼虾,闪着耀眼的鳞光跳跃而起。
那一年的扶桑花开得如火如荼。一朵朵嫣红的花穗,象一把把朝天的喇叭,不知疲倦地吹着欢愉的乐曲。长长的花蕊象调皮的少女,不听管束地从花芯匍匐而出,探头探脑看到外面五颜六色的世界后,又羞涩地低下了头,把纤巧的腰身弯曲成一道美丽的弧线,象对人们行着优雅的“扶”礼,衬以苍翠如滴桑叶形的叶子,难怪人们要称它为“扶桑”了。
哥哥洪毅将一朵扶桑花,插到小妹发中。
“阿默,你答应我的‘百子图’,可要快快织,不得偷懒哟!”
洪毅就要同父亲驾舟渡海北上,一家人在海滩上为他们送行。洪毅与小妹说着玩笑,他下月便要赴京赶考,默娘答应要送哥哥一幅百子图织锦,因为今日看天,明日观海,锦上一百个孩童,竟总也织不完。
“哥哥,你与阿爸此次出海,几时回来?”
“三天后定可回来。”林洪毅很有把握地说。
“百子己织了九十,还有五双,三天后定可织完。”林默娘也很有把握地说。她猛一抬头,看见哥哥,突然象看到一位陌生人,再看父亲,也觉得与平日有异,不安象潮水般铺天盖地而来。
这是怎么回事?亲人出海,该带走美好的祝福,林默娘极力排解着心中的忧郁。情感的潮水退去了,但不安的思绪却象礁石般屹立在原处,噬咬着她的心灵。
“阿爸,阿爸,今天就不要出海了。改一改行期吧!”林默娘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天蓝得令人眼晕,在极高远的天际,飘拂着丝缕状的云翳。云层轻薄得几乎透明,唯有四周垂下耳环般细致精巧的钩簇。阳光沁过薄纱般的云网飘然而下,化作点点金屑,装点着平滑如镜的海面,看不出丝毫恶兆。
“阿默,阿爸公务在身,要去缉拿一伙作恶多端的盗贼,时间紧逼。”林惟悫对女儿说。
“小妹,有我做阿爸的左膀右臂,你就放心好了!”林洪毅充满信心。
爸爸和哥哥走了,林默娘的心,也跟着走了。她强制自己坐下织锦,心中却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哀伤。她忍不住丢下梭子,又跑到海边。两天两夜平平安安过去了,到了第三天早上,天上的云,迅速地聚和又分离,仿佛彼此间在争斗不已,终于又恢复了暂时的安宁,但顷刻间云丝又变幻得犬牙交错,精巧的钩簇膨胀锋利起来,象一柄柄青钢打铸的利箭,从变成苍黑的天穹俯探下来,直楔海面。
西风起了,大海掀起狂涛。
林默娘忧心如焚,把自己关在室中拼命织锦,这可是哥哥要的百子图啊!头上的扶桑花已经枯萎,哥哥今天就要回家了。一百个快乐无比的孩子已经织完了九十九个,只剩下最后一个。正确地讲,这最后一个孩子也已经织完,只剩下他一双胖乎乎的小手。
织机声铿锵,海涛声匐然……
忽然,眼前的锦缎陡起波澜,林默娘看到父兄的帆船在狂风中激烈颠簸,橹倾舵折,情形万分危急……
妈妈听到织房内声响怪异,完全不象默娘平日织锦时的从容镇定,急忙走进去看。只见女儿一手抓梭,一手扶抒,两脚将机轴踏得上下翻飞,脸色如霜雪一般惨白,珠贝似的牙齿将嘴唇咬得渗出血丝,一粒粒汗珠把漆黑的鬓发胶粘在一起,象一片片被淋湿的鸦羽。
“阿默,你怎么了?快醒醒!”妈妈惊恐万分,连声呼叫。丈夫和儿子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生死未卜,最心爱的小女儿又突发急病,怎不叫她心如刀绞!
林默娘手中的织梭,象一条濒死的鱼,沉重地坠落到地上,溅起一片飞尘。她疲惫地睁开双眼,茫然地打量四周,仿佛完全不认识这个家了。待看到哺育自己一十六个春秋的母亲时,这才猛然清醒过来,顿足痛哭道:“妈妈,妈妈!您不该把我叫醒啊!我刚才脚下踏着阿爸的船,手里抓着阿哥的船,我想把两条船拢到一起,正在拼命与风浪相搏……现在,父亲得救了,哥哥他已经……不在了……”
妈妈半信半疑,只当女儿是忧思过甚,忙安顿默娘躺下好好歇息,一边派人去打探消息,没想到结果竟同默娘所说一模一样。
多少年过去了,林惟悫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怒涛中,似乎有一股神力自天而降,帮他稳舵操桨,与爱子的船一寸寸靠近……他伸出自己青筋毕露的手,握住女儿纤巧秀丽的手。当年,这双手挽狂澜于既倒,把父亲从风暴中拯救出来,现在,父亲要把最后的力量,传递给从此孤独地留在世上的女儿。
林默娘还沉浸在悲苦之中。哥哥要的那幅百子图,终于没有织完。第一百个孩子手中所捧的寿桃,永远地失落了。
“默娘,你见过江河是怎样人海的吗?”垂危之人的思缕,也如风筝一般飘忽无踪,林惟悫又跳跃到另一个话题了。
“江河入海,见过的,阿爸。不就是淡水汇到咸水里去了吗!”林默娘强忍悲槍,顺着父亲的思绪说去。只要父亲不再追忆失去爱子的痛苦,她愿意同父亲谈论任何话题。
“那江河入海之处,江便渐渐地宽,岸便渐渐地远,水便渐渐地缓,终于和浩翰无涯的大海,汇成茫然不分的一片。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江和海的界限了。”林惟悫深邃的目光望着遥远的地方说。
林默娘点点头。她虽然聪敏,却还悟不出阿爸这番话的深意。
“默娘,在为父看来,这江河好比是人的生,这浩森的大海,就是人的死。无论人的一生多少跌宕起伏,逶迤蟠曲,最后终要归人横无际涯的大海。阿爸现在,就已到了这江与海的交汇之处了。”林惟悫安详地说。
“阿爸……”
林默娘想反驳父亲几句,想安慰父亲几句,但在林惟悫肃穆如天寥阔如海的睿智面前,所有的语言都褪为苍白。
“阿默,不要为父亲悲伤。作为一个驰骋海疆的都巡检,同至险至恶的风浪海匪为伴,我能享此高寿,已是天幸了。”林惟喜深长地吸了一口气,抖擞精神又往下说道:“默娘,你已经长大了。这些年来,阿爸看着你为乡亲们治病解难,造福桑粹,心中甚感宽慰。我与你母亲一生为善,菩萨便给了我们你这样一个好女儿,我和你阿妈,也可以含笑九泉了。我就要去了,你万不要太悲伤。你看,在江和海的交接处,江和海都是那样的博大而平稳。何况,在海的那一边,站着你的列祖列宗,站着你元疾而终的母亲,站着你英年早逝的阿哥……我们会在海的那一边,天天为你祝福。”
“阿爸啊……”林默娘压抑了许久的泪水,象扯断的珠链一样纷披而下,她痛彻地哭泣着,天地为之动容。
阿爸的手,握着她的手。一种源远流长的生命,在其中传递。
“阿默,该说的活,阿爸都已经说过了。阿爸不懂你的神术,但相信你所说的观天测海须要心静。生生死死,犹如潮起潮落,皆是天命,非人力可以抗拒。乡亲们既来问你海象,你就最后听一次阿爸的话,安心测海去吧!”林惟怠说完这长长一席话,已是殚精竭虑渐入弥留了。
林默娘的泪水已经干涸,她怔怔地望着面容清癯形色枯槁的父亲,看到他的眼睛如同暗夜中的火把一样熠熠发光,那光芒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它充满博大的智慧,也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深诣医术的林默娘,知道父亲最后的时刻到了。
“默娘,你快去呀!”父亲的口唇翁动,声音已微弱得几乎听不清了。
一切针砭药石都已无济于事,但默娘不能走,不能走啊!
父亲还在喃喃低语,梦吃般地重复着他的嘱托。
林默娘犹若石雕一般地站起身,巨大的悲戚象台风一样旋转翻腾,她的心却如风墙中的风眼,铁水般地凝结了。
父精母血,曾经给了林默娘血肉之躯,现在,父亲的爱与智慧,象温馨的巨掌,将林默娘托举到了一个超凡人圣的境界。父亲的血脉在她身上涌动,父亲的生命,在她躯体中延续。父亲将永远与默娘同在!
“阿爸,我去了。”林默娘俯在林惟患耳边轻轻说。仿佛一个小女孩告诉正在午后小憩的父亲,她要到海边去捡贝壳。
林惟悫突然睁大了眼睛,脸上因此显得生机勃勃:“阿默,穿那件红衣吧。碧涛万顷之上,朱红最鲜明悦目,阿爸远远地也能望得到你。”
林默娘换上一套朱衣,裙裙飘飘,宛若一片灿烂的红霞,来与父亲辞行。
“你若上湄洲屿,带上小眉一起去吧。”林惟悫说。
“不。阿爸,小眉还是留在您身边,也好有个人服侍。我不要紧。”一向温顺的林默娘,这一次不再听从父亲。
“我身边有邻人照料。湄洲屿风大浪急,你一个人去,我实在是不放心啊!”林惟悫的感情向来锁闭很深,也许意识到诀别在即,他难以自制,声音硬咽。
林默娘不敢再忤父意,与邻人交持了几句,服侍父亲喝下参汤,携了小眉,便出门去了。
林惟悫困难地侧转身子,用昏花的老眼伴随着林默娘远去的身影。紫衣红裙,飘然而去,象一片越飞越远的枫叶……他多么希望女儿能再回一次头。看一眼他,他再看一眼女儿啊!
林默娘始终没有回头。她一步又一步,艰难却决不迟疑地向前走去。她知道自己若回一次头,就再也没有勇气举起脚步了……
于是,在林惟悫渐渐涣散冷却下去的瞳孔里,便永远留下了女儿火焰一样的背影……
无垠的东海如同一张喜怒无常的神秘之面,傲然漠视人世间的一切疾苦。随心所欲地翻云复雨。湄洲屿象一道黛色的浓眉,横亘于海涛之上。湄洲峰象攒起的眉棱,冷对着苍天碧海。
林默娘挽着小眉,行走于犬牙交错的礁石之上。小眉是穷家女儿,筋骨强健,她日夜照顾默娘起居,知道因为父亲病重,林默娘忧心如焚,多日几乎水米不进,身体十分赢弱。但一到海滨,默娘轻捷如鸟,竟完全甩开小眉,跳越于礁盘之上,仿佛一股游动的蜃气,海风将她黑色的秀发吹拂而起,象一面忧伤而悲壮的灵旗。
“默娘姐,等等我!”小眉气喘吁吁地叫道。
“我等你,潮水不等人哪!”林默娘无暇他顾,飘然向大海深处越去。
海在一瞬间,向林默娘展开了它的全部秘密。
默娘眼中,海象柑桔一样地裂开了,一层层的海浪象书卷一样排列分明。在重重叠叠的水波之中,鱼和虾在缝隙中行走。那青莲色的水流,是东海的老住户了,是父老乡亲们耕海的辽阔土地。那黑瓷色的水流面带险恶,其实并不伤人。它从远道奔涉而来,不过是东海水国的匆匆过客,还将挟着万钩之力奔流而去。它象一匹烈马,脚力雄健,只要驾驶得当,远航的番舶便可以飞快地返回故乡了。不好!在恍若绿色梯田一般的水带中,林默娘突然发现丝丝缕缕血色的纹路。她以为自己体虚眼花,闭起眼睛,调理气息。待再睁开眼时,那红色不但没有消失,反倒渐渐丰厚起来,象一股锈水,无声无息地潜入碧绿的海域之中。
林默娘感到红色的潜流那么神秘,那么陌生,裹携着一种恐怖的寒冷的气息,蜿蜒而来。
林默娘焦灼地紧绞起手指,还是理不出头绪。观天测海这么多年,她已经很有经验。再遇到父兄出海时那种貌似温柔的钩钩云,她是再也不会放他们出海了。天上钩钩云,三日之后雨淋淋……可眼前这股险恶的浊流,它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全不知晓。怎样才能进开它们的灾祸,乡亲们在等着默娘!
还是父亲说得对,默娘该来测海了。现在,几天前的海潮一无所知,林默娘面对着的是一片残简,却要推断出一本书的学识。
默娘知道,人们都称自己为神女,但自己是人不是神,此刻,便感到束手无策。
“小眉,我要上湄峰”,海天毗连,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林默娘决心攀上湄洲屿最高峰。
“默娘姐,万不能上。湄峰山高峰险,小姐万一有个闪失,小眉如何向老爷交待!”小眉一把抱住林默娘,不让她走。
提到老父亲,林默娘的心象放入滚油中烹了一下,痛彻入骨,她屈指一算,父亲正在病榻上辗转反侧,切盼她归去,但这一团未解之谜,如何向父亲陈说?面对乡亲们渴求的眼睛,默娘是让他们升帆还是收橹?
林默娘鼓起勇气,用力推开小眉。小眉一个趔趄,仆倒在地。一向宽厚的林默娘也顾不上管她,兀自向湄峰爬去。
湄峰终于象一条卧蚕,臣伏在林默娘脚下了。湄峰上怪石耸立,阴森可怖鳞峋峥嵘。林默娘傲立其上,面对着苍茫的海天。
南来北往的风,象一条条勾摄人的绳索,缠绕林默娘而过,每一股都想将她攫入深渊。林默娘纤纤素手攀住岩石,仔细地观察着风的轨迹。渐渐,熙熙嚷嚷的风便在她面前规矩起来,象莆田街上过往的行人,有熟面孔,也有异邦人。
林默娘伸出食指,试那瞬息而过的风的温凉;林默娘探出舌尖,吮那飞逝而去的水雾,分辨蕴含其中的极细微的酸辣苦咸。风和雾便乖乖地把自己的奥秘告诉林默娘。
蓦的,林默娘嗅到一股极怪异的气味,她急忙耸动鼻翅,那气息又幽灵般地散失了,遗留给人莫名其妙的恍惚。
“默娘姐,快快回去吧,天就要黑了……”小眉跌跌撞撞而来。
“小眉,这山顶风大,你快回家去。我还要到那块风动石上去看一看。”
前人说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山野之中,只有去登那最高的顽石。
风动石仅一点触地,庞大的身躯被海风拨弄得如同滚珠,不要说登上去,就是看着也眼晕。
小眉知道劝阻不住,只得用全力稳住风动石,想给默娘助一臂之力。
林默娘站在风动石上,风象残酷的巨掌,想把她抛进大海。她的双脚象生了根,钉在石缝之中,随风仰合。天和地象两页巨大的扇贝,林默娘屹立天地之间,象一颗红光烨烨的珍珠。
终于,林默娘看到了,在几千里之外,有一树黑色的棕榈开放在云间,它结着毒蘑菇一样的花朵,放散着煤炭般的黑光,旋转着向这里逼来。那血色的颗粒,那冷腥的气息,都是那黑色的怪物蒸蔚而来,那是龙卷风的踪迹啊!
“小眉,快走!”林默娘一个箭步跳下风动石,一阵飓风袭来,差点将她掳去,多亏小眉死死将她抱住。
她们快步下山,仍是默娘在前,小眉在后。林默娘一看到几艘帆船要起航,更是脚下生风,飘逸如飞。
海,真是诡橘之极。山下无风,海也异样的平静,几艘船已起锚。
“乡亲们,快快收帆。今夜必有……”林默娘大声呼唤,未及说完,一位邻居狂奔过来:“小姐,大事不好!老爷他……他过世了!”
林默娘一霎时并没弄懂这句话的含义,她还在想着即将来临的风暴。倒是小眉哇地一声先哭了出来。
林默娘如遭雷殛一般僵立着。阿爸,您真的不等默娘,就这样走了!就这样走了吗?!
连日忧心如焚,加上方才与狂风巨浪精气相搏,林默娘一声未响,象被刀砍斧劈一样,直挺挺颓然倒在冰冷的海滩上。
人们忙着救护林默娘。
许久,林默娘才从昏迷中醒来。
“小眉,快告诉乡亲们,不能出海。”林默娘无力地吩咐完,这才大睁着无泪的双眼问大家:“阿爸他仙逝之时,您们谁在近旁?”
“阿默,我在近旁。”一位邻人垂手而立。
“阿爸他走时说什么?他可留下什么话?”林默娘急不可侍地问。
“他……他老人家没留下什么话……他说……”邻人左右为难,慌不择言。
“你倒是快说呀!我家老爷最疼爱小姐,他一定给小姐留下话了!”小眉急得恨不能伸手从邻居喉咙里掏出话来。
“老爷他说”,邻人下了决心,不管是何结果,他都该把老爷最后的话,告诉他最心爱的女儿。“老爷最后一直在呼唤:‘默娘,你在哪里……’直到瞑目
“默娘,你在哪里?”
林惟悫临终时的殷切呼唤,在寂静的海滩上回荡,被无数座礁盘重复着,化作巨大的轰鸣,敲击着所有人的心扉。
林默娘就在那里。在冰冷的海滩上,无泪、无声,宛若亿万斯年前就坐化在那里了。
不知过了多久,林默娘突然从自己胶结的睫毛之中,看到了一个移动的黑点。她以为那是一个蠓虫。蠓虫却越来越大,生出白色的翅膀。那不是翅膀,是帆。那是一条商船。
“小眉,你把巨风的消息告诉大家了吗?”
林默娘焦的地问。
“告诉了。当地的乡亲们都听了您的话,收帆回港了。这是艘番舶,我也同他们讲了,但就是不听。”小眉委屈地说。
林默娘困难地向番舶走去,乡亲们默默地跟随着她。
“请问,你们是到哪里去?”林默娘用尽气力,声音还是很微弱。乡亲们七嘴八舌地招呼,番舶靠近岸来,船上走下一位长髯飘飘的番客,两只眼睛如鹰隼般锐利,被一袭雪白的长袍。“我们要回大食国去。”他的汉话竟说得相当好,看得出是浪迹天涯的常客。
“大食国距闽海有十万里之遥,那是个极远的地方。”林默娘缓缓地说。
“看不出小姐闺阁之人,深谙海事,舟船日夜兼程,也需半年才可达。”番客略微收敛了一些傲气。
“既是半年才可到达,并不争片刻之时。你们今天不能走。”林默娘道出本意。
“海上此刻风平浪静,小姐为何阻拦我们?”番客佯做不知。
“今夜必起风暴,强行开船,恐有性命之虞。”林默娘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听的人无不为之一凛。
番客却朗声大笑起来:“鄙人舟揖海上数十年,这看天测海,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八九不离十。看这天清如水,海平如镜,正是一路顺风之兆,请小姐不要阻拦。”
“今夜风之怪诞,前所未见。为了船上舟子身家性命,客人万不能走船。”林默娘口气坚决,毫无商榷之意,好象她是这般上的主人。
番客拂然变色:“这船上所载瓷器丝帛、珍珠翡翠,价值数十万金,压在港口一天,便要坐失利息千金。小姐百般拦阻,不知小姐可愿负担这笔巨息?”
众哗然。大家说:“这番客不识好歹,由他去吧。”番客见动了众怒,毕竟是在大宋国的境内,他缓缓口气说:“实是赶路心焦。你们看,这不是风和日丽、海晏天清吗!”
大家仰头望去,红日西悬,海鸟翱翔,果然一片太平景象,不禁心中也有了几分疑惑。
番客号令开船。
大家劝默娘先回家去料理丧事。
林默娘这才微微有些急了,她高声对番客说:“天道无常。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未。你既会看天,”她朱衣长袖一甩,伸手掠来空中一缕流云:“你过来看,这云中饱含肃杀之气,不过今夜子时三刻,必有血雨腥风而至。”
番客惊惧不已,忙跳下船来,众人也好奇地聚过来看。
林默娘惨白如蜡的手中,一无所有,只粘着几粒她刚才跌倒在海滩上未及拂净的素沙。
面对着大家一脸骇然之色,林默娘又弯腰掬起一捧海水:“你们看这海浪之中,已点点滴滴散布血色颗粒。这是巨风前兆,是从万里之外的海域冲刷而来的。”
众人每人依样画葫芦,各掬起一捧海水,连番客也照此办理,把漂亮的长髯也浸湿了。
海水清冽见底,偶尔舀进的透明小虾,在水中活泼泼地嬉戏着。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齐刷刷地聚在林默娘身上。
番客的神色已变得倨傲而冷漠。
一阵无尽的哀愁和孤独,雾一样地向林默娘扑来。她惊疑地问小眉:“你真的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闻不出么?”小眉大睁着迷悯的双眼,摇摇头:“真的,小姐。我不能骗你,我一点也看不出这海水与平日有什么不同,也看不到你手中的云。”
林默娘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无力地把挂在袖口上的云摘下来。一松手,那云摆摆尾巴,飘飘悠悠,直上九天去了。
番客再令开船。
林默娘已然绝望了,但一船舟子的性命,把她的心压得铅舵一样滞重,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她也要拯救生灵。猛一抬头,她心有所得,指着东方天际说:“你们看不到云,月亮总是看得到的吧!你们看这今晚的月亮,有多么大的一轮华晕包皮绕。月晕而风,这是一句古话,人人都晓,今夜是万万开不得船的。”
大家再一次将信将疑地向东方望去。夕阳尚未下山,天际还很明亮。蔚蓝色的天幕上,有几只鸥鸟雪白的剪影。别说月亮,就是连一片圆形的云彩也没有,洁净得令人生出寒意。
“小姐,您是不是因为老爷过世而太悲伤,此刻那月亮还没有升起来呢!”小眉心痛地说。
“月亮虽没升起,也是看得到的!你们看那月晕……”林默娘执着地望着一无所有的东方。
“小姐,”番客从鼻子里冷笑一声:“小姐号称一方灵女,实为妖言惑众。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去看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不是太愚蠢了吗?或者仁慈地说小姐年纪虽轻,眼睛却已昏花,将跃起的一尾银鱼鱼腹,当成了温柔可爱的月亮,尽管它们一个是长的,另一个是圆的。听说小姐的父亲已然仙逝,我们深表悲痛。还是请小姐先回家去把身上的红装换成黑色的丧服,再来管别人的闲事不迟。开船!”
番舶无可挽回地驶向大海。
身心交瘁的林默娘,再次昏厥在小眉怀里。
子时三刻到了。
大海象接到了一道黑色符咒,顷刻之间腾起狂涛。无数巨浪你攀着我,我擎着你,组成森严恐怖的水墙,黑黝黝地自天而降。整个海面一项巨大的黑鼓,狂燥地擂响了地狱之声。大海用黑色的舌头舔着菲薄的海岸,好象要把整个世界一口吞下。
林默娘从恶梦中惊醒。这是父亲离去后的第一个夜晚。父亲已移往他处,林默娘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她真想纵身跳入大海,同父亲一同到那永恒的彼岸。
起风了。恰恰午时三刻。林默娘感到小小的欣慰。再暴虐狡诈的风,也休想瞒过默娘了。
小眉一直守候在默娘身边,见她醒来,心中松了一口气。她说道:“默娘姐,你真是越来越神灵,好象会呼风唤雨似的。那番舶不听小姐劝阻,还恶语伤人,这一回,叫他们自讨苦吃去吧!”
林默娘被小眉的话一提醒,心倏地紧了起来。那狂傲不羁的番舶,现在哪里?
她披起衣服,走到屋外。海天如墨,人象置身于墨鱼汁中,一片混饨。林默娘调起真气,凝眸远望,但见大海深处,庞大的番舶如同一枚陀螺,正滴溜溜打转,已完全辨不得方向了。
“小眉,快!随我去屋顶!将红灯拿来,待我为番舶指出一条生路。”林默娘头也不回地吩咐道。
等了许久,身后却毫无声响,回头一看一向做事麻利的小眉,竟然倚着床栏睡着了。
这些天,小眉也太累了!林默娘一阵心酸,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个小妹妹。她将一件衣服轻轻盖在小眉身上,自己找来红灯,刚刚点燃,灯芯却呼地熄灭了。
今夜这风确实来得蹊跷,林默娘颤抖着手,二次点燃灯芯。灯芯刚快活地腾跃了两下,便又扑闪着要熄。
这风……林默娘一阵狐疑,回头一看,只见小眉远远地坐在床边,圆瞪着双眼,鼓着腮帮,正送过一股怨尤之气。
“小眉,你好些了?”林默娘赶紧走过去扶她。
“我根本就没睡着,只是不屑点灯就是。”小眉气哼哼地说。
“你不点,我自己点好了”,林默娘温和地说:“只要再不要吐恶气。救人如救火,耽误不得的。”
“我也不许你点!”小眉执拗地一把夺过红灯,“番舶刁蛮无理,这叫作人不报应天报应。”
“小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番舶恶语伤人,但并无死罪。况且一船舟子,皆是生灵,你我哪能见死不救!”林默娘急得要抢灯笼。
小眉的手,慢慢地放松了,猛地又抓紧了:“默娘姐,还是我来点吧。”
小眉与林默娘搀扶着走上屋顶。风夹杂着雨,鞭子似地抽来。两个单薄的黑色身影,高高地擎起一盏红灯。那灯在漆黑的暗夜中,象萤火虫一样,发出美丽而凄冷的光。
“默娘姐……番舶怎……么样了?”小眉冷得如落叶般籁籁发抖。两人紧紧偎依,彼此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一些温暖,也温暖着对方。
林默娘已适应了暗夜,洞若观火,看远在深海的番舶,如看指掌之纹,番舶已半船进水,随时都有可能被巨浪所噬,那骄横的番客早已被风暴击昏了头脑,不辨东西,一边令舟人全力淘水,一边竟令船向风暴的中心驶去……
“回头是岸……”林默娘真想拼尽全力震耳欲聋地大喊,将番舶引回港湾。但她知道自己的目力已绝非常人,看着飓尺之遥,实则隔着万顷巨涛。
红灯被风雨浇灭了。纵是不灭,这区区豆大的火光,在无边的黑暗中,不啻流星,已完全失去了导引航向的功能。
怎么办?怎么办?
林默娘焦的地在院中奔走。院中的柴薪已被猛雨浇湿,燃不起一丝火星。
林默娘仿佛听到番舶上舟子求救的呼唤,还有他们父母妻女悲痛的哭诉……林默娘禁不住热泪盈眶。事已至此,仅有一法了!
“小眉,取火把来。”林默娘的语调平等得近乎冷漠。
小眉不知何用,乖乖把火把递给林默娘。
猩红的火把给一身素白衣裙的林默娘,镀上了一层金红的色彩。她苍白的面庞闪现出新鲜明艳的活力。她的眼睛因为含了泪水,如深潭中的寒星,决然地闪着不容抗拒的光辉……
当林默娘的火把伸向光洁如铁的木门时,小眉才猛然醒悟了:“小姐,你要做什么?”
“我要把这祖屋,化作一支冲天的火炬。”林默娘平静如秋天的港湾。
“使不得啊,小姐!”小眉声泪俱下,“您要救番舶,小眉阻挡不了。但这祖屋,万万烧不得呀!您在这世上,已无父无母,无兄无家,仅这一幢祖屋为伴。烧了它,天地之间,就只剩下您孤零零一个人了!”小眉在默娘面前跪下了。
林默娘高举火把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飞扬的火把便在空中划出金红的曲线。林默娘最后看了一眼她的祖屋。
重檐斗拱的祖屋在黑夜之中蹲踞着,尤如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这是先祖几代人心血所凝,这里盛满了无尽的天伦之爱。林默娘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这祖屋中渡过的。如今这一切,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永远地消失了吗?
火把在空中抖动出更粗大的曲线。
风驱赶着雨,象驱赶着无数条黑色的毒蛇,绵延于天地之间。林默娘抬眼望去,番舶在进行最后的挣扎,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了。
林默娘轻轻扶起小眉,仔细拭干她眼上的泪:“小眉,我的好妹妹!你的心意,我知道了。记得当年我初学医道之时,阿爸送我一句话:‘愿将人病犹己病,救得他生是我生。’倘我们自己此刻在险风恶浪之中,该多么渴望能看到一团指路的火把!屋,可以再造;人,却永不可复生。我想,尚未远去的阿爸英灵,各位在天的列祖列宗,该不会以为默娘不孝吧!为了救天下黎民,默娘今日愿献祖屋,他日若需身家性命,默娘也万死不辞!”
祖屋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了。棉麻丝帛燃起轻快得象水波一样的涟漪,它们轻盈地不规划地扩大着自己的疆域。书籍宣纸燃起阴沉的火焰,因为通气不良它们偶尔只冒青烟,但火的版图还是在无声扩展着,忽地从一处相距很远的地方冒起尺把高的烈焰,书上的字在火中先变得很大继而飞快地缩小,画上的景物则象幽灵般活动起来,仿佛就要站立在火海之中。钵罐瓮缸发出沉闷的爆裂声,在为自身的命运表示着抗议。最难燃烧而又最持久地燃烧着的,是漆了彩画的木梁。它们沉默着,久久不肯参加这火的合唱,但终于被越来越高的温度撩拨起了热情,它们象火山爆发一样突兀而起,迸射出最高亢最纯粹的烈焰。
林默娘注视着自己熟悉的老屋,变成一座陌生的金色宫殿。有一瞬间、风雨几乎把所有的火焰熄灭。林默娘多么希望那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啊,那样火焰就会真的熄灭,她的祖屋就可以在这世界上多存在一刻了。虽然她知道自己马上就会从另一个更易燃烧的地方,将它重新更广泛地点燃。
祖屋辉煌而壮丽,仿佛每一道梁模,每一把桌椅、都是用纯金打造而成。它们射出万道金焰,象利箭一样,刺破夜的帷幕,象一座光焰万丈的灯塔,屹立于湄洲湾畔。
在铁桶般恶浪中盘旋的番舶,宛若看见了太阳,急忙调转船头,向着光明驶来。
林默娘披一身金光,站在金色的风雨之中。她的脸上,蜿蜒着两道金色的小溪。火焰如莲花般簇拥在她的脚下,迸溅出点点火星。
【作者简介】
毕淑敏,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文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心理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班毕业,注册心理咨询师。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毕淑敏以36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4位,引发广泛关注。 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畅销书。她的《学会看病》选入语文(人教版)5年级上册第20课。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