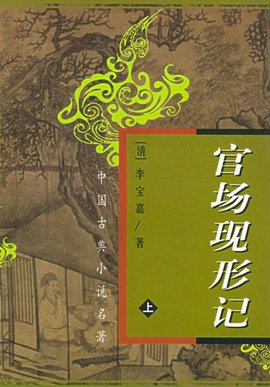鲍昌在《萃华街记事》里,写到一位“爆炸诗人”。这位诗人写过《以查拉图什特拉的名义》、《我的宇宙是绝望的熵》、《塌陷在宇宙的黑洞里》、《红移用死舌微笑》等诗作,以证实他的“诗爆炸”理论。其名句有云:
我举起发光的日冕
对着那馨香的偶像
在天鼓般众生的欢呼里
我升华于红铜的海洋。
前来登门求教的TNT诗社社员们的油印诗刊上,也有佳句与之辉映: 爆炸!一切从1—20秒开始……
柏拉图说: “有本事的诗人,总是通过一种神赐的灵感,把神的一些话解释给我们听。” (《理想国》)看来,爆炸诗人和TNT诗社诸君的诗,不但以“神赐的灵感”把“神的一些话”愈“解释”愈神,连诗人自己也“神”了起来,弄得几夫俗子只感到高深莫测,不知所云。这叫做在“淡化现实”之下的诗和诗人的神化,相当摩登。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 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闲,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这是《山海经·中山经》告诉我们的“天方夜谭”,你就不知道那两手“操蛇” “状如人”,也许还和“帝之二女”一样,出入“飘风暴雨”的怪神,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读某些诗,便有此感觉——虽然我并不想亵渎新感觉派。
其实,又何止是诗,某些文艺理论也够你感觉一气儿的。
有一种高论,认为 “只有曲高和寡才是真理” ,对于“俗” 的东西固然不放在眼里,就是雅俗共赏的东西也不屑一顾,大有羞与俗众为伍的气派。好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很有点儿 “革新” 精神。问题是: 你雅独有雅独的真理,他俗众也有俗众的真理。俗众离了雅独固然缺少了点雅味,也不过就是缺少了点雅味,天是塌不下来的; 而雅独要是离开了俗众,恐怕会连日子也没法过,所谓: 无以养君子。高雅的君子并不能靠 “餐朝露之精英” 而颐养天年,他也得把肚子现实主义地弄饱,这玩意是不能淡化的。现代派的吃西餐、饮可口可乐,可也并不拒绝传统的盐焗鸡、五粮液。这时候,就不太讲究是雅还是俗了,此之谓: 万物皆备于我。时髦的说法是: 发现了自我的价值(也有说本质的)。
一种 “强调” “艺术自身的要素” 的绘画理论告诉我们: “人们欣赏现代绘画,有可辨认的形象时可辨认; 没有可辨认的形象时,画面便是一切。” 而欣赏这 “便是一切”的 “画面” ,“需要一种新的观点才能体会” 。因为那 “色与色之间相撞与相融的微妙” ,“线条奔走的张力” ,以及“特有材料的肌理” ,可以任你联想,“苍穹、大河、雪山、云海、泥沼、坑洼……都无妨” 。这真叫妙哉画面! 据说那价值就在于它的 “不确定性”。依此,我们看见太阳,而 “不确定” 它为太阳,“无妨” “定” 为烧饼,或是面盆、唱片、树洞、贵妇人的脸……也可悉由尊“想”。这也可称为形象化的爆炸诗,摩登极了。
吸收外来的营养完全是必要的,包括 “现代派” 中一些优点特色,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固步自封只会造成停滞,但吸收的必须是营养,而不是糟粕,更不要连黄曲霉素也拿来当宝贝。鲁迅先生早年间就指出过,当我们 “拿来”之时,“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 ,占有而且挑选,见 了鸦片,“只送到药房去” ,不弄什么 “ ‘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就得拿来者自己 “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我常以为,凡热衷于“拿来”的人,大都是忧国忧民且忧文学艺术之不彰的热心人士,哪来什么自私不自私的问题?不太理解鲁迅特别提出“不自私”的命意。后来看见确有人搞“出售存膏”的玄虚,而且“售完”不止,才感到了鲁迅眼光之锐利,虽说“出售”的已不是古老大屋里搬出来的土膏,而换了包装精美的洋膏借以唬人,其对于拿来者,确是如鲁迅所预见的,“未免有些危机”。
那么,在吞下去之前,还是拆开包装看看究竟是什么货色为好吧。
(1986年9月3日《人民日报》)
【赏析】
杂文性辣,味辛。当年,鲁迅先生写《拿来主义》,酣畅地讥讽清王朝的“送去主义”,而称不敢拿来的人为孱头、昏蛋和废物。《拆开包装》是《拿来主义》的具体化,两者相比,主题类似,药性也都是辛辣的。
《拆开包装》的讽刺对象之一,是西方的新感觉派,其代表则是“爆炸诗人”和它的“诗爆炸”理论。大家知道,任何文艺创作都离不开生活,生活给了作家以素材和灵感,但新感觉派理论则相反,他们认为要“淡化现实”,“一切从1—20秒开始……”。这就构成了讽刺的材料。于是,作者巧借古代哲学家柏拉图的话说他们“不但以‘神赐的灵感’把‘神的一些话’愈‘解释’愈神,连诗人自己也‘神’了起来,弄得凡夫俗子只感到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结果,他们的作品也就成了“怪神”,使人们搞不清它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一连串的讽刺,尖锐、泼辣、入木三分。
讽刺对象之二,是认为“只有曲高和寡才是真理”的高论。这种高论,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批评过。下面,我们将批评与讽刺对比一下:
“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毛泽东)
“俗众离了雅独固然缺少了点雅味,也不过就是缺少了点雅味,天是塌不下来的;而雅独要是离开了俗众,恐怕会连日子也没法过,所谓:无以养君子。高雅的君子并不能靠‘餐朝露之精英’而颐养天年,他也得把肚子现实主义地弄饱,这玩意是不能淡化的。”很显然,上面那段是一般的批评,而下面这段是讽刺。批评是直截了当地用道理指出正误,是一种抽象的议论; 而这篇杂文的讽刺则是把议论溶化于叙述之中,并用旁征博引的方法使之形象化。
讽刺的对象之三,是一种强调 “艺术自身的要素”的绘画理论。讽刺这种理论,作者用了归谬法。不是说“欣赏不可辨认的形象”时可以 “任意联想”吗?那好,作者写道: “依此,我们看见太阳,而‘不确定’它为太阳,‘无妨’ ‘定’ 为烧饼,或是面盆、唱片、树洞、贵妇人的脸……也可悉由尊 ‘想’。”通过归谬,这一理论让人笑掉大牙。
由此看来,杂文的讽刺手法,说到底是一种语言运用的技巧。同是一件不合情理之事,非艺术地批评,不构成讽刺,而“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 ——写出来(鲁迅语),就构成讽刺。讽刺永远是辛辣的,这也正是《拆开包装》的战斗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