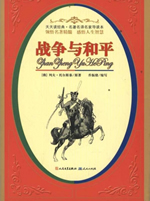第十六章 缺氧
就这样,在鹦鹉螺号的上方、下方,都是无法穿透的冰墙。我们成了大浮冰的囚徒了!加拿大人用他粗大的拳头捶打着桌子,龚赛伊一声不吭。我盯着尼莫船长,他脸上又恢复了平常的冷漠神情。他交叉双臂,思索着。鹦鹉螺号再也动弹不了了。
终于,船长发话了。
“先生们,”他语气平静地说,“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有两条死路。”
这个不可理喻的人物好像是一个在给学生做论证的数学老师。
“第一,”他接着说,“是被压死。第二,是窒息而死。我还没说到有饿死的可能性,因为鹦鹉螺号船上的食物储备肯定坚持得比我们还久。那让我们考虑一下被压死和窒息而死的可能性吧。”
“对于窒息,船长,”我回答,“是不足为患的,因为我们的储气罐储备是满的。”
“说得对,”尼莫船长说,“可它只能提供两天的空气。而且我们目前已经潜入水中36小时了,鹦鹉螺号船上的混浊空气已经需要更换了。在48小时以后,我们的储气就会耗光。”
“那好!船长,我们一定要在48小时前脱身。”
“我们至少会试一试凿穿包围着我们的冰墙的。”
“凿哪一边?”我问。
“探测器会告诉我们的。我将让鹦鹉螺号停在下面的冰层上,我的人穿上潜水服,就可以打穿冰山上最薄的冰壁。”
“我们可以打开客厅的嵌板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再也不走了。”
尼莫船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一阵笛声传来,我知道储水器正在充水。鹦鹉螺号慢慢地往下沉,最后在350米深度的一块冰面上停下来,这是下层冰层沉在水中的深度。
“我的朋友们,”我说,“情况严峻,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能力。”
“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说,“在这种时候,我是不会指责为难您,使您烦躁的。我时刻准备着为大家的脱险贡献一切。”
“好,尼德,”我握着加拿大人的手说。
“我补充一句,”他接着说,“我拿铁镐就像拿鱼叉一样得心应手,如果我对船长有用的话,他可以吩咐我干活。”
“他是不会拒绝您的帮助的,请这边来,尼德。”
我领着加拿大人来到鹦鹉螺号船员正在穿潜水服的房间里。我向船长转达了尼德的提议,船长马上就接受了。于是加拿大人穿上海底工作服,一会儿就和他的工友一样准备妥当了。他们每个人背上背着一个充满着大量纯净空气的卢卡罗尔空气箱。鹦鹉螺号船上的储气罐已经抽出了不少空气,但这是必要的。至于兰可夫灯,在这片灯光通明的水中是毫无用处的。
当尼德准备完毕后,我就回到客厅里。玻璃窗打开着,我站在龚赛伊旁边,观察着支撑着鹦鹉螺号船只四周的冰层。
几分钟后,我们看到了大约有十二个船组人员走到了冰层上,其中有尼德·兰,他身材高大,容易辨认出来,尼莫船长也跟他们在一起。
在凿墙之前,为了保证工作方向的正确性,尼莫船长让人做了一些探测。船员把长长的探测针钉进每侧的冰壁中,但钉到15米处,探测针还是受到厚厚的冰墙的阻挡。开凿上面的天花板是没用的,因为大浮冰本身的高度就超过400米。于是尼莫船长探测了脚下的冰层。结果是在那里,有10米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隔开了,这片冰地的厚度就是这样。从这以后,我们就要凿开一块与鹦鹉螺号从浮标线处算的面积一样大的冰块。也就是要挖出约6500立方米的冰,才能凿开一个我们能由此下沉到冰块下面的水中的大洞。
工作立即开始,并以一种不知疲倦的乐观精神进行着。但我们不能在鹦鹉螺号的周围挖掘,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于是尼莫船长让人在距船左舷后部8米处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他的人就同时在这个圆圈里的几个点上挖掘。一会儿,铁镐就开始猛烈地敲击着这块坚硬的物质,一些大碎冰从大冰块上被挖了出来。由于特殊的重力作用,这些比水轻的冰块,浮到了隧道的顶部去。于是下方的厚度在变薄,而上方的厚度不断加厚。这无关要紧,只要下面的冰壁随着上面的冰壁变厚而减薄同样的厚度就行。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奋战,尼德·兰精疲力竭地回来。他的同伴由新的工作人员换下来,我和龚赛伊也加入了新的工作人员行列,这回是鹦鹉螺号的船副指挥我们。
我觉得海水出奇的冷,但我挥舞起铁锹,一会儿就暖和了。尽管是在30个大气压下干活儿,我的行动却很自如。
干了两个小时的活儿后,当我进去吃点儿东西和休息一下时,我感觉到卢卡罗尔空气箱提供的空气与鹦鹉螺号中的空气有明显的不同:鹦鹉螺号船上的空气中已经充满了二氧化碳。船上已有48个小时没有更新空气了,空气中的氧气明显很稀薄。然而,在12小时里,我们只从画出的范围内挖掉了一层厚1米的冰块,大约是600平方米。如果按每12小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算,那要彻底完成这项工作还需五夜四天的时间。
“五夜四天!”我对我的同伴们说,“而我们只有两天的空气储备。”
“且不提一旦逃出这个该死的监狱后,我们还可能被囚禁在大浮冰下,还不可能和上面的空气接触呢!”尼德说。
他考虑得对极了。那谁能预测出我们脱身需要的最少时间呢?在鹦鹉螺号能够重新浮出水面之前,我们难道不会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吗?难道和这冰墓中所有的一切一起葬身在这冰墓中是命中注定的吗?情形显得很可怕。但每个人都正视它,而且所有人都决定尽自己的义务,坚持到最终。
根据我的预测,在夜间,又有一层1米厚的冰层从这个大洞穴中被挖掉。但早晨,当我穿上潜水服走到温度为零下6℃至7℃的海水中时,我发现两侧的冰墙正在逐渐合拢。由于里面的海水与外面的海水隔离,人的工作和工具的作用不能使它恒温,所以出现了冻结的趋势。面对着这个迫在眉睫的新危险,我们获救的机会还有多少呢?而且怎样阻止中间的海水冻结呢?这会使鹦鹉螺号的壁板像玻璃杯一样爆裂的。
我丝毫不敢跟我的两个同伴提起这个新危险。这除了会打击他们为了自救而做的艰苦工作的积极性外,还会有什么用呢?但我一回到船上,就向尼莫船长汇报了这个严重复杂的情况。
“我知道了,”他用他那种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镇定口气对我说,“这又多了一个危险,可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逃避它。唯一的获救机会,就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干得比海水冻结快,关键是谁抢在前面,就是这样。”
谁抢在前面!最终,我还得接受这种说法!
这一天的好几个小时里,我鼓足干劲儿地挥动着铁镐。工作一直支持着我。再说,干活儿,就是离开鹦鹉螺号,就是能直接呼吸从储气罐里抽出来储在空气箱里的纯净空气,就是离开鹦鹉螺号船上的稀薄混浊的空气。
到了傍晚,冰坑又被挖出了1米。当我回到船上时,我差一点儿因空气中饱含的二氧化碳窒息而死。啊!为什么我们没能找到一些化学方法把这种有毒的气体清除掉呢?氧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缺乏的,所有的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氧,我们可以用强力电池把氧气电解出来,水说不定能为我们恢复生机。我美美地想着这个,但有什么用呢?我们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满了船里的所有角落。要把二氧化碳吸收掉,就得把苛性钾盛在接收器中不断摇动。可是,船上没有这种物质,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物。
那天晚上,尼莫船长不得不打开储气罐的闸门,在鹦鹉螺号船内放出几股清新的空气。如果没有这种预防措施,我们就都会醒不过来的。
第二天,3月26日,我又继续干我的挖矿活,挖掘第5米的冰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的下部明显地增厚了。显然,在鹦鹉螺号脱身之前,它们会合拢到一起的。失望一下子攫住了我,铁镐差点儿从我的手中飞出。如果我就要被这些凝结得像石头一般坚硬的海水挤压得窒息而死——这是一种连凶残的野蛮人还没发明的肉刑,那挖下去还有什么用呢?我仿佛掉进了一只怪兽那正合拢上的大嘴中。
尼莫船长指挥着工作,他本人也加入到干活的行列中。这时,他从我身边走过。我用手碰碰他,给他指了指两侧墙壁,船右舷的冰墙至少向鹦鹉螺号的船壳靠近了4米。
船长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向我做了一个跟他走的手势。我们回到了船上。我脱下了潜水服,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对我说,“应该表现出一些英雄气概,否则我们就会被封冻在这冻结的海水中,就像被封在水泥中一样。”
“是的!”我说,“可该怎么做呢?”
“啊!”他喊道,“如果我的鹦鹉螺号能顶住这种压力,不被挤碎,那会怎么样呢?”
“什么?”我没听明白船长的意思。
“您不明白,”他回答说,“水的凝固作用会帮我们的忙的!您没发现,由于水的固化,它会把囚禁着我们的冰田绷裂,就像它凝固时会把最硬的石头绷裂一样!难道您没意识到它是拯救的力量,而不是毁灭的力量?”
“是的,船长,可能吧。但鹦鹉螺号对挤压的承受能力有多强呢?它是不可能承受如此惊人的压力的,它会被压成一张铁皮的。”
“这我知道,先生。那就不能指望自然的援助,而要指望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冻结。现在不仅船两侧的冰墙在收紧,而且后部和前部也只剩下10英尺的水了。冻结正朝着各个方向向我们逼来,我们必须消除它。”
“储气罐的空气能供我们在船上呼吸多长时间呢?”我问。
“过了明天,”船长说,“储气罐就会空了!”
我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可是,对他的回答我难道还感到惊讶吗?鹦鹉螺号在3月22日就潜入了南极的自由海中,而现在是26日。5天来,我们一直靠着船上的储气罐维持生命!这样一来,剩下来的空气应该留给干活的人用。当我记录下这些事情的那一刻,我仍活生生地记得当时那种情形,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攫住了我的整个身心,我的肺里仿佛都缺氧了!
然而,尼莫船长默默地思考着,一动不动。显然,在他的脑子里刚有一个念头闪过,但他仿佛想把它推开:他自己在否定自己。终于,从他的嘴唇里蹦出这几个字:
“滚开水!”他喃喃地说。
“滚开水?”我喊道。
“是的,先生。我们被困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空间里。如果鹦鹉螺号船上的水泵不断地泵出滚开水,这难道不会使水层的温度上升并推迟它的冻结吗?”
“应该试一试。”我坚决地说。
“我们试一试吧,教授先生。”
温度计显示出当时外面是零下7℃以下。尼莫船长把我带到厨房里,里面有许多为我们提供饮用水的大型蒸馏器正在运作。蒸馏器装满了水,电池的所有电热通过浸在水中的蛇形管传送出去。几分钟后,水温就达到了100℃。随着滚水被抽到水泵里,又有一些新的水补充进来煮。电池发出的热力相当强,从海中抽进来的冷水只要一通过这些蒸馏器进入水泵中,就变成了沸水。
滚水注射开始了。三个小时后,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赢回了1℃了。两个小时后,温度计指示在零下4℃。
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被这项操作的许多显著效果折服了。我对船长说:“我们会成功的。”
“我想会的,”他回答我说,“我们不会被压碎了。我们担心的只是窒息问题了。”
夜里,水温上升到零上1℃,注射开水再也不能使温度上升了。但因为只有再低2℃海水才会冻结,所以我最终确信海水冻结的危险过去了。
第二天,3月27日,已经有6米的冰层被挖开了,只剩下4米要挖掘,可这是48小时才能干得完的活儿。鹦鹉螺号船内的空气再也不能更新了。因此,这一天的情况一直越来越糟。
一种无法忍受的沉重感压抑着我。到了下午3点钟,这种忧虑的情绪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种强烈的程度。打哈欠时我的颌骨都歪了,我的肺喘息着寻找那种可燃的、呼吸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来越稀薄的气体。我处于一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毫无气力地瘫着,几乎没了知觉。老实的龚赛伊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忍受着同样的痛苦。但他一刻儿也没离开过我,而是握着我的手,鼓励着我,我还听到他喃喃地说:
“啊!如果我可以不呼吸而留点儿空气给先生呼吸就好了!”
听到他这么说,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的情形,对于所有在船内的人来说,是那么难以忍受。所以每当轮到我们干活儿时,我们是多么迅速、多么幸福地穿上了潜水服啊!铁镐在冰层上回响。手臂累了,手掌也破了,但疲劳算得了什么?这点儿伤痛又算得了什么?生命的气体进入了肺中!我们呼吸着!我们呼吸着!
然而,却没有人延长自己在水中工作的时间。任务一完成,每个人都把维持生命的空气箱交还给气喘吁吁的同伴。尼莫船长身先士卒做出表率,他第一个遵守这条严格的纪律。时间一到,他就把空气箱让给另一个人,走进船内混浊的空气中。而他总是很镇定,没有一声怨言,没有丝毫消沉的表现。
那天,正常的工作更有效地完成了,整个范围内只剩下两米厚的冰层要挖。只有两米厚的冰层把我们与自由海隔开了,但储气罐中的空气也几乎空了。剩下的一点儿空气要留给干活的人,一点儿也不能再供给鹦鹉螺号船上。
当我回到船上时,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多么难熬的夜晚啊!我简直无法表达,这样的痛苦是无法描述出来的。第二天,我的呼吸受阻,头痛夹杂着昏眩,看起来就像个醉汉一样。我的同伴也经受着同样的症状,船组的几个船员也不断地喘气。
那一天,我们被困住的第六天,尼莫船长发现用铁镐、铁锹挖太慢了,便决定压碎把我们同水层分隔开的那层冰层。他这个人靠着精神力量抑制住肉体的痛苦,总保持着镇定和十足的精力。他不断地思考、计划、行动。
于是按船长的指示,船轻减了重量,也就是说,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心,从冰层上浮起来。当船浮起来时,我们就准备把船拖到根据它的浮标线画出来的大坑上,让它的储水器充满水,再把船往下一沉填进坑里。
这时,所有的船组人员都回到了船上,两道与外面相通的门都被关上。鹦鹉螺号于是停在1米厚、被探测器钻了上千个洞眼的冰层上。
储水池的闸门完全打开,100立方米海水涌了进来,鹦鹉螺号的重量一下子增加了10万公斤。
我们充满希望地等待着,聆听着,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我们把获救的宝押在这最后一招上。
尽管我的脑袋在嗡嗡作响,但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了鹦鹉螺号船体下传来了一阵颤动,撞击开始了。随着一声奇特的、像纸被撕破一样的声音的撞击声,冰层被撞开了,鹦鹉螺号往下沉。
“我们穿过去了!”龚赛伊附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
我不能回答他的话。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
突然,由于吓人的过度负重,鹦鹉螺号像一发炮弹一样陷进水中,仿佛在真空中一样往下掉。
于是所有的电力都又输送到水泵上,水泵立即开始把储水池里的水排出来。几分钟后,船的下滑停止了。而且几乎同时,压力表就指示出船在上升。机轮全速地转动,从船壳到铁钉整个都在颤抖,船载着我们向北疾驶。
但从大浮冰到自由的海水中,还有多少航程呢?还要一天吗?那我在到达之前早就死掉了。
我半躺在图书室的沙发上,喘不过气来。我的脸色发紫,嘴唇变蓝,我的机体丧失了一切功能。我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时间的概念已经在我的意念中消失了,我的肌肉也不能收缩了。
我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几个小时。但我意识到我已经到了垂危之际,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突然,几丝空气渗进了我的肺部,我苏醒过来。我们回到了水面上吗?我们穿过了大浮冰吗?
不!是尼德和龚赛伊,我的两个忠诚的朋友,他们牺牲了自己来救我。空气箱底还剩下几丝空气,但他们没有把它呼吸掉,而是留下来给我。而且,当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却一点儿一点儿地给我注入了生命之源!我想把空气箱推开。但他们按住了我的手,就在那几分钟内,我痛痛快快地呼吸了几口。
我的眼光移到时钟上,是早上11点,应该是3月28日。鹦鹉螺号正以每小时40海里的速度发疯般地疾驶着,在海水中挣扎着。
尼莫船长在哪儿呢?他死了吗?他的同伴与他一起死了吗?
这时,压力表指示我们离水面仅有20英尺,可是有一片薄薄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面隔开,我们不能把它撞开吗?
应该是可以的!总之,鹦鹉螺号会试一试的。的确,我感觉到它采取倾斜的位置,后部下沉,冲角仰起——这时要是有一股水灌进来就会打破它的平衡。然后,在强大的机轮推动下,它像一头强壮的公牛一样向冰地下部顶去,然后再往后退,再全速向冰层冲去,渐渐地把冰层撞开。终于,冰层裂开了,鹦鹉螺号猛地一冲,冲到了被它的重量撞破的冰层上面。
此时,嵌板一下子打开,我们可以说是解脱了,纯净的空气像潮水般涌进鹦鹉螺号船内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