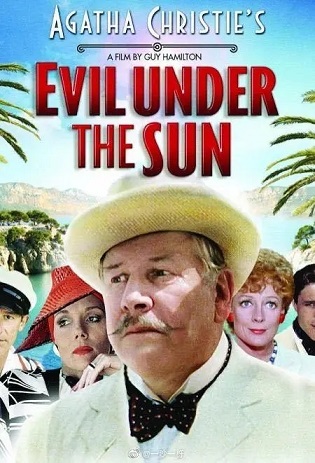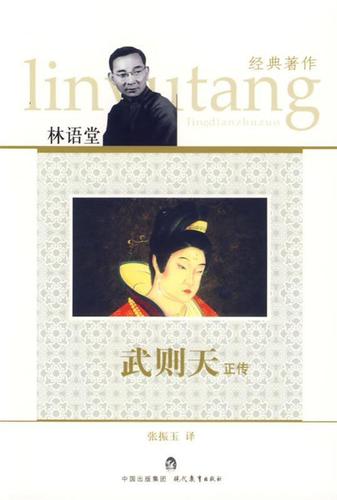卯时三刻,只听得东华门内九声炮响,接着就见到四名骑着一色枣红马,身着金盔甲,腰悬金牌、绣春刀,手执大金瓜斧的锦衣卫大汉将军作为前驱使,引出两列约摸有两百人的肃卫仪仗来。跟着就抬出来一顶十六人抬的雕花锦栏杏黄围帘的大凉轿,后面跟着二十多乘舆轿,八人抬四人抬二人抬不等。接下来又是二百名身穿红盔青甲骑着高头大马的扈从禁卫。大凉轿两侧,还各有四个身着红皮盔戗金甲,手执开鞘大刀的锦衣卫力士充任防护属车使。这规模气势,只是比皇帝出行少了两百名府军前卫带刀舍人,以及隶属神枢营的两百叉刀围子手。因为不必沿途理刑,因此随驾负责提调缉事的锦衣卫东司房理刑官一员也就免掉了。坐在大凉轿中的李太后,此时心情好极了。昨天,她正式得到了礼部特为她颁制的慈圣皇太后的铁券金书,她一方面心里头感谢张居正忠忱皇室,斡旋有力;另一方面,她更加深信这是无远弗届的佛力所佑,便听从冯保的建议,选定吉日前往昭宁寺敬香礼佛。
大凉轿抬出东华门后,穿过棋盘街往前门迤逦而来。一路上,但见伞盖遮路,彩旗蔽天,每前行一里地,便会“嗵、嗵、嗵”响起三声礼炮。这是告诉前面各路负责巡视警跸的官兵太后的凤辇就要到了。凤辇所经之处,道路肃清,连平日摩肩接踵的棋盘街,此刻也清旷无人。坐在大凉轿中的李太后,全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但第一次以皇太后的身份出行,这等威严仪仗,自然令她心旷神怡。这李太后乘坐的大凉轿十分宽敝。除她本人外,在她坐着的黄绫衬绣的藤椅两侧,还侍立了两名宫女,其中有一名就是容儿。如今容儿已晋升为尚仪局尚仪,是个正五品的女官了。宫中太监有二十四局,女官也有六局,名曰尚官、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尚仪局掌礼乐起居,下设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四司。容儿善解人意,又精丝竹之艺,李太后便把这个官儿赐给了她。眼下节令虽过白露,但因久未下雨,暑气尚有余威,扈从卫士一个个汗得盔甲尽湿。大凉轿里因搁了一盆冰,倒不觉得燠热。耳听得又有三声炮响,李太后问容儿:“咱们到了哪儿?”
容儿轻轻撩起轿帘一角,望到不远处的崇文门城楼,答道:“启禀太后,奴婢看到崇文门城楼了。”
“啊,应该是快到了,”李太后伸手整了整头上戴着的凤冠,又笑着问道,“容儿,你训练的女乐,现在究竟怎样了?”
皇城大内本有一个教坊司,负责宫中一应大事仪制伎乐。两宫太后平时都好听散曲,容儿投其所好,提议选拔通晓钟吕音律的宫女训练一支女乐,李太后当即表示赞同。如今已经训练了一些时日。昨日,容儿征得李太后同意,今天便带了这支女乐一块去昭宁寺,在李太后礼佛拜香时演奏佛曲。现在见李太后问及此事,容儿答道:
“一般常听的散曲,女乐都已演奏娴熟,只是今儿个演奏的佛乐,因是赶排的,恐怕有污太后的耳目。”
李太后笑笑没有作答。这时又传来九声炮响,昭宁寺到了。
大凉轿在昭宁寺门口稳稳停住,当容儿掀开轿门帘,搀扶李太后走出凉轿时,只听得铙钹迭响鼓乐齐鸣。但见早来一个时辰的冯保领着一帮内侍,还有一如和尚领着大小僧众在昭宁寺前黑鸦鸦跪了一片接驾。
李太后今日来昭宁寺敬香,内容安排得满满的。首先是往各殿敬香拜佛,接着是将大内收藏多年的一尊藤胎海潮观音像赠予昭宁寺观音阁收藏,顺便还要施赠一千两银子的香资——都有仪式举行。当李太后在一如师傅导引下开始燃香拜佛时,容儿指挥女乐在大雄宝殿一侧奏起了佛乐。只见这班宫女乐工一色身着绯红琐幅质地月色鱼冻布滚边的六幅拖地长裙,头上梳的也是一色的云髻,各插一支玲珑琥珀如意簪,簪头上都坠了一颗亮晶晶的垂珠,摇晃晃光芒四射。她们个个身段窈窕,玉手纤纤;齿白唇红,仪态万方。馋得坐在另一厢放焰口的那帮小沙弥一个个意马心猿,眼睛发直,常常唱错经文。这帮女乐工端的训练有素,都能目不斜视,一门心思用在奏乐上。这皆因容儿对宋朝姜夔的《大乐议》别有心得,深懂古人
槁木贯珠之意,对女工要求甚严。一时间,只见她们击钟磬、吹匏竹、操琴瑟——同奏则五音谐和,迭奏若空灵出穴。俨然仙乐,又不失皇家气派与典雅。而此时李太后敬香的各殿,经过重新装点,也是流丹炫紫,锦绣错综。那些佛像、悬幛、梁楹与炉尊,若琉璃映彻,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玛瑙散辉,文彩晃耀;若渊澄而珠朗,若山明而玉润;若翠羽之陆离,若龙章之焱灼;若旄旌孔盖之飘摇,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庆云之炳焕,紫葩瑶草之斑斓。铃索撞摇,宝轮层叠。瓦鳞比,栏槛纵横;玲珑疏透,神动光溢。置身于这股子天花灿烂的佛国庄严气象之中,本来就雍容华贵不容逼视的李太后,越发显得神采飞扬。李太后拜佛特别认真,不要说在如来佛、欢喜佛、药师佛与观音菩萨面前一律三拜九叩,就连护法韦驮,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面前,也必稽首行礼,献上檀香三支。这一趟三大殿的礼佛下来,足有大半个时辰。李太后也有些乏了,便由侍女搀扶着到客堂落座休息。一如与冯保也相陪着进来,李太后给他们赐座。待喝了一小盅从宫中带来的冰镇菊花茶后,李太后命侍女把容儿喊了进来,问她:“容儿,你们方才演奏的,是什么曲子?”
容儿轻轻提起裙子,正要跪下作答,李太后说:“这砖地不比宫中地毯,会弄污你的罗裙,还是坐下答吧。”
容儿蹲了个万福谢过,坐下来答道:“启禀太后,奴婢们演奏的曲牌,叫《善世佛乐》。”
“善世佛乐,唔,这名儿好,也好听。我拜佛多长时辰,你们就演奏了多长时辰,不短哪。”“这是套曲,一共有七支曲子组成。”
“哪七支曲子?”
李太后心情忒好,所以不厌其烦地问下去,容儿只得细细回答:
“这开头的第一支曲子,就叫善世曲,接下来是昭信曲,第三是延慈曲,第四是法喜曲,第五是禅悦曲,第六是遍应曲,最后有一个圆满的收曲,叫善成曲。本来,配合这套善世佛乐,还有一套悦佛舞,用舞女二十人,手上或执香,或执灯,或珠玉,或明水,或青莲花,或冰桃,一起在佛像前载歌载舞。若是舞得好,莲花座上,便会有佛光出现。”
“啊,有这等神奇?”李太后眼神发亮,追问道,“今天,你们为何只是演奏而不起舞呢?”容儿答:“这套善世佛乐也才刚刚排练出来,悦佛舞还来不及排演。”
“啊,”李太后点点头,脸上略呈遗憾之色,“回宫后,你们加紧排演,何时排演好了,再演给我看。”
“奴婢遵太后令旨。”容儿又起身蹲了个万福。
一直坐在旁边静听对话的冯保,这时插进来问道:“王尚仪,请问你这套善世佛乐用的是何处的谱本?”
“就取自宫中教坊司。”
“啊,怎么从来没有听到教坊司演奏。”
“这套曲子是洪武五年,洪武皇帝龙驾亲临蒋山礼佛时,由蒋山寺的僧人度谱创作的。宋濂学士当时躬逢其盛,便在笔记中记下了这次佛会,并将曲谱带回来交给了教坊司。”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奴婢是先读了宋学士的笔记,然后再去教坊司,从那十多只盛谱的大红柜中,找到了这套曲谱。”
“王尚仪不愧是有心人。”冯保口中赞叹,心里头却酸溜溜的。
容儿虽是太后跟前的红人,但对这位笑里藏刀的“内相”向来谨慎有加。她听出冯公公的话中含有讥讽之意,赶紧赔着笑脸答道:
“冯公公的琴艺天下无双,跟您老比起来,我们这班女乐都成了儿戏。今后,还望冯公公多指教才是。”
“王尚仪太谦虚了,方才太后还夸赞你们演奏得好。”
“是演奏得不错,”李太后接过话茬,“容儿,回宫后,让邱得用给你们赏银。”
“谢太后。”
容儿道福谢过,然后知趣地退出。歇了这半会儿,李太后缓过了劲,问冯公公:
“现在该做啥?”
“赠观音。”
冯保说着,朝门口一抬手,立刻就有两名小内侍抬了一个高约四尺的红木匣子进来。在砖地上小心翼翼地放稳,然后打开木匣,那尊藤胎海潮观音像就赫然映入眼帘。以下情形不必细说,一如师傅先是给李太后叩首谢恩,然后让两名小沙弥进来抬起那尊观音请去大士殿落座,一时间,僧众夹道长跪接送,女乐工们再次鼓吹奏乐。
短暂的仪式过后,一如师傅又回到客堂,刚坐定,冯保就提起话头说:“一如师傅,今儿可是昭宁寺千载难逢的喜事,一下子来了两个观音,那尊藤胎海潮观音,已经永久留在寺中,还有母仪天下的李太后,本就是观音转世……”
“算了,算了,冯公公瞎唠叨什么,”李太后明是嗔怪暗是高兴地打断冯保的话说,“在佛门清净地讲这种话,不怕犯忌?”
“太后本来就是观音转世嘛,”冯保猜透了李太后的心思,因此也就敢放肆讲话,“一如师傅,听说你是练出了天眼通的得道高僧,想必你看得更准。”
“是啊。”一如忽然变得心思重重,抬眼再三,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冯保尚在兴奋中,也顾不得看一如的表情又抢着说:“既是这样,太后,奴才倒有个建议。”“说。”
“既然太后亲自把大内收藏的藤胎海潮观音送到昭宁寺供奉,干脆,这昭宁寺就此更名,叫灵藏观音寺,岂不更好?”
“这……”
李太后把目光转向了一如,这一下可让一如为难了。京城梵刹,昭宁寺并不是最有名的,以一如的影响地位,他本可以住持一座更大的庙宇,但他宁可住在昭宁寺,原因是这一带穷苦百姓多,在他们中宏扬佛法,正好符合他的“普度众生”的佛家襟抱,若更名灵藏观音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座皇家寺庙,一般百姓庶民就会敬而远之,这实非一如所愿。但冯保这一提议,明显是为了拍李太后的马屁。一如若表示异议,后果不堪设想。思来想去,一如只得合掌念道:
“阿弥陀佛,一切听李太后作主。”
李太后看出一如似有什么难言之隐,便追问了一句:“一如师傅,冯公公的提议有何不妥吗?”“啊……没有。”
“那,就改作灵藏观音寺吧。”
“谢太后。”
一如双手合十,又念起“阿弥陀佛”来了,老和尚的这份木讷与虔诚,倒让李太后大受感动,她对冯保说:
“冯公公,回宫后,您瞅机会奏请皇上,给这灵藏观音寺赐个匾额。”
冯保答:“奴才记住了。”
“唔,还有什么?”
李太后欠欠身子,那样子有回宫的意思,一如努努嘴唇似有话说,又是冯保赶紧奏道:“启禀李太后,还有一件事情,还望您老人家在此定夺。”
“何事?”
“万岁爷登基那天,您让奴才替万岁爷找个替身剃度出家,这孩子,奴才找着了。现就在外头,等着太后过目。”
“啊,传他进来。”
冯保出去片刻,便领了一个孩子进来。
这孩子身材偏瘦,但皮肤白皙,挺挺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骤然见到这些大人物,难免畏葸紧张,站在李太后面前,禁不住浑身发抖。李太后慈母心肠,她让孩子站得更近些,一面帮他扯了扯弄皱的衣衫,一面亲切问道:“你叫什么?”
“牵牛。”
“为啥叫这名字?”
“俺娘七月七生了我,所以叫牵牛。”
“今年多大?”
“十岁。”
“哟,你同当今万岁爷同年。”李太后怜爱之心溢于言表,“牵牛,你哪里人?”
“县。”
“县?”李太后又大吃一惊,越发亲切起来,“原来你是咱的小老乡。”
牵牛点点头算是作答,冯保一旁插话道:“奴才领旨后,心里头琢磨着,给万岁爷找一个替身,也不是什么地儿的人都行。若能在太后的家乡县物色一个,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就吩咐手下人一门心思去了县,花了这一个多月时间,终于从数千名孩子中,找出了这个牵牛。他年纪同万岁爷一样大,长相虽不及万岁爷,但奴才看他眉宇间也还有佛相,奴才觉得理想,就把他领过来了。”
李太后微微颔首,算是对冯保的赞赏,她的注意力仍集中在牵牛身上。她见牵牛身上穿的衫裤并不是家乡农家自织的土布制成,而是松江府产的细梭子布。这么热天,还穿了一双城里少爷才穿的鸭头袜。因此问道:“牵牛,你这身穿戴,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牵牛摇摇头。
冯保仍是包揽着解答:“牵牛穿得破烂,这身衣服是来京后新买的。”
“牵牛,你爹做甚?”
“种庄稼。”
“收成好不好?”
“不知道,俺来的时候,地里正旱着呢。”
“哦,”李太后心里头像被螫了一下,她自十三岁随父亲逃荒从县流落京城,十五年过去了,她再没有回过县。牵牛的出现,勾起她对故乡的怀念,“县这地方,三年倒有两年旱,庄稼人日子不好过啊。牵牛,能吃饱饭不?”
“吃……”牵牛欲言又止。
“说真话。”
“吃,吃不饱。”牵牛答话声音细弱。
“可怜的孩子,”李太后把牵牛揽进怀中,眼角溢出细碎的泪花,“现在饿吗?”
“现在不饿,到京城来,我顿顿都吃得好。”
“你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知道,”牵牛开始兴奋起来,“咱是来替万岁爷出家的。”
“你愿意吗?”
“愿意。”
“为啥愿意呢?”李太后叮问道,“当和尚并不好耍,长大了也不能娶媳妇。”
牵牛使劲地点头,说,“咱还是愿意。”
李太后笑了起来,对在坐的一如和尚和冯保说:“牵牛一口一个愿意,说的都是孩子话。”
“不是孩子话,咱娘就这样教的。”牵牛眼睛睁得溜溜圆,认起真来。
这样子逗得李太后很开心,她用手指头戳了戳牵牛的鼻梁,笑问:“啊,是你娘教的,她怎么说?”
“咱娘说,要是真能替万岁爷出家,那可是十代人修来的福气,也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还有,还有……余下的话,咱娘不让说。”
牵牛说着又止住了。他的这份天真质朴让李太后很喜欢,因此更加饶有兴趣地追问:
“有什么好话儿,你娘不让说?”
“咱娘说,咱若是被李太后相中,真的出了家,咱家就可以免差免赋,日子会好过一些。”
“就这话?”
“就这话,咱娘说,这是悄悄话,不让咱告诉任何人。”
李太后听了大受感动,她毕竟是穷苦人家出身,深知丁门小户过日子的艰辛。她让人把牵牛带下去休息,然后问一如:
“一如师傅,你看牵牛这孩子如何?”
一直静坐一旁认真听着谈话的一如,往常只觉得李太后不苟言笑甚为威严,今日却看到她和蔼可亲极富人情的一面,心中平添了对她的十分好感。同时他也觉得牵牛纯真可爱,不过对这孩子他是同情大于赞赏,便答道:
“这孩子让人疼爱。”
“牵牛的确是个好孩子,”李太后由衷地赞叹,接着问,“一如师傅,你愿意收牵牛为徒吗?”“这个……”一如略一思忖,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佛家也讲缘分。”
“牵牛这孩子既然让一如师傅疼爱,这就是缘份,”冯保虽然对一如尊敬,但对他不痛不痒的答话又甚为不满,“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牵牛在昭宁寺出家。”
“如此善哉,善哉。”
一如迫于无奈,算是作了一个委婉的表态。
谈话至此,李太后想告辞了,她便对一如师傅说起道别的话:
“一如师傅,咱只想到昭宁寺来敬香还愿,没想到宫里来了这么多人,对寺中多有叨扰,还望师傅海涵。”
一如师傅双手合十,悠悠说道:“太后玉辇亲临,实乃寒寺的无上荣幸。新主登基,万方吉庆,老衲深信,有太后表率天下,从此后,人皆敬三宝,佛门重振之日,为时不远。”
“现在,京城各寺庙香火不是都很旺么?老和尚为何要说佛门重振?”逮住一如的话把儿,李太后问道。
“这个,老衲不好明言。”
“越是不好明言,咱越是喜欢听,一如师傅,但讲无妨。”
李太后本说道别即走,但从一如师傅的话风中听出难言之隐,顿时来了兴趣,遂调正坐姿,一定要问出个子丑寅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