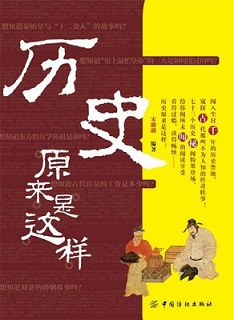一大早,王希烈的大轿子刚抬到礼部,立刻就有司务官纪有功上前禀报童立本上吊自尽的消息。
“死了?”他问。
“死了。”纪有功答。
“死在哪?”
“家里。”
“唉,寻短见干嘛。”
王希烈嘟哝一句,再不说二话,背着手走向自己的值房。前几日吕调阳入阁后,虽然名义上他仍挂着礼部尚书,但每日到内阁上班,已不大过问这边的事儿,王希烈这个左侍郎又临时负起全责来。这名不正言不顺一会儿管事,一会儿“让贤”的堂官,不晓得让王希烈几憋气,他直感到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
隆庆皇帝病重期间,王希烈就被高拱派往天寿山督修隆庆皇帝的陵寝。按本朝惯例,这是一个升官的信号。其时高仪已入阁,他所担任的礼部尚书照例不应兼任。已担任礼部佐贰官三年的王希烈,自以为督修陵寝归来,即可升任尚书。谁知其间高拱去职,高仪去世,礼部尚书一职竟给了本无竞争力的吕调阳。王希烈因是高拱线上的人,对张居正本就没什么好感,这一来意见更大。那天晚上假座薰风阁聚饮,就有意联络魏学曾寻衅滋事,铁定了心与张居正作对。
这些时他可没少活动,一是联络一班官员凑份子给武清伯李伟送礼,怂恿这个见钱眼开的老国丈入宫告刁状,这一招可说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道给王侯勋戚免去胡椒苏木折俸的谕旨到了户部,王希烈可谓欣喜若狂。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乡谊去信劝说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上折弹劾王国光,这折子也送进了宫中。其间,他还与魏学曾一起去王崧家中抚慰,痛骂章大郎的凶蛮无理,激起王崧之子王岩的愤怒,在章大郎出狱之日,不惜以身试法,替父报仇刺死了章大郎。这一连三件事的发生,的确给张居正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他的目的就是要离间君臣关系,让李太后与小皇上对张居正产生怀疑,从而达到把他逐出内阁的目的。
前几天,魏学曾向他透露,吕调阳入阁后,吏部议荐了三个人接替他,打头第一个就是他王希烈;第二个是从詹事府詹事的任上已退下来十八年的陆树声,此人是士林中清流领袖,这是吏部推荐的理由;第三是现任南京礼部左侍郎的万士和。和后两人比,王希烈觉得自己有优越之处,这就使得他的本来已经落寞的心情重又兴奋起来。但他知道皇上幼小,此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居正,因此又不作多大指望。他的一帮朋友与部属,却劝他暂忍一口气,把职务扶正再作打算。他想想也有道理,大丈夫能屈能伸,该低头时就得低头。前天夜里,他坐一乘小轿,携了贵重礼品偷偷摸摸来到纱帽胡同张学士府邸拜谒。原想捐弃前嫌重新修好,以期能得到令他久已垂涎的大司伯一职。没想到张居正拒见,让管家游七丢出一句话来:“若谈公事,明日去内阁朝房,若谈私事,首辅无私事可言。”说罢,狗眼看人低的游七,也昂头一丈转身离去,把他堂堂一个礼部佐贰晾在轿厅里。他当时气得四肢冰凉,五官挪位,吼了一句:“回轿!”
自吃了这个闭门羹,王希烈已是去尽最后一点侥幸心理,发誓要同张居正拼个鱼死网破。因为他知道,这次京察带给自己的下场,不外乎两个,轻则外谪,重则削籍。从对高拱的处置来看,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事情既到了这个地步,想不通也得通。这两日他像吃了狂药似的,不知疲倦地四下活动,还真不能小瞧他,京师大臣中,像他这样能够兴风作浪的,委实没有几个。
却说他前脚刚进值房,纪有功后脚就跟了进来。他本是王希烈的心腹,所以被安排到司务一职,负责本衙各司间的协调,一应上传下达的事儿也都该他负责。因这层关系,他见堂官的礼节也就随便一些。
“你还有啥事?”王希烈坐下问。
“有,”纪有功站在案前,请示道,“有两件事,一是泰山提点杨用成昨日到京,他是来京向户部交纳泰山的香税钱。有些账目,在同户部核对之前,想先征询部堂大人的意见。”
账目有问题吗?”
“大问题也没有,但有一笔开销,大约有五千多两银子挂在账上,一时还无法冲销。”
“做什么用的?”
“是今年四月,李太后派慈宁宫邱公公前往泰山为先帝禳灾祈福,花掉的礼品钱。”
“啊,有这等事?”
“杨用成就这么说的。”
王希烈觉得这里头有戏,当即下令:“你去告诉杨用成,今儿下午,到这里来见我。”
“是。”纪有功点头哈腰,接着说,“第二件事,是朝鲜国的特使,昨日已在京南驿宿下,陪同官派人来请示,何时进京面圣。”
却说万历皇帝登基后,邻近一些外域的国王或番主都派特使前来恭贺。此前安南、西凉等地番王已先后进京,盘桓几天就打发走了。听说暹罗、老挝等国的特使也已上路,正在进京路上。这朝鲜国仰我天朝,世代友好,睦邻关系更进一层。该国特使每次进京,皇上都要接见两次,并赠送诸多礼品。这次前来朝觐恭贺,更是不能怠慢。循常例,外国特使到京,礼部都要派专员陪同,住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会同馆。吃皇上恩赐的鸿胪寺大宴,然后游览名胜,置办礼物,一应开销,由礼部报单户部拨款。这次也不能例外。王希烈把这事儿掂量一番,觉得这里头的“戏”,比杨用成那里还要足,于是兴奋问道:
“特使来了几个,带了些什么?”
“特使就一个,但跟班儿的有二十多个人,礼物有两大车,有马尾丝、螺钿、老山参什么的,都是朝鲜的特产,听说还有一只猫。”
“猫?什么猫?”
“小的只是听差官言说,也未见过。这猫也没啥好名字,直直儿就叫猫王。”
“猫王?它何以称王?”
“听说每日夜间,把关着猫王的笼子搬到屋子里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这笼子四周,密匝匝儿都是伏着的死鼠。”
“这是咋回事?”王希烈惊愕。
“这就是猫王的厉害,”纪有功虽是道听途说,却像真的看见过一般,起劲儿渲染道,“它根本不用出笼去捕抓什么的,只要蹲在哪儿,附近的老鼠都会主动跑到笼子跟前来,见着它就死。”
“这才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王希烈感叹道,“这礼物送到小皇上跟前,他还不要喜得跳起来。”
“是啊,朝鲜特使会办事。”纪有功随声附和。
王希烈兴奋得满脸通红,示道:“你去告诉差官,今天就让朝鲜特使进京。一应如仪,接待费用嘛,你详细造个单子,到户部要去。”
纪有功搔搔脑袋,忧心说:“听说户部没有钱,里里外外演的是空城计。”
“这不是你管的事儿,”王希烈横了纪有功一眼,“你的任务是造好报单,到户部要钱。”
“是,小的这就去办。”
纪有功挪转身,刚要出门,王希烈又把他喊住,说道:
“给我备轿,去童立本府上。”
半上午时分,秋高气爽的北京城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一如往昔。王希烈乘着八人大轿,带着礼部一帮官员各乘官轿像示威似的,浩浩荡荡来到童立本家。顿时间,童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被各色官轿塞满,引来不少街坊邻里驻足围观。
童立本的侍妾桂儿,早已哭哑了嗓子,这会儿躺在床上起不来。坐在木圈椅上的童从社,傻乎乎地嚷着“饿”,并不明白父亲的死是怎么回事。内内外外,只苍头老郑一个人忙。以至
王希烈一帮官员涌进门来,既无孝子还礼,也无半点哭声。这情形反倒比合规合矩的丧礼更觉凄惨。这些官员虽然都是童立本的多年同事,但谁也没有来过他家,乍一看这股子穷酸光景,四壁萧然,蛛网联窗,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具,顿时心里都酸楚得不得了。再听老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了童立本寻死的前后经过,大家更是难过。王希烈当即倡议大家凑份子钱来帮助料理童立本的丧事,并带头捐了二十两银子。众官员不拘多少,你十几两,他三五两,竟也凑出了一百两银子。王希烈又指示礼部仪制司的几位吏员说:“你们是童大人的属下,童家没有人,这丧事就由你们来操办。我看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祭的人有个落脚处。你们还要花钱请几个哭婆子来,本官听说,哭是很有讲究的,你们务必请几个会哭的,要哭得昏天黑地、撕肝裂肺那才叫好,并且要保证一天十二时辰哭声不断。另外,再请一班吹鼓手,有人来祭奠,就大奏哀乐。童立本在礼部这些年,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因此丧事尽可能办得隆重,以慰他在天之灵。”想了想,王希烈又补充说:“当下最要紧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以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遍告在京各衙门官员。要把童立本的苦处写得淋漓尽致,以争取更多官员的同情,都来捐助点银两,给童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赡养费,使他们不致于冻馁而死。这些事都务必做好。”王希烈说完,准备起轿回衙,忽见苍头老郑把半死不活的桂儿扶了出来,朝王希烈面前一跪,气若游丝地说道:
“部堂大人,奴家有份东西给您。”
“什么东西?”王希烈俯身注目。
桂儿从怀中摸出一张纸,王希烈接过,原来是童立本的绝命诗。王希烈吟哦一遍,顿时如获至宝,让在场官员传阅。众人看了,好一阵窃窃私语。王希烈看出大家的不满,趁机抖着那张纸说道:
“你们看看,这是胡椒苏木折俸以来,死的第三个人。第一个是储济仓大使王崧,第二个是章大郎,童立本童大人是第三个。这是谁的罪过,谁的呀?”
屋子里鸦雀无声,大家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向的是谁,但谁也不敢接这个茬。这时候,一直跪在地上的桂儿又呜呜地哭起来,王希烈赶紧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关切地问:
“童夫人,童大人死时,除了这首绝命诗,可还有遗言。”
桂儿木讷地摇摇头。苍头老郑在一旁小声答道:“部堂大人,咱家主人死时,是把那两小袋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的。”
“看看看,这就是遗言,”王希烈情绪激动,义愤填膺说道,“童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不能拂死人之意,王得才!”
“小的在。”
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子从人缝儿站了出来。此人是一个老典吏,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王希烈盯着他,说道:
“你现在就把童大人的这两袋胡椒苏木,送还给户部。”
“这……”
王典吏知道这是个麻烦事,怕惹火烧身。王希烈看透他的心思,讥道:“你怕担干系是不是?拿着童大人的绝命诗去给他们看,就说是咱王希烈让送的,你怕什么!”
“小的遵命。”
王典吏退回一步,这时有人小声插话道:“听说七彩霞的老板郝一标,今儿早上贴了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
商人有几个是好东西?”王希烈没好气地斥道,“咱宁可丢到粪窖里去,也不卖给他。”
“部堂大人说得对,无论无何,不能让铜臭熏染士林。”有人大声附和,“有种的,就学童大人,把这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
“对,退回去,为童大人伸冤!”
众官员的情绪终于被撩拨起来,童家小屋里,已是一片沸腾。
第二天,在京各衙门官员,几乎都收到了如下这份讣告:
诸世伯世叔:
家父礼部仪制司六品主事童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两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着,求借无门,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六品乌纱,举家如同乞丐;廿载宦海,到头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恸哉!
不孝之子
童从社
童从稷泣告
这份讣告由吏员起草,本司郎官修改,最后送给王希烈亲自审定再行誊抄,然后送达京城各大小衙门。讣告虽短,却相当煽情。许多官员读后都动了恻隐之心,莫不相邀前往童立本家祭奠。按京城吊仪,每位前往的官员都会送去一道挽幛。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胡同都摆满了灵旗挽幛。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被请来哭丧的十几个哭婆子特别卖力,只要人一来,她们就撕肝裂胆地干嚎,加之吹鼓手们也各尽其责,吹吹打打弄得气气势势,特别是那一只唢呐,时而呜咽时而凄厉,直聒噪得几条街都不得安宁。
这天上午,在祭吊的人中,来了两个显眼的人物,一个是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另一个则是张居正的亲家刑部右侍郎刘一儒。两人都是三品大员,到目前为止,前来祭吊的官员就数他俩品秩最高。一看到他俩的轿子抬进胡同,在现场指挥操办丧事的王典吏赶紧让吹鼓手们大奏哀乐,在呜哩哇啦的唢呐声中,十几个哭婆子尖着嗓子,一齐放了悲声:
哎哟——
我的童大人嘞,我的童大人,你凭什么这样的狠心,丢下傻子儿,丢下苦命的老婆
一脚踏上奈何桥,要去阴曹会阎罗,满街的人都在说,这是胡椒苏木惹的祸……
哭婆子们个个嘴巴滑溜,编词儿应景都是高手。加之哭功到了家,嘴一瘪就哭,一哭就有眼泪。听得她们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的吊客有几个不动情的。
却说魏学曾与刘一儒两人在哀乐声中一前一后进了灵堂,祭拜完毕,早有人把灵堂中挤满的挽幛挪走了两副,临时把他们的挽幛换了上去。挽幛上照例都书了挽联,众人挤上前来吟读,刘一儒写的是:
天下斯文同骨肉
人间涕泪动参商
魏学曾写的是:〖HT5F〗〖GK2!〗
赴黄泉已无告,管不得社稷生死
卖胡椒而不售,又遑论官帙荣衰
这两副挽联,刘一儒纯粹是举哀,其心也沉,其情也殷。魏学曾则不然,字里行间,都是借题发挥的怨气。刘一儒做人一贯拘谨,不巧在这里碰上了京城里有名的“魏大炮”,且知道他专门与自己的亲家作对,心知再呆下去会惹出是非来。连忙把随身带来的十两银子放在操办丧事的王典吏手上,拔腿就出了门,正欲登轿,后面传来重重的一声喊:“刘大人,请慢走一步!”一听就知道是魏学曾的声音。刘一儒无法,只好放下刚刚撩起的轿帘儿,回转
身来,魏学曾已站在对面了。
这些时,魏学曾虽然不像王希烈那样上蹿下跳几近疯狂,却也不曾闲过。一是就京察之事向王希烈通风报信,二是凡来吏部拜会他的人,一概接待毫不闪躲。这个人同王希烈不同,他不搞阴谋,但“阳谋”却一天也不曾停止。王崧死后,他本着对太监内侍天生的仇恨,一次次到王崧家里慰问,正是受了他的影响,王岩才铤而走险为父报仇。今日来吊唁童立本没想到会遇到刘一儒,便想通过他把自己的怨气传给张居正,于是拦住了他。“啊,魏大人,”
刘一儒弯身一揖。喊了一句,竟没有了下文,只站在那里干笑。
“刘大人,举哀一完,你就赶紧撤身,是怕咱魏大炮把你吃了?”魏学曾开口就呛。
刘一儒仍是干笑着,答非所问地说:“童立本实在可怜,所以下官略具薄仪,前来一奠。”
“现在的京官,又有几个不可怜呢?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俸,童立本会死吗?”魏学曾说着,抬头望了望高远的蓝天,长叹一声,接着说:“以实物折俸,国朝一百多年来,仅有那么几次,没想到我辈会轮上。先帝在的时候,宁可减后宫嫔妃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外廷官员们的俸银。如今大行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怆然离京,你那位亲家江陵先生辅佐幼主开展新政,原也无可厚非,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瞩目的新政,竟从苏木胡椒折俸开始。刘大人,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刘一儒是荆州府夷陵县人,与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榜进士,因此两人过从甚密结为亲家,张居正唯独一个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儒的大儿子刘勘之。刘一儒向来居官自守颇有清名。张居正入阁数年,他从来不攀附,不结纳,只是老老实实做自家职位份内之事,因此在京官同僚中颇有好评。魏学曾正因为这一点,才敢在刘一儒面前泼辣说话。
刘一儒听了魏学曾夹枪夹棒一席话后,心里头颇不是滋味。但问上脸的话不答又不行,只得敷衍道:
“听说国库空虚,胡椒苏木折俸,实不得已而为之。”
魏学曾指着满巷的悬幛,悻悻说道:“首辅这一个不得已,害得童大人丢了一条命啊!”
刘一儒一言不发,他从来就是遇到是非三缄其口。魏学曾也不指望他有什么表态,又换了个话题说:
“刘大人,先不与你谈胡椒苏木的事儿,目下外头有些传言,对你不利啊。”
“啊,有何传言?”刘一儒问。
“如今的刑部,堂官王之诰,佐贰官你刘大人,都是首辅张江陵的儿女姻亲。因此有人说刑部成了首辅的私囊之物。”
魏大炮这一“炮”轰得刘一儒面红耳赤,嘴唇嚅动了几下,说道:
“高阁老的姻亲曹大人,不是也在刑部么,怎好说这是张江陵的私囊之物。”
“曹大人尚在刑部不假,但这次京察,他恐怕同我魏大炮一样,都是第一批遭受清洗之人。”魏学曾话音一落,刘一儒马上回答:“魏大人放心,我刘某恐怕比你们走得还早。”
“啊?”
刘一儒的回答多少令魏学曾有些诧异。还不及理论,忽见得巷子口又落下一乘官轿,内中走下一名身穿杂色文绮白鹇五品官服的半老官员。魏学曾一眼认出这是都御史衙门的佥事李大人。李大人也认出了眼前两位三品大臣,忙拱手行礼。
魏学曾抱拳一揖,问:“李大人也来祭吊?”
李大人恭谨回答:“葛大人委派卑职前来代祭。”
“是都御史葛大人?”魏学曾问。
“正是。”
李大人答罢,便命掾吏将手中挽幛送进灵堂,只听得哀乐齐奏,哭婆子又一阵干嚎。魏学曾与刘一儒禁不住好奇,又一齐回到灵堂观看。只见灵堂正中最显眼的位置,已是高高悬起了左都御史葛守礼送来的挽幛,上面也书了一对挽联:
任上清官,瘦骨苍颜形影只
胸前遗物,苏木胡椒袋子双
这一联写得冷峭,寓意深沉,自不可以同情怜悯指斥时事等简单解之,魏学曾玩味再三,不
“终于有一个大九卿出面了,刘大人,这联句如此老辣,可见葛老别有襟抱。”
话说完,却不见有人应声,掉头一看,却不知刘一儒何时已经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