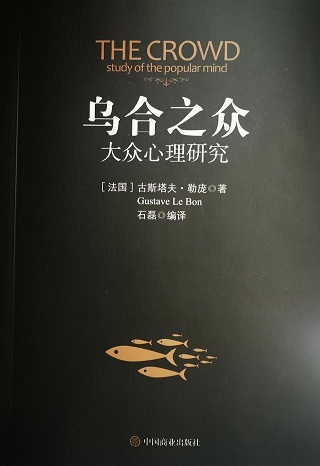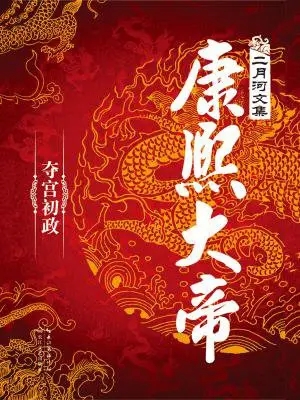“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极两年以来,虽垂髫少年,却天纵英姿,决心开拓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幸。自前年京察始,臣每有建议,皇上都虚心采纳,并颁旨例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事量权,揣情谋断。且喜今日,普天之下,百端补治清慎勤明的吏治新局面已经出现。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还不是盛世。因为,时下国家的财政,尚在非常艰难的境地。”
李太后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如此意气风发地议论国事,包括她的已经大行的丈夫隆庆皇帝,也包括她的一言九鼎的儿子万历小皇上。趁张居正喝茶润嗓子之机,她插话问道:
“如何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想必张先生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臣自隆庆二年人阁担任辅臣,就一直关注财政问题,”张居正怕说哕嗦了李太后不耐烦,故尽量言简意赅,“江南三大政,漕政、盐政、河政,都是财政,北边之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方才太后问及的子粒田问题,就更是财政了。天下田亩,额有定数,勋贵手中多一亩子粒田,朝廷就少一亩田赋。臣算过一下,如果仅从宗室所有子粒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交国家,朝廷就多了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这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麾下十万将士一年的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子粒田都如此办理,则北方九边的军费几可解决一半。”
“有这么多吗?”李太后问。
“臣认真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
李太后立刻盘算起来:慈宁宫在宛平县的子粒田一百七十多公顷,若征三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五千多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带了这个头,天下所有子粒田的拥有者,则都不敢违抗。仅此一项,朝廷一年就多了几百万两银子的收人。张先生为天下计,方有此议,自己断不可为些小私利而不支持他,何况这天下又攥在自己儿子手中。主意既定,她便对张居正说:
“张先生心忧财政,本是替皇上操心,哪一个想当英明君主的人,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一个丁门小户的人家,打开门来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大事,何况一个国家?手上没有银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咱看你提议的财政改革,就从子粒田改起。每亩加征三分银,这数码儿不大。你回去让户部拟条折子送给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就是。”
张居正没想到李太后答应得这么爽快,感动地说:“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惟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国家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墨侈糜之风,另一方面针尖削铁广开财路,臣保证不出两年,财政拮据的状况,就会根本转变。”
“有你这句话,咱就放心了,皇上也就放心了。”李太后说着浅浅一笑,又道,“本当说今天到大隆福寺来散散心的,谁知又板起面孔谈了这半天的国事,咱真是有些乏了。”
“是臣烦累了太后。”张居正一脸歉意说道,“请太后回大内歇息。”
“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李太后忽然咯咯地笑起来,问冯保,“冯公公,人带来了吗?“
“带来了。“
冯保答罢朝张居正诡谲地一笑,已是闪身出门。
客厅里,只剩下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个人。忽然,两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李太后瞅了瞅正襟危坐的张居正,脸上泛起了红晕,她伸手抚了抚云鬓,问道:
“张先生,咱刚才发脾气的时候,样子很难看吧?”
张居正不禁诧异:太后怎好拿这样的话来问一个外廷的大臣?但他还是老实答道:
“臣当时一门心思只想如何训斥金学曾,倒是没有注意到太后。”
李太后娇甜的眼神里掠过一丝失望,又问道:“你想知道刚才你论述国家财政时,咱在想什么吗?”
“臣想知道,请太后详示。”
“咱在想,这位张先生脑瓜儿怎么这么好使,那么多枯燥的数字全都记得,张口就来,连哽都不打一个。仅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政事的人。”
“太后过奖了。”
“咱说的是实情,”李太后感叹道,“当皇上的,最怕大臣文恬武嬉,有张先生作文武百官的楷模,皇上再不用担心朝局了。”
张居正心底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局的是她自己,便回道:
“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他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君主。”
“但愿如此,”李太后心存感激,投向张居正的目光也就更为大胆,“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器?咱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更不同常人,幸好钧儿在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研政事,已有一个好的开端。”
张居正赶紧纠正:“臣不敢教导皇上。”
“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李太后真情流溢,感叹说道,“作为母亲,咱看得清清楚楚,对钧儿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另一个就是你!”
“太后!”张居正不知所措喊了一声。
“张先生不必紧张,这是咱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虚假,咱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还用得着虚情假意巴结人吗?”
李太后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张居正浑身不自在。但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哽咽答道:
“太后如此器重下臣,臣无以为报,当结草衔环,誓死效忠皇上。”
同刚才议论国事慷慨陈词相比,这张居正好像换了一个人,面对首辅的这份拘谨,李太后仰面吁了一口气,又问:
“张先生,你觉得太后不像一个女人么?”
“不.....。”张居正语塞了。
“不,不什么?”李太后追问,不等回答,她又问道,“你觉得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太后端庄贤淑。”
“还有呢?”
“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
“这是张先生的真心话?”
“是真心话,”
张居正已是浑身燥热,嗓子干得冒烟,却又想不到喝水。李太后看着他的窘态,忽然有了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说道:“骆宾王的《讨武檄文》,骂武则天‘入门见嫉,狐媚偏能惑主。’这是穷酸文人的谰言!狐媚是女人的本钱,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儿,也没有不喜欢狐媚女子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帝身边美眷如云,后宫嫔妃尽是佳丽,你若不狐媚,又怎能技压群芳而获宠?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
守到白头?当然,狐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若要固宠,还得端庄贤淑。所以说,狐媚与端庄,乃是一个女人的两面,二者不可偏废。”
这一番奇论,张居正闻所未闻。不过也让他就此找到了李太后当年在后宫脱颖而出的理由。他觉得眼前这位年不过三十的美丽太后不但可敬,而且可爱,不免由衷赞叹:
“太后真乃巾帼英雄!”
谁知李太后不领情,把嘴一噘,讥道:“张先生,你这一评价,咱就俗了。”
“啊?”
“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够博得男人的欢心。”
张居正的心怦然一动,他看到李太后眼光中有某种企盼,便小声言道:
“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也许寂寞了一些。”
“是啊,”李太后的心思被勾动,只见她眼眶中溢出晶莹的泪花,感叹道,“作为女人,咱有七情六欲,但作为太后,咱又不能不把这些七情六欲扼制下去。”
“太后母仪天下.....。”
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出口又觉得不像,便打住了。这时,只听得门外有一声轻轻的咳嗽。
“谁呀?”
“是咱。”
冯保的声音,他出去喊人,本用不了这长时间。但他看出李太后有单独与张居正多呆一会儿的意思,就在外头磨蹭了半天。
“人带来了吗?”李太后问。
冯保隔着门答:“带来了。”
“进来吧。”
门被推开,冯保一让身子,让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子打前走了进来,张居正注目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宠爱的玉娘。
“怎么会是你?”张居正情不自禁站起身来。
玉娘也看到了张居正,但来不及打招呼,只见冯保指着李太后对她言道:
“这是慈圣皇太后。”
玉娘赶紧跪下磕头,李太后紧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才吩咐赐座,然后笑着问张居正:
“张先生,没想到吧?”
“臣.....。”张居正脸色燥红,不知说什么好。
却说在前几日的一次闲聊中,李太后从冯保口中得知张居正宠上了一位叫玉娘的小女子,她顿觉好奇。在她的印象中,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没有想到他也会花前月下情意绵绵。今天上午到了大隆福寺后,与张居正谈话时,她突然灵机一动,想把玉娘找到这里来见上一面,于是在中午用膳时偷偷吩咐冯保派人去办这件事。
乍一见玉娘,李太后惊叹她的美貌,看她走几步路儿,袅袅娜娜,却没有轻薄之态,又问了她几句闲话,无非身世籍贯之类,玉娘也不怯场,大大方方应对无误,心中对她已是产生了几分好感。看到张居正在一旁局促不安,李太后笑道:
“张先生,听说你身边多了一位玉娘,咱就想看看是何等的一个标致人儿,所以今天就让冯公公去积香庐把她请了来。”
张居正一听李太后什么都知道,心里头有些紧张,不安地答道:“臣行为不检点,有失大臣风范。”
“先生不必自劾,”李太后以少有的亲热语气说道,“咱这个太后不是呆板之人,前些时,看到张先生为国事如此操劳,咱还寻思着,在宫里头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宫女赐给张先生,让她好好儿的侍候你。谁知宫女还没选出来,这位玉娘倒捷足先登了。这是好事,你不要自责。”
“谢太后。”张居正心存感激。
“玉娘,你过来。”李太后忽然喊道。
玉娘起身走到李太后跟前,李太后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又看了看她的一双扑闪闪的杏眼,白皙圆润的下巴颏儿,叹道:
“看你这副长相,也是个有福的人,跟着张先生,不致败他的运。”
“多谢太后夸奖。”玉娘蹲了个万福。
李太后朝张居正瞥了一眼,又对玉娘说:“咱若不是太后,肯定就要起你的醋意儿,玉娘,从今天起,你就算从我身边选拔的宫女,好好服侍张先生,不可耍娇使性子,你记住了。”
“奴婢记住了。”玉娘羞涩地一笑。
“记住了就好,没事儿的时候,咱会宣你进宫拉拉嗑子的。”李太后说着,又问,“听说你很会唱曲儿?”
“奴婢学过几支。”玉娘谦虚地答。
“现在,你给咱唱一支吧。”
“不知太后要听什么?”
“你这妮子,正是怀春的年龄,你就拣怀春的曲子唱一支吧,张先生,你说可好?”
“臣听太后的。”
说话间,冯保让人将玉娘随身带来的琵琶拿进来,玉娘略一沉思,就捻指弹唱起来:
念多情,抛不掉他的情意儿厚,清晨起闷悠悠,桃红纱帐挂金钩。
孤孤单单无陪伴。
懒对菱花怕梳头。
热扑扑的离别恨,把奴的魂勾。
谁能够把情留、把情留?
背地里,奴的泪双流。
奴是一颗实落心,生生教你温存透。
温存透、温存透,可恨奴家无来由,梦赴阳台把佳期凑,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看天边,残月如钩......
玉娘唱的是《岭儿调》,凄切哀婉。唱着唱着,她已是泪流满面。冯保在一旁观察,只见张居正眼睑低垂,负疚之情已在脸上显露。而李太后受到的感染更深,几颗晶莹的泪珠,正滚动在她的发烫的脸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