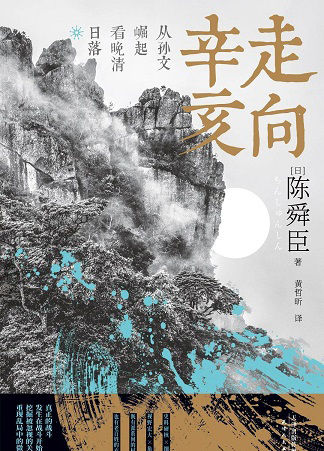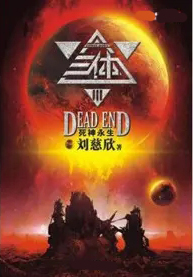毛泽东的车经常被人群挡住。成群结队的农民群众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毛泽东,否则,他们会发出震天的欢呼声,甚至会把车堵住,要围着自己的领袖看个够、问个够的。所以,司机尽量把车开得快一点。毛泽东到合肥后,十分高兴地说:
“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此时已近傍晚时分。毛泽东稍事休息,与江青一起接见了来合肥的全国妇联干部和省妇联干部。他说:
“我看沿途晚稻长得好,宣传工作也不错,你们看怎么样?”
全国妇联负责人说,她们已经看了三八社和东方红一社妇女卫星棉田。毛泽东逗趣地说:
“不要光看女的,男的也要看一看嘛。”
曾希圣说起无为县响山大队有一个复员军人叫陈广夏,原来在部队上做过供给工作,当了大队干部后,在大队试行了供给制。毛泽东听了,称赞陈广夏是一个人才。他还不无幽默地笑着说:
“无为不单出了个《水浒》人物黄文炳,还能出这个陈广夏。搞供给制,好嘛!如果每年每人没有1000斤、2000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毛泽东了解到妇联干部中有几个曾在新四军待过,还有部队培养的作家,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都是新四军!共产主义的传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从前是红军,后来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变成一个军——人民解放军。部队多好啊,就是有战争年代那样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多好啊!”
晚上8点半,毛泽东、江青、张治中等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庐剧团新编的一个喜剧《牛郎织女笑开颜》。剧中表现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管神仙。演出结束了,毛泽东笑着说:
“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打一仗哩!”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借阅了《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他翻了一会儿书,还是很兴奋,就给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称赞这几天在湖北“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
接着,他又为新建的“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并就不同意把省会迁到芜湖的事,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曾希圣同志:
校名遵嘱写了4张,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为何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9月16日
这一夜,毛泽东通宵没有睡,一直到17日早上8点才上床休息。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参观安徽省博物馆,他在矿产馆观察了矿石标本和安徽矿藏分布图。在机械馆和轻工业馆新产品展台前,他笑着对曾希圣说:
“看来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的好东西都偷来了,你是存心抢上海的生意吧?”
农业馆陈列的巢县复兴乡的棉花标本,棉杆有一人高。毛泽东用手摸摸棉杆和棉桃,说:
“这株棉花的桃子不少。”
从凤阳县烟草试验田采集的两株烟叶标本,也有1人多高,叶子像水芭蕉一样。毛泽东说:
“这两株烟叶很好!”
他在小麦和水稻丰收的图片前,看着图片上的新民歌,忍不住朗声念道: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
水利馆里挂有一幅淮北实行河网化成就和规划示意图,以及濉溪县河网化示意图。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后对曾希圣说:
“啊,大工程!明年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你们应该把这张图挂到北京去。”
他在“除四害”展馆前,念了一遍“除四害”成就的文字说明,说道:
“你们消灭的老鼠、麻雀真不少呢。消灭这么多鼠雀可以节省多少粮食?”
省“除四害”指挥部副指挥杨杰说:
“节约的粮食以每人每年500斤计算,可供600万人吃一年。”
毛泽东又观看了展馆里陈列的多种捕鼠器具操作表演,他笑着说:
“这对老鼠真是大为不利咧!”
他看了卫生陈列馆,对安徽省已有14个县100多个乡消灭血吸虫病表示高兴。在历史文物馆,他对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芜湖铁画家汤鹏的作品很感兴趣。
汤鹏,号天池,安徽芜湖人,少为铁工,与画室为邻,每天看人作画,受到启发,便大胆地融汇笔墨艺术于炉锤焊接之中,创立铁画,因而名噪一时。以铁作画,以铁书联,是中国独特的书画品种。
毛泽东读着汤鹏的草书对联,很有兴味:
“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
读完了,他盯着“露”字,又仔细端详了一下,说:
“露字脱掉了末尾一笔,应当添起来。”
毛泽东在休息的时候,很满意地说:
“相当丰富,看不完。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他在博物馆一连看了2个半小时,这是他在安徽视察中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是日晚,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的住处聊天,说到群众的习俗问题,毛泽东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有两个人为了意见不合,大抬其杠,乃至动武,正打得不可开交,来了一个过路人,手上提着一大捆雪白的大葱。这两个人马上停了手,迎着过路人走去。”
在座的人见毛泽东住了口,故意卖关子,就不懈地问:
“为什么?”
毛泽东说:
“原来他们是山东人,酷爱吃大葱,兴趣比打架还要大。”
众人闻言,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又谈起《三国演义》中的吕蒙,他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他又谈到陆机、陆云兄弟,他说: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毛泽东指着《楚辞集注》,问张治中:
“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说:
“未读过。”
毛泽东说:
“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他又说:
“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张治中说:
“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
毛泽东说:
“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接下来,他谈到了《论语》,谈到了《论语》的朱注,谈到了朱熹的思想。又由朱熹谈到了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4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9月18日下午4点多,毛泽东视察省委办的钢铁厂,看了两座13立方米高炉的出铁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介绍说:
“这是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每天出铁20多吨。”
毛泽东说:
“对啊,省委应该带头办嘛。参加劳动的是不是都是工人?”
曾希圣说:
“除少数技术工人外,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
毛泽东看了2号炉出铁后,说:
“铁不少啊!”
车间副主任曾传火笑着说:
“毛主席来了,铁也多了。”
毛泽东微笑着看看他,问:
“你们有没有休息时间?”
曾传火说有。毛泽东打量着他的小胡子,做了一个手势,说:
“你的胡子也该剃一剃了。”
从这个厂出来,毛泽东又去视察了合肥钢铁厂,观看了转炉出铁的情况。
傍晚时分,毛泽东到了设在西郊野外的新式农具展览馆,观看了各种改进和发明的农具。看了人力绞车和改良深耕犁的表演,他说:
“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1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1亩当3亩。总之,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
天已经黑了,毛泽东才离开展览馆。按照视察计划的行程,9月19日毛泽东要离开合肥去芜湖。张治中再一次动员毛泽东去游黄山,毛泽东不屑地说:
“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
张治中怎么也想不明白,毛泽东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原来,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他说: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他动员毛泽东去安徽游黄山。毛泽东问:
“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
张治中答道:
“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
毛泽东闻言不快,正色道:
“我不能坐滑竿!”
当时,张治中就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坐滑竿。这一次,毛泽东的话,更使张治中如入五里雾中。
9月18日晚,毛泽东在合肥得知,美国在华沙的谈判代表提出了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所谓“停火”方案。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也提出要尽快“停火”。他立即用电话传信给周恩来,对谈判提出建议。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并连夜以周恩来的名义用电话将研究结果报告给毛泽东。
9月19日凌晨,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事。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
报告中提出了5项具体措施:1、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在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2、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3、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驻华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的行动。4、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5、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他们注意。
凌晨4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这份报告上批道:
“18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然形态。”
9月19日,美国声称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
苏联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核攻击,那么,美国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
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指示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9月19日午后,毛泽东要离开合肥了,曾希圣按照原来的计划,组织群众欢送毛泽东的安排也已经就绪。原计划人数为15万,可是消息传开后,邻近几个县的群众也闻风而至,竟多达二三十万之众,从省委到火车站,长达数公里的道路两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天上飘着雨点,脚下一片泥泞,人们却没有丝毫感觉,纷纷议论着,翘首以待。
下午2点15分,毛泽东由曾希圣陪同,乘坐第一辆绿色敞篷车,由金寨路缓缓驶进市区;后面跟着的是张治中、江青、罗瑞卿和安徽省长黄岩乘坐的吉普车及其它车辆。
毛泽东站在车上,冒着霏霏细雨,频频向两边的群众挥动着手臂,所到之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车队走了半个小时才到火车站。毛泽东进了站台,群众跟进站台,拥到车厢旁欢呼万岁。毛泽东几次从车厢里走出来,向大家招手,每一次都激起更热烈的欢腾。
将近3点钟,列车徐徐开动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罗瑞卿对张治中说:
“今天这种夹道欢送的做法,是毛主席出来视察的第一次。”
张治中说:
“今天群众情绪这样狂热,他们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令人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作主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张治中说:
“这话对。不过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正确英明的领导,国家不能这么快强大,人民生活不能这么快改善,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热烈欢乐的表现。过去人们都是愁眉苦脸,而今人人喜笑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
毛泽东笑了,他说:
“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的美好远景了。”
停了一会儿,张治中当着罗瑞卿、曾希圣的面,又提到了5月22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世界观的问题。他问毛泽东:
“你在5月22日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在世界观方面有距离,指的是哪些方面?”
毛泽东坦率地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模糊的,而在今年所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
张治中解释道: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年—1948年时期的思想,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留居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包括马、恩、列的著作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
毛泽东一边点头,一边轻轻地“噢”了一声,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中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
张治中既是回答,也是询问。毛泽东却说: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你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张治中解释说:“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毛泽东和张治中还谈到了文学、历史、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彼此都感到很轻松愉快。
专列抵达芜湖时,适逢天上下着毛毛细雨。
下午6点时分,毛泽东一行人分乘几辆小轿车来到芜湖市铁山宾馆。毛泽东下了车子,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宾馆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你们辛苦了。”
来到下榻的二楼一个房间门口,他随手脱下雨帽和雨衣,服务员小翟赶忙伸手去接。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自己来。”
说着走过去把衣帽挂在右侧的衣架上,还对小翟和另一个服务员小王说:
“你们辛苦了。”
小翟说:
“毛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询问了小翟和小王的姓名和年龄,鼓励她们要好好学习,接着问:
“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
小翟说声“有”,转身去取来报纸,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边翻看报纸边说: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不一会儿,小王告诉毛泽东说:
“毛主席,晚饭好了,请您到小餐厅用饭。”
毛泽东问:
“其他同志在哪儿吃饭?”
“在外边的大餐厅里。”
“我也到大餐厅里去吃。”
毛泽东说罢,起身就往门外走。下了楼,外边还在下着小雨,小王撑起了一把伞,竭力想罩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踮着脚顺着小山坡跟在他身后往下跑。毛泽东回头看了她一眼,微笑着说:
“我自己来吧。”
说着,他接过伞,大步朝餐厅走去,就餐的人们立起身热烈鼓掌。毛泽东在餐厅里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然后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招呼大家说:
“开饭了!来,坐,坐。”
餐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女服务员跑过来要为毛泽东盛饭,毛泽东不肯,他说:
“我自己来。”
说着端起碗就去盛饭,却发现饭桶里没有饭勺。服务员顿时慌了,急忙去找饭勺。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伸手从餐桌上抄起一把长柄汤勺,笑着说:
“这个不能盛饭吗?”
说罢从饭桶里盛了大半碗饭。张治中也自己去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看他盛的。”
曾希圣说:
“真像个窝窝头。”
毛泽东要来了一小碟生腌辣椒,尝了尝说:
“很好,大家来尝尝。”
张治中说:
“我怕辣,不敢吃。”
毛泽东说:
“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吃过晚饭,毛泽东出席了两个集会,还接见了芜湖地、市1000多名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代表。回到住地,已经11点多了。他要小王找张桌子来。小王把走廊里的一个两屉桌子搬了来,毛泽东和她一起抬着放到床前。小王转身去找椅子,毛泽东说:
“不要找了,坐在床上就行。”
他把床头柜上的台灯移到桌子上,见台灯太矮,顺手把一个方形茶叶筒放倒垫在下面,就开始批阅起文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