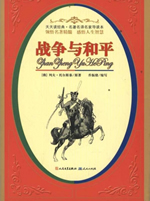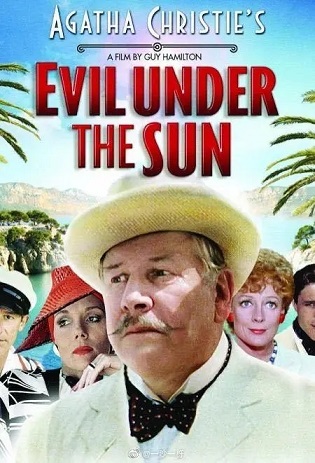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正月初八,家住张掖郡觻得县北乡义成里的百姓崔自当想要前往居延县买一些生活用品。居延汉简记录下了他此次出行得以实现的经过:
1.崔自当向当地政府提交申请。
2.一位叫“忠”的基层官员受理了他的申请,他审查了崔的经济状况(逃税、漏税)与犯罪记录,确认其有出行资格。
3.觻得县丞“彭”出具相关文件,发往崔前往居延县必经的两个城关,该文件同时需要有县掾“晏”和令史“建”的附笔(签字)才能生效。(1)
所有这些手续,都是为了确保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崔自当不会逃往匈奴。审查崔的经济状况和犯罪记录,是为了确保他没有逃亡的动机,而且崔只能在居住地和特定的目的地之间流动。毕竟,只有将人口控制在汉帝国的疆域以内,汉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
小民崔自当出门的故事,显示了汉帝国对自己在边境地区的统治并无自信。新莽政权正是在汉帝国丧失自信,知识界也在激烈批判汉帝国、说它天命已尽的背景下诞生的。王莽登上帝位之时,可谓前所未有的天下归心。但仅仅过了十五年,新莽政权就从天下归心走向了天人共弃,王莽也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从统治术的角度来审视,王莽究竟做错了什么?
一、表演赢得万民拥戴
王莽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与他近乎变态的政治表演有直接关系。比如,在遭汉哀帝逐出京城、在封地闲居期间,王莽曾逼迫儿子王获自杀,原因是王获杀死了一名家奴。这样极端的做法给王莽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史载,王莽在封地闲居的三年里,“吏民上书冤讼莽者百数”,有上百人给朝廷递陈情书,认为王莽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求皇帝将他召回朝堂。(2)
同行的衬托也让闲居期间的王莽形象变得更加高大。汉哀帝刘欣为重塑皇权,驱逐已故汉成帝的王氏外戚,提拔重用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丁氏、傅氏。结果,丁、傅两家外戚皆以不学无术与贪得无厌闻名。两相比较,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怀念起了遭驱逐的王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王莽才能在元寿元年,趁着发生日食的机会运作舆论,成功迫使汉哀帝将自己召回朝堂。
汉哀帝去世后,太皇太后王政君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朝廷中枢,急派使者召王莽入宫,掌控兵权。属于王莽的表演时代就此全面开启。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重修了明堂、辟雍和灵台等礼仪性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是存在于儒家经典中的建筑。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府,灵台是上古的天文台,是天子直接与上天交流的地方。这些缥缈的礼仪性建筑是上古时代圣人的标志。大约同期,王莽还奏请为长安城的儒生修筑了舒适的高级住宅和用来聚会、发表演说的广场。他还在太学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征召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重制礼乐……(3)
王莽的举措高度契合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所以,只要王莽稍加运作,长安城内就出现了对朝廷汹涌澎湃的批评。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堆满了来自“民间”的抗议信。写信者既有支持王莽的“普通百姓”,也有许多王公、列侯与刘氏宗亲。写信的缘由是王莽推辞了朝廷奖赏的田地,引发了“百姓”的极度不满,他们批评王莽的作风太过谦让,又批评朝廷对王莽的赏赐太过迟缓、太过微薄。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4)
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王莽继续表演,再次拒绝了“百姓”的要求。“百姓”的情绪配合着他的拒绝,随之达到了高潮。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认证为当代周公。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九百零二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意即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5)
此时的王莽是执掌“宰衡”大权的安汉公,权力已至巅峰。九锡之赏的有无并不影响他对汉帝国的实际控制,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因为这是《周礼》记载的终极荣誉,只有周公这样的伟大人物才有资格得到。成为当代周公对王莽而言意义非凡。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的仪式上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无人知晓仪式是否合规,因为六百多年前的礼仪规矩早已失传。
同年秋天,王莽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陆续回到了长安。他们带回了“天下风俗齐同”的好消息,说民间的风俗已在王莽的引领下回归纯朴,百姓的生活也在王莽的关怀下走向美满。他们还带回了“百姓”赞颂王莽的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也是在这一年,王莽提出了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6)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王莽创下了如此伟大的功业,上天理应赐下相应等级的祥瑞。于是,南方的越裳氏献上了白雉,东方的黄支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变更了首领的称呼以示归顺。西方迟迟未见动静,王莽就自己动手来弥补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贿赂一位羌族酋长,将他带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短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他们感激安汉公(王莽)的英明神武,甘愿退回深山老林,献出现在拥有的肥沃土地。“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且根据《周礼》的记载,将汉帝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宣示西周盛世得到了复兴。(7)
如此种种,让诸多对“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帝国心存不满的儒生热血沸腾。
扬雄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患有严重口吃的大学者在40岁那年离开蜀地,来到京城。他没有任何背景,历经三朝,仍是个小小的黄门侍郎,多年来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元始四年,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扬雄正在撰写新著《法言》,带上十万钱来到长安,希望能够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与事迹,却被扬雄拒绝。(8)这样耿直的扬雄却在《法言》一书中为王莽留下了一段极尽歌颂之能事的文字:
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9)
在扬雄的眼里,王莽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他勤于政务,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的伟大人物。这些话大概率是扬雄的肺腑之言,因为扬雄不是一个谄媚之人,也因为同时代的其他儒生,比如治《春秋》的权威左咸、治《诗》的权威满昌、治《易》的权威国由、治《书》的权威唐昌、治《礼》的权威陈咸、治《乐》的权威崔发也都对王莽有过相似的认同。(10)
所以,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公元8年腊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了帝位。新莽取代了汉,长安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没人在意王莽受禅前夕的那些弄虚作假(比如盲流哀章伪造了受禅天命),那些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重要的是,上古的禅让终于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终于诞生,一个有别于“以霸王道杂之”的时代即将到来。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了新朝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做皇帝是如何的天命所归,如何的无可推辞。
二、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新莽政权存在的十五年里,王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具体包括:
1.恢复井田制。王莽在诏书中写道:天下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11)
2.释放奴婢。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西汉极为庞大,共约有官、私奴婢230万之多(西汉末年的数字可能要更高一些),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奴婢(汉元帝时朝廷有“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对一个约有5800多万编户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会严重影响到朝廷征收税赋、徭役与兵役的体量。(12)
3.改革币制。王莽的货币改革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政治账。政治账有两笔,第一笔见于王莽的诏书:我当年为了挽救大汉,而推出以刀币取代圆钱的币制改革。然而如今刘汉已亡,天命在我。“刘”(繁体字为“劉”)乃卯、金、刀的组合,所以金刀钱已经不符合天意和民心,应该彻底废除。(13)第二笔见于某个不知姓名之人的上书,说什么“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14)——放弃贝壳,改用铜钱是百姓贫困的根源,这番谬论还得到了大臣师丹的认同。对王莽来说,铜钱是不是导致百姓贫困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定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就是龟、贝,而自己要做的正是当代周公。所以,龟、贝在退出货币系统数百年之后,再次在新莽时代粉墨登场。
4.盐、铁、布帛等商品生产、销售的国有化,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儒家经典著作。比如,新莽的羲和(大司农)鲁匡主张国家控制酿酒业的理由有二:第一,据《诗经》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是控制在官府手里的。孔子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第二,酒水官营才有质量保证,放开民营一定会造成质量低劣。(15)这两条理由,一是硬凑教条,二是想当然的胡说八道。
5.官名、地名改革。在王莽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众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而那些伟大的名称包括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都存在于《周礼》《礼记》等古代圣贤的名著里。王莽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光怪陆离的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从古籍中翻查出来,古籍中找不到的,则以吉利的政治寓意为第一位。比如将琅玡郡改名“填夷郡”、陇西郡改名“厌戎郡”、天水郡改为“填戎郡”、雁门郡改为“填狄郡”、代郡改为“厌狄郡”、诸暨县改为“疏虏县”、黟县改为“愬虏县”、武都县改为“循虏县”……(16)
王莽的五项改革当中,改官名、改地名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盐、铁、布帛生产、销售的国有化也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生产、生活的负担;货币改革更是让百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但对王莽的权位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受到损害的主体是百姓而非权贵、官僚集团,后者才是王莽的统治基础。
而让新莽政权短命夭折的是王莽的前两项改革——恢复井田和释放奴婢。后者很容易理解——奴婢是权贵、官僚的私产。释放奴婢可以增加朝廷编户民的数量,增加朝廷的纳税户和徭役户,就等于从权贵、官僚手里抢钱。恢复井田的情况则要稍微复杂一些。
按王莽的说法,恢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土地兼并对秦制政权而言,自然不是好事,因为它会直接导致两种后果:1.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减少,进而影响到赋税收入和兵役、徭役的数量。2.田主,也就是大宗土地的拥有者,有可能变成割据势力,变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两种后果都不利于政权稳定。故而,“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所认可,且为历代政府重点打击的目标”(17)。
至于王莽所宣传的抑制土地兼并是为了普通百姓,他的话是否成立,要分情况来看。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土地兼并,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将土地卖给他人,一种是豪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将自耕农及其土地吞并。后者不必赘言,历史上凭借政治权力而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数不胜数。直到近代也还有很多依赖枪杆子而起的军阀地主。豪族的土地兼并自然是坏事,说打击它们有利于普通百姓,自然是成立的。但第一种土地兼并未必全然对百姓有害。
自耕农主动卖地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剥夺。清乾隆时期,做过广东学政的李调元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卖田说》,是讲自耕农卖地的经典文章。
李调元是罗江(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人。《卖田说》记录了他家乡的一位自耕农王泽润卖掉耕地后的愉快心情。王泽润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来解释自己为何卖了地,做了佃农,还非常高兴。王说:卖田之前,自己是一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十亩地的出产可以支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计。当地官府按田亩分摊赋税,“每十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交完赋税,还可以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但是偶尔遇上大事,官府会加征赋税,“每钱加至一两”,他家的生活凑合过得去。但问题是,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而是每年加征十次、二十次,搞得他苦不堪言。官府的诸多开支,乃至官老爷请客吃饭的酒席钱,也要按田亩向百姓征收。正如李调元在文中总结的:“十亩之田,不足以食十口家。如有五子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亩之所入,不敌所出,故不如卖田以佃田。”
农户卖了田,给地主做佃户,能更好地维持生计吗?
王泽润告诉李调元,他每亩田卖了“五十千缗”,卖掉十亩,可以得到“五百千缗”。他用卖田的钱做压佃的本钱,他还说:“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既足食,以免家室之饥寒;又无粮,以免官役之追呼。”(注:压田,一般又做“押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以低于田地实际价格的费用获取田地使用权的方式。)卖了自家的田换来的一百亩押田足够王泽润一家温饱,还可以免除官府的税赋。他种田的产出和田主平分,减去成本,留下一小半。他和家人干农活闲暇的时候,还可以织布,养一点鸡鸭,积攒下钱,还可以买牛犊、养牛,生活确实比种自家的田给官府缴纳田赋好得多。
王泽润这么一说,李调元也不想种自己的地,打算卖了田,做佃户,押田来种。王泽润告诉他:“君曾为达官,有直声,官犹待以礼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门也。所冀者,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耳。若一日无官,诚恐亦与我辈等也。”官员不仅可以免除徭役,税赋还有家丁代劳前去缴纳,官府的粮差、里正不敢催促、逼迫。李调元一听,送走王泽润,赶快告诉他的子孙,要勤奋读书,将来考取功名,保住官员的身份。因为没有了官员的身份,就会变成和王泽润一样,日子想过得好一点,只能卖掉自家的田,租种地主的田。(18)
李调元在《卖田说》中描述的皇权(及其代理人)、豪族与自耕农之间的“压榨—逃亡—庇荫”游戏贯穿了中国的整个秦制时代。自耕农主动把田地卖给豪族的土地兼并相当于给了自耕农一条逃避皇权(及其代理人)残酷压榨的生路。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赞颂豪族兼并。自耕农遁入豪族寻求荫庇,只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
回到西汉,如前文所言,秦制时代的土地兼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卖地,一种是被迫卖地。同样,在秦制时代,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循正规途径,通过耕作、经商致富的人,用金钱购买田宅,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经营性田主”。一类是手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以权力寻租,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寻租性田主”。
这两类人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大不相同的。
秦制政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保障任何人的私有财产,随时可以用政策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经营性田主”没有政治后盾,面对朝廷汲取,往往形同蝼蚁,一碾即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9)汉初有许多没有爵位和俸禄,凭借舞文弄墨、作奸犯科致富的人,他们靠经商发了财,购买田宅,经营农业成了大宗土地拥有者。汉武帝对付这类人有的是办法。比如,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即以收资产税(商业性收入)为名,鼓励百姓举报未纳税的有钱人,搞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20)的程度。再比如,推行均输、平准政策,由官府全面垄断民间商业,直接切断了经营性田主的致富之路。
但是,真正能够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是那些寻租性田主。史载,自汉武帝中晚期开始,寻租性田主即成了土地兼并的主力军。朝廷为了解决流民问题(主要是皇权的横征暴敛造成的流民问题,《汉书》中有多处记载称武帝时代“天下户口减半”,可见流民问题之严重)而拿出来分给流民耕种的公田也多遭寻租性田主霸占,造成一种“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21)的顽疾——为吸引流民重新成为朝廷的编户民,他们耕种的公田只需要按三十税一缴纳税赋,而寻租性田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把朝廷的公田控制在自己手里(比如让亲属伪装成流民或编造并不存在的流民来认领公田),再租给真正的流民,向他们榨取高达50%的田租。《盐铁论》把以上顽疾总结为:“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权家。”(22)——皇权只得了个虚名,真正的利益和财富全被权贵和豪族拿走了。
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抑制土地兼并固然有助于维护皇权,但若因此开罪权贵和豪族,开罪皇权的统治基础,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终西汉之世,权贵、豪族对土地的兼并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抑制。
王莽代汉后,雄心勃勃地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进而使皇权掌握更多的土地和编户民,故强硬推出了“王田制”。按王田制,天下所有耕地收归国有,不许买卖,家中男丁不超过八人、拥有土地却超过一井(可能相当于900亩)的须把多余的土地交出来,分给其他没有田的人。王莽改革的初衷是巩固皇权,增加皇权可汲取的财富和人力,但他改革的手段直接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就是权贵、豪族与官僚的利益。
与自己的统治基础作对是一件风险非常高的事情。在王莽的新政之下,“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23),大批权贵、豪族因为王田制而获罪。于是这些曾经拥护王莽称帝的权贵、豪族纷纷弃他而去,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比如,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的造反理由之一即王莽登基之后,“民田奴婢不得卖买……百姓怨恨”(24);出身陇右大族的隗嚣起兵的檄文里也把“田为王田,卖买不得”(25)直接列为王莽的罪状。
同时,号称要让每户自耕农都拥有土地的王田制推行下去之后,却加剧了流民问题。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左将军公孙禄曾面对面批评王莽和他的王田制,其中提到:“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26)张邯、孙阳搞出井田,使百姓不得不抛弃土地,沦为流民,应该诛杀他们以谢天下。公孙禄自然不至于当着王莽的面子虚乌有地污蔑他。赤眉、铜马等流民集团也确实出现在王田制颁布之后。
为什么一项旨在让自耕农人人有地的政策会导致自耕农集体变成流民?
道理并不复杂。不搞王田制,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多一种可以用脚投票的次坏选择总比只有一种最坏选择要好——当然,这并不是要赞美那些寻租性田主。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秋天,起义军逼近长安。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经过,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27)王莽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长安死于乱军之中,他留在史书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28)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高高悬挂起来,成了当地百姓“提击”的目标,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新莽的废墟上建立了东汉王朝。自建国伊始,刘秀和他的大臣们就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1.西汉为什么会被王莽和平取代?2.万民拥戴的新莽政权为何会短命而亡?
君臣的思考结果化为历史教训,历史教训再化为现实政策。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今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这两派的区别,简单说来就是:古文经学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今文经学更看重后人对经典的诠释。具体到汉代的政治思想领域,相比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更重视谶纬,也就是依据天人感应之说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来言说天命吉凶。自汉武帝以降,西汉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今文经胜过古文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今文经学与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纠缠在一起,玩的是割裂文辞、牵强附会的游戏,不像古文经学那样动辄拿出孔孟之言来对社会问题展开批判。支持今文经学,既可以用谶纬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刘秀登基初期,为笼络在野知识分子,曾一度将古文经《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待他权位稳固,又将《左氏春秋》从官学里剔除,理由是搞古文经的学者不懂谶纬,不能为东汉王朝的合法性添砖加瓦。(29)
对那些不认同今文经学、不愿意玩谶纬游戏之人,刘秀是极不喜欢的。桓谭是一位古文经学家,“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做学问只重视书中表达的思想主旨,不玩割裂章句、附会谶纬的把戏。而且,他非但自己不玩,还两次冒死上奏,劝谏光武帝也不要玩。他在奏章里说:先王、先贤的著述均以仁义正道为本,不妄谈怪力乱神。圣人也难以参透天道,从贤者子贡而下已无人得闻天道,后世那些浅薄的儒生就更不要奢望。如今那些妄谈谶纬的都是小人,陛下要远离他们。他们偶然说对了,也不过如同猜数字的单双,只是运气所致。刘秀读了桓谭的奏章之后很不高兴。稍后,刘秀想要修一座灵台,故意询问反对谶纬的桓谭:“我想用谶来做决定,你以为如何?”如其所料,桓谭梗着脖子回答:“臣不读谶。”刘秀遂借机给桓谭扣了一顶“非圣无法”的帽子,欲将他下狱,斩杀。70岁的桓谭“叩头流血”,良久才免于一死,被逐出了京城。(30)另一位大儒郑兴也是古文经的拥护者。刘秀曾与他谈论郊祀之事,问道:“我想用谶来决定祭祀的方案,你以为如何?”郑兴回答:“臣不为谶。”刘秀同样当场翻脸,逼问他:“你不为谶,难不成你是反对谶?”郑兴被吓了个半死,跪下,诚惶诚恐地解释:“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他说自己只是没有学会谶纬之术,并没有任何反对谶纬的意思,才保住了一条性命。(31)
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这主要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因为刘秀的提倡,谶纬在东汉被视为“内学”,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成了“外学”。自起兵反抗新莽到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长期使用谶纬作为工具来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他可以因某些人的姓名与谶纬相合,就起用他们为官,也可以与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展开谶纬之战,来回辩论天命究竟在谁身上。所以,史称“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32)。为了将谶纬的解释固定下来,刘秀将谶纬定为洛阳太学的必修课程,大力征召全国通晓谶纬的儒生前来洛阳校订谶纬典籍。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也就是刘秀去世的前一年,整理谶纬典籍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朝廷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33)。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
刘秀的两项有关谶纬的政策分别针对西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西汉末年以天命约束皇权的思想潮流。刘秀希望以“怪力乱神”的今文经学来弱化前者,以皇权垄断谶纬的解释权来消弭后者。他也确实部分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对皇权有利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有利。在朝廷尊儒政策的引导下,东汉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全民好学”的氛围。官学繁盛自不必说,开设私学的名师的弟子多至数百,乃至数千人也是常态,还出现了不少几代人专门研读一部经书的世家大族。但好学的气氛又非常诡异,因为绝大多数人学习的内容是怪力乱神的谶纬儒学——不但官学如此,私学也一样。谶纬与知识分子个人的上升渠道捆绑在一起,若不教谶纬之学,私学就会收不到学生。结果是大量的读书人被方士化了,虽名为儒生,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全民向学,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光武帝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西汉灭亡和新莽短命而亡的反思来自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冬天,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百姓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的成果由班固等人编成《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中国秦制时代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此正式成为官方认定、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
根据《白虎通义》中的要求,合格大臣的基本标准是“善称君,过称己。臣有功,归于君”,功劳是皇帝的,过错是自己的。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父亲活着,就“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也就是说,儿子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还有“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父子不可以分开,即使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更甚的是《白虎通义》对女性的要求。女性必须拥有“顺德”,即柔顺的美德,在家扮演女儿,出嫁扮演妻子的角色,都要对家中的男性——父亲、丈夫、儿子唯命是从。(34)针对女性,《白虎通义》还特别制定了“妇人无爵”的规定:“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什么是“妇人无爵”?就是女性作为“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这相当于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35)
汉章帝召集学者在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针对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进而导致外戚坐大的现象。“君为臣纲”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夫为妻纲”“妇人无爵”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戚势力,“父为子纲”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皇帝希望参与制定三纲之人成为遵守三纲的楷模。受了三纲之害的贵戚、朝臣和知识分子则更乐见制定三纲之人带头违反三纲,陷入罗网。于是,在众人的审视下,负责将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结果编撰成书的班固和他的家人就成了三纲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在文章里说过“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36)这样的话。三纲出炉后,班固只好另写文章,违心批判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数怀王”,不该“沉江而死”,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37)班固的妹妹班昭,即使自身才华横溢,也不得不在婆家谨小慎微地过着低眉顺眼、低人一等的生活。她后来在《女诫》里说,自己嫁到曹家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在夫家四十多年,熬到公公、婆婆、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38)
(1) [日]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14页。
(3)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69页。
(4)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0页。
(5)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2页。
(6)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6页。
(7)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7页。
(8) 《论衡·佚文》: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
(9) 扬雄:《扬子法言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0) 班固:《汉书·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27页。
(11) 《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的诏书:“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0—4111页。
(12) 尚新丽:《西汉人口数量变化的社会因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3) 《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的诏书:“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2页。
(14) 班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06—3507页。
(15) 《汉书·食货志下》载鲁匡之言:“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2页。
(16) 邢艺、李建雄:《地名改易所见王莽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7) 王家范:《权力背景下“土地兼并”辨》,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6页。
(18) 李调元:《卖田说》,见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9)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1页。
(20)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5页。
(21)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3页。
(22) 桓宽:《盐铁论·园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页。
(23) 班固:《汉书·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2页。
(24)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66页。
(25) 范晔:《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16页。
(26)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70页。
(27)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87—4188页。
(28)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0页。
(29) 汉章帝时,古文经学家贾逵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见范晔:《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7页。
(30)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上》载桓谭之言:“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9—960页。
(31) 范晔:《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3页。
(32) 范晔:《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9页。
(33)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页。
(34) 徐广东:《三纲五常的形成和确立:从董仲舒到〈白虎通〉》,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27页。
(35) [日]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20页。
(36) 《奏记东平王苍》,见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1页。
(37) 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章句补注·楚辞集注》,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9页。
(38) 班昭:《女诫序》,见范晔:《后汉书·列女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