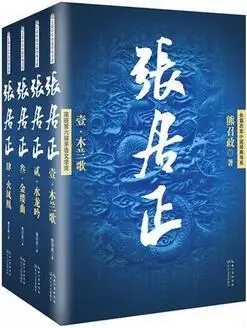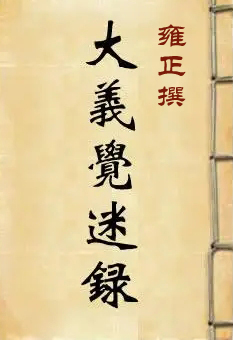《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的“袁绍传”是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袁绍的传记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敌袁绍塑造成了一个大蠢货。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田丰与沮授之智。按书中的说法,田丰与沮授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却被袁绍几乎全部拒绝,最终落了个败亡的下场。袁绍的拒绝共计有八次之多,具体如下:
1.沮授劝袁绍把汉献帝接到邺城来,袁绍“不从”。2.袁绍让长子袁谭执掌青州,沮授劝他别这样干,袁绍“不听”。3.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攻击曹操后方,袁绍“不许”。4.袁绍计划南征曹操,田丰、沮授强烈反对,袁绍“疑”而不听。5.沮授对袁绍说颜良“促狭”不可重用,袁绍“不听”。6.袁绍想要亲自率军过黄河,沮授劝阻,袁绍“弗从”。7.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沮授劝他与曹操打持久战,袁绍“不从”。8.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以保护粮草运输,袁绍“复不从”。(1)
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病故),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的事,可谓昏聩到了极致。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这八个“不听”“不从”的来源是《魏书》。王沈的《魏书》是曹魏官修史书,其中的《献帝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整理文书档案也是魏明帝时期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其编撰和整理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显然,这是胜利者有意想要证明一个结论:胜利来自胜利者的雄才大略。
即使这八条“不听”“不从”全部为真(2),它们也不是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的核心原因。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只不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拖家带口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3)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也无法驱动十余万人跟着自己背井离乡。但那个时代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其中,又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征讨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4)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许多粉饰。《武帝纪》选择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5)六个字。《二公孙陶四张传》则移花接木,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6)。只有《荀彧荀攸贾诩传》里留下了荀彧力劝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7)“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地表现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怖。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该法令见于《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和《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记载,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8)于禁说: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作“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记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氏的统治,将军贾信带人平定起义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投降的俘虏,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做,理由是:“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9)他想告诉曹丕的是: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综合《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与《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一道“常令”,曾被曹魏的将领们长期付诸实践。另据《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这道法令针对的并非只是敌军官兵,包括城内百姓在内的其他投降者也在“不赦”之列。《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10)
田银、苏伯在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被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后有余党,皆应伏法”一句显示了“围而后降者不赦”其实是一道屠城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百姓。曹操的制度性屠杀也许连以残暴著称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风。荆州百姓对曹操的屠杀法令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毕竟,天知道刺史、郡守会不会抵抗,天知道会不会有围城,天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不赦”的一分子。总之,稳妥起见,还是先跑了再说。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胜出。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1.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本文的“曹魏”字样是一种广义指称,既包括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时期的政权,也包括曹丕称帝后的魏王朝)对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一种统称,带有强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11)的口号,说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户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户民用脚投票的机会。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以寻求庇护。在豪强的庇护下,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
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比如单骑入荆州后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难度也高,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于是,依赖与豪强合作的军阀即使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很难有付诸实行的机会。
也就是说,曹操所谓的摧抑豪强,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地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摧抑豪强与租调制配套运作,“曹魏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赋(两种人头税),大约加重了四倍”(12);同时,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考虑到亩产有限,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较之汉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也高出了四倍有余(13)。若放任地方上豪强存在,百姓用脚投票,寻求庇护,如此强的榨取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2.兴办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本质上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的农奴,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官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14)用张大可先生的话说就是,“屯民所处地位是军事管制下的农奴,每一个屯田点就是一座劳役集中营”(15)。
自然,屯田的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16)的现象。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结果“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17)。曹魏的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而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被称作“士妻”,其家被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服从官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和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生产。(18)
为防止“士”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后来修改为籍设逃亡“士”的家属为官奴婢。但是即便如此,“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19),让曹操头疼的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可见对百姓压榨之严重。
《晋书·文苑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官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官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的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低贱的“士息”出身,成为可以做官的自由民。(20)
所以,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下文还会提到,与之鼎立的蜀汉也是相似的情形。
二、直百五铢钱的奥秘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的益州百姓大概会很怀念刘璋。因为他们发现,益州的新主人刘备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一套强大的新汲取机制,对益州的百姓进行搜刮。
新的汲取机制来自刘巴与诸葛亮等人的设计。据《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的裴松之注记载,刘巴在建安十九年曾就如何有效敛财向刘备献计:“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21)刘备苦于军用不足,刘巴建议实施两条政策,第一条是铸造“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种新货币,一枚新币的面值相当于一百枚过去蜀地的五铢钱;第二条是由官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官府的波动。刘备采纳刘巴的建议,蜀国的国库很快丰盈。
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出土甚多,绝大多数重8—9克,钱上的文字显示,它们或在成都铸造,或在犍为郡铸造。而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铸造的蜀地的五铢钱的重量一般在2—3.7克左右,以2.5克较为常见。(22)也就是说,刘备铸造的新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他一手铸钱,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空手套白狼,迅速从百姓手中汲取了30倍上下的财物。
保障蜀汉的高强度汲取政策顺利推行的是由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
建安十九年,在刘备的授意下,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造“蜀科”(23),亦即在汉律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一套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对它的大致面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裴注中有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4)意思是: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对百姓的盘剥。益州的百姓,上至豪族、士人,下至庶民、奴婢,都心怀怨言。
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起初未能理解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他跑去跟诸葛亮提意见:“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25)法正建议诸葛亮,学学汉高帝刘邦入关的做法,约法三章,不要搞大部头的律典。毕竟刘备是外来的政治势力,应该先用宽大政策来笼络本土的势力,获得他们的支持。
诸葛亮的回答深得商鞅、韩非之道,他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26)
诸葛亮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和汉高帝当年不同。秦实行暴政,征敛无度,豪族与庶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匹夫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汉高帝必须顺应当时的潮流。但是刘璋父子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豪族合作,与他们共享权力与利益,结果导致刘璋父子与豪族之间已不存在“君臣之道”。有刘璋父子的宠信在前,我们再拿官职、爵位、财富笼络他们,就显不出区别,没有意义,他们也不会感恩。我们需要的是严刑峻法,用刑罚来威吓他们。被律法狠狠地修理过,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用地位来诱惑他们,被阶层难以提升的忧虑折磨过,他们才会懂得获得的官爵有多么荣耀。简言之,益州的豪族与庶民之前的日子过得太舒服,我们要把政策变一变。
不过,蜀汉的高压统治也会因人而异。在诸葛亮心中,什么人可以无法无天,什么人不可以乱说乱动,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法正在蜀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有人跑到诸葛亮那里,求他主持公道,他告诉那个人从前主公落魄,多亏法正襄助才有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反问那个人,为何不能让法正随心所欲。(27)另一位因得庞统、法正推荐而得刘备重用的彭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他也想随心所欲,于是“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却被诸葛亮打了小报告,对刘备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导致其失宠。(28)
法正可以乱说乱动,是因为他来自雍州,是一位客居者。纵容他乱说乱动,不会妨害蜀汉政权针对益州的汲取政策。彭羕不可以乱说乱动,因为他是益州本地人,纵容他乱说乱动,等同于增强他在益州本地豪强中的声望,等于将他推上“益州本土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地位。二人身份的差别是理解法正与彭羕命运迥异的关键。对刘备和诸葛亮而言,一切都得为汲取让位。是否能够维持高强度的汲取机制,是蜀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
因史料匮乏,今人已无法还原蜀汉的民力汲取机制全貌。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汉昭烈帝(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百五铢钱”,还发现了诸葛亮辅佐刘禅时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由出土的蜀汉钱币可以推断,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也与滥铸货币的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迟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下跌至1克,极端的甚至不足1克。(29)
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的加重。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诸葛丞相家中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很容易让大多数人忘了直百五铢钱与太平百钱对自身带来的伤害,一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所写的那样:
(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30)
遗憾的是,诸葛亮死后,刘禅放飞自我,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苑(31)。“平等的贫穷”破产,那些满脸菜色的百姓(32)开始怀念诸葛丞相,“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33)。
三、皇权缘何“破浮华”?
何晏活跃于曹魏,他的祖父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何晏的父亲早逝后,母亲尹氏被曹操收为妾,他遂与曹丕等人一并在魏王宫中成长。成年后,何晏又“尚公主”,做了曹操的女婿。
何晏一生经历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个时代,死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在曹操时代,何晏是一个非常注重学识和修养的人。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34),且对兵书也有独到的见解,《何晏别传》里说曹操“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35)。《何晏别传》里还说,何晏在魏王宫与曹氏子弟相处时,“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36)在曹魏的第三位皇帝曹芳时代,也就是何晏人生的末年,他位列朝堂,也是一个有“大儒之风”(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的评语)的人。比如,鉴于皇宫内大搞装修,大玩舞乐、饮宴,骑马射箭,何晏曾劝谏曹芳“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37),淫乱的声音不要去听,奸佞的小人也不要去亲近。
这样重学识、讲修养、有大儒之风的人物在曹丕、曹叡父子主政的时代却穿起了女装,闹得洛阳城中无人不知。史载,何晏不但“好服妇人之服”,被人斥为“妖服”(38),还“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39)。
这样的反差与何晏的政治抱负不为皇权所容、长期遭受政治打压与思想管控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身份尴尬的边缘“官二代”,何晏在仕途上很不得志。曹丕不喜欢他,故“黄初时无所事任”(40),未能进入官场。曹叡也不喜欢他,故“颇为冗官”(41),只担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曹丕的不喜欢,可能与何晏被曹操收养却又不肯做曹操的养子有关。曹叡的不喜欢,则缘于何晏的政治思想与皇权的需求背道而驰。
何晏、王弼与夏侯玄一干人等是开魏晋玄学先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按顾炎武的说法,是“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42)。简单说来就是:曹魏以法家权术为治国手段,辅以儒学礼教作为粉饰;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则尊孔子为圣人,且援老庄之说入儒,试图用自然秩序来规范政治秩序(本质上仍不脱离董仲舒用天命来约束“皇权”的思路),主张君主抛弃严刑峻法、退而无为,将治理天下的责任交托给官僚集团。这些人不具备《白虎通义》定义的那种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如见皇帝有难就像碰上路人遭厄而无动于衷。
这样的主张自然不会为曹魏皇权所容。魏明帝即位次年,就下诏警告“浮华交游”之风,针对的便是何晏、夏侯玄这类人物。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又有司徒董昭上书魏明帝,请求皇帝对浮华交游之徒采取更具实质性的惩治措施。董昭在奏章中攻击何晏等人,说他们不用心钻研学问,专爱交游,聚在一起褒扬彼此、批评他人(主要是批评朝政)。董昭说:“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43)随后,魏明帝下诏:“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44)
知识分子旨趣相投,彼此来往,交流议论时事,本无任何过错,给他们扣上一顶“浮华交游”的帽子不过是曹魏打压舆论的惯用手段。建安年间,孔融曾对曹操推行的政策多有批评,曹操即写信恐吓孔融,说自己“破浮华交会之徒”的办法,也就是镇压异己的手段,是相当多的。这封信由曹操的幕僚路粹起草,原文是:“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45)
据《三国志》中的蛛丝马迹,魏明帝“破浮华交游”后,诸多与何晏旨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如邓飏、李胜、诸葛诞、夏侯玄等,“凡十五人……皆免官废锢”(46)。“废锢”即免除官职、监视居住。魏明帝本有意如曹操杀孔融一般制造一场文字狱,且已将李胜等人逮捕,后因牵涉之人太多,其中还有夏侯玄、何晏这样的“官二代”名士,为免造成政局震荡,才改以“废锢”作为惩罚。
或许是因为“尚公主”之类的原因,何晏未被列入“废锢”名单,但现实的高压也让他不得不屈服。“破浮华交游”的同一年,魏明帝巡幸许昌,大兴土木修筑景福殿,命何晏作《景福殿赋》。何晏在赋的末尾写了这样一段话:“圣上……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47)“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指的正是“破浮华交游”的思想禁锢与言论打压。为求自保,何晏不得不违心赞颂魏明帝做得好、做得对,其英明神武直追传说中的周公。
大约在同期,何晏爱穿女人衣服、喜欢涂脂抹粉的特殊癖好传入了魏明帝耳中。为验证真假,魏明帝做了一次实验:“何平叔(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48)何晏仅存的两首《言志》诗,一首说自己“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一首说自己“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49),其惴惴不安、朝不保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明显。涂脂抹粉,穿上“妖服”,成了何晏自污求存的无奈手段。
从何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名士抛弃了阳刚之美,转走阴柔路线。皇权既然以集权为阳刚,追求阴柔的审美也就自然成了臣僚寻求政治安全的常规路径。在西晋,有潘岳“妙有姿容”(50),与夏侯湛合称“连璧”(51);有裴楷号为“玉人”(52),卫玠号为“璧人”(53),王衍“容貌整丽”(54),手润如玉。东晋则有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55);王恭身材婀娜,唐朝时人称赞他“春风濯濯柳容仪”(56)。进入南北朝,皇权愈加残暴,朝堂之上的阴柔之风更盛。何炯“白皙,美容貌”(57);韩子高“容貌美丽,状似妇人”(58);谢晦“眉目分明,鬓发如墨”,被皇帝赞为“玉人”(59)。这些阴柔的美男子均闻名于世。《颜氏家训》里也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60)
个体审美异于常人是一件应该得到充分理解的事情,集体审美异于常人则往往意味着社会出了毛病,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堂上的阴柔之风正是如此。西晋建国后,很快就走向了上有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下有“八王之乱”蹂躏、屠杀天下百姓的丛林社会。南北朝的情况也大体相仿。理想无处安放,有志者遭逆向淘汰,留存在权力游戏之中的人为了让皇权(或皇权的代理人)放心,也只好“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阴柔之态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1) 陈寿:《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201页。
(2) 这八条“不听”“不从”多数并非事实,详见拙文《胜利者撰修官史的丑陋嘴脸》,“史料搬运工”公众号2019年7月6日。
(3) 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7页。
(4) 范晔:《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5)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6) 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页。
(7) 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310页。
(8) 陈寿:《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3页。
(9) 陈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9页。
(10) 陈寿:《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
(11)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12) 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13) 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增刊。
(14) 王仲荦:《曹魏屯田制度的几个问题》,见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15页。高敏:《再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15) 张大可:《三国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2页。
(16) 陈寿:《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4页。
(17) 陈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0页。
(18) 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33页。
(19) 陈寿:《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4页。
(20) 房玄龄等:《晋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2379页。
(21) 陈寿:《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82页。
(22) 朱活:《古钱小辞典》,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2页。
(23) 陈寿:《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1页。
(24)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25)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26)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27) 陈寿:《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0页。
(28) 陈寿:《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95页。
(29) 曾维华:《蜀汉是“太平百钱”的铸主》,见《中国古史与文物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86页。安剑华:《蜀汉钱币探微:以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为例》,见《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0)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4页。
(31) 《三国志·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载谯周劝谏刘禅,有“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之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28页。
(32) 《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有吴国使臣薛翊自蜀国归来后,给吴主孙休的汇报:“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5页。
(33)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8页。
(34)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35) 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何晏别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79页。
(36) 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何晏别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7页。
(37)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2—123页。
(38) 房玄龄:《晋书·志第十七·五行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2页。
(39)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40)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41)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42)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12页。
(43) 陈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2页。
(44) 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页。
(45) 范晔:《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73页。
(46) 陈寿:《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裴松之注引《世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69页。
(47) 萧统编:《文选·何平叔景福殿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7页。
(48)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页。
(49) 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16—217页。
(50)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6页。
(51)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8页。
(52)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0页。
(53)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4页。
(54)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7页。
(55)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6页。
(56)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9页。
(57) 姚思廉:《梁书·孝行列传·何炯》,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55页。
(58) 姚思廉:《陈书·韩子高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69页。
(59) 李延寿:《南史·谢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页。
(60)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勉学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