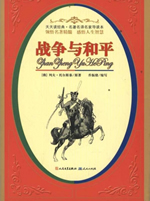令我极为烦恼的是波洛不在,而给我开门的那个比利时老伯告诉我,他认为他去伦敦了。
我惊呆了。波洛到伦敦去干什么啊!他是突然决定的,还是几小时前离开我时就下定决心了呢?
我有些烦恼地折回斯泰尔斯。波洛离开了,我不太确定该如何行动。他是否已经预见到了这次逮捕?他很可能不是因为这个?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在这期间我要做些什么呢?我应不应该在斯泰尔斯公开逮捕的消息?虽然我不肯对自己承认,但关于玛丽·卡文迪什的想法一直压在我心头。对她会不会是个可怕的打击?现在,我完全否定了对她的怀疑。她不会被牵连进去的——不然我肯定会听到一些风声。
当然,不可能永远瞒着她包斯坦医生被捕的事,这消息会在第二天出现在每一份报纸上。然而我还是担心自己会脱口说出来。要是能看到波洛,我就可以问问他的意见了。是什么事让他这么莫名其妙地突然赶往伦敦呢?
不知不觉中,我更加赞赏波洛的睿智了。要不是波洛给我灌输了这种想法,我做梦也不会疑心这位医生的。没错,这个小个子男人显然很聪明。
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和约翰推心置腹,让他见机行事,来决定是否公开这件事。
我向他透漏这个消息时,他吹了一声惊人的口哨。
“天哪!那你是对的了。可我现在都无法相信。”
“你习惯了就不那么吃惊了,而且这样一来,每件事都说得通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明天所有人就都知道了。”
约翰想了想。
“没关系,”最后他说道,“现在我们什么也不用说。没必要。像你说的,人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但让我极为吃惊的是,第二天一早下楼,我急切地打开报纸时,却发现关于这次逮捕只字未提!只有一个全都是废话的专栏“斯泰尔斯毒杀案件”,便再没什么了,真是让人费解,不过我猜,由于某个原因,杰普不想让它见报。这让我有些担心,因为很有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逮捕行动。
早饭后,我打算去村子里看看波洛是否已经回来了;然而在我出发之前,一张熟悉的面孔挡住了其中一个窗口,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早啊,我的朋友!”
“波洛!”我如释重负般地喊了起来,抓住他的双手拉他进屋,“我看到任何人都没有这么高兴过。听我说,除了约翰,我对谁都没有说过什么。对吗?”
“我的朋友,”波洛回答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当然是包斯坦医生被逮捕的事。”我不耐烦地说。
“我这么说,包斯坦医生被捕了?”
“你不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顿了顿,他又说,“不过,这并没有让我吃惊,毕竟我们离海岸只有四英里远。”
“海岸?”我疑惑地问,“跟这有什么关系?”
波洛耸耸肩。
“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明白啊。很可能是我太愚笨了,可我看不出接近海岸跟英格尔索普太太的谋杀有何关系。”
“当然没有关系,”波洛笑着回答说,“可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包斯坦医生的被捕啊。”
“嗯,他因为谋杀英格尔索普太太而被捕——”
“什么?”波洛大喊,显然非常吃惊,“包斯坦医生因为谋杀英格尔索普太太而被捕?”
“是啊。”
“不可能!这肯定是一场精彩的闹剧!是谁告诉你的,我的朋友?”
“呃,没有人明确告诉过我,”我承认道,“但他就是被捕了。”
“哦,是的,很有可能。但那是因为他从事间谍活动,我的朋友。”
“间谍活动?”我透不过气来了。
“一点儿没错。”
“不是因为毒死英格尔索普太太?”
“除非我们的朋友杰普神经错乱了。”波洛泰然自若地回答道。
“可是——可是我以为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波洛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包含着一种吃惊的遗憾,还有认为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神情。
“你是说,”我说,慢慢地调整自己适应这种新想法,“那个包斯坦医生是个间谍?”
波洛点点头。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我想都没想过。”
“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著名的伦敦医生把自己埋没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整晚整晚衣着整齐地漫步?”
“没有,”我承认说,“我从未想过这种事。”
“当然,他是个德国人,”波洛若有所思地说,“虽然他在这个国家工作了很久,人人都以为他是个英国人。十五年前,他加入英国国籍。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然,是犹太人。”
“无赖!”我愤怒地喊着。
“当然不是。相反,他是个爱国者,想想他遭受的损失吧。我很佩服这种人。”
但是我可不会用波洛那套哲学理论看待此事。
“这个人,就是一直和卡文迪什太太在村子里闲逛的那个人!”我愤然叫道。
“没错。我想是因为他发觉她很有用,”波洛说,“只要这些流言飞语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那人们就不会注意这位医生的其他诡异行为了。”
“那你觉得他从未在乎过她吗?”我着急地问——也许,在此情形下,稍微过于着急了一些。
“那个,当然,我说不好,不过——我要不要告诉你我的个人意见,黑斯廷斯?”
“是的。”
“好吧,是这样的:卡文迪什太太不喜欢他,她对包斯坦医生没有一丝喜欢。”
“你真是这么认为的?”我掩饰不住开心地问。
“我非常确定这一点,而且我会告诉你原因。”
“是什么?”
“因为她心有所属,我的朋友。”
“哦!”他是什么意思?一阵沁人心脾的温暖不由自由地席卷了我的全身,我不是那种一说到女人就自负的男人,但是我想到某些迹象,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太容易了,可似乎的确表明——
我那些愉快的念头被霍华德小姐的突然闯入打断了。她匆匆环视了一下四周,确保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然后飞快地拿出一张旧的牛皮纸,递给波洛,还嘟囔了这么一句神秘的话:
“在衣橱顶上。”接着便匆匆离去了。
波洛急切地打开这张纸,满意地感慨了一声。他把它铺在桌上。
“过来,黑斯廷斯,现在,告诉我,首字母是什么:J还是L?”
这是一张中等大小的纸,布满灰尘,看样子放置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上面的标签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上面盖有公司的印戳,百盛,著名的戏剧服装公司,寄给“埃塞克斯,斯泰尔斯郡,斯泰尔斯庄园,(首字母仍有争议)卡文迪什先生”。
“可能是T或L,”我研究了一会儿之后说,“肯定不是J。”
“很好。”波洛回答道,又把纸折了起来,“我和你想的一样,是L!”
“这纸从哪儿来的?”我好奇地问,“重要吗?”
“一般吧。这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推测到这张纸存在,便让霍德华小姐去找,结果,你看到了,她找到了。”
“她说‘在衣橱顶上’是什么意思?”
“她是说,”波洛飞快地回答,“她在一个衣橱顶上找到了它。”
“放在这么奇怪的地方。”我深思着。
“一点儿也不奇怪。衣橱顶上是放牛皮纸和纸箱最合适的地方了。我自己就把它们放在那儿。排列整齐,不刺眼。”
“波洛,”我诚恳地问,“你对这次犯罪有自己的想法了吗?”
“是的,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我知道是如何实施犯罪的了。”
“啊!”
“遗憾的是,我只有猜测而没有证据,除非——”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打着转儿地带到了楼下大厅里,用法语兴奋地喊道:“多卡丝小姐,多卡丝小姐,方便的话请过来一下!”
多卡丝被这喊声弄得十分慌张,急急忙忙从食品储藏室里跑了过来。
“我的好多卡丝,我有个想法———个小想法——如果能证明是正确的,那运气真是太好了!告诉我,星期一,不是星期二,多卡丝,就是星期一,悲剧发生的前一天,英格尔索普太太的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多卡丝的样子很是吃惊。
“没错,先生,既然你提到了,是的;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说的。一定是老鼠一类的什么东西把电线给啃了,星期二早上来人把它修好了。”
波洛惊喜地拖长声音大叫一声,把我带回起居室。
“你瞧,一个人不应该只找表面的证据——不,推理就足够了。可人是软弱的,发现自己在正确的轨道上就觉得安慰了。啊,我的朋友,我现在就像一个精神振作的巨人。我跑!我飞跃!”
而且,他居然真的又跑又跳的,疯狂地蹦到落地窗外面的草坪上去了。
“你那位非同凡响的小个子朋友在干什么?”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扭头看见玛丽·卡文迪什站在我旁边。她面带微笑,于是我也笑了。“发生什么事了?”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他问了多卡丝一个关于铃铛的问题,得到她的回答之后,他就如你所见这般兴奋了。”
玛丽大笑起来。
“太滑稽了!他走出大门了,今天不回来了吗?”
“我不知道。我已经不去猜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他很疯狂吗,黑斯廷斯先生?”
“我真是不清楚。有时候,我敢肯定他是无比疯狂的;然后,在他最疯狂的时候,我发现这疯狂之中还是有条理可循的。”
“我明白了。”
尽管玛丽笑了,可是今天早上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看起来很严肃,几乎有些伤心。
我想这可能是跟她谈一谈辛西亚的好机会。我以为开始我还是比较委婉巧妙的,可没说几句就被她命令式地打断了。
“我毫不怀疑你是个优秀的律师,黑斯廷斯先生,可在这件事上,你的才能真的是派不上用场了。我不会对辛西亚无情无义的。”
我无力地结巴着说希望她不要认为——可是她又一次打断了,而且她的话非常出人意料,我马上就把辛西亚和她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黑斯廷斯先生,”她说,“你觉得我和我丈夫在一起幸福吗?”
我大为吃惊,只好嘟囔着说了一些我没有权利考虑这类事情之类的话。
“嗯,”她静静地说,“不管你有没有权利,我都会告诉你我们不幸福。”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看到她话没说完。
她在房间里缓缓地来回踱着步子,头微微侧着,纤细而柔软的身体也随之轻轻摇曳着。忽然,她停下了,抬头看着我。
“你对我一无所知,是吗?”她问,“我是哪里人,嫁给约翰之前我是谁——其实你都不知道对吧?好吧,我告诉你。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忏悔神父的。你很善良,我觉得——没错,我相信你很善良。”
不知为何,我并没有感到那种应该有的高兴。我想到辛西亚也是用差不多的方式吐露秘密的。而且忏悔神父的年纪都很大,完全不是年轻男子扮演的角色。
“我父亲是英国人,”卡文迪什太太说,“但我母亲是个俄国人。”
“啊,”我说,“现在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总是给人一种异国的感觉——与众不同的。”
“我相信我母亲非常漂亮。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她。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认为她的死亡是个悲剧——她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不管怎么说,我父亲的心碎了。没过多久,他去了领事馆工作,走到哪儿都带着我。二十三岁时,我已经几乎走遍了全世界。这是一种非常辉煌的生活——我爱这种生活!”
她脸上浮现出笑容,头向后仰着,仿佛沉浸在对旧日欢乐时光的回忆中。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什么钱也没留下,我不得不去约克郡(注:约克郡原为英格兰东北部一郡。)和几个老姑妈住在一起。”她颤抖着,“如果我说,对于我这样一个有如此成长经历的女孩而言,那种生活是致命的,你会明白的。狭小的、致命的单调生活,几乎快把我给逼疯了。”她顿了顿,换了一种声调接着说道,“之后,我遇见了约翰·卡文迪什。”
“是吗?”
“你可以想象,按照我姑妈们的观点,对我来说他是个很好的结婚对象。但是,说实话,不是这样的。这只是我逃离难以忍受的单调生活的一种途径。”
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
“不要误会我。我对他很忠诚。我对他说出了实情,说我很喜欢他,也希望以后会更喜欢他,但我还说,我对他没有那种世上叫做‘深爱’的感觉。他说他很满意,所以——我们结婚了。”
她很久没再说话,微微蹙起了眉头,好像在认真地回顾过去的那些日子。
“我想——我肯定——开始他是喜欢我的。可我觉得我们不那么般配,几乎没几天我们就疏远了。他——对我的自尊而言这并非一件乐事,但却是事实——很快就厌倦了我。”我只小声说了几句抗议的话,因为她很快又继续说道,“哦,是的,他就是!现在不重要了——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岔路口。”
“什么意思?”
她平静地说:
“我是说我不打算留在斯泰尔斯了。”
“你和约翰不准备住在这里了?”
“约翰可能住在这里,但我不会了。”
“你要离开他?”
“是的。”
“但是为什么呀?”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道:
“也许——因为我想要——自由。”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忽然开阔起来,一大片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的土地——对玛丽·卡文迪什而言,自由的实现可能指的就是这样的景致。一瞬间,我好像看到她变成了骄傲的野生生物,或者是未经文明驯服的山上害羞的鸟儿。她忽然啜泣起来: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可恨的地方是如何囚禁我的!”
“我理解,”我说,“但——别鲁莽行事。”
“哦,鲁莽!”她的声音嘲笑了我的谨慎。
这时我忽然说了一件我本不应该说的事。
“你知道包斯坦医生被捕了吗?”
瞬间,一股寒气像面具那样罩在了她的脸上,遮住了所有的表情。
“今天早上约翰好心地告诉我了。”
“呃,你怎么想的?”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想什么?”
“被捕?”
“我能怎么想?很明显他是个德国间谍,就像花匠们告诉约翰的。”
她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她是关心还是不关心呢?
她挪动了几步,摆弄着一只花瓶。
“它们全都死了。我得换些新的。你介意挪一下——谢谢你,黑斯廷斯先生。”她静静地从我身旁走向落地窗,冷冷地点点头,出去了。
不,她肯定不会喜欢包斯坦。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表现得如此冷淡而漠不关心。
第二天早上波洛没有出现,而且也没见到苏格兰场的人。
但是,午饭时间有了一个新的证据——或者说是没用的证据。我们一直尽力查找英格尔索普太太临死前那个傍晚写的第四封信,却徒劳无功。由于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因此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件事,希望有一天它自己能出现,而这恰恰以通信的形式实现了。在第二批邮件中,有一家法国音乐出版社公司的信,说收到了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支票,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找到某套俄罗斯民歌系列。因此,通过英格尔索普太太在那个要命的夜晚所写信件来解答谜题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
在喝茶之前,我走去告诉波洛这个新的失望,却吃惊地发现,他又出门了。
“又去伦敦了?”
“哦,不,先生,他只不过是坐火车去了塔明斯特。‘去参观一位年轻女士的药房。’他说。”
“笨蛋!”我脱口而出,“我跟他说过星期三她不在!好吧,请跟他说明天一早来找我们,好吗?”
“当然可以,先生。”
可是第二天,波洛连个人影也没有。我生起气来。他真的用这种最为傲慢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午饭之后,劳伦斯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要去看他。
“不,我不会去的。要是他想见我们,可以来这儿。”
“哦!”劳伦斯的态度模棱两可,举手投足间有种异常的紧张和激动,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怎么了?”我问,“要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我可以过去。”
“也没什么,只是——好吧,如果你要去,请你告诉他——”他压低声音小声说道,“我想我找到了另外的那只咖啡杯!”
我都快把波洛那个神秘的口信给忘了,但是现在我的好奇心又被唤醒了。
劳伦斯不会多说什么的,所以我决定放下架子再去里斯特维斯小屋一趟,找波洛。
这次,我受到了微笑的迎接。波洛先生在里面。我还要装吗?当然要装。
波洛正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托着脑袋。我的出现让他跳了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我关切地问,“你没生病吧?”
“不,不,不是生病。我在决定一件重大的事情。”
“是抓罪犯吗?”我戏谑地问道。
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波洛居然点了点头。
“‘说还是不说,’正如你们那位伟大的莎士比亚所言,‘这是个问题。’”
我没有费事地去纠正他的引用错误。 (注:“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是莎士比亚出戏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王子说的话。这里波洛说成了“To speak or not to speak”。)
“你不是开玩笑吧,波洛?”
“我绝对认真。最严肃的事情尚未明朗。”
“什么事啊?”
“一个女人的幸福,我的朋友。”他郑重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一时刻到来了,”波洛沉思着说,“可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我下的最大的赌注,除我,赫尔克里·波洛,没有人敢去尝试!”他说着骄傲地拍拍胸膛。
我毕恭毕敬地等了一会儿,为的是不损害他的形象,之后,我转告给他了劳伦斯的口信。
“啊哈!”他大叫,“这么说他发现了另外的那只咖啡杯!非常好。他要比他表现出来的更加聪明些,你那位绷着脸的劳伦斯先生!”
虽然我并不认为劳伦斯有多聪明,但还是克制着不去反驳波洛,而是温和地责备他忘记了我所说的辛西亚休息的话。
“是真的,我漏掉了你的话。但是,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士人很好,她不忍心看到我失望,所以就和善地带我参观了所有的东西。”
“哦,好吧,算了,那你得另外找一天跟辛西亚喝茶了。”
我向他说了信的事情。
“很遗憾,”他说,“我一直对那封信抱有希望。但是,没有希望了。这件事必须从内部寻找解决方法了。”他拍拍脑门,“这些小小的灰色细胞,‘依靠它们’,就像你在这里说的那样。”接着,他忽然问道,“你会鉴别指纹吗,我的朋友?”
“不会,”我很吃惊地说道,“我知道没有两枚指纹是相同的,不过我的科学知识也就这么多了。”
“没错。”
他打开一个小抽屉,拿出几张照片铺在桌上。
“我给它们编了号:一、二、三。你能把它们给我描述一下吗?”
我专心地研究起这些样本来。
“我看到全部都大幅度地放大了。我得说,一号是个男人的指纹,大拇指和食指;二号是位女士的,都很小,每个方面都不同;三号——”我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有很多指纹混杂在一起,但是很明显,这儿,是一号的!”
“和其他重叠的?”
“是的。”
“你确定认对了?”
“哦,是的,它们是一样的。”
波洛点点头,从我手上轻轻地拿过照片,又锁了回去。
“我想,”我说,“你照例不作解释吧?”
“相反。一号是劳伦斯先生的指纹。二号是辛西亚小姐的,它们不重要,我只是拿它们比照一下。三号有点复杂。”
“怎么复杂?”
“正如你所看到的,照片都高倍数放大了。可能你已经留意到照片上有一片模糊的延伸,我就不多跟你解释那些特殊装备了,指纹粉一类的。对警方而言这是常用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你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任何人的指纹照片。那么,我的朋友,你已经看过这些指纹标记了,接下来只要告诉你留下这种指纹的特定物体就可以了。”
“接着说吧——我很激动。”
“好的。三号代表了塔明斯特红十字医院药房毒药橱柜顶部的一个小瓶子高倍数放大之后的表面——这听着像个重复的故事。(注:原文是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杰克造的房子,故事的内容是:杰克建的房子里有麦芽,麦芽给老鼠吃掉了,老鼠给猫咬死了,猫又给狗无限烦恼,这就是那条狗了。在这里用来比喻重复。)”
“天哪!”我大声说,“可上面怎么会有劳伦斯·卡文迪什的指纹?那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可没靠近过那柜子!”
“哦,不,他靠近了!”
“不可能!从头到尾我们一直在一起。”
波洛摇摇头。
“不,我的朋友,有那么一会儿你们没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刻你们不可能在一起,不然就不会喊劳伦斯先生上阳台找你们去了。”
“我把这个给忘了,”我承认道,“可只有那么一小会儿。”
“足够了。”
“什么足够了?”
波洛的笑容变得神秘起来。
“对一位曾经学习过医药学的先生来说,满足其天生的兴趣和好奇心,那段时间足够充裕了。”
我们对视了一眼。波洛的眼神愉快、蒙眬。他站起身,哼着小调,而我则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他。
“波洛,”我说,“这个特别的小瓶子里装了什么?”
波洛望向窗外。
“盐酸士的宁,”他回过头说道,接着又哼起了小调。
“天哪!”我十分平静地说,并没有吃惊,因为我已经预料到这个答案了。
“他们很少使用纯盐酸士的宁——只是偶尔才添加到药物里。法定的方法是使用液体盐酸士的宁,所以指纹从那会儿到现在仍没有被破坏。”
“你怎么拍到这张照片的?”
“我把帽子从阳台丢了下去,”波洛简单地解释道,“在那段时间,来访者不能下去,所以由于我再三表示歉意,辛西亚小姐的同事只好下去帮我捡了回来。”
“这样你就知道你能发现什么了?”
“不,不是这样。我听你说过,劳伦斯先生有可能靠近过毒药橱柜。这一可能性需要被证实或者排除。”
“波洛,”我说,“你的若无其事骗不了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我不知道,”波洛说,“但是有件事确实冲击了我。不用说,对你也是。”
“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案子中,有太多的士的宁了。这是我们第三次意外地碰到它了。英格尔索普太太的补药中有士的宁;斯泰尔斯的梅斯柜台上出售过士的宁;现在,我们又发现这个家里的人有士的宁。太混乱了,可你知道,我不喜欢混乱。”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比利时人打开门,把脑袋探了进来。
“楼下有位女士找黑斯廷斯先生。”
“一位女士?”
我跳了起来。波洛跟在我后面走下狭窄的楼梯。玛丽·卡文迪什正站在门口。
“我去村里看望了一位老妇人,”她解释说,“劳伦斯告诉我你和波洛先生在一起,所以我想过来叫上你。”
“啊,太太,”波洛说,“我以为你是专程赏脸看望我的呢!”
“如果你邀请,我一定另找一天过来。”她微笑着答应了他。
“太好了。如果你还需要一个忏悔神父,太太——”她有一点点吃惊,“记住,波洛神父随时为您服务。”
她盯着他看了片刻,似乎想从他的话里解读出更深层的含义。之后,她忽然转身离开了。
“波洛先生,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非常乐意,太太。”
在回斯泰尔斯的路上,玛丽一直兴奋地说着。我想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她害怕波洛的眼睛。
忽然变天了,凛冽寒风的撒泼架势都快赶上秋风了。玛丽有些发抖,把她那件黑色外套裹得更紧了。冷风刮过树林发出悲哀的噪音,像个巨人在叹息。
走到斯泰尔斯的大门口,我们马上就意识到出事了。
多卡丝跑出来接我们。她哭着绞着双手。我注意到,其他仆人在后面神情专注地聚在一起。
“哦,太太!哦,太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怎么了,多卡丝?”我焦急地问,“快告诉我们!”
“那些缺德的侦探,他们抓走他了——他们逮捕了卡文迪什先生!”
“逮捕了劳伦斯?”我倒抽一口气。
我看到多卡丝眼中透出惊讶的神情。
“不,先生,不是劳伦斯先生——是约翰先生。”
我背后传来一声惊呼,玛丽·卡文迪什重重地倒向我。我转身接住她,这时,我看到波洛眼中有种平静的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