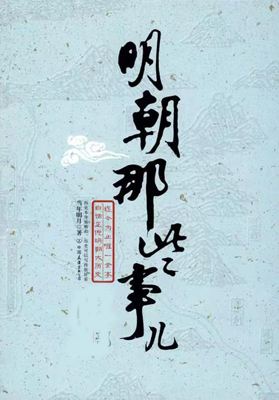1
从今年春天以来就时常听说这一带出现色情狂。
我寄宿的西内家房东太太也不时告诫长女美树:“晚上不能单独走路。”美树今年春天才高中毕业,找到一份工作,做的很起劲。公司加班,回来晚的时候,他就在前面商店街转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回来。于是,她的父母,或是念高中的弟弟直彦,就到那里去接她。
“只是四十公尺的距离而已嘛!”开头的时候,我对西内太太的神经质感到好笑。
“不过,上回之丁目牙医师家的小姐受到惊吓时,离自己家里才五公尺左右而已。宁可小心一点,免得发生万一就后悔莫及了。”
不错,西内太太的话言之有理。
换言之——不,还是先自我介绍我自己好了0我叫做真锅敦夫,二十七岁,职业时东都新报社会部记者。家乡在富山县,但从大学以来就一直在东京。学生时代是住在学生宿舍,毕业后立刻迁出学生宿舍,寄宿于母亲的远亲,位于世田谷区的西内家,一转眼就过了四年半。
西内家主任西内昌彦先生世二流制药会社的总务课长,有两个孩子。女儿美树,我刚来时时初中生,现在已经是十九岁,亭亭玉立,纯洁可爱的少女。可能因为高中时代是排球选手的缘故,有一副均匀健美的身材,而且聪明伶俐,目前在一家印刷公司担任办事员。弟弟直彦是都立百濑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是个敦厚开朗,讨人喜欢的少年。但同时有些软弱,不可靠的感觉。他每天步行二十分钟到学校去,有脚踏车却不骑,据说是为了要和附近的一位同学一起上学的关系。西内太太皮肤白皙,肥肥胖胖,好脾气,典型的中等家庭主妇。
关于西内太太所说的牙医女儿被强暴的案子,是发生于这年的三月。牙医的女儿二十二岁,她是新剧团的研究生,那天因为舞台排练,到深夜将近十二点才回家。快到住家附近时,一个男人突然从背后冲过来。她想叫喊,但是脖子被勒住,喊不出来。她因为恐惧而昏迷时,被拖到旁边的黑暗小巷被强暴,等她恢复意识时,已经不见暴徒踪影。这件案子,我得到的消息,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详细。据说被害人告诉调查官:“男人的大手从背后勒住我的脖子,我拼命挣扎,那男人以很重的腔调说:‘再抵抗就勒死你。’”其后附近又连续发生了几件的类似的强暴妇女的案件,认为可能是同一个歹徒。据说,是个年轻人,个子略高,北关东腔,就是次城或励木那一带口音的人。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案子始终未破。
夏天将结束的时候,一位二十岁的职业妇女在下班归途中同样受到袭击,这一次终于发展成杀人案。被杀的不是这位女性,而是听到叫声赶往营救的一个青年,被歹徒刺杀身亡。碰巧那时侯人们正在议论:“一般民众协助警察与歹徒格斗而受伤或死亡的赔偿微保还是袖手旁观比较聪明。”因此警方对本案特别重视,一方面紧急修正法规,给予受害人一百五十万的抚恤金,另方面全力追查本案。向来清闲的这郊外住宅区派出所P署,少有的设置了专案总部,唯一的证物——砂仁凶器菜刀——放大照片,除了派出所前面以外,车站前面,路旁电线杆等到处张贴,让民众辨认。根绝曾经受到过惊吓,获救的女性证言,歹徒确实是操北关东腔,高个子的男人。从菜刀上面采到几个不明显的指纹,但查明不在前科者的名单内。我任职的东都新报,以及其他各报,莫不综合以往各类似的案子,加以分析,研究歹徒的种种,试图协助破案,但都徒然白费。我再也不敢笑西内太太是神经质了。
下面的案子是发生再十一月二十二日,碰巧这天我休假在家。平常东奔西跑,忙的团团转,所以偶尔休假,反而闲的无聊。这天由于有轻微的感冒,加上有两本尚未阅读的侦探小说,所以难得的在家里待了一天。
到了晚上九点半左右,我忽然想起打个电话到警视厅的俱乐部。因为要打听逃亡中的五百万元抢劫犯的最新消息。我的同事水野记者住在俱乐部,但拨了几次都打不出去,再拨其他号码也是一样。
“伯母,电话坏了。”我向西内太太报告。
“啊,贞德?刚才打给横滨的亲戚时还好好的.....外面打的进来么?”
“恐怕打不进来。”
“糟糕......”西内太太露出焦急的表情。“也许美树已经回来了,必须去接她。”
“美树还没回来么?”
“傍晚打电话回来说,今天要加班,整理帐簿,但十点以前一定回来。所以我叫她到了转弯的电话亭九打电话回来。”
“那我去接她好了,顺便看看是这一带全都坏了,还是只有我们的故障。”
“好,好,那就拜托你了。”
我披上外套出来,没有风,是个暖和的晚秋,但是没有星星和月亮。也许会下雨。
从水银灯明亮的街角转弯,接下的路近乎漆黑。我按亮手电,照着脚前的路。我并不需要手电,但是我认为手电能让美树安心。大约走了五六公尺吧,黑暗中忽然爆发出慌乱的脚步声。,接着,听见年轻女性的尖叫声。
“是她,美树!”
“喂,混蛋,你要对这位小姐做什么!”
男人的叫声,奔跑的脚步声,以及扭在一起的模糊人影。接着的瞬间,又听到一声男人的惨叫声。当地面发出笨重物跌落的声音时,我离他们已经很近了。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突然飞也似的逃走了。
“等一下!”
我要追过去,美树不知从哪里跑出来抓住我。
“敦夫先生!”
“你还好么?美树。”
美树全身发抖,一面点头。我放弃追那个逃走的人,移动手电照着脚下,看到一个男人仰躺在地上。
“喂!振作一点。”
我把地上的男人扶起来,但是已经太迟了。他的左胸上插了一把刀,插的相当深的样子,还闻到一股酒臭味。这男人很面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家的,但可以确定是附近的居民。我掏出口袋里的手帕覆在死者脸上。因为我不希望让美树看见那对瞪着空中的白眼。
把美树送回家,我再度经过尸体旁边,走到转角的电话亭。果然打不通。事后才知道这一带的电缆坏了,从傍晚以后就不能通话。我到附近敲药房的门,借用电话,先打给警视俱乐部的水野,接着打一一零电话。不知道怎么,这家药房的电话竟是好的。
回家的路上,看到尸体旁边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不知谁通报的,巡逻的警官也来了。我径自回家。虽然只是扫了一眼,但该观察的都已经看过了。西内太太正在安抚脸色苍白的美树。
“美树,你还记得逃走的人是什么模样吗?”我问。
“敦夫先生,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问这些问题。美树已经吓坏了,希望你不要打搅她。”西内太太歇斯底里的叫道。
“不过,等一下还是要向警方说明不可。即使想的起来,最好是现在想想,整理一下。”
“我很好。”美树说。声音虽然沙哑,却相当冷静,似乎没有母亲所担心的那样紧张。她开始断断续续的说明。
“我从公共电话打电话回家,可是打了几次都打不通,我只好自己走。走到那里的时候。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而且好象是掂起脚尖轻轻走。我心里害怕,所以就拔腿跑起来,我一跑马上就听到低哑的声音说,‘小姐,等一下,不要急。’我吓的惊叫起来,对方就突然冲过来......”美树打了个冷颤。
“然后呢?”
“他要勒我的脖子。好大的手呢,这时候一个路过的人冲过来,一面嚷着:‘喂,混蛋!你要对这位小姐做什么!’我立刻听出来是裱糊店的叔叔。他要把那个男人拉开,一面打那个男人,一面不停的骂:‘混蛋,混蛋!’但接着,叔叔就尖叫一声,倒在地上。我很害怕,好象已经死掉一样,要不是敦夫先生那时侯赶来,说不定我就昏倒了。”
“幸好平安无事。”西内太太紧张的说。
“可是,裱糊店的老板因为这事而丧生......”西内先生黯然神伤。
“就是说呀,而且对不起清君,怎么办呢?妈。”美树扑进母亲怀里哭了起来。
“哪一家裱糊店?”
“从这里过去五六家,左边不是有一条小巷吗?就是在小巷尽头的山坂先生,他的儿子清君和直彦很要好,也是读高中二年级。”
“和直彦同样读百濑高中么?”
“对,他们从小学就在一块儿了。啊,对了,今晚直彦也是到他们家去了。”
说到这里,正巧直彦苍白着脸跑进来。
“妈,不得了,清君的爸爸被人杀死了!他不晓得要救哪一个女人,结果给歹徒杀死了。!”
“那个女人就是美树。”
“什么?是姐姐?”直彦一下楞住了。
这时候门零急响起来,我去应门。
“我是警察,被歹徒骚扰的是这家的小姐吧?”
是个表情紧张的年轻刑警。
2
美树比预料中更冷静的回答刑警的询问。
“好象有点鼻塞的声音,而且是茨城,栗木那一带的腔调,个子高高的,力气很大,我觉得好象是年轻人。”
接下去的说明是我看到的情形,但是遗憾的是对于歹徒的体格和相貌没有足够供参考的资料。也难怪,那一带太黑了。
“如果想到什么,请立刻告诉我们。”
刑警说着,离开后,轮到我询问美树和他父母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想。没有这些就写不出精彩的特别报道。
“别的报社记者来采访,讲什么都不要说。我说美树受到严重的惊吓,不能接见记者。”
“好现实的人。”
丢下苦笑的一家人,我奔回房间,匆匆换上衬衫,领带。我必须争取时间,否则来不及明早见报。山坂的遗族要先见一面,访问一下,还要到P署,打听警方的看法。
抓了一本新的记事簿塞进衣袋,从楼上下来时,看到直彦站在走廊里发呆。我把他叫到角落里问他:“被歹徒杀死的山坂先生的儿子,听说是你的同学?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山坂太太......”“伯母已经死了,三年前车祸死了。”
“那么家里只剩孩子了?”
“对,三个孩子。”
“哪三个?”
“清君和妹妹幸代——她念初三,还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弟弟小宏。”
“那么,谁煮犯,做家事什么的?”
“清君和幸代轮流做。清君很能干,他虽然在打工,可是学校的成绩从来没有在第四名以后,今晚我也是去请他教我代数的。”
“你说打工,是自己攒零用钱?”
“不是,学费都是他自己付的,因为他们生活很苦。现在他爸爸死了,也许不能再念下去了。”直彦垂头丧气的说。
顽皮傲慢的男孩子,想不到这么体贴朋友,直彦的长处就是能由衷的称赞朋友。
“不过,清君的爸爸不是裱糊师傅么?”
“是的,不过……”直彦踌躇了一下才说:“叔叔喜欢喝酒,一个劲的喝酒,不做事。伯母死后,喝的更厉害。不喝酒的时候,其实是很和蔼的人。”
大概的情形已经了解了,我便直奔山坂家。
夜已深,但我想山坂家一定有许多听到噩耗赶来的亲戚朋友。以往好几次到命案被害人家采访时,除非独居公寓者外,毫无例外的都是这样。然而,山坂家的情形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只有三个孩子依偎在灯光昏暗的四席半房间,看不见一个大人。
“你是清君么?这次的事真不幸。”我说着,一面对自己无聊的话感到生气。
山坂清的面貌酷似父亲,但身材瘦高,一脸聪明相。高二学生,年龄大概十六七岁吧?
眼神冷静,仿佛很有见解的“男人”。与直彦比起来,好象年长两三岁。
“是的,我们还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清君以沉重的声音回答,成熟的口吻反而令人同情。
妹妹幸代是个小巧精致的古典型少女,流露出一副憔悴哀伤的表情。
跟哥哥姐姐比起来,小学生的弟弟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到底是老幺,特别受到宠爱的关系吧?看到我的名片“社会部记者”,好奇的仰着头看我。
这时候,一个男人跑进来,一面发出沙哑的声音问:“喂,清君在么?”
是个二十四五岁,穿黑色夹克,高大的男人。脸色黝黑,却留了一撮胡子,看起来十分不协调。
“我刚刚听岛田君说了,便马上过来。不要伤心,小幸和小宏不要怕。你们不拿出勇气,你爹就成不了佛。喏,有我在,你们什么都不用怕。”
虽然是夸大的安慰词,但对这三个可怜的孤儿仍然产生了作用,妹妹幸代首先哇的一声哭了,弟弟也跟着哭起来。
“不要哭,不要哭。”夹克男人摸摸他们的头说。
“我不要爸爸死,爸爸喝酒也不要紧。”小宏哭着说。
“爸爸喝酒也是伟大的人,爸爸做了伟大的事情才死的。”清君咬着牙说。
这时候,一个五十岁光景的女人匆匆走进来。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和他们同声而哭的人。
我在心中喃喃自语,同时示意夹克男人到外面去。
“请问,你和山坂先生是朋友么?”
对方迎着街灯看我拿出的名片。
“哦,是记者?不算老朋友,我是岛田工厂的小林。和山坂先生比起来,我是年轻多了。我们是酒友,常常在一起喝酒。”
“你认为山坂先生是怎样的人?”
“他是个好父亲,只是有点固执,而且太太死后喝酒喝的更凶,所以大家都讨厌他。太太在世的时候,在车站前面有一家店。可是他一喝酒酒发酒疯,主顾都被他赶走了,最后便沦落岛这种地步。不过,他是有侠义心肠的人,看到弱小者被欺负,他一定挺身相助,所以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我都认为他是好人。晤,我是唯一了解他的人。”
“刚来的那位太太是亲戚么?”
“不是,她是前面烤地瓜店的老板娘。平常见了山坂先生酒骂他酒鬼,可是很疼爱他的孩子们。”
“他们没有亲戚么?”
“好象没有。据说,山坂先生有位伯母,单独住在赤羽,已经八十多岁了,而且眼睛看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照料孩子们。”
这时又来了一个男人,是西内先生,显然是来探望刚成为孤儿的山坂家的孩子们。我透过西内先生索取了被害人的照片就离开了。
P警署灯火通明,刑警们,鉴识人员进进出出,充满了紧张气氛。先前到西内家调查的年轻刑警显然是新来的,我不认识,其他的人我大部分认识。由于我在这一区,了解这一带的风俗民情,所以这附近发生的这些色情狂骚扰妇女的案子,都由我负责采访。上回竹井被刺杀的案子提供资料的朝井警长正好从外面进来,我立刻拦住他。
“目前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因为手法相同,只是这一次更小心,刀柄上没有指纹,也许是带了手套。一刀刺进心脏里,所以当场死亡。死前没有多久才在邮局转角的那家‘赤松’喝酒,喝到十点多才离开。这个人喝了酒虽然会发酒疯,但听说今晚是高高兴兴离开的。这个人不是坏人,脑筋也不错,最可贵的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好几次看到学生被小流氓欺负,他就奋不顾身的去协助。他就是这样富有正义感的人。”
我致谢后离开P署。这件案子我有把握可以写出精彩的报道。
山坂龙平的葬礼在两天后举行。由于他的固执喝暴躁而吵架分手的一些从前的同行,纷纷前来帮忙。警方与防犯协会也送大花环来,附近的人成群来送葬,场面盛大感人。西内家的西内夫妇和直彦都出席。再没有人批评已故者,注视着三个孤儿的目光尤其充满同情。
出殡后的第二天,我提早离开报社,到山坂家去。因为有一些东西要给孩子们。我在报上写了一篇“孤苦伶仃的遗儿们”,引起人们的同情,好心人送来图书,文具等用品,当然捐款金额也不少。不过现金方面仍在研究如何处理当中,用品报社则交给我先行送给孩子们。
山坂家的清君和小宏兄弟不在,只有幸代独自看家,对我的来访,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这些礼物,要等哥哥弟弟回来后,再一块打开。”我把一包包礼物放下,接着问:“听说你们要继续留在这里?”
据西内太太说,没有亲戚朋友收容他们,所以三个孩子要留在这里。
“是的。哥哥说,他要休学,找工作做。他已经习惯了,一定没有问题,不要担心。隔壁的伯母说,家里的事情,她会替我们做,叫我们放心。”
“隔壁?啊,烤地瓜的伯母。”
“其实我也快毕业了,初中毕业我就可以出去做事。我的功课不好,也不特别喜欢读书,所以哥哥和小宏继续读书,我去做事也好。”幸代很懂事的说。
兄妹三人被分开收养,送进孤儿院,也许还不如三个人相依为命来的幸福。人情味浓的裱糊同业们已经为孤儿们发起捐款运动,西内家也表示将长期负担孩子们的学费,而且警方也应该会拿出一笔抚恤金才对。前一次的竹井案件,因为是单身汉,所以才一次付清。山坂家的孩子还没成年,也许会以年金的形式,在他们十八岁以前分次给他们。但无论如何,生活清苦,前途艰辛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就算生活上不必担忧,父亲仍然是子女们千金不可换的人物。
“我不要爸爸死,爸爸喝酒也不要紧。”想起小宏的这句话,我也为之心痛。
“发生这件意外的不幸,你们的打击一定很大。”
“好象被人打到头,昏昏沉沉的。爸爸被人杀死的消息,我最先知道。警察来说的。小宏已经睡了。哥哥和直彦在房内作功课。平常哥哥在房内作功课的时候,不准人家吵他。可是我吓的忘记了,冲进屋内喊说:‘爸爸被人杀死了!’哥哥就生气的骂我:‘我在作功课的时候不要来吵我!’也许我太紧张,没有说清楚。不过,等他明白过来以后,哥哥和直彦的脸色都变了。这时候小宏也被吵醒了,他说:‘爸爸死了?不要骗我。’小宏硬是不相信我的话。”
“这也难怪。我差点抓到凶手,真遗憾。”
感到遗憾不是客套话,如果能逮到凶手,不但为这些孤儿们出一口气,为社会大众除害,而且将可成为独家新闻。
3
“敦夫先生,还没有凶手的线索么?”
美树至少每隔两天就问我一次。尽管警方全力追查,山坂的命案发生至今已经有一周了,仍然没有任何凶嫌的蛛丝马迹。
“美树,我们再来详细的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怎样?凶嫌逃走的背影,我匆匆看了一眼,觉得个子高高的,是不是?”
“是的。从背后跳过来抓住我的时候,好象比我高这么多。我也对警察说过,好象一百七十公分左右的人。勒着我的脖子的手好大,手指好长。”
“就是说,也许这个凶手和前一镇子在这附近出没的色情狂是同一个人?不过,我总觉得不明白。那个色情狂本来只是纯粹的性变态者,杀死松井的时候,并没有预谋,而是被追上,两人在格斗中引起的结果。只是他身上带着刀,当然是危险人物。但杀人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对他也是一种打击。所以从那件命案发生以来,北关东腔高个子歹徒的骚扰案就忽然中断了?会不会是别人,模仿前面的案子?”
“可是,我那天遇到歹徒确实操北关东腔,我的同事有栗木和茨城的人,所以我常常听到那一带的腔调。别个地方的人要模仿,是不会那么自然的。”
“哦,歹徒以北关东腔叫你,然后在背后勒住你的脖子。就在这个时候,山坂先生跑来……”“什么?”
“不,没什么。”
我内心突然产生了疑问。据说,山坂先生曾喝道:“喂,混蛋!你要对这位小姐做什么?”山坂本来就认识美树,所以他说的“这位小姐”当然指的就是西内家的小姐。那么,他为什么知道在黑暗中受到骚扰的女性是西内美树?美树吓的尖叫,从声音可以听出是年轻女性,但为什么要特地说:这位小姐?
第二天下午,我抽空到赤坂。要调查山坂龙平的伯母日野静子老太太的住址,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龙平被人杀死的消息,我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我很想去参加他的葬礼,但眼睛快看不见了,脚力也不行了,太可怕了。唉,那三个孩子怎么办呢?真可怜!”
八十二岁的老太太独自坐在走廊的阳光下唏嘘不已。据说,一对认识的年轻夫妇把房子借给她住,还帮她煮饭。这位伯母虽然老迈,但是脑筋清楚,说的一口标准的东京腔。我试着问了几个关于山坂龙平的问题。
“龙平么?他没有兄弟姐妹。是的,东京出生的,道地的东京人。”
“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么?”
“没有。啊,不!有,很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大约几岁?”
“我记得是六岁到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死了,暂时把他寄养在乡下。本来我是想收养他的,但我那时刚守寡,而且有四个孩子……不过都死了。”
“哪里的乡下?”
“栗木县的乡下。”
“栗木县!”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着。
“是的。但是现在已经开发了,那时侯相当偏僻,龙平就在那变成了乡下孩子。不过暑假他就到东京来。住在我家。他实在是聪明伶俐的孩子……在乡下的时候,龙平和大地主栗原先生的儿子成为好朋友。不过,人家后来做了医生,在东京的池袋开了一家大医院。龙平却变成了裱糊师,最后还被人杀死。唉!”
老太太不住的眨动着蒙着一层灰膜的眼睛。
告别老太太我兴奋的走着。这一下谜题总算解开了,袭击美树的色情狂原来是山坂龙平。从今年春天以来连续发生的案子,可能不是他干的,因为据说是高个子的年轻人。山坂一定看了报上的报道。操北关东腔的男人。山坂小时侯住过栗木县,六岁到十岁已经能够记住当地的语言。而他本来就是东京人,住在乡下的期间也不时到东京来,住在伯母家,所以东京腔也不会忘记,回到东京就恢复了东京腔。但栗木腔要讲的话也可以讲。自从妻子死后,他就孤寡一个,不能说不渴望女色。他想到以北关东腔冒充别人。为避免被人认出声音,于是捏着鼻子说:“小姐,等一下。”当他勒住美树的脖子时,路过的男人发挥骑士精神跑过来。山坂便拔出身上藏着的刀应战,结果反被一刀刺入胸膛。刺杀他的男人想不到自己会杀了人,而惊慌逃走了。我瞥见的男人就是这个人。
不过我的推理遇到两个障碍处。其一是美树的证言“歹徒是个子高,手指长的男人”。
其二是山坂从后面跑来,一面说“要对这位小姐做什么?”的证言。山坂龙平绝对算不上高个子,他的手指也可能是粗短的。不过,当时美树在恐怖惊慌当中,难免会觉得加害者的身高比实际上的更大吧?此外,山坂的叫喊,也许是他想出的演技之一吧?据说,他原本是聪明的人。美树在惊恐中,错觉的以为山坂是要来救他的吧?
然而,我的推理在傍晚把美树约到咖啡店晤谈时,一下子就被她推翻了。她对我的说明嗤之以鼻说:“不要太瞧不起人,敦夫先生,从背后捉住我的男人身高至少有一米七零,绝对不会错。山坂叔叔是跑来救我的,这一点也不会错。我虽然害怕,还没到神志不清的地步。还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背后捉住我的男人没有酒味,山坂叔叔的酒味很重。敦夫先生,也许你又要说我是惊慌过度,但就算惊慌的时候,嗅觉还不至于消失吧?说不定更敏感,印象更强烈呢!”
这番条理分明的话,说的我哑口无言。不错,案发当夜,美树虽然脸色苍白,应该不至于重复三项错觉。她对我和刑警的说明,都相当的冷静清楚。
4
勇敢的市井骑士奋战歹徒壮烈牺牲性命的案子——而且连续两案——在胶着状态中迎新的一年。年底罪案频发,警察人员几乎忙不过来。但新年过后,似乎显得平静多了。
元月五日,表面上政府机关公司行号,当然包括报社在内,年假都已结束,恢复工作,但事实上仍然是清闲的下午。我把因吃年糕而噎死的老人消息送到报社后,回程经过池袋车站附近,看到一幢幢三层楼钢筋水泥前面的大招牌写着:内科小儿科——栗原医院。一个记忆忽然在我脑中闪现,半盲老妇告诉我的,必是这里。我涌起了好奇心,立刻叫司机把车子掉回头。而医院中一对可爱的少女,和几名护士在玩着毽子。今天医院的生意很清淡吧,穿着白色罩衫的医师,含笑在边上看着。我走进他,递上名片。
“是栗原先生吧?请问,你认识山坂龙平这个人么?”
“认识,,他是我在家乡读小学时的同学。你也认识他么?”栗原医师看着我,爽快的回答,他的话带着几分北关东腔。
“是的,认识。”
“山坂先生现在好么?”
“他去世了。”
“去世了?果然不错。”
“果然不错?怎么说呢?”我吸着气问。
“因为胃癌去世的,不是么?”
“胃癌?不是生病去世的。”
我扼要的说明了案情,医师睁大了眼睛听着。
“原来如此,我好象也看到报纸报道的消息,只是没有留意遇害者的姓名。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话,就是我们见面不久以后的事。”
“见面?他来看过病么?”
“不是,是偶然遇到的。那是礼拜天,我拜访朋友回来,车子经过甲州街道,看到他在行人道上走着。三十多年不见,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我马上把车子停下来,他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们彼此都很怀念往事,便站着谈了一会话。他说最近胃不大好,我就请他和我同车回来,为他诊察,结果发现贲门附近有可能是癌的肿瘤,而且肝脏也已受到感染。我尽量轻描淡写,装出乐观的样子。他严肃的对我说:‘如果有什么不治之症,希望你坦白告诉我,我有三个孩子,内人已经死了。如果是致命的疾病,我必须为孩子们做些准备。’因此,我下定决心,把实际情形告诉他。癌症的进行速度因人的体质而异,无法正确预言,但最快一两个月,最慢也只有六七个月而已。哦,原来如此,是被人杀死的。不过,说不定这样对他反而好。只要孩子们的事情准备好。”
我在医师的追问下,把命案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一面说,一面发现两个月来在我心中的结已经渐渐解开了。
这天晚上,我回寄宿处以后,马上到山坂家去。幸代和小宏已经睡了,只有清君在做功课。我听说,他于十二月初开始,在附近一家铁板工厂做事。
“等寒假一结束,我就改做钟点的。辛苦一点,我不在乎。”清君悄然说。
为避免吵醒两个熟睡的孩子,我靠近清君的耳边低声说:“父亲是你杀的吧?”
清君的眼睛闪了闪,盯着我问:“原来你已经知道?”
“你父亲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长,必须为你们三个兄妹做点准备。因此,你父亲就和你演出了一出戏。事先决定时间,在黑暗的路上会合。你父亲捏着鼻子以栗木腔叫唤路过的少女,少女一跑起来,你就追过去勒她的脖子。你父亲斥骂着跑过来,与你打斗,然后自己拔刀刺杀胸膛。为了不留下痕迹,刀柄上大概包着手帕,而由你拿下手帕跑掉吧?你父亲事先已经在明亮的地方看清走过来的少女是美树。对不对?”
清君垂着头,点点头。
“公司职员为了拯救被歹徒骚扰的女性而被杀死,抚恤金是一百五十万元。你父亲在考虑他的身后事时,想起这个案子吧?”
“一点也不错,因为爸爸没有能力参加人寿保险,也没有钱住院看玻爸爸说,假使以这种方式死掉,世人会同情我们。不过,你的推理有一个地方错了。”
“哪里?”
“爸爸的死不算自杀。”清君坚定的抬起头:“爸爸把一切计划告诉我,连续三天,我和爸爸不停的争论。然而,除了按照爸爸的计划做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我一个人的话,还勉强可以度日,但还有幸代和小宏。不过,我很了解自己的爸爸,他是个非常软弱的人。其实爸爸酗酒,也是由于软弱的关系。因此,对爸爸而言,要把刀子刺入自己的胸膛,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我协助爸爸做了……这是我唯一能帮助爸爸的一件事。这个计划,有一个人从头到味全知道。”
“直彦吧?以为他是不懂事的孩子是我的疏忽。”
“为了万一我被怀疑时,能有人替我作证,所以请他到我家来做功课。事实上只有他一个人在房内,而我从窗口溜出去了。”
清君说完,问我是不是要去报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粗布窗帘外面响起枯枝干叶的沙沙声。
元月底,P署逮捕了茨城县出生,住所不定的二十四岁男子。他除了最后一件强暴妇女未遂案和杀人案以外,其他案件都俯首承认了。
山坂家的三兄妹则平安的并肩努力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