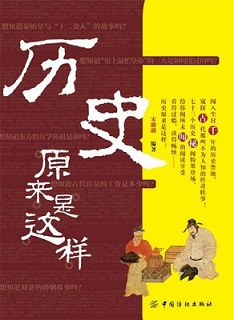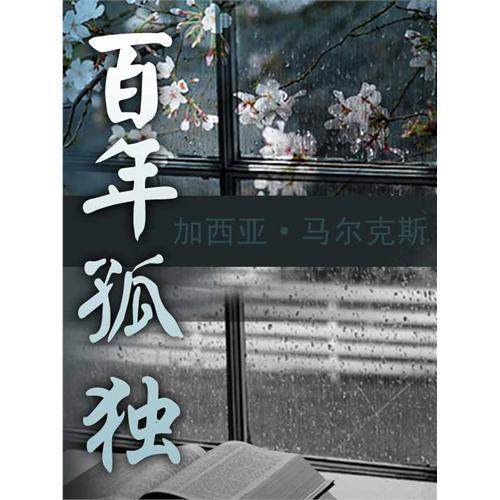哈罗德三、四岁的一天,父母带他去游泳。这事显得有点稀奇,因为在此之前,一家人除了去离家两个街区的电影院,很少去其它地方。在游泳池,他们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天,在这之后,哈罗德就再没见过他父母穿过泳衣。他只记得:他几乎全裸的父亲,站在游泳池里,踏着水,而他站在湿漉漉的瓷砖边缘,瑟瑟发抖,悬浮在氯粉深不可测的气息里。水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蓝绿色,哈罗德看着那明亮的波浪轻轻舐岸,感到一阵眩晕。他母亲穿着一身黑色的泳装,衬托出白皙的皮肤,不过他当时的注意力并不在她身上。他父亲让他跳下来。“来吧,小家伙,跳!”父亲用温柔的声音鼓励他,“别怕,我会接住你的。”他的声音在游泳池、瓷砖和阳光下单调地回响着。哈罗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洁白的皮肤在阳光下暴露着,这平添了他想要赤身下水的念头。他父亲稳稳当当地站在水中,看上去相当镇静,当哈罗德纵身一跃的刹那,他的脑海中还在漫不经心地想着,他父亲究竟站在什么上面。
蓝绿色的液体瞬间包裹了他,浓密而纷乱。他试图喘气,但却感到有一只拳头塞进了喉咙。他看到气泡在眼前上升,一串串的气泡,随着他的下沉而上升。他感到自己下沉了很久,直到沉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然后,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胳膊。
哈罗德被重新提回水上的世界,他趴在父亲的肩头拼命喘气。当父子二人爬出游泳池时,哈罗德的母亲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当着哈罗德的面,异常熟练地给了他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那声音似乎在整个游泳池里回荡,甚至被所有游泳的人都听到了;当然,这或许只是哈罗德记忆中的回声。哈罗德带着一身亮闪闪的水珠,从父亲湿漉漉的手上转移到母亲干爽的怀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的窘迫心情,直到喘过气来还没有消失。他母亲对他也是怒目而视。他全身裹着浴巾,站在母亲膝边的草地上,当他咳出最后一颗肺里烧灼的水珠时,他感到了永久性的羞耻。
哈罗德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掉进水里的;很多年过去了,当他询问父亲,父亲早已将此事淡忘。“那不是一件明摆着丢脸的事吗,”他父亲带着温柔的悲喜交加说,“要么沉下去,要么游上来,你沉了下去。”也许哈罗德当时跳得早了点,要不就是他的体重超出了父亲的意料,于是父亲没能接住他。不过,在哈罗德的成长过程中,他依然对父亲保持着信任;他不信任的倒是他母亲,她迅速而熟练的愤怒。
他直到大学都没有学会游泳。大学里,他是用仰泳加蛙泳的混合动作通过的考试。每当他惊慌失措,开始下沉的时候,他就抓住旁边老师挥舞的粗棍子。游泳池的气味总是让他惊恐万分,好像他闻到的是青龙吐出的气息。
他的几个孩子,成长在夏令营和乡村俱乐部的两栖世界里,全都轻松成为了游泳高手。他们试着教他潜水。“你必须先把头扎进水里,爸爸。要不,你就会一跳水就先打肚子。”
“我害怕浮不上来,”他坦白道0他在水下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串串气泡从眼前升起的景象。
他的第一任妻子怕坐飞机,但他们还是经常乘坐。“要么坐飞机,”他对她说,“要么就甭想在20世纪过日子。”他们飞往加利福尼亚,路上有两架飞机在大峡谷上空相撞。他们飞离波士顿。前一天,几只欧椋鸟阻塞了一架飞机无线电导航的引擎,使它一头栽进了港口。因为冲击力过大,乘客们的身体被扣上的安全带一截为二。哈罗德和妻子飞越非洲大陆,他们在夜晚横穿赤道。此时大陆如同墨色的深渊,被星星点点的部落营火点亮。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跑道上着陆,舱门砰然作响。她那么害怕,他向她保证,她以后再也不必和他一起坐飞机了。可最终,他们还是从非洲的衣索比亚高原,横越广袤、荒凉的利比亚沙漠,直至地中海沿岸,最后飞抵罗马。
这架从罗马起飞的泛美航空公司客机,拥有最为舒适的设施——像房子一样宽大的机舱,供应各类美国杂志和零嘴,美妙的音乐在机舱里流淌,且只有为数不多的乘客。飞机起飞之后,哈罗德埋首于一本《美国新闻周刊》,心里憧憬着吃一顿大餐,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就到家了。可十分钟之后,妻子问:“飞机为什么没有升起来?”
哈罗德向窗外看去。果然,窗外的海面依然没有缩小;他能清楚地看到小船和翻腾的白浪。空姐匆匆忙忙地在过道里穿梭,迷人的脸上带着异样的神色。哈罗德盯着自己的手掌,它们变得黏湿而潮红,就像晕机时出现的反应。而不管他怎么使劲盯着机翼下的海面,它们间的距离都没有渐渐拉大。阳光跳跃着,海面上钉着一只小帆船。
这时,飞行员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方噼啪作响。“乘客们,飞机的右翼引擎有一个警示灯亮了,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们将飞回罗马,等待降落。”
返航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空姐们坐在机舱后面的座位上,绑上安全带,而过道对面的那个男人仍然捧着一本法国《观察》杂志。哈罗德的妻子,是安全须知的虔诚信徒,她脱掉高跟鞋,摘下头发上的发卡,这让哈罗德再次惊服于女人临危不乱的气度。
他握住妻子黏湿的手,坚定地向窗外望去。他用目光抵住海面,用求生的意志把它远远推开。他感到,如果他眨一下眼,那整个世界就会崩塌。他们飞向罗马,不时掠过海上的小船。在哈罗德看来,蓝色的海洋和银白色、泛着冷调的机翼融为一体,只有奥林匹亚山肃立如故,浑然不知这其间正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透过飞机椭圆型的窗子,哈罗德时常感到,这些精心焊接在一起的铝皮不过是某种错误的证明。这一片金属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信任我;而在哈罗德心里,和他妻子一样,他拒绝信任它。这种拒绝在他体内形成了一个幽深的空洞,任由恐惧在其中泛滥成灾。
这架波音747飞机在罗马平稳着陆。机械师花了一小时时间排除故障,然后它再次起飞,飞往美国。回到家里,他们的恐惧变成了谈资和笑话。但他还是履行了诺言,她再也不用和他一起坐飞机了。然后,不到一年,他们就分开了。
在分开的那段日子里,哈罗德似乎在把他的孩子们从一个房顶抛到另一个房顶,默默乞求他们的信任。就像几年前,他曾用针头钳给女儿调整牙箍。她捂着腮帮找到他,一根铁丝戳到她嘴里面了。但是当他把手指笨拙地伸进她嘴里时,她瞪大了眼睛,害怕会更痛。“你不信任我,”他取笑她。他快活的语气揭示了一处关键的隔膜,这是他们处境间的罅隙:在他这只是犯个错,而对她来说这却是痛楚。他人的痛苦不是我们自己的,他认为,只有宗教在寻求修补这一认识,但是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痛苦,这种认识上的罅隙无法弥补。假如没有这个罅隙,我们就会受不了感情的压力,亏得这一角冷漠的隙地,我们才得以苟延残喘。在飞行员说“乘客们”的话音里,在他父亲叫他“跳水”的催促声中,哈罗德都曾感到其中必要的冷漠,甚至在他安慰女儿时,他也觉察了。“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但是如果你别动……看到这小尖儿了……噢。你又动了。”
哈罗德带着女朋友去雪山滑雪。他已经好几年没交女朋友了,不免要重拾那套巧妙的追逐女人的两面手法:既要娇宠,又要善于挑逗。他的女朋友普里西拉已是当妈妈的年龄,这把年纪的初学者只能对滑雪运动保持敬畏。她一整天都在一个小坡上练习转弯,一点点地建立信心,而哈罗德则和孩子们在雪山上纵横驰骋。黄昏来临,哈罗德雪沫飞溅地冲回普里西拉身边。她求着他说:“给你表演我的耙式滑降吧。”
“如果你能在这儿滑,你也能从山顶上滑下来,”哈罗德告诉她。
“真的?”在小坡上滑了一天,她的两颊绯红。她戴着一顶白线帽,眼睛是那种婴儿般的蓝色。
“绝对!咱们滑新手的线路。”
她相信了他。不过随着缆车越爬越高,高处的寒风横贯双耳,她的脸上现出了犹疑之色。随着施虐者所体验到的不正常的隐秘快感扩散开来,哈罗德意识到,这件事他做错了。缆车隆隆地向上爬,越来越高,“我真的能从这儿滑下来吗?”普里西拉问道,像孩子似的等待着回答。哈罗德睹物移情,不禁又勾起了当年游泳池畔的一幕。
他说:“不滑这一段。看这儿的风景,太美了!”
他们摇摇摆摆地经过一段山谷,她的身体僵直地坐在缆车上,顺从地扭过头。她看到下面林木茂密的山谷和冰冻的湖泊,它们构成一道蓝绿色的风景。山脚的停车场像一只小盘子镶嵌着汽车的花纹。索道不可遏止地颠荡着,温度下降,周围低矮的松树盘根错节。薄雾舔舐着冰面,他们已深处云中。普里西拉站在山顶浑身颤抖,几乎无法站立。
“我做不到,”她宣布。
“照我的样子做,”哈罗德矫健地向下滑了几码说,“先把你的重心放到一只滑雪板上,然后再放到另一只上。不要管山的坡度,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重心的移动上。”
她把重心向后移,从坡上站起来,但马上又摔倒了。她的眼里噙着泪水,他害怕泪水会很快凝固,把她的眼睛冻瞎。他滑到她身边,鼓足了怜爱的心意,一个劲儿想融化她的恐惧,“只看你的滑雪板,别管你在哪里。”
“这里根本没有雪,”她说,“只有冰。”
“边上没有冰。”
“边上全是树。”
“振作起来,宝贝,天快黑了。”
“我们会被冻死的。”
“别瞎想了,最不济也有巡逻员来巡视滑雪道的。把你的重心向下,然后借助重力往下滑。你必须这么做,该死,这很简单!”
“对你来说倒容易,”普里西拉说。按照他的指点,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下滑。她撞到一小块石头上,再次摔倒。她尖叫起来,想把滑雪撬扔掉,可它们系在手腕上。她踢着雪,婴儿般的大发脾气,一只滑雪板被她踢掉了。“我恨你,”她哭道,“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在小坡那里我本来很自豪,我所有的要求不过是想让你看我在那儿滑,哪怕只看糟糕的一分钟,我所有的要求就这些。你知道我做不到,你干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为什么?”
“我以为你没问题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带你上来看风景。”毫无疑问,他父亲当初也想让他体验下水的快乐来着。
黄昏在山间降临。一群群少年雪山健儿,穿戴得五光十色,天崩地裂似的从高处滑下,呼啸而过,只偶尔出于好奇,侧目瞟他们几眼。哈罗德和普里西拉商定脱掉滑雪板走下去。这花了他们整整一小时,让哈罗德付出了脚后跟各磨出一个水泡的代价。路边的树木注视着这场格外缓慢的行进,带着奇异的冷冰冰的隔膜感,那是与飞机上的铆钉如出一辙的讽刺的镇静。孩子们坐等在空旷的停车场边,眼含泪花。“我本来想带她好好玩一下,”哈罗德向孩子们解释着,“但是你们的妈妈不信任我。”
还是在这段危险的时期,哈罗德去前妻家里给儿子过17岁生日。在他正准备去赶回城里公寓的火车时,他注意到一盘子刚出炉的布朗尼蛋糕正凉在烤炉上。这有些奇怪,因为生日蛋糕已经上过了。他问儿子,“这是什么?”
男孩天真无邪地微笑道:“掺了点麻醉剂的布朗尼。尝一块,爸爸,你可以带到火车上吃。”
“我吃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不会的。只是其他孩子做了和我闹着玩的。意思意思罢了,不碍事的。”
哈罗德从小就喜欢吃甜食,他挑了一块大的,在儿子开车带他去火车站的路上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在火车上,他把头靠在外面漆黑一片的车窗上,玩味着一个离婚男人的心酸。慢慢地,他开始感到口干舌燥,同样的思绪反复出现,一层层堆砌,在大脑皮层中呈现出格外流光异彩的形态:既像彩色印刷的地层图,又像比赛场上的彩带。当他摇摇晃晃地下了车,立刻感到头重脚轻,不得不靠在什么上,要么就得倒在地上。他的身体拖累着他,不听使唤。他感觉自己被人流裹挟着出了车站,穿过一群披着大衣的陌生人,经过一条停满了肿胀的汽车的街道。他琢磨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那半清醒的大脑猛然意识到:他吃了一块掺麻醉剂的布朗尼。
他的半边脑子一直对另一半吼着谨慎的指令:瞧着两边。掏一块钱出来。慢着,这儿有代用的零钱。把钱放进收款机里。等16路来。别上错了去辛丰尼的那趟车。别慌神。每一步似乎都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他彩带般的思绪以电脑运算的速度不断叠加和穿梭。半边大脑在回家路上喊着指令和祝贺,而这些想法不断堆积成胡话。地铁上的乘客全都盯着他,好像能听到他内心的躁动。但是他躲在面容背后,感到安全,就像躲在一副钢制面具后面。车轮发出尖锐的刹车声,一串彩灯从窗边飞逝而过。
走出地铁站,离公寓还有三个街区。他再次感到如在云中,嗓子火辣辣的,一阵阵想吐。他拣着树篱或垃圾桶呕吐,虽然一路上很少有树篱和垃圾桶。就像在验证一条深奥的公理,他用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锁,门背后挤着满满一屋子让他熟悉又眼花缭乱的家具。他拿起电话,拨给普里西拉。
“嗨,亲爱的!”
她的声音警觉起来,“哈罗德,你出什么事了?”
“我的声音听着反常吗?”
“很反常,”她的声音尖得像豪猪的刺,黑色的刺带着白尖,“他们把你怎么了?”他们——他的孩子,他的前妻。
“他们让我吃了一块掺麻醉剂的布朗尼。吉米说不会有事的,但在火车上,我的精神变得特别恍惚和紧张,然后从车站回家的路上,我不得不老提醒自己怎么走。”那半边保驾护航的,值得信赖的脑子祝贺着他的话听上去很有说服力。
但是,什么东西触怒了普里西拉。她哭道:“噢,真让人厌恶!我一点不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意思,我一点不觉得你们谁做得有意思。”
“我们谁?”
“你知道我指的谁。”
“我不知道,”尽管他明白。他看着自己的手心,它们汗津津的。“亲爱的,我想吐。帮帮我!”
“帮不了,”普里西拉挂了电话。那“啪嗒”的挂机声像是一记耳光,那记曾经炸响在他耳边,回响不已的耳光——除了父亲变成了他的儿子,母亲变成了他的女友。本质上的一点是相同的:明明过错不在他,只因他幸免无事,于是好歹总要归罪于他。
现在,他的手掌不那么黏湿了,但它们看上去苍白而褶皱,像不舒服的枕头。在上衣口袋里,哈罗德发现了一张很久之前地铁换乘时被退回的一元钞票。他一边等待着普里西拉回心转意,打电话过来,一边翻过纸币。他审视着纸币背面上残缺的金字塔,以及上面那双神秘的眼睛,一边反复读着“ONE”字上方印有的那句格言:“唯神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