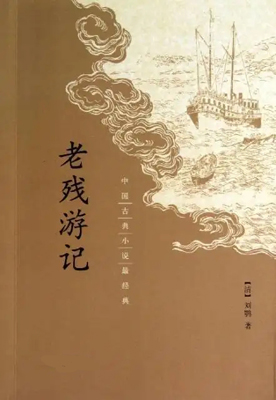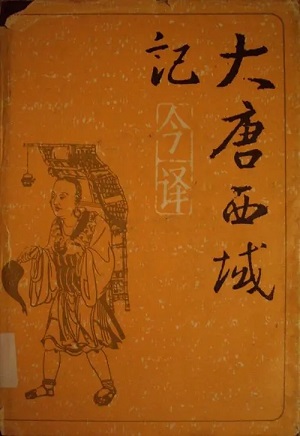人文学科在某些国家是谈不上繁荣的,更不用说艺术了。尽管我们对此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艺术上为何有此遭遇,例也很难说明。因为有时正是最贫痛的土壤上会出现盛开那种鲜花的花园,那些花朵会被我们一致认定是人生的荣耀和正直,由于有这么一个事实,使得我们最后很难断言:为什么赞比西亚①的土壤会长出如此难以培养的植物来。
赞比西亚这片土地,终日骄阳似火,百姓精力充沛,能吃苦耐劳,实事求是,不很敏感,也瞧不起精致的玩意儿;不过有几个这般情况的州也产生过艺术,虽然有点笨拙。赞比西亚对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早巳被人接受的那些观念,如自由、博爱等,说得婉转一点吧,也是不表同感的。有那么一些入,他们之中不乏优秀人物,坚持说,要是没有劳苦大众所保障的少数人的闲运,就不可能有艺术。不管生活舒适的少数赞比西亚入可能短少些什么,可并不缺少闲逸。
够了,别再对赞比西亚发议论了;出于自尊和对科学严密性的尊重,我们不应该匆促地作出结论。特别是当有人回亿起一位艺术家真的出现在他们之中的时候,赞比西亚入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尊敬。
举个例,且来看看米开尔的事迹吧。
二次大战期间,当意大利成了道义上的同盟国时,米开尔从战俘营出来了。当局在这段时间里,极其紧张忙碌,因为一方面要对数干名必须以某种公认的标准对待的战俘负责,另一方面,日复一日地面临着把这数千人用某种国际上的手法转变为战友。这几千人中有一些留在原来的营房里,在那儿,他们至少有饭吃,有房子住。其余的,虽然人数不多,去农场当劳工。当时农民们一直缺乏劳力,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这批和他们肤色相同的白种劳工;赞比西亚以前可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些人走市镇,干临活,他们得时刻提防当地工会,因为当地工会既不接纳他们入会,也不同意他们做工。
这伙人真是命途多舛啊。不过幸而时间不长,不久,战争结束了,他们也就能回家了。
正如上文所说的,政府当局的日子也不好过0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极想从这样的形势里捞取点好处。米开尔无疑就是一个能结当局带来好处的人。
当他还是一名战俘时,他的才能就已被人发现了。当时战俘营造了一座教堂,来开尔装饰教堂的内部。战俘营中的铁皮顶子教堂变成了展览馆。白粉墙上,画满了壁画:黝黑皮肤的农民在采摘葡萄酿酒,漂克的意大利姑娘在跳舞,以及胖乎乎的黑眼珠孩童。在熙熙攘攘的意大利风浴画里,出现了圣母和圣子,圣母慈祥地微笑着,愉快地在她的子民中间随便走动。
贿赂了当局、被允许进战俘营来参观的爱好艺术的女士们会说:“可怜的人啊,他多么想家啊。”她们还会恳请给艺术家留下半个克朗。有些人则满腔义愤。他毕竟是一名囚犯,一名在反抗正义和民主的战争中被俘的囚犯,他有什么权利表示抗议?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画就是一种抗议。意大利有的东西,难道我们这儿,赞比西亚的首都和中心韦斯顿维尔没有吗?这儿难道没有阳光、高山、胖娃娃和漂亮姑娘吗?即使我们没有栽培葡萄,我们不是至少也栽培了许多柠檬、桔子和鲜花吗?
人们的思燃混乱了——简陋教堂的白粉墙上的壁画表现了一种绝望的恋乡之情,按照各人的气质,而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米开尔—获自由,他的才能又被人想起来了。人们称他为“意大利艺术家”。而事实上,他只是个砖瓦匠。那些壁画的优点被人们大大地夸张了。若是在一个壁画相当普遍的国家可能就一点儿也不起眼。
有一位来访的太大,从自备汽车里跳下来,径直冲进营房,要求他给她为孩子们画像。他起先说干不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在镇上弄了间房子,画好好几张孩子们的漂亮肖像。接着化又结最先来访的太太的许多朋友们的小孩画像,每次收费十先令。后来有位太大要画一张她自己的肖像,他要价十镑。他用了一个月时间画了那张像,太太很不高兴,不过还是付了钱。
米开尔带了一个朋友回到自己房里,他们呆在那儿饮着好望角的红酒,谈着家乡的事。只要他手头上有钱花,谁也不能说服他再去给人画像了。
太太们大谈劳动的尊严,这题目她们可烂熟了;一位女士觉得她们讲得大多了,几乎说到把白种人和非洲卡菲尔黑人作比较,而卡菲尔人并不懂什么劳动的尊严。
人们觉得米开尔缺乏感恩戴德之心。有位太太跟踪他,看到他拿着一瓶酒躺在树下的一张行军床上,便一本正经跟他讲起墨索里尼的暴行以及意大利人不中用的气质来。接着她要求他立刻为她画一幅身穿簇新晚礼服的画像。他一口拒绝。太大十分气愤地回了家。
碰巧她是一位顶重要的公民的妻子,这位公民是位将军或者诸如此类的大人物。那时他正为公众利益筹备一次军事演习或军事展览。几周来整个威斯顿维尔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我们对跳舞啊,化妆舞会啊,集市啊,有奖彩券啊,以及其他种种慈善性质的娱乐活动部厌烦已极。一些人在为自由献躯,而另一些人却在为自由跳舞。这话说得并不过分。一切事物都有个极限。自然罗,当战争真的结束时,驻扎在这个国家的几千名军人都得解甲归田。总之,当快乐生活不再是一桩义务时,会听到许多人感叹生活将不再是同样的了。
这时候,军事演习可以让我们大家换换口味。对这项计划负责的搞军事的先生们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们想让我们了解一下真正的战争是个什么样子的,以此来振奋一下士气。报纸上用通栏标题进行宣传还不够,为了使之家喻户晓,他们计划让我们看见炮火摧毁一座村庄。
要摧毁一座村庄,首先得建造一度村庄。
将军和他的僚属,头顶烈日。在阅兵场的红色尘埃中站了一整天。他们的周围堆满建筑材料,一群群非洲劳工拿着木板和钉子跑来跑去,正在设法造一座看上去象村庄那样的东西。显然,为了摧残一座衬庄他们将不得不先造一座适当的村庄,而这样做的费用将会超过整个表演所允许的开支。将军回家时心情很不好,他太太说他们需要一名艺术家,她们需要米开尔。这倒不是因为她想给米开尔一个好机会,她一想到他有事情不干而躺在那里唱歌,就受不了。将军说他如果去求一个意大利小子,那不算人了,而太太又拒绝担任任问微妙的外交使命。她用她自己的办法帮丈夫解决了这个问题:派一名叫斯托克的上尉去接米开尔。
上尉仍然在那株树下的那张行军床上找到了他。他身穿无领衬衫,裤腿卷起,没有刮胡子,微露醉态,在他身边的地上放着一瓶酒。他正哼着一支粗野而悲凉的小曲,上尉听了很不舒服。他在离这个肮脏落拓的家伙十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感到自己的地位受了侮辱。一年以前,这人还是一个一见就要开枪的不共鼓天的仇敌。六个月前,也还是一个战俘。而此刻却穿着一件邋塌的军用衬衫,竖起膝盖躺着。依上尉的意思,米开尔遇到这种清况,应该问他致敬。
“喂!”他厉声说。
米开尔转过头,从地平线望着上尉,和蔼地说了声“早安”。
“有人叫你去,”上尉说。
“谁啊?”米开尔说着坐了起来。他是个胖胖的、橄榄色皮肤的小个子,眼睛里露出愤怒的神色。
“政府当局。”
“仗不是打完了吗?”
上尉穿着烫过的黄卡其军装,腰板笔挺,容光焕发。他把头一仰,下巴一翘,皱紧了眉头。上尉个子高大,金黄头发,身上露出来的肌肉呈砖红色,蓝色的小眼睛满含怒气,布满漂亮的黄色汗毛的通红的双手,握成拳头摆在身旁。他在米开尔眼中看到了沮丧的神情,两只拳头就松开了。“仗没打完,”他说,“需要你来出力。”
“为战争出力?”
“为战争出力。我想你对击败德寇会感兴趣的。”
米开尔望着上尉,黑眼珠的小个子手艺人看着魁伟的白人军官,看着他那冷淡的眼睛,狭小的嘴,那双象布满毫毛的牛排一样的手;他看着他说:“我对战争结束最感兴趣。”
“是吗?”上尉从牙缝臣说。
“那么有报酬吗?”米开尔说。
“会给报酬的。”
米开尔站起来,对着太阳举起酒瓶喝了口酒,用酒嗽嗽口又吐掉。接着他把剩酒倒在红土上,地上泛起一摊起泡的紫色酒迹。
“这就走吧,”他说着与上尉一起朝停在那里的卡车走去。他爬上车坐在司机座的旁边,没有按上尉希望,坐在卡车后部。他们到达阅兵场时,军官们已经留下口信,要上尉亲自对米开尔和那村庄负责,也对一百名左右工人负责,他们坐在周围草地上等侯命令。
上尉说明了他们所要的东西。米开尔点点头,对那伙非洲人挥挥手说:“我不要这些人。”
“你独个儿干这事儿——造一座村庄?”
“是的。”
“不要人帮忙?”
米开尔第一次露出笑容。“不要人帮忙。”
上尉犹豫不决。他原则上是不赞成白人干重活的。他说:“我留下六个人干重活。”
米开尔耸耸肩;上尉走过去把非洲入解散了,只留下其中六个人。他领着他们回到米开尔站的地方。
“天真热,”米开尔说。
“夏热,”上尉说。他们正站在阅兵场中央,场地周围有树木、草地、片片阴影。而阅兵场上,只有热风低吹,红土飞扬。
“好渴啊。”米开尔咧着嘴说。上尉回答时,绷紧的嘴唇也不知不觉地松开了。两人的目光一相遇,双方的思想沟通了。上尉觉得这个意大利小子突然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了。“我去安排,”他说完就离开米开尔,到城里去了。等到他向有关的人谈了情况,填写了表格,作好安排后,天色已晚。他带着一箱好望角牌的白兰地酒回到阅兵场,看见米开尔和那六名黑入正一块儿坐在树下。米开尔给他们唱一支意大利歌曲,他们和着他唱。上尉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他走上前去,非洲人都站起身立正。米开尔还是坐着。
“你不是说你自己来干那活儿?”
“我说过。”
上尉解散了非洲人。他们友好地和米开尔分手,米开尔也向他们挥手告别。上尉气得满脸通红。“你还没有动手吗?”
“给我多少时间?”
“三星期。”
“时间够多了。”米开尔盯看上尉手中的那瓶白兰地说。上尉另一只手拿着两只玻璃杯。“天晚了。”他提醒说。上尉皱着眉头站了一会儿,然后在草地上坐下来,斟满两杯白兰地。
“干杯,”米开尔说。
“干杯,”上尉说。三个星期,他思忖着,要和这该死的意大利小子挨过三个星期!喝干一杯,又斟上一杯,放在草地上。草地凉爽而柔软。近旁有株树正在开花,微风送来伴随着花香的阵阵热浪。
“这儿美极了,”米开尔说。“我们一起过得挺愉快。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有快活的时光,也有友谊。为战争结束干杯。”
第二天,上尉直到午饭后才到阅兵场上来。他看到米开尔拿着一瓶酒呆在树下,阅兵场的那一头竖起了许多薄板筑成两垛墙以及另外半垛墙,几根柱子支撑着一座尖尖的屋顶。
“那是什么东西?”上尉大发雷霆。
“教堂,”米开尔说。
“什——么?”
“以后你会明白的。天气真热啊。”他瞧着横放在地上的白兰地酒瓶说。上尉朝卡车走去,把那箱白兰地提了来。他们喝酒,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上尉在树下草地上坐了好久,也就是说他大喝其酒消磨了好长时间。他时常喝大量的酒,不过他喝酒能够受情势和时令的节制。他是一个守纪律的人。此刻,他坐在草地上,坐在那个他仍然不得不认为是敌人的小个子旁边,并不是丧失了自我约束,而是感到自己有点异样,感到自己的行为一时有些不大正常。米开尔满不在乎。他听米开尔讲意大利,似乎在听一些原始野蛮的故事:类乎南海诸岛神秘的传说,象他那样的人最好一生中能到那儿去一趟。他觉得他说过很想在战后去意大利旅行。实际上,他只是被北方和北方入吸引住了。他游览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虽然此刻不宜这么说,他还是认为那地方令人十分满意。接着米开尔对他唱了几支意大利歌放,上尉也唱了几支英国歌曲。后来米开尔拿出他妻儿的照片来,他们住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的一个村庄里。他问上尉结过婚没有。上尉从来不谈自己的私生活。
在他一生中,他在一两个非洲殖民地担任过警察、文官、地方官员或别的相当的职务。打仗了,他很习惯军旅生活,但是他厌恶城市生活。希望战争结束,有他自己的理由。他经常和一两名白人,或者独自一人住在远离严格的文明世界的丛林驻地里。他和本地妇女有来往。他有时去妻子住的城市逗留一段时间。他妻子和她自己的父母以及孩子住在一起。他老是为妻子对他不贞这种想法而苦恼。近米他甚至委托了一名私家侦探去监视她,他认为那侦探十分无能。从他妻子住的L城来的部队朋友说起她在舞会上玩得很快活。如果战争结束了,她就会发觉不能那么轻易寻欢作乐了。那么为什么他不干脆和她一同生活呢?事实上他不能够。他长期离家远居丛林驻地就是为了要找个借口不和妻子住在一起。对妻子的事情考虑久了,他便忍受不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永远不能使之就范的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现在他跟米开尔谈起妻子来了。他还谈到他心爱的丛林太大娜迪娅。他坐在树下给米开尔讲他生活的经历,直到他发觉那树影已从阅兵场延伸到了看台,他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道:“还有事干呢,你干活是给报酬的。”
“天色一暗,我就给你看我造的教堂。”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米开尔便叫上尉把卡车开到离阅兵场二百码的地方,把灯开亮。立刻,一座白色的教堂从一堆堆木板构奇形怪状的阴影中涌现出来。
“明天,咱们再造几幢房子。”米开尔快活地说。
到了周末,阅兵场一端的空地上,筑起了一堆木板和板条钉成的歪歪斜料、粗糙拙劣的建筑物,在阳光下看起来什么也不象。私下里,上尉感到迷惑,这堆骨架一样的东西,在灯光和黑暗的幻象下,竟能使他相信是一座衬庄,这简直象一场梦魇。夜间,上尉驾驶卡车前来,开亮电灯,那儿就出现一座村庄,一座在绿树浓荫衬托下的坚固真实的村庄。然后,在早晨的阳光的照耀下,就什么都不见了,只剩下矗立在沙地上的一些木板。
“完工了,”米开尔说。
“给了你三周的时间你哪。”上尉说。这段假期是他自己弄来的,他不愿让它就此结束。
米开尔耸耸肩说,“军队就是有钱。”现在,他们为了避开人们好奇的目光,就带上那箱白兰地,坐到那座教堂的影子里去了。上尉没完没了地提老婆,谈着女人,一个劲地谈个不停。
米开尔听着,有一回他说:“等我一回到家里,我一回到家里,我就要张开双臂……”他大大地张开双臂,闭上眼睛,眼泪从面颊上流下来。“我要把妻子抱在怀里,我什么也不问,不问。我不在乎。能生活在一起就够了,这是战争教我的。够了,够了,我什么也不问,我会很幸福。”
上尉在他面前痛苦地瞪着眼睛。他想他自己是多么惧怕老婆啊。她是个厚颜无耻的东西,阴郁,冷酷,对他冷嘲热讽。结婚后便一直嘲笑他。打仗了,就叫他小希特勒,叫他冲锋队员。“滚吧,小希特勒,”他们上次见面时她大喊道。“滚吧,冲锋队员。如果你要把钱花在私家侦探身上,那么就滚吧。但是别以为我不如道你在丛林里的所作所为,你干什么我都不在乎,不过你要记住,我是知道的……”
上尉想起了她说过的话。米开尔坐在木板箱上,说道,“我的朋友,侦探和法律对有钱人是件乐事,甚至妒嫉也是乐事,我可不要那玩意儿。啊,我的朋友,我只要和妻儿重逢,这就是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我们生活在一起,喝酒,吃饭,到了晚上就唱唱歌。”他的泪水沾湿了面颊,落到衬衣上。
男人这样流泪哭泣,我的天哪!上尉想,真是不知害臊!他抓起酒瓶痛饮起来。
在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前三天,几名高级军官穿过尘埃走来,看到米开尔和上尉正坐在板箱上唱歌。上尉的衬衫敞开前襟,上面全是酒迹。
上尉起身立正,手中拿着酒瓶,米开尔出自对朋友的同情也站了起来立正。军官们都是上尉的老朋友,他们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他是否明白他到底在于什么?为什么村庄还没有造好?
他们说完就走了。
“告诉他们村庄已经造好了,”米开尔说。“告诉他们我要走了。”
“别走,”上尉说,“别走。喂,米开尔,你会怎么样,如果你老婆……”
“这世界不错,我们会幸福的,那就是一切。”
“米开尔……”
“我要走了,没事可于了。他们昨天给了我工钱。”
“坐下,米开尔。还有三天呢,然后才结束。”
“那我就来画教堂内部,就象给战俘营教堂搞的那样。”
上尉在木板上躺下睡着了。待他一觉醒来,米开尔已给一罐耀颜料团团围住,这些颜料都是他在画树庄外部时用过的。上尉面前有一幅黑人姑娘的画,年轻而丰满,身穿蓝色绣花衣裳,柔滑的肩膀袒露在上衣外面,背上背着一个系着红呢带子的婴孩。她的脸转向上尉微笑着。
“是娜迪娅,”上尉说。“娜迪娅……”他大声哼着。他瞧一眼黑孩子,闭起了眼睛。一会儿睁眼一看,那母子俩仍在那儿。米开尔小心翼翼地在黑姑娘和孩子的头上画着细细的黄色光圈。
“上帝啊,”上尉说,“你别那样画啊。”
“为什么不能画?”
“你不能有一个黑圣母。”
“她是农民,我画的是农民,黑人国家里黑人农民的圣母。”
“可这是一座德国人的村庄。”上尉说。
“但她是我的圣母。”米开尔发怒了。“德国村庄是你们的,圣母是我的。我把这幅画贡献给圣母,她会高兴的,我知道。”
上尉又躺下了,他感到周身不适,又睡着了。他第二次醒来,天色已暗。米开尔拿来一盏灯光闪烁的煤油灯,就着这灯光在长长的板壁上绘画,身边放着一瓶白兰地。他一直画到深夜。上尉就躺在一边看着,神态迟钝,象是给梦魇住了。后来他俩在木板上睡着了。第二天,米开尔一整天钻在那儿画着黑圣母,黑圣人,黑天使。外头太阳底下,军队在操练,乐队在奏乐,摩托车轰鸣着来回奔驰。米开尔继续画画喝酒,什么都不在意。上尉仰面躺着,喝着酒,咕咕哝哝地抱怨妻子。后来,他好象叫着“娜迪娅,娜迪娅,”呜呜地哭了。
傍晚,军队开走了。军官们回转来,上尉领着他们走过去,他要给军官们看看,阅兵场那头的电灯一亮,那座村庄是怎样显现的。他们都静静地注视着村庄。电灯一关,那儿只有一些搭成尖顶的木板,在月光下象墓碑一样高矗立着。灯一亮——又成了一座村庄。他们满腹狐疑,沉默不语,似乎和上尉一样觉得不太对头。说这事儿怪诞不经吧,又不好这么说。反正是不对头——就是这句话。这是欺骗,是彻头彻尾的捣鬼。
“你那个意大利小子真是个机灵鬼,”将军说。
到那时为止一直呆板端正的上尉,突然间摇摇摆摆向将军走去,用手扶着将军尊严的肩膀让自己站稳了,口中嚷道:“该死的意大利人,该死的卡菲尔入,该死的……不过让我告诉你,有个意大利入还算不错,是不错。我正要告诉你,他实际上是我的朋友。”
将军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部下点头示意。上尉因触犯纪律而被带走了。不过,他病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这样荒唐的行为。他被安顿在自己房内的床上,由一位护士照看他。
二十四小时以后他才醒来,几周来他第一次清醒。慢慢回想起所发生的事儿,从床上跃起,匆匆套上衣服。跑上小路,跨进卡车,护士才看见他。
他高速度地朝阅兵场驶去,场地上一片灯光,衬庄仿佛融化在灯光之中不存在了。一切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广场周围停了三重汽车,跑道上,甚至屋顶上都有人。看台也挤得满满的。妇女们打扮成吉卜赛女郎,乡村姑娘,伊丽莎白王朝的官廷仕女等等,手拿托盘走来走去。托盘里装着姜汁啤酒,香肠面包以及节目单,每份五个先令。为战争募捐。广场上,军队调动着,士兵们把老式机关枪拖来拖去,军乐队在奏乐,摩托车隆隆地穿过火焰。
上尉刚把卡车停放好,所有的活动突然停止了,灯光也随之熄灭。上尉开始沿着广场外围奔跑,想跑到隐蔽在大堆网和树枝下的枪炮工事去。他费劲地喘着气。他是个大块头,不惯于运动,又被白兰地灌得昏头昏脑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阻止枪炮发射,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枪炮发射。
幸亏出了点故障,电灯仍然不亮,广场那头神秘的墓地在一片月光下白花花地闪烁。接着电灯忽然亮了一下,村庄又出现了,足以使人们看到教堂旁边的一片白色建筑物上有几个巨大的红十字架。电灯又熄灭了。月光重又普盖大地,十字架又消失了。“咳,这该死的傻瓜!”上尉喘着气继续奔跑,他似乎在为自己的性命而奔跑。他不再想跑到枪炮跟前去了。他抄近路穿过广场一角,径直往教堂奔去。他听到背后一些军官在咒骂:“是准把红十字架放在那儿的?是谁?我们可不能朝红十字架开火。”
上尉跑到教堂时,探照灯突然大放光明。教堂里,米开尔脆在地上凝视着他画的头一幅圣母像。“他们要杀死我的圣母了,”他悲哀地说。
“快离开,米开尔,快离开。”
“他们要杀死……”
上尉抓住他的手臂拖着他走。可是他扭脱了上尉,拿起一把锯子乱锯起板壁来。外面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听到扩音器里一个声音在吼叫着:“将遭炮击的村庄是座英国村庄,不是节目单上所写的德国村庄。重复一遍,将遭炮击的村庄是座……”
米开尔已经把一方块画着圣母像的板壁锯成两半。
“米开尔!”上尉喘息着说,“快离开这儿。”
米开尔手中的锯子掉落在地,他抓住板壁的毛边,挤命地扳,这样一来,教堂开始摇晃、倾斜。一块破板折断了,米开尔一个踉跄跌入上尉怀中。轰隆一声巨响,教堂似乎绕过他们投入火焰之中。上尉紧拉着米开尔的手臂住外冲。“下去。”他突然叫道,把米开尔扔到地上,自己也扑到在米开尔身边。上尉从弯曲的手臂下向外望着,一声爆炸,他瞥见一股巨大的火焰柱子,村庄在一堆飞扬的碎片中完蛋了。米开尔跪着凝视火光中的圣母,圣母像蒙上了尘土,巳经面目全非。米开尔脸色苍白,看上去可怕极了。一缕鲜血从他头发里渗了出来,流满半边面颊。
“他们炮轰我的圣母,”他说。
“咳,真该死,你可以再画一张嘛,”上尉说,他的声音自己听来觉得异常陌生,象是梦吃一般。他一定发疯了,和米开尔一样发疯了……他站起身,把米开尔也拉了起来,推着他朝场地边上跑去。在那儿他们遇上了救护入员。米开尔被送进医院,上尉也被送回床上去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上尉住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他显然得了某种精神衰竭症,有两个护士照看他。他有时睡得很安稳,有时喃喃自语,有时候用粗重的嗓音唱看几段歌剧,唱着意大利歌曲的片断,还一遍一遍地唱:“有一条漫长的小路。”他简直什么都不想。也竭力不去想米开尔,似乎思想也是危险的。因此,当他听到一个悦耳的女人的声音说:有位朋友来,会使他高兴起来的,有个人作伴对他有好处,而且朦胧中他看到白色绷带向他过来,他赶紧转过身面对墙壁。
“走开,”他说。“走开,米开尔。”
“我来看望你,”米开尔说。“带给你一件礼物。”
上尉慢慢地转过身来。那是米开尔,站在昏暗的房间里,象个快活的幽灵。“你这个傻瓜,”他说,“把什么都弄糟了。你画那些十字架干吗?”
“那是座医院,”米开尔说,“村子里有医院,医院上面有红十字,美丽的红十字,不是吗?”
“我差点儿受到军法审判。”
“这是我的错,”米开尔说。“我喝醉了。”
“我得负责。”
“我做的事怎么让你担当责任?不过一切都过去了。休身体好点儿了吗?”
“瞧,我猜想是那些十字架救了你的性命。”
“我可不这么想,”米开尔说,“我在回想我们当战俘时那些好心的红十字会人员。”
“啊,你给我住口,住口,住口。”
“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上尉在黑暗中看见米开尔拿着一幅画。一个背婴孩的黑人妇女,似乎在斜对着画框外微笑。
米开尔说,“你不喜欢光圈,这回不画光环。这是专为上尉画的,不是圣母。”他笑了起来,“你喜欢么?这是给你的,为你画的。”
“该死的!”上尉说。
“你不喜欢吗?”米开尔说,他伤心极了。
上尉闭上了眼睛。“那么你接下来准备干些什么呢?”他厌倦地问。
米开尔又笑了起来。“将军太太潘纳赫斯特夫人要画一幅穿白色礼服的画像,我画了。”
“你该为此感到荣幸罗。”
“那个蠢货,她以为我挺高兴。他们什么都不懂——原始人,野蛮人。上尉,你不是的,你是我的朋友。不过那伙人什么也不懂。”
上尉安静地躺着,胸中积聚着一团怒火。他想起将军的妻子。他不喜欢她,但对她十分了解。
“这些人,”米开尔说,“他们不识好画和坏画。我画啊,画啊,随意涂抹。有一张画,我看着心中直发笑。”米开尔笑出声来。“他们说,他是米开朗琪罗②。就是这个,他们杀我的价,米开尔——米开朗琪罗——真可笑,不是吗?”
上尉一声不吭。
“不过我为你画这幅面是要让你记得我们造那村庄时度过的好时光。你是我的朋友,我会水远元得你的。”
上尉斜着眼睛凝视画中的黑姑娘。她对他微笑着,一半天真,一半怨恨。
“滚!”他突然说。
米开尔走近一点,俯身看上尉的脸。“你要我走?”他难过地说。“你救了我的命。那天晚上我真是个傻瓜。我在想着对圣母的奉献——我是个傻瓜,我自己也这么说。我醉了,我们喝醉时都成了傻瓜。”
“从这儿滚出去!”上尉又说。
白色绷带依然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向下一鞠躬。
米开尔转身向门口走夫。
“把那幅该死的画也拿走。”
一阵沉默。接着,在幽暗之中,上尉看见米开尔朝那幅画走去,白色的脑袋十分恭敬地鞠躬。米开尔挺直身子立正,一手拿着画,一手僵直地垂在一边,向上尉敬礼。
“是的,先生。”他说完就转身带着画走出门去。
上尉静静地躺着。他感到——他感到什么呢7他肋骨下面有些疼痛,呼吸起来很难受。他明白他十分痛苦,是的,一种可伯的痛苦感正侵慢地充塞胸间。他感到痛苦是因为米开尔走了。在上尉一生中,从来没有象那声嘲弄似的“是的,先生”使他更痛心的了。从来没有。他默默地转身面对墙壁流泪,但是悄悄的。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怕护士们听见。
注释:
①赞比西亚现为莫桑比克的一个州。
②米开朗琪罗(1415-1564)意大利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米开尔这名字和米开朗琪罗同一个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