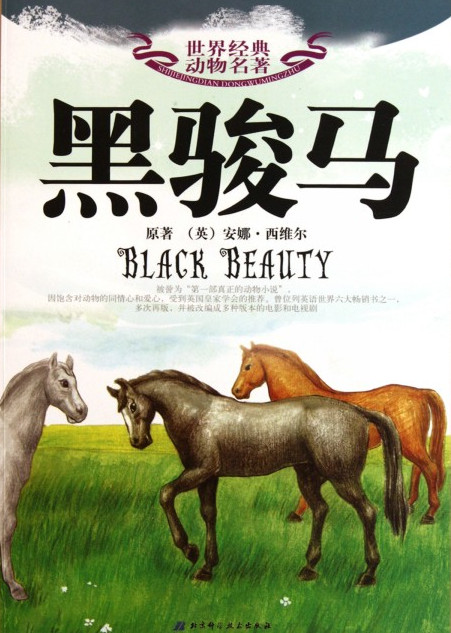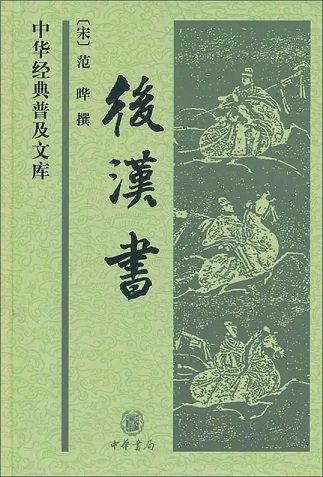在经过简单的思索之后,卡米拉很爽快地答应了阿曼达的邀请,同意出席明晚由她安排在博卡区一家酒馆的重逢会。她只所以会有些犹豫,当然主要是出于害怕见到阿尔弗雷多。然而世事总是喜欢与人作对,当她驱车到达时,出车门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其实在她刚停稳车子时就觉得一个人很眼熟。他还是那么瘦削利落,一身正式的黑西服穿在他身上并不觉得有一丝拘谨。她明白,他总是能找到那个最合适自己的东西。如果可以推而广之的话,她自己也是属于这一行列的,并且是在最为正确的时间,最为正确的地点为他而存在。当境随事迁,她也就淡出了他的生活。是的,现在,当她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她突然明白了在那个时刻离开他是多么的正确。
整整二十年了,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她首先认出了他,然后径由他走进那个她也要进入的酒馆。现在她还不愿意与他单独会面。到酒馆内之后,一切都会适时开启,这像两个人跳的探戈,隐秘而炽烈。
卡米拉并没有特别的期待过他的到来,尽管她曾希望过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要阿尔福雷多还活着,阿曼达几乎一定会邀请他。这么说并不是在暗示阿曼达和阿尔福雷多之间有多么亲密,而是出于卡米拉自己有些固执的个人想象或是预感,而她的预感又总会灵验,让她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她所喜欢的博尔赫斯那些动人的小说世界里。
今天的卡米拉同样也是一袭黑色装束。她想要实现自己多年来的一个愿望:穿着男士的装束与阿尔弗雷多跳一支探戈舞。往常,在那些二十年前的激情岁月中,他们总是把跳探戈当作一种仪式,必须有统一的着装才显出庄重。于是,每次卡米拉都是身着红裙子,将头发挽成发髻,显得高贵而典雅,犹如斗牛场上的斗牛士。而身着深色服装的阿尔弗雷多就是她的强悍对手。每次跳舞,他们之间都只能有一个赢家。他们用自己仪式性的死亡为观者呈现一场美轮美奂的高超探戈表演。而表演的结束通常又会是另一场战斗的开始,在那个战场上,她成了毫无疑问的猎获物与战利品:整个过程有如对古代战争的完美模仿。她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阿尔弗雷多对自由的看法。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她看得出来阿尔弗雷多依然固守着自己的自由观——那样贴身的西服不可能来自哪一个女人的挑选,而只可能是他对自我苛求的结果。
进入酒馆,一股暖流顿时将她包围。柔和的灯光下,是一些同样柔和的脸,一起迎向刚进来的卡米拉。
“Bravo!”他们的欢呼声又一次将卡米拉置于斗牛士的位置上,尽管她少了那块红布。
虽然对回首往事有些不情愿,卡米拉还是很自然地对大家笑笑0在座的有一半是她曾经认识的,还有另一半,年纪和她一般大的大概是当时她还没机会认识到的,毕竟当时她走得有些匆忙;其他年纪小一些的大概就是这里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像她和她当时被认为的那样。
她走到他们中间,确信自己的步态足够优雅,足够自信,因为刚才打招呼时,她刻意没有去看他。要做到这一点很简单,你只需让自己的目光避开光线最暗的地方就行:不是他的衣服吸光,而是他本人吸光。至少在她看来,他是一处黑暗的所在,她曾经想要探到黑暗的尽头,后来才发现这简直就不可能,你只会被他的黑暗淹没,然后当你有机会到达它的尽头时,你也许早已经窒息了。大概连他自己也探测不出自己的深度,就如恶魔对自己恶的属性并不知情一样。
然而在坐定之后,她再也无法强制自己的目光。在阿曼达给她递杯子时,她扫了一眼阿尔弗雷多。这样,一个完整的阿尔弗雷多又再次回到她身边,尽管她始终觉得他未曾远离。他的情况也确实如她经常想象的那样,这让她更坚信自己的感觉,并有理由相信她为他这二十年所作的种种设想最后都会在与他的进一步沟通中上升成为现实。她微笑着看了看酒馆边上的一小块空地,红色木质地板泛出撩人的诱惑。
这是一次不太正式的见面会,为了怀旧,为了认识新人,为了在某个看来不是太严肃的问题上达成相对上的一致。你甚至不必赞成,但只要不站出来反对就行。这种氛围对卡米拉而言是再熟悉不过了。二十年前的那些日子里,聚会也通常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结束之后,大家总会让她和他伴着酒馆内即兴的米隆加跳上一支。这样的场面通常会引起很多人的围观,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没有人会想到和大家融到一起的一伙人会在做着什么密谋活动。他们甚至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如邦乔们说的江湖黑话,这套话语系统可以确保他们即使在别人在场时也能就某些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不过所有人都明白有些事是一定要发生的,否则便不足以证明他们所从事的可以被冠以“事业”一词。比起其他小组来,他们这个小组所遭受的打击可以说是很小的,要不然今天晚上出席的成员里,老成员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例。
卡米拉和阿尔弗雷多就是在那次事件之后分开的。
而在那之前,他们之间就已经有了很深的裂隙,只是除他们两人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察觉罢了。或者准确点说,早在阿尔弗雷多挽起卡米拉的手跳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支舞时起,这一裂隙就已经存在了:不论他们贴得多么紧,配合得多么默契,他们之间总是存在一丝差异。他们也似乎从伴奏的音乐中听出了些许悲剧的味道——在音乐激情流畅的旋律背后,隐隐有一种急迫的不安全感,好像一开始就在抗拒着自己的结束。可能就是出于对这一共同印象的挑战,在他们的第一支舞过后,他们变成了相互的所有物。
那次事件之后,卡米拉和阿尔弗雷多先后离开了阿根廷,各自走向不同的世界。像两个有意要避开对方的仇敌,他们都尽量远离对方,不去打探对方的情况,他们都把那次事件当作了一个天赐良机,可以以此作为借口反身不顾地走开,之后的恐怖形势也为他们的杳无音信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解释。同时,所有这些不明不白的客观条件也并不有损于他们日后见面后的感情——尽管他们各自也许都心知肚明。
再次相遇的问题在他们离开阿根廷那一刻起就已经作为一个必定要发生的事件提到了他们的正常日程上来。他们对这件事的确信与其说是出于对自己所从事事业必胜的信心,毋宁说是出于他们对探戈舞曲本身所蕴含悲剧意味的深切领悟——就这样分开在任何人看来都有些糊糊涂涂,就像那次他们不明不白地遭到重创一样。
卡米拉在小组中的角色不仅仅是Tango Queen那么简单,在某些情况下她还会成为组织者,一个中心议题的提出人或倡导者:她灵动犀利的目光总是在向别人证明自己见解之独到,并让所有人为之震慑,包括她的阿尔弗雷多。这个称呼来自一次秘密集会中她的一次发言。在那次发言中,她似乎是有意将“我的阿尔弗雷多同志”误说成“我的阿尔弗雷多”,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甚至没有时间去震惊或是错愕,因为她的一如既往地演说家姿态暂时将所有与聚会无关的想法排除在外。然而当然,只有卡米拉本人明白当时自己的真正想法:只要有阿尔弗雷多在,她的所有言行就只是一场表演,一次挑逗,更露骨地说,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前戏。
阿尔弗雷多的出现于卡米拉而言完全是生命中的偶然。几乎从所有方面来看,阿尔弗雷多都应该是自己小组中的中坚力量,于是他的远道而来就成了一个谜,除非是更高一级的组织选派他到卡米拉所在小组的。有段时间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可疑分子进行了全面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卡米拉于他就成了一张通行证,他挽着她可以在这个新的小组中自由出入,他的发言也变得掷地有声起来,整个小组也如他和卡米拉的感情一样如日中天。
小组的光芒终于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而且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阿尔弗雷多似乎有过这样的经历:被追捕,然后是流亡。但这些对卡米拉而言却都是第一次。她的镇定又一次让阿尔弗雷多感到震撼:她让他明白自己是和他彻底一样的人,信奉自由,不可能被征服。当其他小组成员忙着在自己的脸上牢牢地贴上秘密小组成员的标签时,正与阿尔弗雷多跳舞的卡米拉流露出相当不耐烦的情绪,并适时地随着探戈舞曲的中断爆发出来。她很愤然地坐到一把椅子上,嘴上旁若无人地骂着:“我们实在不该来这种鬼才喜欢的地方。我们应该去阿瓜布拉卡,或者是埃斯塔多斯。总之离这里越远越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就像市中心那块高高竖起来的石头一样喜欢出风头。”
“那可不是一般的石头,尊贵的夫人,那是方尖碑。”一名穿着便衣的暗探到他们边上不动声色地说,“可否请您出示一下有效证件。我们份内差事,请原谅!”
“是吗?”她边忍住笑边说,脸对着自己的阿尔弗雷多,“他刚才称呼我什么?”
“夫人。有错吗?难道您不是圣罗莎城的卡米拉夫人吗?”阿尔弗雷多马上接着说道。
“对,不错,圣罗莎城有名的卡米拉夫人携新欢阿尔弗雷多于首都彻夜狂欢。”她一边说,一边有开怀大笑起来,同时伸手去掏自己的证件,“也许明天一大早我那位远在美国料理生意的老可爱就会知晓这一切,最迟不会拖到晚上。你可以保证吗?”最后一句她是对着那名令人深恶痛绝的暗探说的。阿尔弗雷多看到她的目光被调整得恰到好处,准确的让他不得不怀疑他的卡米拉是否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高贵、风骚,对政治毫无兴趣,将男人狂野地分成两大类——对于她感兴趣的第一类用诱惑加征服的眼光来看,对于她不感兴趣的第二类就用鄙夷加征服的眼光。总之,她要征服所有的男人,不存在让她感到讨厌的男人,就像一只雌性动物不可能讨厌与自己同一种类的雄性动物一样。这样的女人对男人而言就是一种绝对的对立物,绝对的危胁。
阿尔弗雷多看见在卡米拉掏出自己的证件之前,那名暗探就已经被征服了,那是出自本能的被征服,不会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被征服,也不会让哪一种后天的责任感所冲淡,更何况他本人的责任感并不强烈。
“是的,卡米拉夫人,”暗探扫了一眼卡米拉的证件,马上又还给了她,“祝您接下来能玩得愉快!”这句话是对卡米拉的道歉,也是对她真诚的祝愿,他甚至不再去查验阿尔弗雷多的证件。他把阿尔弗雷多当作了卡米拉的一个所有物,一个地位明显高于他自己的卡米拉的所有物。
“你觉得可能吗?”卡米拉摊开双手,笑得有些咄咄逼人。
就这样,几个小组成员被捕了。在他们被带走之前,坐在椅子上的卡米拉用打趣的音调向他们高喊:“再见啦,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这段时间不要太长。”
时间仅停顿了一秒钟,紧接着,撩人的探戈又再次响起来。
“我们还可能再玩得愉快吗?”她的阿尔弗雷多问。
“当然。别忘了我是卡米拉夫人!”卡米拉甚至没有犹豫就站起身,把阿尔弗雷多拉向仅仅为他们准备的舞池。就是在那一曲舞中,卡米拉深切地体会到探戈那深深蕴含的悲剧性,那种孤独、无助,对将要失去某物的不可逆转的先见意识。当他们发现其他成员已经安全离开后,当乐曲戛然而止,阿尔弗雷多左手挽着卡米拉的腰,右手与她的右手紧紧相握,而卡米拉的左手轻轻的贴在他的左脸上,目光无限深情地望着他,猩红的裙子也在一瞬间停止了摆动。在轰鸣的掌声中,他们退了下来,精疲力竭。阿尔弗雷多看到卡米拉那将要忍不住的眼泪,就过去紧紧地抱住她,并开始吻她的脸。卡米拉在阿尔弗雷多的鼻息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第二天,卡米拉果真到了北部的边城阿瓜布兰卡,然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巴西。当她在飞机上向下观望那一望无际,浓得发黑的热带雨林时,她的阿尔弗雷多按照他们的约定也到达了埃斯塔多斯岛。在岛上,阿尔弗雷多感受了一夜的寒风,那来自南极的寒风。在几近于荒芜的岛上,他想起了卡米拉对他的一个形容:“有时你朝我走来时,就像是从南极吹来的一阵寒风。我的心会猛地紧缩起来,鼻子被冻僵了,吸不上一口气。但这种寒意又只有你的拥抱才可以驱散。中国人有把人分成水命和火命的,大概你我就是分属于这两种命吧。”当时他只是笑笑。等到他真的来到南极边上并被寒风吹拂时,他才真切的体会到卡米拉与他在一起时的复杂感受,也明白了前一天晚上她为何会演得那么出神入化,那完全是因为她一直就在自己敌人怀抱里的缘故。她内在的生活总是处于极端的对立状态,就像一团火,不停的动荡,动荡于革命的激情与爱情的激情之间。在这个游人占了人口大多数的岛上,人与人之间也像这里的温度一样冷漠。在这些人之中,阿尔弗雷多想,有哪些人是来体验人生的寒意的,又有哪些人只是来看风景的。第二天早上,他看到了一座冰山,在洋流的推送下孤独地驶向北方,驶向自己的死亡。
在那次分别之后,他们各自安静了二十年。
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还是有很多机会让他们再走到一起的。他们是同时代人,同为阿根廷人,一同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同一件事做着相同的努力。所有这些让他们的踪迹相互交叉,或者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他)刚刚辞别了某一个人,他(她)便跟着接踵而来,继续就同一个问题作更深入地探讨。而当被采访人谈到不久前的另一个采访者时,他(她)都会礼貌性的拘谨地笑笑,以免被采访者会把他(她)心中经常念到的那个名字说出来。
阿尔弗雷多和卡米拉,卡米拉和阿尔弗雷多,相互缺失的二十年,也是相互之间最为默契的二十年。不过两人在独自静坐时还是不太敢去揣测对方的近况,太过具体的想像总是会像极细的针一样扎痛人的神经。
美丽的阿根廷,这块让人魂牵梦绕的故土,终于重新打扮一新,以翘首以盼的姿态等待深爱着自己的人归来。
卡米拉和阿尔弗雷多几乎同时得到消息,开始了回归前的准备。卡米拉对此还有所保留,占自己此生一半时间的在外漂泊让她把自己的阿根廷也当成了一个暂时的寄居国。她不敢相信自己为她所做的努力会在某一天真的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成为别人可以分享的东西。虽说这就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但还是无法从理想的幻灭中打起精神来。理想在实现自身后就即刻自行死亡,这无疑是所有热爱革命的人的悲哀——卡米拉试图如此安慰自己,她当然知道其他的革命者不可能与她相仿。于是,她寄希望于新的阿根廷,寄希望于她的阿尔弗雷多,寄希望于更富有建设激情的国内生活。
阿尔弗雷多当然比卡米拉要现实稳重的多。他不单单为理想而生活,更为生活而生活,为一切美好的事物而生活。所以,他是怀着十分的信心坚定地回来的,并且希望就此安顿下来,为阿根廷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如果有挫折,那就坚强地挺过去。
这样,当阿尔弗雷多在聚会的酒馆再一次见到卡米拉时,他立刻认识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他同样安慰自己说,这可能是因为卡米拉刚刚回来,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环境。而当他接受卡米拉的有所掩饰的一扫过后,他就在自己心里骂自己混蛋,不敢正视现实,就因为这一现实会刺痛他。他明白,他的卡米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有关水与火的叙述也再一次响起,也许她从来就没有成为他的——他不无悲哀的想。同时他又有些释然地告诉自己,当时让她离开自己的决定是对的,自己后来所做的一件事也同样是对的——他们是不同世界里的两个人。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好友阿曼达用不太能激发听众好奇心的语调提到了他们,当然是将重心放在了他们所跳的探戈上,一切都回到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光景。
听到组织者的介绍后,卡米拉和阿尔弗雷多会意地笑笑,并同志般坦诚地看了看对方。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好像今天的议题不是之前大家刚才讨论的内容,而就是她和阿尔弗雷多的事。作为当时小组的核心成员,作为同在国外为阿根廷的现在而努力工作的两个人,作为曾经的恋人,他们理应得到如此的礼遇。但他们两人此时却又真的不愿。
然而当卡米拉从阿尔弗雷多的微笑中也察觉到那种悲剧意识时(尽管他的这种意识来源与她的有根本的不同),她不禁有些兴奋起来,这种兴奋让她知道自己对阿尔弗雷多的爱依然炽烈,并且欣喜地感到他对自己的理解,那来自探戈深层意蕴的理解。于是她不禁又一次朝他笑笑,告诉他,只要努力,我们可以把悲剧变为喜剧的。
所有的人都起立,小乐队在他们的示意下演奏起来。这是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卡米拉曾在许多个夜晚,在不同的国家倾听他的作品,这个像他们一样孤独地坚守自己理想的人的作品。他是阿根廷的骄傲,过去是,现在也是,他比他们更能体现阿根廷精神;他的作品让人相信,之前的阿根廷和现在的阿根廷同为一个阿根廷。
很显然,阿尔弗雷多对这首曲子也很熟悉。他和卡米拉,这对探戈舞的绝佳组合,在阔别二十年后又第一次跳起舞来。他笑着看看她穿的和自己一样的深色裤子,表示对她独立的承认。他们面对面站着,等待那个合适的音符,突然地分开,旋转,相互顾盼,面无表情却又内心炽热如火,脚下的嗒嗒声应和着皮亚佐拉的琴声。对分离的抗拒,对时光的抗拒,对失意的抗拒,所有的抗拒都在述说着自己的悲惨身世,因为它知道一切都将无法挽回,自己只是用华丽的语言来讲述一个已经发生的凄惨故事。即使是对人人向往的自由,探戈也是弥漫着不可遏制的悲哀。
他们就这样旁若无人的跳着,如同在密室中做爱的两个人,难舍难分,抗拒着乐曲最后一个音符的到来,只有在音乐的掩护中他们才各自成为相互对等的对方的所有物,才能将其他人阻隔在外,才能最深地抵达对方的灵魂,那个以哀叹的音乐为底色的赤裸裸的灵魂。
终曲还是到来了。卡米拉一只手钩住阿尔弗雷多的脖子,一只脚反向钩住他的腿,把自己半吊在空中,陶醉地停留在他们的世界中不舍得出来。他们听得出来众人掌声中那种如释重负的味道,好像是对窥探的自我谴责。
“爸爸!”
一声清脆的喊声过后,一个小女孩笃笃笃地跑到他们面前。阿尔弗雷多把卡米拉放开,抱起小女孩。
刹那间,卡米拉崩溃了。
小女孩的母亲走进来。
“妈妈!”小女孩幸福地喊着。
母亲对小女孩笑笑,然后转向卡米拉:“你好,很高兴能见到你。”
“啊,您好!”卡米拉回答地有些生硬,她的目光在惊恐地寻找阿曼达。
“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二十年后卡米拉第一次听到她的阿尔弗雷多说话,“这是我女儿卡米拉,这是——”
“我是小卡米拉的母亲蕾蓓卡。他还是不愿意结婚。”蕾蓓卡接着说,与其说是在帮助阿尔弗雷多,不如说是在更深地刺痛卡米拉: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还”字简直就是对卡米拉的一种羞辱。但又正是这一羞辱,让卡米拉再次坚强起来。
“小卡米拉看起来很聪明呀!”卡米拉用一只手去捧小卡米拉的小脸蛋。
“就像她母亲一样。”她的阿尔弗雷多和善地说。
“Jet'aime maman.”小卡米拉高声喊了一句。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聚会总的来说好像还算圆满。
“我们也回去吧,已经凌晨了吧。”当只剩下她和阿曼达之后,卡米拉首先开口说道。
阿曼达朝她看了看,笑了笑:“好吧。”
两个人相伴着来到外面,才发现大街上早已聚集了一支不算太长的队伍,伴着高音喇叭传送出来的探戈边跳边向前行进。
“啊,想起来了,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呀!你看,这么早就跑出来庆祝国庆了。”阿曼达兴奋地说。
卡米拉也想了起来,苦笑了一下,看着年轻人手里举着新任女总统的漂亮画像——在国外时卡米拉曾见过她两次。
她们避开热闹的庆祝人群,各自钻到自己冷冰冰的汽车里。卡米拉木然地坐着,想象着她和阿尔弗雷多不可能再继续的,结局为悲剧的爱情。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活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而是生活在硬邦邦的现实中。
生活是谁也无法涵盖的,卡米拉想,怎么当时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让她做小卡米拉的教母呢?“就像她母亲一样。”自己为什么就没有那么聪明,允许阿尔弗雷多有自己的自由呢?爱是分享,而不是征服。
卡米拉发动汽车,慢慢驶过人群。那些她深爱的旋律远去了。爱就是对责任勇敢的承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人这么喜欢被哀愁浸泡透了的探戈的原因。
还是叫米隆加更有味道,她想,虽说自己不是寄身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但却寄身于他生活过的国家中。真正理解探戈的人都会是孤独的,孤独的成为一个个个体。卡米拉相信,此时的阿尔弗雷多也同样是孤独的。
前方是灯光辉映下高耸的方尖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