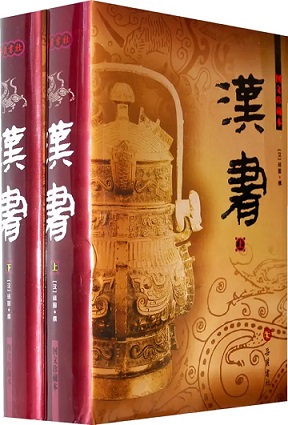星期四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尸体。今天是星期天,无事可忙。天气很热,没想到英格兰也能这么热。临近中午,我决定出去走走。我站在屋外,迟疑着,一时拿不准该往左还是往右。查理猫在街对面一辆汽车底下。他肯定是看见我的腿了,只听他叫道:
“喂,怎么样?”
这类问话总是让人无从回答。我愣了几秒钟,支吾道,“你好吗,查理?”他爬了出来。阳光从我站的街这边径直射入他的双眼。他伸手搭住眼眉,说道,“你这会儿是要去哪儿呢?”我再一次被问住了。适逢星期天,无事可忙,天又太热……“出去”,我说,“走走……”。我走过去打量着汽车引擎,尽管对此我一窍不通。查理是个对机械很在行的老家伙。他帮街坊们和他们的朋友修车。他从车边兜过来,两只手拎着一套沉重的工具。
“这么说,她死了?”他站在那儿用一块废布擦着一把扳手。自然,他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想听听我的说法。
“是啊,”我对他说,“她是死了。”他在等我继续说下去。我斜靠在车的一侧。车顶烫得摸不上手。查理牵着话题,“你最后见到她在……”
“在桥上,我看见她沿着运河跑。”
“那你看到她……”
“我没看见她掉下去。”查理把扳手收进工具箱。他正准备爬回汽车底下,同时以这种方式宣告谈话结束。我仍然在踌躇该走哪条路。在消失之前查理说道,“作孽,真是作孽。”
我朝左边走去,因为我恰好面朝那边。我走过几条由女贞树篱笆和滚烫的泊车分割成的街道。每条街上都闻到同一股煮午饭的味道,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同一套电台节目的声音。我碰见几条猫狗,却很少看到人,就算有也都隔着一段距离。我脱下外衣搭在胳膊上。能依树临水当然最好,可在伦敦的这一区没有公园,只有泊车位。倒是有一条运河,褐色的河水在工厂之间穿梭,流经一处废品站,小简就淹死在里面。我走到公共图书馆,尽管一早知道今天它不开门,我还是喜欢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现在我就这么坐着,坐在一块不断萎缩的荫影里。一阵热风吹进街道,卷起我脚边的杂物。我看见路中央吹起一张报纸,是《每日镜报》的某一页,头条标题露出一部分“……的人……”。四下无人。街角传来冰激凌车的叮当声让我意识到自己渴了。铃珰奏出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一段,在旋律当中突然嘎然而止,好像被人踹了一脚。我快步走过去,可是当我走到街角时它已经不在了。不一会儿又传来它的声音,听上去分明已走出了很远。
往回走的路上我一个人也没碰见。查理已经进屋,他刚才修理的那辆车也不见了。我从厨房水龙头里接了点水喝,不知从哪儿读到过,伦敦的水龙头里放出来的一杯水相当于已经被五个人喝过了。水里一股金属味,这使我想起他们停放小女孩的不锈钢台,她的尸体。晚上七点我要去见女孩的父母,不是我想见,这是警官的主意,帮我做笔录的那个。我本该强硬一点,可他在我身边转悠,让我害怕。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用手抓住我的肘部,这大概是他们从警校里学来的伎俩,用以获得所需的权威。我正准备离开那幢大楼时他叫住了我,把我押到一个角落。我没法挣脱,除非与他搏斗。他声音低哑,话不失礼却语锋迫人,“你是女孩死前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他把死字拖得很长。“她的父母,嗯,当然想要见见你。”他握住我的时候就有那种权威,话中夹杂的暗示让我害怕,不管他其实是在暗示些什么。他那双握住我的手又紧了紧,“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会来的。你和他们差不多算是隔壁邻居吧?”我看向别处,点了点头。他笑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尽管如此,这也算是件事,一次见面,好歹让这一天有点意义。下午晚些时候我决定洗个澡,打扮一番。大把时间有待消磨。我翻出一瓶从没打开过的古龙水和一件干净的衬衫。放洗澡水的时候我脱掉衣服,凝视着镜子里面自己的身体。我是个长相可疑的人,我知道,因为我没有下巴。尽管说不出缘由,在警察局里甚至还没等我作陈述他们就开始怀疑我了。我告诉他们当时我站在桥上,我从桥上看见她沿着运河跑。那个警官说,“哦,那倒是相当巧合,不是吗?我是说,她和你住在同一条街上。”我的下巴就是我的脖子,它们不分彼此,滋生怀疑。我母亲也长成这样,直到我离家之后才发觉她形容怪异。去年她死了。女人不喜欢我的下巴,她们从不靠近我。我母亲也一样,她从未有过朋友,无论去哪儿都是一个人,哪怕是节日。每一年她前往利特尔汉普顿的时候,都是独自坐在甲板的椅子上,面朝大海。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尖瘦而乖戾,活像一条小灵犬。
在上星期四见到简的尸体以前,我未曾对死有过什么特别的想法。有一回我见到过一条狗被碾死,车轮从它头颈上轧过,眼珠迸裂。可我无动于衷。我母亲死的时候我躲得远远的,多半出于冷漠,也因为厌恶我的那些亲戚们。对她死去的样子我也没有好奇心。我想我自己的死将会和她一样,苍老而瘦削地躺在花簇中。可那时我并没有看见尸体。尸体把生和死摆在了一起。他们带我走下石阶来到一条走廊,我原以为太平间会独自矗立,实际却在一幢七层高的办公大楼里。我们是在地下室,我能听到楼梯脚传来打字机的声音。警官已经到了,身边还有另外两个穿制服的,他拉开弹簧门让我进去。我没料到她真的会在里面。现在我想不起来当时我以为会是什么,照片?也许,可能还会要签一些文件。我没有认真考虑过整件事。可她真的在里面。五张高高的不锈钢台排成一列,天花板上荡下的长长的链条上悬着带绿色铁皮罩的荧光灯。她在离门最近的那张台上,仰躺着,手掌朝上,双腿并拢,嘴张得很开,眼睛睁得很大,非常苍白,非常安静。她的头发还有一点潮。她红色的裙子看上起好像刚刚洗过。身体散发出淡淡的运河的气味。我猜要是你见惯尸体,比如那位警官,这场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她右眼上有一小块瘀伤。我忍不住想要摸摸她,但我意识到他们就在咫尺之外盯着我。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像是在卖二手车似的轻巧地说:“只有九岁。”无人答腔。我们都看着她的脸。警官手里拿着一些文件转到我站的台子这边。
“好了吗?”他说。我们由那条长长的走廊往回走。上楼后我签了一些笔录,表明当时我正横过铁道线上的人行天桥,看见一个小女孩——经辨认即楼下那位,在运河边的纤道上奔跑。我没怎么在意,可不一会儿,我看到水面有一团红色的东西沉下去不见了。由于我不会游泳,于是叫来了一位警察,他朝河面端详良久,说什么也没有。我留下姓名和地址然后就回家了。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用绳索把她从河底拉了上来。我一共签了三份。完事后我久久没有离开那幢大楼。在其中的一条走廊里,我找了张塑料椅子坐下。在我对面,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见两个姑娘正在办公室里打字。她们见我在朝她们看,互相嘀咕了几句,笑了。其中一个走出来,笑着问我是不是被约见的。我跟她说我只是坐坐,想点事。那女孩回到办公室,靠过身去告诉她的朋友。她们不自然地扫了我一眼。她们在怀疑我什么,和其他人一样。我倒并没有认真回想楼下死去的女孩。她的影子在我脑子里有些迷乱,活着的和死去的,我努力不去理会它们。我坐在那里一下午只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想去。那两个姑娘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后来我走是因为所有人都回家了,他们得锁门。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幢楼的人。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穿戴好。我先把黑色西服烫了一遍,黑色在我看来是恰如其分的,然后我挑了一条蓝色的领带,因为我不想黑过头。可就在差不多要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回到楼上把西服、衬衫和领带全都脱了下来,我对自己的一番精心准备感到厌恶。为什么我那么迫切地想获得他们的认可?我又换上了刚才穿过的那套旧裤子和运动衫。我后悔洗了澡,只好拼命地把脖子后面的古龙水洗掉。可是还留着一种味道,那是我洗澡时用的香皂的气味。星期四我用的就是同一块香皂,那个小女孩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身上有股花香。”我出门恰巧走过她家的小院子。我没理她。我尽量避免和小孩说话,因为面对他们很难拿准腔调,还有他们的直截了当也令我困扰,让我无所适从。这个孩子以前我见过很多次,通常自己一个人在街上玩,或者看查理干活。她从院子里走出来跟着我。
“你去哪儿?”她说。我还是没理她,最好她快点失去耐性。况且我也没想清楚要到哪儿去。她又问我,“你要去哪儿?”
我停了一下,说,“不关你的事。”她跟在我的正后面,我正好看不到她。我感觉她在模仿我走路,不过没有转过身去看。
“你是去屈臣氏店吗?”
“对,我是去屈臣氏。”
她走上前和我并排。“可是今天它关门,”她说,“今天星期三。”我没答话。当我们走到街尾拐角的时候,她说,“你到底要到哪里去?”我头一回如此近距离看她。她细长的脸,眼睛大而哀怨,细密的棕色头发用红色的橡皮筋扎成一束,和红色的棉布裙子相衬。她有一种诡异的美丽,近乎不祥的意味,像莫迪利阿尼画中的人物。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出去走走。”
“我也要去。”我没说话,于是我们一起朝商场方向走去。她也一声不吭,落在我后面一点点,好像在随时等我通知她向后转。她手里玩一种这一带孩子都会的游戏。几根弦两头各拴着一个硬球,用手操动,硬球相互弹击,就能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有点像足球啦啦队手里的小摇旗。我觉得她这么做是在有意取悦我。这样赶她走就变得更加困难。加上我已经好几天没和任何人说过话了。
当我重新换好衣服下楼的时候已是六点一刻。简的父母也住在街这边,与我相距十二栋房子。鉴于我提前四十五分钟准备完毕,我决定出去走走消磨些时间。天色昏暗。我站在门口思忖着最佳线路。查理在街对面修理另一辆汽车。他看见我了,于是我不自觉地朝他走过去。他抬起头,但没有笑。
“这时候你要去哪儿?”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个孩子。
“透透气,”我说,“透透傍晚的空气。”查理喜欢打听街坊的八卦。他认识这一带每一个人,包括所有小孩。我经常看到那个小女孩和他在一起。最后一次是在给他递扳手。由于某种原因,查理因为她的死而迁怒于我,他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个事。他想从我这儿打听详情,却又不好直接问我。
“去见她父母,嗯?七点钟?”
“对,七点钟。”他还想听我继续说。我绕着车转。福特黄道带,又旧又笨,锈迹斑驳,和这条街相得益彰。这是街尾开小店的巴基斯坦人家的。天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店取名屈臣氏。他们的两个儿子是被街边的蛊惑仔揍大的。他们正在攒钱准备回白沙瓦。有一次我去他店里的时候,男主人这么告诉我,他正准备携家回乡因为伦敦的暴力和鬼天气。查理隔着屈臣氏先生的车对我说,“她是他们的独生女。”他像是在控诉我。
“是啊,我知道。”我说,“真作孽。”我们绕着车转。查理接着说,“报上登了。你看了吗?说是你见到她沉下去的。”
“确实这样。”
“那你抓不住她吗?”
“不行,她沉下去了。”我绕着车慢慢越转越开,而后顺势溜走。我知道查理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的背影,不过我没有回头去迎合他的怀疑。
到街尾我假装抬头看飞机朝背后瞟了一眼。查理站在车边,双手叉腰,还在注视着我。他脚边蹲着一头黑白相间的大猫。我一瞟而过后便拐入街角。六点半。我决定到图书馆去混掉剩下这点时光。这和我先前走的那条路一模一样,不过街上游荡的人多了。我走过在街边踢足球的一帮西印度孩子。他们的球朝我滚过来被我抬脚跨过。其中一个小一点的男孩出来捡球,其他人则站在原地等着。当我和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所有人都默默地望着我。我刚一走过,有个家伙沿着路面扔来一块小石头想打我的脚。我没有转身,甚至根本没有看它一眼,就干净利落地用脚把石头踩住。我的动作如此漂亮纯属巧合。他们爆发出笑声,并鼓掌喝彩,刹那间的飘飘然几乎让我以为转过身就能和他们一起踢球。球又回来到他们中间,比赛重新开始。短暂的片刻就这样过去,我继续朝前走。我的心跳由于刚才的兴奋而加快,甚至到了图书馆坐在台阶上以后,我还能感觉到太阳穴上脉搏的颤动。对我而言这样的机会十分罕见。我不太见人,实际上我只跟查理和屈臣氏先生说话。我和查理说话是因为我一出门他总在对面,永远都首先开口,只要我想离家就避不开他。而与屈臣氏先生我则是说得少听得多,我听是因为我得到他店里买日用品。星期三能有一个人和我一起散步也是一种机会,哪怕是个闲极无聊的小女孩。尽管如此,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她对我天真的好奇使我感到满足,她吸引了我,我想要她成为我的朋友。
不过一开始我很不自然。她走在我后面一点,手里拨弄着玩具,我敢肯定,还在我背后指手画脚,玩小孩的把戏。后来我们上了商业街,她就走到我身边。
“你怎么不上班?”她说,“我爸爸除了星期天每天都要去上班。”
“我用不着上班。”
“那你已经有很多钱了吗?”我点点头。“真的很多吗?”
“是啊。”
“那你能给我买点东西吗,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我愿意的话。”她指着一间玩具店的橱窗。
“买一件,求你啦,去嘛,随便一件,去嘛。”她吊在我的胳膊上摇来晃去,做出贪心的模样,想把我推入那间店。甚至从我孩提时算起,都从来没有人如此主动地触摸我这么长时间。我只觉得胃里一阵寒颤,脚下不稳。我口袋里还有点钱,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给她买点东西。我让她在门外等着,自己进店买了她想要的一个粉红色的光身洋娃娃,那是用一整块塑胶铸成的。可是她一拿到手好像就对它失去了兴趣。沿着这条街又走了一段,她要我给她买冰激凌。她在一家店门口站着不动等我买。这一次她没有碰我。我有些犹疑,不知该如何把握。可是此时我已经对她,以及她正在我身上产生的效力欲罢不能。我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进去给我们俩买冰激凌。她显然对礼物习以为常。我们走远一点后,我用最友善的语气问她,“别人买东西给你你从不说谢谢的吗?”她轻蔑地望着我,薄而暗淡的嘴唇上涂着一圈冰激凌:“不。”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想让谈话的气氛变得友好些。
“简。”
“我给你买的洋娃娃呢,简?”她朝手里看了看。
“我把它放在甜品店了。”
“你不想要了吗?”
“我忘了。”我刚想开口叫她跑回去拿,可就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不愿意让她离开,而我们距运河已经那么近了。
运河是这附近唯一的一条蜿蜒水道。走在水边总能给人不同感受,哪怕是工厂区背后这条又黑又臭的水道。俯瞰运河的工厂大部分已经废弃,没有窗户。你沿着纤道可以走上一里半,通常一个人也碰不到。途中会经过一处年头久远的废品站。直到两年多前,都一直有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守着这堆垃圾,他住在一间铁皮小屋里,屋外的木杆上拴着他养的一条硕大的德国牧羊犬。那狗已经老得叫不动了。后来铁皮屋、老人和狗一齐消失了,废品站的大门也随之封闭。久而久之,周围的篱笆全都被当地的孩子糟蹋殆尽,如今只剩下大门还没倒。废品站是这一里半路上唯一的景致,其余路段全都紧挨着工厂后墙。可是我对运河情有独钟,和附近任何地方相比,这里靠近水边没那么逼仄。和我一起默默走了一会以后,简又问我,“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走?”
“运河边。”
她想了片刻。“我不许到运河边去的。”
“怎么不行?”
“因为。”这时她略略走在我前面一点,嘴边的一圈白色已经干了。我的双腿发软,太阳的热力从路面蒸腾上来令我窒息。说服她和我一起走运河已经变成当务之需,这念头让我恶心,我扔掉手中没吃完的冰激凌,说,“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运河边走。”
“为什么?”
“那儿非常安静…什么都有。”
“有什么?”
“蝴蝶。”话一出口想收都收不回来。她转过身来,突然很感兴趣。蝴蝶不可能在运河边生存,臭气早就把它们熏跑了。不用多久她就会发现。
“什么颜色的蝴蝶?”
“红的……黄的。”
“还有什么?”
我嗫嚅道,“还有废品站。”她皱了皱眉头。我连忙说,“还有船,运河上还有船。”
“真的船?”
“是啊,当然是真的船。”这也不是我原本想说的。她停下脚步,我也跟着停下。她说,“如果我去,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不会,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不过在运河边你得一直靠紧我,懂吗?”她点点头。“把嘴巴上的冰激凌擦掉。”她用手背在脸上胡乱蹭了蹭。“过来,让我来擦。”我把她拉过来,左手扶着她的脖子。我舔湿了右手食指,就像过去我见过父母做的那样,沿着她的嘴唇擦拭。我从未碰过别人的嘴唇,我也无从经历这种快感。它令人痛苦地从小腹一路涌到胸口,堵在心头,仿佛两肋被重拳猛击。我重新舔湿这根手指,指尖带着粘稠的甜味。我再次擦她的嘴唇,可这回被她推开了。
“你弄疼我啦。”她说,“你按得太重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她开始紧挨着我。
要下到纤道上我们得先横过运河上的一座小桥,桥是黑色的,两边有高墙。走到桥中间,简踮起脚尖,想从墙头往外看。
“把我举起来,”她说,“我要看船。”
“这里看不到。”我还是用手揽住她的腰,把她举起来。她红色的短裙向身后翻起,我心口的涌堵再次袭来。她扭过头朝我叫道,“河水很脏。”
“一直都这么脏,”我说,“这是条运河。”我们沿石阶向下走到纤道的时候,简靠我更紧了。我能感觉到她屏住呼吸。通常运河向北流,可今天它静若死水。空气中没有一丝风,连水面上一块块黄色的浮渣,也纹丝不动。偶尔有一辆车从我们头顶的桥上开过,远处是市区的车水马龙。除此之外运河周围非常安静。天气炎热,令运河今天的气味更加浓烈。浮渣散发出的不像是化学品的味道却更似动物的体味。简嘟哝着,“蝴蝶在哪儿呢?”
“它们不远了。我们要先钻过两座桥洞。”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此时我们离开石阶已有一百多码。我极力怂恿她向前走,而她却想停下来。可是她又感到害怕,不敢离开我一个人跑回石阶。
“离这儿不远就能见到蝴蝶。红的、黄的,有时还有绿的。”我放任自己胡言,到此刻我已不在乎跟她怎么说了。她伸出手让我牵着。
“那船呢?”
“还要远一点。你会看见的。”我们继续往前走,我脑子里只想着如何把她留住。运河途经工厂、马路或铁道线时会由隧道穿过。我们经过的第一处隧道是一座三层结构的建筑,与运河另一边的工厂相连。那里和眼下所有工厂一样,空荡荡的,目光可及处窗户都已被打烂。走到隧道入口,简想把我往回拉。
“那是什么声音?我们别进去了。”隧道顶的凝聚水滴到运河里,空洞而怪异地回荡。
“那不过是滴水声。”我说,“瞧,你能一直看到对面洞口。”隧道里面的通道很窄,我只好让她走在我前面,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她在发抖。到出口处,她突然停下,用手一指。在阳光射进隧道口的地方,有一条砖缝中生出一朵花。看上去像是一种蒲公英,从一小撮草中冒出来。
“是款冬。”她一边叫着一边把它摘下来插在耳朵后面。我说,“我以前从来没在这里看到过花。”
“应该有花的,”她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有蝴蝶。”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默默地走着。简又问了我一次蝴蝶的事。她松开我的手,显得已经不那么害怕了。我想碰她,可是又想不出如何才能不吓着她。我想试着起个话头,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小道开始向右展开变得宽阔。在工厂和货仓之间,运河下一道弯旁边的开阔地,就是那个废品站。有一群男孩围立在一堆点燃的火边。他们像是一伙的,都穿同样的蓝上衣,剃平头。据我判断,他们正准备活烤一头猫。烟在他们头上凝固的空气中悬浮,在他们身后废品层层堆积像座山。他们把猫的脖子绑在过去拴狗的那根木杆上,猫的前肢和后腿也被捆在一起。他们用几块铁丝网做了个笼子架在火上。我们走过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扯着猫脖子上的绳子把它往火里拽。我拉住简的手加快脚步。他们十分专注,默不作声,甚至都无暇抬头看我们一眼。简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透过她的手我能感觉到她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他们要把猫怎么样?”
“我不知道。”回头望去,黑烟已使我难以看清他们此时的举动。我们远远抛离他们以后,小路再次贴着工厂的墙垣边。简快要哭出来了,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让她无法挣脱。其实这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哪里她敢一个人跑去的:沿原路回去要经过废品站,向前则正要走近另一个隧道。我不知道走完这段路将会如何,她会想要跑回家,而我只知道自己不能放她走。我发疯般地这么想。在第二个隧道的入口处简站住。
“根本就没有蝴蝶,是不是?”话音变成了哭腔。我只好跟她说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可她根本不听,开始哭。
“你撒谎,根本就没有蝴蝶,你撒谎。”她有气无力,可怜巴巴地哭着,想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我跟她讲道理可她不听。我用力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隧道。这时她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持续从隧道四壁反射回来,充斥我的大脑。我又拉又拽一直把她拖到隧道中央。突然间,她的尖叫被正从我们头顶开过的一列火车的轰隆声淹没,空气和大地一齐在颤抖。火车开了很久才通过。我抱住她的双肩,这回她没有挣扎,巨大的喧嚣声镇服了她。当最后一声回响消逝殆尽,她含混地说,“我要妈妈。”我拉开裤子拉链。我不知道在黑暗中她是否看得清伸向她的东西。
“摸摸它。”我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肩膀。她没有动,我又摇了摇她。
“摸摸它,快点。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要的其实十分简单。这一次我双手抓住她用力摇晃,叫道,“摸它,快摸它。”她伸出手,手指草草地从我体尖拂过。可这已经足够,我弯下身,到了,我射在了自己的手掌里。就好像火车,它持续了很久,将一切都喷泄到我的手上。所有那些我独自消磨的时间,所有那些我一个人走过的路,所有那些我曾经有过的想法,全都喷泄在我的手上。过后的几分钟,我依然保持着这种姿势,弯着身手握在前面。我的头脑变得清晰,身体放松,心无一物。我伏在地上往下探,伸到运河里去洗手。冷水很难把那玩意儿给洗掉,它像浮渣一样粘在手指上。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剥离。这时我才想起那女孩,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可不能让她现在跑回家,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我得去追她。我站起来,隧道口透进的阳光显出她的剪影。她恍恍惚惚沿着运河缓缓地走。因为看不清前面的路,我无法跑得太快,越是接近隧道口的阳光就越难看得清楚。简就快要走出隧道了,她听到身后响起我的脚步,回过头骇怕地尖叫了一声。她又开始跑,脚步马上跌跌撞撞。从我身处的位置很难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剪影一下子消逝在黑暗中。当我赶到的时候,她脸朝下躺在地上,左腿斜出路边几乎插进水里。她跌倒时撞着头了,右眼肿起。她的右臂向前伸展,差一点就能够着阳光。我弯下身贴近她的脸听,她的呼吸深沉而均匀。她的眼睛紧闭,睫毛因为哭过还是湿的。我不再想碰她,那已经从我体内喷泄出去进入运河了。我掸掉了她脸上的泥土,又掸了掸她背后的红裙子。
“傻姑娘,”我说,“没有蝴蝶。”然后我轻轻把她抱起,尽可能轻以免弄醒她,悄悄地慢慢地把她放入运河。
我通常坐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而不是走进去看书。外面学到的更多。现在我就这样坐着,星期天的傍晚,听我的心跳慢下来回到平常节奏。一遍又一遍我重新推演所发生的事和我应有的作为。我看见石头擦着路面飞来,我看见自己干净利落地用脚把它踩住,根本都没有转身。那时我本该转过身去,要慢,用淡淡一笑回敬他们的喝彩。然后我该把石头踢回去,最好是跨过石头,顺势向他们走去,那样,等球回来我就会和他们一起,变成其中一员。许多个傍晚我将和他们一起在街上玩,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也知道我。白天我可能在城里邂逅他们,他们会从对街叫我,走过来攀谈。比赛结束时有人走过来握住我的胳膊。
“那明天见……”
“好的,明天见。”等他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就一块儿去喝酒,而我也将学会爱上啤酒。我站起身开始缓缓地沿原路往回走。我明白我将不会参加任何足球比赛。机会渺茫,就像蝴蝶。你一伸手,它们就飞走了。我走过他们刚才踢球的地方,如今空无一人,我用脚踩住的那块石头还躺在路中央。我把它捡起来,放进口袋,才继续往前走,去赴我的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