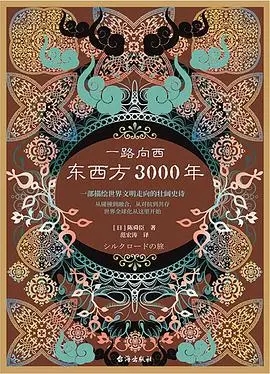龚祥瑞(1911-1996),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作者历时三年完成自传,并于成书后十六年、去世后十五年出版。作者在“后记”中声明:
“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威;更不想为所经历的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和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鳞半爪的感受。”
“最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斗争从“三反”、“五反”起不断“扩大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我在这里只能叙述我所遭受和接触的那一鳞半爪,好比倾盆大雨中的点点滴滴,以供后人品味,共享其中的是是非非。
01
挂牌游园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开始至1977年6月6日止,为期十年。我是从1966年6月18日起被隔离反省的,即与当时所谓“黑帮分子”在一起,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成了北京市民来校参观者起哄的对象。
有一天,我被造反派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黑帮分子×××”,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了“×”。敲锣打鼓,在校园内示众游行。观看热闹的群众中,有高名凯的女儿高苏(当时她是大一的学生),见我这个模样,笑不遏止。好像她正在告诉左右同学:挂牌游行的法律系教授是他父亲的好友。如果她父亲在世,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我这么想,毛泽东曾一度使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非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规定,而是人们自我选择的行动。本人并没有因挂牌游园这类举措而伤筋动骨,也不怨天尤人。高苏的笑声反而使我骤然感到这场闹剧非凡,滑稽可笑。
02
隔离反省
我们全系七八人被关在一个教研室里,夜以继日地写检查作交代,没完没了。当聂元梓名震全国的时候,北京市民蜂拥到了北大校园,群众要见见关在房里的黑帮分子,我想,大概是出于好奇吧。曾经一度是著名人士,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成了另一类人种,自然成了罕见的观赏品。一天四院(我系所在地)来了一群北京市民,他们高呼口号,敲打窗口,高喊:“黑帮分子滚出来示众!”确有人进入院内要打开房门,把我们一个个揪出去批斗。我们把门紧闭着,几个人躲在书桌下不敢露面;窗外的观众狂喊猛叫,要叫我们“出来,出来”!呼叫声越吼越大,敲门声越敲越响。我怕房门被踢开,与其被动揪出,不如主动向群众交代自己的历史较为上策。当时,我确实是相信群众的。这次运动是整走资派,是整当权派,像我这样历史上有问题的不过是陪绑者,关系不大;为了其他人的安全,不如让我出去转移群众的目标为上策。我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难友轻声说:“还是让我出去向他们交代,就将人群引向院子外面去了!”桌子下面所有的人都不同意,认为:“出去你这条命就没有了。”他们都怕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都不让我走。幸而,敲了一阵,群众见没有动静,也就转移阵地,往别处去了。一时平静下来,我们一个个又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那天中午晚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家里。
03
一身湿透
我们29名教师在42楼南侧,背上个个挂着“黑帮分子”的牌子,姓名上打了 “×”,伏在地上拔草,旁边有两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看管我们,数以千计的人围观,犹如动物园里的牲口那样,一个个成了被观赏取笑的对象。
这天中午,在拔草完毕解甲回家的路上,遇到外语系女教授俞大絪,我见她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低头走路,似有无言之苦在心头。我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感到被侮辱了,以往那种自信的神态在她身上消失了。谁知就在那天晚上,她服了安眠药自尽了。
在校园里拔草,是运动初期惩罚我们的一种办法。校园内凡有草的地方几乎全被我们这帮人拔了个精光。一天下了大雨,全身淋得湿透,衣服也还没换掉,红卫兵就把我们召集起来,谈谈雨中劳动的感想。好在是夏天,全身湿透的身子边谈边干了。大家谈的都是好话,有的说:“这阵大雨把我们身上的臭气都淋掉了!”有的说:“很痛快,好比洗了个澡!”有的说:“把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洗了一遍!”如此等等,引起红卫兵的笑声和赞赏。
“走吧,有收获就好!”
04
一次毒打
在展览稀有物质的同一会场上(即今25楼),原是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楼,有个60平方米的会场。那天或许是井冈山兵团召开批斗会。本无我的,我正在38楼应召交代问题以免挨斗的一项有意安排,不知怎的又被叫去参加。当我被带入会场时,系里的挨斗对象多半肉体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动弹不得。我不知道前因后果,只见前面是黑漆漆的人群,有站着的,有坐着的,群情激昂,不由分说。在这种气氛下,本能地低下头来,无可奈何地任人“摆布”了,连思维能力也丧失殆尽,唯有任人宰割。一阵眼花缭乱,只见一个青年举足猛然踢我一脚,并说:“我这双新皮鞋是专门买来踢你们这帮‘坏蛋’的。”这一脚踢在我的左腿上,其用力之大,已使我站立不稳,似乎立刻就要往后倒下了,竟然还敢“站稳”,那双黑色的崭新皮鞋准确地又在原来的部位上再来一脚,这次果然跌倒在地,混混然只闻一片打倒声,另外就是身旁躺在地上的人的微弱的呻吟声。不久就散会了,人群一个个呼啸而去,剩下来七八个挨打的人躺着起不来身。年轻些的陆续从地上爬起来,企图往外走,一个个勉强站起来走到过道上,还没有到楼梯就站立不住,个个又扶着栏杆席地而坐或半躺了下来,稍事休息想恢复体力。被毒打成这个样子,还是第一次。人们不能理解这是为了什么。人失去了思维。
我们眼前的打手难道是新中国培育出来的?不!人有时比野兽更残酷。
我们一个个一拐一拐从楼梯上半爬半走下楼时,有的就只能朝着校医院的方向走去。等我慢慢移走回到家里,脱掉鞋子和袜子,将裤脚筒卷起来时,才发现自己左腿上一块肉竟被踢了下来,四周皮肉都是青肿的。
这样的斗争看来是一个可悲的诱饵,作为治国之道并非一无所获,我活了那么多年,竟从未知道人间还有如此残酷的行动。只有通过掉了块肉才能取得这样有益的学问,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个体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正如邓小平这样的革命前辈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毁了两代人”。中国在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失去了十年!
05
开门办学——当牛倌
北大和清华响应林副主席的号令去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劳改农场。那里原是一个湖,湖底泥浆肥沃,有良田数百亩,并经劳改犯修缮,就是浩瀚的鄱阳湖建造渠坝填湖的稻田。
我被派到牛棚去喂牛。我们一共三个人,养六条水牛。每天早晨天亮就要拿着镰刀去割草,所以当寝室里熙熙攘攘批这批那时,我有权利先睡了,不禁感到这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时刻。
清早割青草,我特别注视着在石缝里抽芽发黄的小草,它铿锵有力地向上长。每天我都见到它长了上来,它渴望阳光,渴望露水,渴望根下的那一丁点儿的土壤。看到了生命自身的力量,我对“教育革命”——把我们这批师生弄到劳改农场来种稻、喂牛,有了微妙的感想,我困惑不解。到底是毛泽东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我躺在草地上沉思着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想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的焦点是:“红”与“专”,即政治与读书的关系,也就是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早就提出过的问题。
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笨。张春桥的名句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这些是与我早已接受的思想恰好相反的啰!
毛泽东告诉学生上课时可以睡觉,考试中可以作弊。他把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挑粪,所有这些和我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当他回顾自己上世纪20年代走遍湖南全省去寻找造成人间苦难悲剧的根源、谈到他自己那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说得好,即使已经开办了十万所政法学校,他们能像农民协会那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男女老少,直到最僻远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受到同样的政治教育吗?毛泽东说,我认为他们办不到。
这些刺耳的、扣人心弦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凡是不放过孔子的诗书济世观念的人,恕难不信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它不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吗?我们教了几年的书,其所起的影响和所造就的人才,岂能与毛泽东的同日而语?岂不是恰恰相反吗?
湖上的凉风吹在我脸上时,我感到困惑,感到恍惚,终于陷入了梦境而不能自拔了。
但是我毕竟看到了,“教育革命”对70年代的一般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空洞词句。毛泽东们年轻时,找到的是与革命有关的知识,而我们却没有。毛泽东在贬低教授时,对教授也怀有敬佩心理,例如,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当他把作家写的史话、轶事贬低为垃圾、废话时,只要见到这些文章,他就想读一读。他甚至说,毒草也可以当肥料,资产阶级教授如梁先生也可以被请来当“反面教授”,或在文章中把我们这帮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不是对中国的兴衰荣辱起过一定的作用吗?尽管是消极作用,但总比没有作用,一事无成、两手空空,“交白卷”强一些吧!
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文化教育领域,是容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就像在极左风暴中被赶下台的教育家蒋南翔,曾向毛泽东简略地说“大学生学中学课本,他们的水平和中学生一样”。年迈的毛泽东听了叹一口气,小声地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会要亡党亡国的。当他说这话时已经晚了。
是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革命派文章,尤其是“梁效”(音“两校”,即北大清华两校)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其中流行这样一句典型的话:你企图把工农兵像排大便一样地撵出大学校园吗?这岂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被撵出大学校园的是工农兵吗?被撵出大学校园而来到江西的还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
有一天当我割完了草,挑着120斤一担的鲜嫩青草,半路上遇到一位革命派,一见我,四周无人,就叫我放下担子,摇着脑袋,摆起架子问道:“好家伙,今天遇到你啦!我偏偏要问个明白,你的这担草值多少钱啊?”
“青草没有价,阿拉勿晓得。”我谦虚地而且谨慎地答道。
“260元一月,小子,你记着。”他是拿我过去的工资来指这担草的价值的!那么说,就太贵了!这意味着工农兵雇用了一个每月工资260元的人来割草喂牛实在是太不合算了。
“有理有理”,我心里想。那时我只拿16元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部工资冻结起来(后来都退还给我了)。但是浪费了时间、蹉跎了光阴!遭损失的是那两代人,我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损失,只有受益,受到深刻的实践教育的益处。
在鲤鱼洲,我锻炼了体魄,学会了割草,驾驭了庞大的耕牛,这不是件易事。有一次,一头水牛在我躺着看书的时候,走下湖面。当我发现时,这头水牛已离得很远,似乎越游越远,没有“回头是岸”的意思。我着急了,不由分说,脱掉鞋袜,放下手表,游将过去。
附近正在劳动的同事匆匆跑去告诉我的妻子(方备),那时她也在鲤鱼洲菜地里干活:“×××投水自杀了,快去啊!”几位热心好奇的人都跟着方备来到湖边看热闹救人。只有方备知道我会游泳。
“不是去牵牛吗?他游得多快啊!”
大家才放心下来。
我牵着牛鼻子上拴住的绳子,把它引到岸上,大家都拍手表示欢迎。当我湿淋淋一身拉着一头全身发亮长膘的大水牛一路从群众中走过时,我感到自豪,特别是我还穿着裤子和衬衫让那鄱阳湖的清水从裤脚筒里往下直淌的时候,方备笑着和见到这场狂欢节目的同伴们解释道:“他怎么会自杀呀!他活得多自在呀!你们多么照顾他呀!他从没这样悠闲地休息过。奇怪!多少年没有游泳了,竟然还能游!”众人都笑了!
这次江西的实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失败的。学校花了许多钱,大家出了许多力,在鲤鱼洲我们既没有与工农在一起,也没有出什么成果。下田插秧、喷农药、下化肥、盖房修路、种菜养牛,喂猪养鸡,过着小农的集体生活。吃了后院自己种的嫩玉米,全组挨了军代表一次革命大批判,说是糟蹋了粮食。
后来我们离开,这里所盖的房、所修的路……全毁了。
06
打入“冷宫”,走进编译室
1971年,我们是在出了林彪问题之后,从鲤鱼洲回到北京的。对外都说是被召回校翻译《六次危机》,以备毛泽东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接见美国总统、了解情况之用。从此我们几位老年教师就集中起来专搞翻译,并为此在我们系里成立了一个 “编译室”,由一位党员任主任,由五个老知识分子组成。直到1980年我才重进教室,给第一届经考试入学的77年级大学生开“比较宪法”课。从1971年至1981年总计十年时间,由于我们没有条件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按人们的说法就叫做“被打入冷宫”,可并不闲。我觉得这十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时期,翻译是治学者的基本功之一。
尼克松是美国头号反共人物,在中国许多人不知道尼克松的政治生涯,连毛泽东和周恩来,尤其是毛泽东也不甚了解。他的唯一著作《六次危机》就最能表明这位总统的思想、出身、经历以及他当选总统的过程,包括他的言行、意志和野心。翻译《六次危机》的任务,也就落在我们几个老知识分子的头上了。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苏联和美国都是“坏蛋”,但是,俄国人更具有欺骗性。毛泽东评论说过,美国人是坏蛋,但他们是诚实的坏蛋,俄国人则是骗子。后来毛泽东甚至开始宣称美国是个好东西。
从1971年到1977年间我们六个人大约译了六七本书,其中有《谁是吉米》(卡特传)、《旧世界新视野》(希思演讲集)、《联合国手册》、《核竞争与和平》、《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宪法》等。我们都是我译你校,你译我校,形成一个“集体”,天天坐班,按时作业。外面的事如工农兵上学啦,我们都不闻不问。常听人说,能够活下来就算不错啦!是的。我这十年没白活,最后七年多少也干出点事来。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日子里被打入“冷宫”,所以我不承认这些年是蹉跎岁月。
在这些年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这些伟人相继逝世。人无一不生,无一不死,在这点上是亘古不变,又是一律平等的。这里没有什么“新”、“旧”社会的区别!没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异!
“四人帮”垮了,“走资派”复辟,都说自己“最正确”、“最马列”。看来,“非此即彼”的哲学没有说服力,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地简单,事实高于任何人的“最高指示”。
但有人好问:什么是“事实”?
那就让各人自陈其说吧,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全能全知的,那就彼此交流补充吧!这是我辈之所以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当然,自由还应衡之以“自律”和“负责”的精神)和依法治国的根据所在。我们所译所写的东西都说明了这一点。
(全文完)
摘自《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