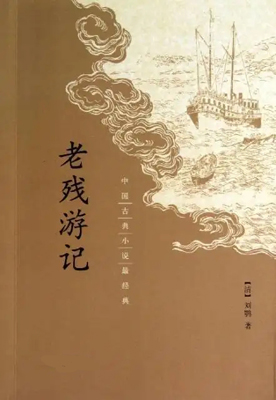谢富治回到北京时,我去南苑机场接他。之后,我们两人同坐一辆车回城。谢富治告诉我,中央又出了问题,以彭真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了全党。《二月提纲》与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正在杭州开会,准备批判和撤销这个文件。
谢富治还告诉我,毛泽东对他说,彭真对北京是一统天下,什么都不准泄露,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什么情况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独立王国。谢富治说,看得出来,毛泽东的言谈之间,表示了对彭真的不满。关于去杭州一事,他告诉我说,这次毛泽东要他去杭州,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告诉他,批判罗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联名,但是这件事情要他对外保密,不要让彭真知道。
这样,我才从谢富治那里知道彭真也出了问题,毛泽东准备要把彭真拿掉了。这个时候,杨成武也和我通气,说中央有个“十四号文件”,是彭真搞的,这个文件有错误,不能向下传达。杨成武和萧华出席了杭州会议,所以他们对彭真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正在杭州开会。四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就不断通知我,要我派飞机去接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到杭州集中。接着,又派专机送中央领导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应的布置,然后每天坐镇指挥所,亲自指挥,直到安全准时地完成运送任务,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当时没告诉我中央在杭州开什么会,但从这些情况来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开重要的会议。
后来我才知道,在杭州,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以及会后,毛主席亲自对彭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这个草案是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的,而且据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的这个提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并为他所采纳。
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毛主席在外地,没有参加。五月十日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从组织上把彭真拿掉了,并将彭真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销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即“中央十四号文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党解释撤销《二月提纲》的理由,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
《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在《五一六通知》里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经为我们所识破,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身边,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那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会议期间之长,在中国空军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
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这次试验,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负责主持。具体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体同志,而空投氢弹的任务,则交给我们空军来完成。接到这一命令后,我认为这是空军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责任重大。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止出现万一。
在征得空军党委常委一些同志的同意,并得到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批准后,我留下政委余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后与当时负责基地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张爱萍的统一领导下,共同主持这次氢弹试验。
五月九日,氢弹空投任务顺利完成,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我与成钧商量,待听完张爱萍的总结报告以后,我们俩顺道去驻在和阗、哈密、张掖、武威、兰州、临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导弹、飞行部队去检查一下工作,并准备在每个单位去住上几天,了解一下情况,与这些单位进行一下交流和沟通。平时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基层的部队。
到了五月底,正当我和成钧按照预定的安排,来到武威航校检查工作时,余立金从北京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准备把这个文件送到西北来,给我和成钧看一看。
第二天,余立金就派了一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五一六通知》。看完这个文件,我心里想,这个文件仅仅是个通知,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办法,究竟应该怎么搞法,谁也没有底,还是等中央和军委有了进一步的文件、部署具体的办法后,再一起开会传达不迟。因此,我继续和成钧一起,来到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
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叶群说的这个“恩克鲁玛”,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纳共和国的总统,一次,在他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成了流亡总统。叶群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当时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我匆匆结束了西北之行,于六月三日清晨乘飞机和成钧一起回到了北京。
六月三日下午,我刚刚回到家里,叶群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说,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告我的状,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五一六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对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由于徐深吉到刘志坚家里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叶群,所以刘志坚在徐深吉走了之后,把他的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这才通过余立金向我发出了警告。
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准备将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
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在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北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
本来我和成钧的关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时,一路上我们两个也协作得很好,成钧对我很尊重,讲话、作报告也都同我很协调,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是在这个时候,成钧也突然跟我翻了脸,说什么“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呀,空军按兵不动不行呀之类的话,与刘震他们搞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常委会刚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对他们一上来就给我扣的那个“对中央通知按兵不动”的罪名,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我解释说:“据我了解,驻京的各部队机关和军委各总部,包括我们的邻居海军机关,都没有动。现在中央只是发了一个通知,主要是叫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而且文件主要是讲地方上的问题,军队方面怎么搞,谁都不清楚,军委也没有安排,不等一下行吗?着什么急呀?”
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形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
刘震他们仗着是多数,在会上咄咄逼人地要我第二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说,来不及呀!空军党委委员有五十多人,就是连夜用电话通知都来不及呀!要开也起码等到六号才行。可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五号晚以前赶到北京报到。我这样一说,他们才总算是同意了。对会议的议程,我提出,第一步是传达学习文件,第二步才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对我这个建议,大家没有异议。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张廷发说:“今天的会议情况不大对头。”张廷发当时也说:“气氛是不大对头,可能有什么名堂。”
六月四日下午,我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请求军委同意我们从六月六日起召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个报告交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
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我首先代表空军党委常委会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我说:“我和成钧刚刚从西北参加氢弹空投试验和检查部队工作回来,由于多数常委同志要求立即召开全会,学习和讨论《五一六通知》,因此匆忙之中召开的这次会议,常委会还来不及讨论和制订出一个贯彻《通知》的具体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和领会好《通知》的精神,然后集思广议,研究和制订出一整套在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最后,拿出一段时间,对空军党委提意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党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静坐在那里,任凭他们自己上台讲话。他们一讲,就是一个上午。很显然,刘震等一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乎我和余立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们指责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不得力,只不过是用来整倒我的一个借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这些是他们事前早已经酝酿好的,只不过是瞒着我和余立金而已。
认真说起来,即便就是他们表面上的这个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央当时才刚刚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具体开展运动的部署,而且军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关于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按照这个精神,我们静候中央和军委的进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召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离《十六条》正式通过的时间还有两个多月,中央的规定当时还没有下来,就更不要说军委和总政的部署了。难道空军能不等军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说,从我们收到《五一六通知》到开会前后,也不过才十多天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迟迟不动,是我有意躲风?
我个人认为,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对刘亚楼逝世后由我来任空军司令员不满。在刘震看来,他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而我却没有进入八届中央委员,并且只是中将军衔(当时在全空军,只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个人是上将军衔),所以刘亚楼逝世以后,如果从条件上来看,似乎应当由刘震来接任空军司令员。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央和军委最后决定由我来接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其次,是他们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时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等都是空军副司令员,但刘亚楼对他们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因此他们对刘亚楼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都很有意见、很不满意,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为经常受到刘亚楼的批评,于是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因而很不满意。他曾经跟人说过,他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与刘亚楼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刘亚楼出国去越南访问期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一些常委对刘亚楼提了不少意见,为此会议还专门延长了两天。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来,以便调解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想法却与我不同,他们是想要我领导大家对刘亚楼开展斗争。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在会上对他们提的一部分意见作了解释。在刘亚楼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刘亚楼,说常委的同志在会议上对你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当时,刘亚楼问我都提了什么些意见,我告诉他说,都是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例如要求太高、批评不留情面、态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间的相互团结。但仅仅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们对刘亚楼的种种不满。于是他们把心中对刘亚楼的那股怨气,就延续到了我的身上。
我想,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使得刘震他们几个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时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这件事,闹了起来。结果在这次党委会上,文件讨论不成,大家也没有兴趣,就是轰呀,闹呀的。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心想,反正文件也学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轰吧,让他们尽量把意见说尽放完。
没想到,刘震他们几个常委这样一闹,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闹了起来,因为有常委带头嘛!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足足有半个来月时间,一直闹到七月中旬。
在所有起来指责我的人里面,以吴富善最为厉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一边用手仗敲着讲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难受。
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提意见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刘亚楼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张廷发。至于他们所提的意见,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没有当时的记录,根据我的仔细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第一、说我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在西北“躲风”,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说刘亚楼、我同彭真的关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里去拜年,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第三、说刘亚楼、我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说东,刘亚楼和我绝不说西。不光如此,我们还把罗瑞卿说过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检查、不要翘尾巴”四句话,到处印发,到处张贴。第四、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好大喜功。说我没有原则,对刘亚楼一味迁就,甚至为刘亚楼助威。第五、说空军每年对师以上干部的集训,系统地一本一本学习毛泽东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学习“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
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
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
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
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仅如此,还告状到了我这里,刘亚楼、吴法宪一共是二十五条罪状。等一下,我让秘书传到你那里去。”接着,林彪开始讲他的意见。他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很快,空军七个常委联合署名的控告材料传到叶剑英副主席那里,叶帅一看心里更有数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叶帅看过信以后,就把信转给了我。
对刘震等人写控告信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叶剑英转给我的控告信后才了解这一情况的。对他们这种背后告状,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毛病,大家给我“洗洗澡”,我是很欢迎的。可这封控告信里的有些内容,也确实是站不住脚的。
大概是七月十五日,叶剑英找总政工作组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说:“你们哪,到空军以后的作法不够妥当,你们不找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吴法宪,也不找第二书记余立金,专门找常委的那几个人,和他们搞在一起,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你们的这种作法是公正的吗?!你们是代表总政去参加空军党委会议的!你们支持他们,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吗?再这样下去你们也要陷进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