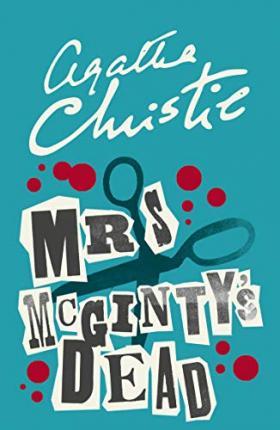岸上十余名蒙着脸的黑衣汉子早就排成了个半圆形,将四人围在弧形之内。这十余人手中所持大都均是长剑,另一小半或持双刀,或握软鞭,没一个使沉重兵刃。俞莲舟抱臂而立,自左而右的扫视一遍,神色冷然,并不说话。中间一个黑衣汉子右手一摆,众人忽地两旁分开,各人微微躬身,手中兵器刃尖向地,抱拳行礼,让出路来。俞莲舟还了一礼,昂然而过。这干人待俞莲舟走出圈子,忽地向中间一合,封住了道路,将张翠山等三人围住,青光闪烁,兵刃一齐挺起。张翠山哈哈一笑,说道:“各位原来冲着张某人而来。摆下这等大阵仗,可将张翠山忒也瞧得重了。”中间那黑衣汉子微一迟疑,垂下剑尖,又让开了道路。张翠山道:“素素,你先走!”殷素素抱着无忌正要走出,猛地里风声响动,五柄长剑一齐指住了无忌。殷素素吃了一惊急忙倒退。那五人跟着踏步而前,剑尖不住颤动,始终不离无忌身周尺许。俞莲舟双足一点,倏地从人丛之外飞越而入,双手连拍四下,每一记都拍在黑衣人的手腕之上,四柄指着无忌的长剑一一飞入半空。这四下拍击出手奇快,四柄长剑竟似同时飞上。他左手跟着反手擒拿,抓住了第五人的手腕,中指顺势点了那人腕上穴道,但觉着手处柔软滑腻,似是女子之手,急忙放开。那人手腕麻痹,当的一声,长剑落地。那五人长剑脱手,急忙退开。月光下青光闪动,又是两柄长剑刺了过来,但见剑刃平刺,锋口向着左右,每人使的都是一招“大漠平沙”,但剑势不劲,似无伤人之意。俞莲舟心道:“昆仑剑法!原来是昆仑派的!”待剑尖离胸将近三寸,突然胸口一缩,双臂回环,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同时击在剑刃的平面上。
这两下敲击中使上了武当心法,照理对方长剑非出手不可,岂知手指和剑刃相触,陡觉剑刃上传出一股柔劲,竟将他这一击之力化解了一小半,长剑并未脱手。但那二人终究抵挡不住,腾腾腾退出三步。一人站立不定,摔倒在地,另一人“啊哟”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自六艘小舟横江以来,对方始终没一人出过声,这时“啊哟”一声惊呼,声音柔脆,听得出是女子口音。中间那黑衣人左手一摆,各人转身便走,顷刻间消失在灌木之后。但见这干人大半身材苗条,显是穿了男装的女子。俞莲舟朗声道:“俞二、张五多多拜上铁琴先生,请恕无礼之罪。”那些黑衣人并不答话,隐隐听得有人轻声一笑,仍是女子之声。殷素素将无忌放下地来,紧紧握住他手,说道:“这些大半是女子啊。二伯,她们都是昆仑派的么?”俞莲舟道:“不,是峨嵋派的。”张翠山奇道:“峨嵋派的?你怎说多多拜上‘铁琴先生’?”俞莲舟叹道:“她们自始至终不出一声,脸上又以黑帕蒙住,那自是不肯以真面目来示人了。五剑指住无忌,那是昆仑派的‘寒梅剑阵’。两人平剑刺我,又使昆仑派的‘大漠平沙’。她们既然冒充昆仑派,我便将错就错,提一提昆仑的掌门铁琴先生何太冲。”殷素素道:“你怎知她们是峨嵋派的?认出了人么?”俞莲舟道:“不,这些人功力都不算深,想是当今峨嵋掌门灭绝师太的徒孙一辈,或许是她的小弟子,我并不认得。但她们以柔劲化解我指击剑刃的功夫,确是峨嵋心法。要学别派的数招阵式不难,但一使到内劲,真相就瞒不住了。”张翠山点头道:“二哥以指击剑,她们还是撒剑的好,受伤倒轻。峨嵋派的内功本是极好的,只是未有适当功力便贸然运使,遇上高手,不免要吃大亏。二哥倘若真将她们当作敌人,这两个女娃娃早就尸横就地了。可是峨嵋派跟咱们向来是客客气气的啊。”俞莲舟道:“恩师少年之时,受过峨嵋派祖师郭襄女侠的好处,因此他老人家谆谆告诫,决不可得罪了峨嵋门下弟子,以保昔年的香火之情。我以指击剑,发觉到对方内劲不对时,收势已然不及,终于伤了二人。虽然这是无心之失,总是违了恩师的训示。”殷素素笑道:“好在你最后说是向铁琴先生请罪,不算是正面得罪了峨嵋派。”这时他们的座船早已顺水向下游,影踪不见。六艘小船均已沉没,舟中桨手湿淋淋的一个个爬上岸来。殷素素道:“这些都是峨嵋派的么?”俞莲舟低声道:“多半是巢湖的粮船帮。”殷素素望了一眼地下明晃晃的五柄长剑,俯身想拾起瞧瞧。俞莲舟道:“别动她们的兵刃,倘若剑上刻得有名字,咱们以后便无法假作不知。这就走罢!”殷素素这时对这位二伯敬服得五体投地,应道:“是!”携了无忌之手,走向江岸大道。经过一丛灌木,只见数丈外的一株大柳树上系着三匹健马。无忌喜呼起来:“有马,有马!”他在冰火岛上从未见过马匹,来到中土后,一直想骑一骑马,只是一路乘船,始终未得其便。四人走近马匹,见柳树上钉着一张纸。张翠山取下看时,见纸上写道:“敬奉坐骑三匹,以谢毁舟之罪。”字是炭条写的,仓卒之际,字迹甚是潦草,笔致柔软,显是女子手笔。殷素素笑道:“峨嵋派姑娘们画眉用的炭笔,今日用来写字条给武当大侠。”俞莲舟道:“她们倒也客气得很。”于是解下马匹,三人分别乘坐。无忌坐在母亲身前,大是兴奋。张翠山道:“反正咱们形迹已露,坐船骑马都是一般。”俞莲舟道:“不错。前边道上必定尚有波折,倘若迫不得已要出手,下手千万不可重了。”他适才无意间伤了两名峨嵋门下弟子,心下耿耿不安。殷素素好生惭愧,心想:“二伯只不过下手重了一些,本意亦非伤人,只是逼对方撒剑,她们自行硬挺,这才受伤。比之我当年肆意杀了这许多少林门人,过错之轻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一身作事一身当,以后不可再让二伯为难。”说道:“二伯,这干人全是冲着我夫妇而来,对你可恭敬得很。前面要是再有阻拦,由弟妹打发便是,倘真不行,再请你出手相援。”俞莲舟道:“你这话可见外了。咱兄弟同生共死,分甚么彼此?”殷素素不便再说,问道:“他们明知二伯跟我夫妇在一起,怎地只派些年轻的弟子来拦截?”俞莲舟道:“想是事急之际,不及调动人手。”张翠山见了适才峨嵋派众女的所为,料是为了寻问谢逊的下落而来,说道:“原来义兄跟峨嵋派也结下了梁子,我在冰火岛上却没听他说起过。”
俞莲舟叹道:“峨嵋派门规极严,派中又大多是女弟子。灭绝师太自来不许女弟子们随便行走江湖。这次峨嵋派竟然也跟天鹰教为难,我们当时颇感诧异,直到最近方始明白了其中缘故,原来河南开封金瓜锤方评方老英雄有一晚突然被害,墙上留下了‘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昆也’十一个血字。”殷素素问道:“那方评是峨嵋派的么?”俞莲舟道:“不是。灭绝师太俗家姓方,那方老英雄是灭绝师太的亲哥哥。”张翠山和殷素素同时“哦”的一声。
无忌忽然问道:“二怕,那方老英雄是好人还是坏人?”俞莲舟道:“听说方老英雄种田读书,从不和人交往,自然不是坏人。”无忌道:“唉,义父这般胡乱杀人,那就不该了。”俞莲舟大喜,轻舒猿臂,将他从殷素素身前抱了过来,抚着他头,说道:“孩子,你知道不能胡乱杀人,二伯很是喜欢。人死不能复生,便是罪孽深重、穷凶极恶之辈,也不能随便下手杀他,须得让他有一条悔改之路。”
无忌道:“二伯,我求你一件事。”俞莲舟道:“甚么?”无忌道:“倘若他们找到了义父,你叫他们别杀他。因为义父眼睛瞎了,打他们不过。”俞莲舟沉吟半晌,道:“这件事我答允不了。但我自己决计不杀他便是。”无忌呆呆不语,眼中垂下泪来。天明时四人到了一个市镇,在客店中睡了半日,午后又再赶路。有时殷素素和丈夫共乘一骑,让无忌一试控缰驰聘之乐。无忌究是孩子心情,骑了一会马,为谢逊担忧的心事也便淡忘了。一路无话,不一日过了汉口。这天午后将到安陆,忽见大路上有十余名客商急奔下来,见了俞莲舟等四人,急忙摇手,叫道:“快回头,快回头,前面有鞑子兵杀人掳掠。”一人对殷素素道:“你这娘子忒也大胆,碰到了鞑子兵可不是好玩的。”俞莲舟道:“有多少鞑子。”一人道:“十来个,凶恶得紧哩。”说着便向东逃窜而去。
武当七侠生平最恨的是元兵残害良民。张三丰平素督训甚严,门人不许轻易和人动手,但若遇到元兵肆虐作恶,对之下手却不必容情。因此武当七侠若是遇上大队元兵,只有走避,若见少数元兵行凶,往往便下手除去。俞张二人听说只有十来名元兵,心想正好为民除害,便纵马迎了上去。行出三里,果听得前面有惨呼之声。张翠山一马当先,但见十余名元兵手执钢刀长矛,正拦住了数十个百姓大肆残暴。地下鲜血淋漓,已有七八个百姓身首异处。只见一名元兵提起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用力一脚,将他高高踢起,那孩子在半空中大声惨呼,落下来时另一个元兵又挥足踢上,将他如同皮球踢来踢去。只踢得几脚,那孩子早没了声息,已然毙命。张翠山怒极,从马背上飞跃而起,人未落地,砰的一拳,已击在一名伸脚欲踢孩子的元兵胸口。那元兵哼也没哼一声,软瘫在地。另一名元兵挺起长矛,往张翠山背心刺到。无忌惊叫:“爹爹小心!”张翠山回过身来,笑道:“你瞧爹爹打鞑子兵。”但见长矛离胸口已不到半尺,左手倏地翻转,抓住矛杆,跟着向前一送,矛柄撞在那元兵胸口。那元兵大叫一声,翻倒在地,眼见不活了。
众元兵见张翠山如此勇猛,发一声喊,四下里围了上来。殷素素纵身下马,抢过元兵手中长刀,砍翻了两个。众元兵见势头不对,落荒逃窜,但这些元兵凶恶成性,便在逃走之时,还是挥刀乱杀百姓。俞莲舟大怒,叫道:“别让鞑子走了。”急奔向西,拦住四名元兵的去路。张翠山和殷素素也分头拦截。三人均知元兵虽然凶恶,武功却是平常,无忌比他们要强得多,不用分心照顾。无忌跳下马来,见二伯和父母纵跃如飞,拍手叫道:“好,好!”突然之间,那名被张翠山用矛杆撞晕的元兵霍地跃起,伸臂抱住了无忌,翻身跃上马背,纵马疾驰。俞莲舟和张翠山夫妇大惊,齐声呼喊,发足追赶。俞莲舟两个起落,已奔到马后,左手拍出一掌,身随掌起,按到了那元兵后心。那元兵竟不回头,倏地反击一掌。波的一声响,双掌相交,俞莲舟只觉对方掌力犹如排山倒海相似,一股极阴寒的内力冲将过来,霎时间全身寒冷透骨,身子晃了几下,倒退了三步。那元兵的坐骑也吃不住俞莲舟这一掌的震力,前足突然跪地。那元兵抱着无忌,顺势向前一跃,已纵出丈余,展开轻身功夫,顷刻间已奔出十余丈。
张翠山跟着追到,见二哥脸色苍白,受伤竟是不轻,急忙扶住。殷素素心系爱子,没命的追赶,但那元兵轻身功夫极高,越追越远,到后来只见远处大道上一个黑点,转了一个弯,再也瞧不到了。殷素素怎肯死心,只是疾追。她不再想到这元兵既能掌伤俞莲舟,自己便算追上了,也决非他的敌手,心中只是一个念头道:“便是性命不保,也要将无忌夺回。”俞莲舟低声道:“快叫弟妹回来,从长......从长计议。”张翠山挺起长矛,刺死了身前的两名元兵,问道:“伤得怎样?”俞莲舟道:“不碍事,先......先将弟妹叫回来要紧。”张翠山生怕剩下来的元兵之中尚有好手在内,自己一走开,他们便过来向俞莲舟下手,当下四下里追逐,一个个的尽数搠死,这才拉住一匹马来,上马向西追去。
赶出数里,只见殷素素兀自狂奔,但脚步蹒跚,显已筋疲力尽,张翠山俯身将她抱上马鞍。殷素素手指前面,哭道:“不见了,追不到啦,追不到啦。”双眼一翻,晕了过去。张翠山终是挂念俞莲舟的安危,心道:“该当先顾二哥,再顾无忌。“勒转马头,奔了回来,见俞莲舟正闭目打坐,调匀气息。过了一会,殷素素悠悠醒转,叫道:“无忌,无忌!”俞莲舟惨白的脸色也渐渐红润,睁开眼来,低声道:“好厉害的掌力!”张翠山听师兄开口说话,知道生命已然无碍,这才放心,但仍是不敢跟他言语。俞莲舟缓缓站起身来,低声道:“无影无踪了罢?”殷素素哭道:“二伯,怎......怎么是好?”俞莲舟道:“你放心,无忌没事。这人武功高得很,决不会伤害小孩。”殷素素道:“可是......可是他掳了无忌去啦。”俞莲舟点了点头,左手扶着张翠山肩头,闭目沉思,隔了好一会,睁眼说道:“我想不出那人是何门派,咱们上山去问师父。”殷素素大急,说道:“二伯,怎生想个法儿,先行夺回无忌才是。那人是何门派,不妨日后再问。”俞莲舟摇了摇头。张翠山道:“素素,眼下二哥身受重伤,那人武功又如此高强,咱们便寻到了他,也是无可奈何。”殷素素急道:“难道便......便罢了不成?”张翠山道:“不用咱们去寻他,他自会来寻咱们。”殷素素原甚聪明,只因爱子被掳这才惊惶失措,这时一怔之下,已然明白。那元兵武功如此了得,连俞莲舟也给他一掌震伤,自然是假扮的。他打伤俞莲舟后,若要取他夫妇二人性命绝非难事,但只将无忌掳去,用意自在逼问谢逊的下落。当时张翠山长矛随手一撞,那人便假装昏晕,其时三人谁也没留心他的身形相貌,此刻回想起来,那人依稀是满腮虬须,和寻常的元兵也没甚么分别。
当下张翠山将师兄抱上马背,自己拉着马缰,三骑马缓缓而行。到了安陆,找一家小客店歇了。张翠山吩咐店伴送来饭菜后,就此闭门不出,生怕遇上元兵,又生事端。他三人在途中杀死了这十余名元兵后,料知大队元兵过得数日便会来大举残杀劫掠,报复泄忿,附近百姓不知将有多少遭殃。但当时遇到这等不平之事,在势又不能袖手不顾。这正是亡国之惨,莽莽神州,人人均在劫难之中。俞莲舟潜运内力,在周身六道流转疗伤。张翠山坐在一旁守护。殷素素倚在椅上,却又怎睡得着?到得中夜,俞莲舟站起身来,在室中缓缓走了三转,舒展筋骨,说道:“五弟,我一生之中,除了恩师之外,从未遇到过如此高手。”殷素素终是记挂爱儿,说道:“他掳去无忌,定是要逼问义兄的下落,不知无忌肯不肯说。”张翠山昂然道:“无忌倘若说了出来,还能是我们的孩儿么?”殷素素道:“对!他一定不会说的。”突然之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张翠山忙问:“怎么啦?”殷素素哽咽道:“无忌不说,那恶贼......那恶贼定会逼他打他,说不定还会用......用毒刑。”
俞莲舟叹了口气。张翠山道:“玉不琢,不成器,让这孩子经历些艰难困苦,未必没有好处。”他话是这么说,但想到爱子此时不免宛转呻吟,正在忍受极大的痛楚,又是不胜悲愤怜惜。然而倘若他这时正平平安安的睡着呢?那定已将谢逊的下落说了出来,如此忘恩负义,却比挨受毒刑又坏得多。张翠山心想:“宁可他即刻死了,也胜于做无义小人。”转眼望了妻子一眼,只见她目光中流露出哀苦乞怜的神色,蓦地一惊:“那恶贼倘若赶来,以无忌的性命相胁,说不定素素便要屈服。”说道:“二哥,你好些了么?”
他师兄弟自幼同门学艺,一句话一个眼色之间,往往便可心意相通。俞莲舟一瞧他夫妇二人的神色,已明白张翠山的用意,说道:“好,咱们连夜赶路。”
三人乘黑绕道,尽拣荒僻小路而行。三人最害怕的,倒不是那人追来下手杀了自己,而是怕他在自己眼前,将诸般惨酷手段加于无忌之身。如此朝宿宵行,差幸一路无事。但殷素素心悬爱子,山中夜骑,又受了风露,忽然生起病来。张翠山雇了两辆骡车,让俞莲舟和殷素素分别乘坐,自己骑马在旁护送。这日过了襄阳,到太平店镇上一家客店投宿。
张翠山安顿好了师兄,正要回自己房去,忽然一条汉子掀开门帘,闯进房来。这汉子身穿青布短衫裤,手提马鞭,打扮似是个赶脚的车夫。他向俞张二人瞪了一眼,冷笑一声,转身便走。张翠山知他不怀好意,心下恼他无礼,眼见那汉子摔下门帘荡向身前,左手抓住门帘,暗运内劲,向外送出。门帘的下摆飞了起来,拍的一声,结结实实打在他背心。那汉子身子一晃,跌了个狗吃屎,爬起身来,喝道:“武当派的小贼,死到临头,还逞凶!”口中这般说,脚下却不敢有丝毫停留,径往外走,但步履踉跄,适才吃门帘这么一击,受创竟是不轻。俞莲舟瞧在眼里,并不说话。到得傍晚,张翠山道:“二哥,咱们动身罢!”俞莲舟道:“不,今晚不走,明天一早再走。”张翠山微一转念,已明白了他的心意,登时豪气勃发,说道:“不错!此处离本山已不过两日之程,咱师兄弟再不济,也不能堕了师门的威风。在武当山脚下,兀自朝宿晚行的赶路避人,那算甚么话?”俞莲舟微笑道:“反正行藏已露,且瞧瞧武当派的弟子如何死到临头。”当下两人一起走到张翠山房中,并肩坐在炕上,闭目打坐。这一晚纸窗之外,屋顶之上,总有七八人来来去去的窥伺,但再也不敢进房滋扰了。殷素素昏昏沉沉的睡着。俞张二人也不去理会屋外敌人。
次日用过早饭后动身。俞莲舟坐在骡车之中,叫车夫去了车厢的四壁,四边空荡荡的,便于观看。
只走出太平店镇甸数里,便有三乘马自东追了上来,跟在骡车之后,相距十余丈,不即不离的蹑着。再走数里,只见前面四名骑者候在道旁,待俞莲舟一行过去,四乘马便跟在后面。数里之后,又有四乘马加入,前后已共有十一人。赶车的惊慌起来,悄声对张翠山道:“客官,这些人路道不正,遮莫是强人?须得小心在意。”张翠山点了点头。在中午打尖之处,又多了六人,这些人打扮各不相同,有的衣饰富丽,有的却似贩夫走卒,但人人身上均带兵刃。一干人只声不出,听不出口音,但大都身材瘦小、肤色黝黑,似乎来自南方。到得午后,已增到二十一人。有几个大胆的纵马逼近,到距骡车两三丈处这才勒马不前。俞莲舟在车中只管闭目养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下。
傍晚时分,迎面两乘马奔了下来。当先乘者是个长须老者,空着双手。第二骑的乘者却是个艳装少妇,左手提着一对双刀。两骑马停在大道正中,挡住了去路。张翠山强抑怒气,在马背上抱拳说道:“武当山俞二、张五这厢有礼,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那老者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金毛狮王谢逊在哪里?你只须说了出来,我们决不跟武当弟子为难。”张翠山道:“此事在下不敢作主,须得先向师尊请示。那老者道:“俞二受伤,张五落单。你孤身一人,不是我们这许多人的敌手。”说着伸手腰间,取出一对判官笔来。判官笔的笔尖铸作蛇头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