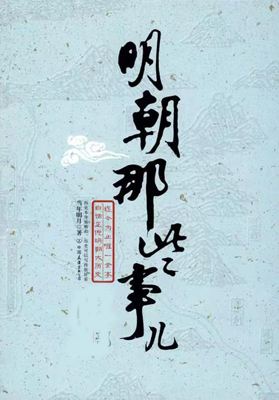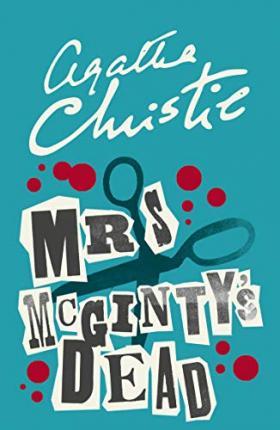当郭文踢踢踏踏走到襄国,走进石勒皇宫的时候,石勒早已回到襄国了。
郭文故意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踏进石勒的宫殿,也不行礼,迳自坐在椅子上。他来的次数多了,不拘礼节,石勒也不以为忤,只抬眼看了看他,说道:“来了,老爷子?”吩咐侍卫看茶,侍卫退出去了,石勒也不说话,只用眼瞄着他。在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这人既不是你的上级,也并非你的下级,更不是你的同事,他无权无势,平民百姓一个,但是,不管你有多高的职位,即或石勒这样的天王,他都可以和你平起平坐,来去自如,说话随便。有人说这叫做个人影响权,是吗?郭文在石勒的王宫里,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郭文喝了口茶,说道:“王安让我告诉你,祖逖西去洛阳。”
石勒说:“知道。”
“浚仪兵力空虚。”
石勒这才听进去。问道:“你的意思?”
“你听不懂吗?”郭文反问道,“该怎么做还用问我吗?”
“你提醒得好。”石勒脸上堆下笑容,又自言自语地说,“光顾生气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石勒说话的当口,郭文已经踢踢踏踏地走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唠叨:“唉,都是为了那个不争气的徒儿啊。”
石勒从河内归来,桃豹、孔苌和石虎也陆续回到襄国。十万大军,连遭败绩,令他气愤不已。可他自己也是逃回来的,没法苛责下属,也只好自己跟自己生气,同时也生祖逖的气,你干嘛也要到豫西去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攻打荥阳、河内、洛阳呢?我堂堂赵国天王,何以每战都要败给你呢?生了两天闷气,郭文来了,一句话提醒了他。
石勒派人找来了张宾,对他说了郭文送来的消息,最后说:“我要抄祖逖的后路,打他个措手不及!”
张宾这两天看够了石勒的脸色,知道他心里憋气,他要报复祖逖。乘祖逖后方空虚之际,进攻浚仪,倒也是一着不错的棋。张宾没有异议。至于人选,他俩异口同声:“陈川!”
银屏一个人呆在雍丘,闲得无聊,就到街上走走,她拉着马,提着马鞭,百无聊赖地朝城外溜跶,一路走,一路抽打路边的枯草。出了城,她看到遍布田野的坟头都填了土,压上了挂纸,有人在坟前烧纸,还有人手里拿着纸钱往坟上走。她明白了,今天是清明节,心里忽然涌起一阵伤感,李头去世以后,除了上次攻打蓬关,她还没有给他上过坟。今天正好没事,她何不去给李头上坟?好在雍丘离浚仪不远,不过一个时辰的路程。一经决定,她立刻回城,买来香烛、纸钱、挂纸和供品,跨马扬鞭,往浚仪驰去。
银屏一踏进李头的墓地,伤痛立即主宰了她。她强忍悲痛为李头上香,填坟,挂纸,然后焚化纸钱,想起和李头在一起时李头对她的呵护、照顾,想起陈川对她的凌辱,想起李头因她而被害,不禁痛哭失声。哭了一场,她站起身来,围着坟墓走了几圈,看着陈川为掩人耳目给李头修建的坟墓,立的墓碑,真想把坟前的墓碑一剑砍了,转念一想,算了,等杀了陈川,血祭李头以后,为李头重新修墓的时候再说吧。
从李头的墓地走出来,银屏想到蓬关去看看,那里有她和李头昔日的驻地。她知道冯宠和韩潜都在蓬关,等到她进入蓬关,才发现祖逖和冯铁也都在这里。祖逖没想到银屏会来蓬关,急忙问道:“你怎么来了?”
银屏从实说道:“我来给李头上坟。”
祖逖点点头:“应该。”
银屏反问道:“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我们从洛阳回来,路过荥阳,李矩在襄国的内线传来消息,石勒派陈川来夺取蓬关,我们就留在蓬关准备迎接他。”
银屏咬着牙说:“好啊,看来是李头阴魂不散,把我领到这儿来,让我替他报仇的。我要亲手宰了这个贼子!”
这时候,一个士卒前来禀报:“陈川已经到达浚仪。”
祖逖一挥手说:“列阵迎接!”说完,和银屏一起带着嵩山营、明道营、水兵营鱼贯而出,摆好阵势。
陈川带着石勒给他的三千兵马,渡过黄河,又一次回到蓬关。
说实话,陈川并不愿意回来夺取蓬关,他和祖逖较量过了,他知道自己不是祖逖的对手。他一开始也不想和祖逖作对,只是因为迷恋银屏,一时冲动,杀了李头,才把自己推到祖逖的对立面。等到后悔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了。他被祖逖赶出蓬关,输得一塌糊涂,不得已投奔了石勒,只想抱着石勒这棵大树,在石勒的王府里弄个一官半职,混碗饭吃也就算了,根本不打算夺回蓬关,重振昔日的威风。他和刘夜堂给桃豹运送给养,驴队被劫,他在外流落数月,和童建结伴回到襄国以后,他明显地感到石勒对他的蔑视,但吃人家的饭,就得看人家的脸色,寄人篱下就得学会忍气吞声。可石勒偏不让他过安生的日子,命令他率三千兵马夺回蓬关,他心里百般不情愿,但也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好在张宾告诉他,祖逖已经西去洛阳,蓬关只有冯宠把守,他的心才算稳住了。
等到他出了浚仪来到蓬关的时候,他看到祖逖、银屏、桓宣、冯铁、韩潜、冯宠一干人都在对面,他顿时魂飞天外,再也无心欣赏银屏在红马白袍映衬下的那张俏脸了。临阵之际,再心虚也要稳住军心,他煞有介事地率兵走到阵前,扎住阵脚,还没想好要说句什么,只听一脸寒光的银屏对祖逖说:“我去杀了这个贼子!”祖逖还没来得及阻拦,银屏就打马冲过来了。
陈川见银屏来到跟前,挥剑就刺,虽然还有点旧情难忘,也只得还手。
陈川使的是从冯铁那里学来的剑法,偏重于刚;银屏使的是祖逖教的剑法,经她自己变化,偏重于柔。两人你来我往,战在一起。一个报仇心切,怒火中烧,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一个剑道虽刚,色厉内荏,犹存怜香惜玉之心。两人缠斗多时,难分胜负。
这时,从旁边冲出一匹马来,骑在马上的人也是一个女子,也是红马白袍,手持宝剑,立刻加入战斗,刚一出手,就可以看出,功力不弱。以一对二,陈川立时捉襟见肘。后来的女子乘陈川忙于应付之时,对银屏说:“姐姐,娘在成皋城南等你,快去!”银屏扭头一看,认得是通知她陈川要加害李头的那个人,就问:“你是谁?”
女子没有直接回答她,只说:“快去见娘!姐夫的仇我来报。”
银屏听说有了娘的下落,一时心情激动,当下退出战斗,也顾不得和祖逖告别,催马直奔成皋去了。祖逖一心观察整个战场的局势,两个红马白袍的女人共斗陈川,也没留心走的是哪一个。
后来的女子自然是青萍。她去嵩山学艺回来,想先找到银屏,一同去成皋见娘,给娘一个惊喜。所以就骑马直奔浚仪,鬼使神差,一到浚仪就碰上了战斗,交战的一方是她要找的银屏,另一方是她日夜不忘要寻仇的陈川,这个机会怎能错过?于是她当即加入战斗,并且替换下银屏。
战场上的两个人继续打斗。陈川当然知道他眼前的对手是青萍,几年不见,不知她如何学得了一身武功?我们说过,陈川的剑法学自冯铁,虽说彼时他的注意力不在剑法,但他靠了自己的颖悟,一招一式,也上得了台面。青萍的剑法也来自嵩山,虽然师门不同,但嵩山的剑法大同小异,也可以算得上是同门。两人招对招,打得难解难分,式对式,让人眼花瞭乱。陈川一招青龙出水,青萍还以一招夜叉探海,然后递出一招鸿雁送书,陈川忙以鹞子翻身化解,接着使出一招蜻蜓点水,青萍回以青龙缩尾。陈川回剑,一招怀中抱月守住门户,青萍以封侯挂印上挑,接着使出一招抽梁换柱,陈川回一招天边扫月,然后接连使出青龙缩尾、黑虎出洞,青萍以一招怀中抱月封住。两人你来我往,战了多时,难分高下。
祖逖有些担心,他怕银屏有个闪失,伸手要摘酒葫芦,冯铁按住他的手说:“她的武功不弱,一时还不致落败。如果她支持不住,不用你出手,我来清理门户。”
祖逖说:“她怎么换了打法?”
冯铁想了想说:“也许是耳濡目染,学会了嵩山剑法吧。看样子倒也有些根底。”
青萍报仇心切,心里焦躁,恨不得一剑杀了陈川,心想,这样打下去,何时是了?于是她改变打法,不再墨守成规,想刺就刺,想劈就劈,完全打乱了规矩,招招都是拼命的打法。陈川先是不知所措,心说,这婊子怎么乱来?一时间倒被她弄得手忙脚乱。
他一边应付,一边说:“青萍,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曾有过肌肤之亲,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一点不念旧情啊?”
青萍骂道:“无赖!”
陈川见青萍动了怒,一阵窃喜。他知道,临阵之际最忌发怒,怒则难以保持冷静,最容易造成疏失。他继续说道:“青萍,你要谋杀亲夫吗?跟我到襄国去吧,我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刀剑相向呢?”
他的话就好像火上浇油,青萍出剑越发狠辣,直指陈川要害。一边出剑,一边骂道:“你找死!”弄得陈川也不得不小心对付了。及至陈川发现她门户大开,不加防守,也就专拣她的空子。祖逖这边的将领们也替她着急,有人甚至大喊:“夫人,守住门户!”打着打着,陈川见青萍的左手剑锋朝自己刺来,右方却毫无防备,于是左手剑锋朝青萍的右胸刺去,青萍躲闪不及,索性奋力刺向陈川左胸,两人都铆足了劲,双双刺入对方胸部,也都同时跌下马来。祖逖一看,急忙冲上前去,他身边的将领们也都跑过去,一边大喊:“夫人,夫人!”
陈川的士卒一看陈川跌下马来,乱了阵脚,蜂拥而退。
此时,一支箭从对方阵地上飞来,迳直射向祖逖,王安眼快,一经发现,纵身跃向祖逖,眼看就要射中祖逖,拨开是来不及了,他把胳膊一伸,挡在祖逖眼前,箭射中他的胳膊,顿时流出了鲜血。祖逖一把抱住他,拔出箭来,撕开战袍,为他包裹止血。收拾好了之后,挥手喊了一声:“追击!”然后迈步向青萍走去。
祖逖蹲下身来,第一眼就看出,这人酷似银屏,但不是银屏。他在青萍的鼻孔试了试,还有气息,他想看看她的脉象,一伸手,发现了青萍腕子上的玉镯,他的心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这人是谁?这玉镯是他们家女人祖辈流传之物,上面还刻着“范阳祖氏”四个字。她怎么会有这玉镯?他想到,只有全力救活她,才能弄个水落石出。他对周边的人们说:“快去浚仪找大夫来!”
有人去浚仪找大夫,剩下的人们还在呼喊着:“夫人,夫人!”
只有祖逖知道此人不是银屏,但他不想说破。银屏去哪儿了?
祖逖扭头问道:“陈川怎么样?”
冯宠踢了踢陈川:“死了。”
祖逖说:“埋了吧。”
冯宠说:“不,要用陈川的头血祭李头。”
祖逖担心银屏,又担心眼前的女人和王安,无心顾及对陈川的处置,没有说话。
大夫来了,仔细察看了青萍的伤势,告诉祖逖:“伤口很深,失血过多,但没伤及心脏,无甚大碍,要好好将养些日子。我先给她开些清淤止血的药,过几天就会见效。”祖逖还让大夫为王安重新上药包扎,和青萍一起送进蓬关。
第二天,冯宠他们还是用陈川的头祭奠了李头,并且砸碎了陈川立的碑,他们要为李头重新修墓。祖逖命各营将领回到各自的驻地,冯铁和韩潜同回雍丘,冯宠仍然驻守蓬关,他自己和桓宣留下来,一起照顾青萍和王安。
青萍被安置在蓬关西台上桃豹住过的那间较大的屋子里。祖逖在旁边搭了一张床铺,日夜看护着她。换药、喂药,喂水、喂饭,无微不至。睏了,就在旁边的床上眯一会儿。桓宣也以为她就是银屏,有些事情他不方便去做,只能管熬熬药,打打饭等一些杂活,冯宠和他的士兵们虽然就在旁边守护着,许多事情他们也不好插手,主要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到祖逖身上了。
祖逖自然是责无旁贷了,虽然他明智床上躺着的人不是银屏,可是青萍手上的玉镯证明了她是祖氏家族的人,他得尽心竭力地照顾她,治好她,问清她是谁?是他的什么人?
可是,几天过去了,青萍还在昏迷之中,高烧也没有退,嘴里一直重复着那几句话:“姐姐,快去……娘在等你……”祖逖猜不透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又不知道银屏去了哪儿,银屏的去向一定和她有关。他的心浮着,干着急,没办法,只能等她醒来,才能问个清楚。可青萍就是不醒。祖逖摸了摸她的额头,还在发烧,把她头上的手巾拿下来,换上一条凉手巾,然后就拿着玉镯发呆。
桓宣端过饭来,祖逖有滋没味地吃了几口,放下碗筷,走出屋门。旁边的屋子里还有一个王安,王安为自己挡了箭,受了伤,他心里不安,每天总要去看几次。
王安的屋里,坐着他的师傅郭文。祖逖对郭文拱手:“先生来了?”
郭文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祖逖要看看王安的伤势,王安躲开,说道:“放心,没事,好了。”
祖逖对郭文说起王安受伤的经过,说起前几天的战事,他忽然想起路过荥阳的时候,李矩对他说,他的内线传来消息,有人去了襄国,告诉石勒,祖逖西去洛阳,后方兵力空虚,建议他出兵浚仪,石勒已经派陈川来夺取蓬关。这人会是谁呢?谁是石勒派到北伐军的卧底呢?想到这里,他就随口问王安:“你在襄国见没见过咱们队伍中的哪一个人?”
王安还没回答,郭文就说:“你是想说这次是谁给石勒送的情报吧?”
祖逖点点头。郭文干脆地说:“是我。”
祖逖一惊:“为什么?”
“一是陈川的死期到了,得通过你的手杀了他。”
王安连忙跪下辩解道:“大人,师傅是算准了你回来的时间,不会被他们乘虚而入,才去见石勒的。”
郭文拦住他:“别多嘴!”然后对祖逖说:“二是为了王安。”
祖逖一脸的不解。郭文继续说:“王安就是石勒派来卧底并且刺杀你的人。但是你的仁慈,你的心胸感化了他,他不忍杀你。再说你还不到回天界的时候,他也杀不了你。”
祖逖见老头云山雾罩,神秘兮兮,觉得好玩,就逗他:“我什么时候回天界?”
郭文说:“中年不问寿。”
祖逖又问:“你看我们恢复中原,前景如何?”
“你随便写一个字。”
祖逖随手写了一个“逖”字。
郭文端详了一下:“逖字,上边一个‘狄’,下边一个‘走’,你可以把狄夷赶走。但‘逖’字里有个‘火’字,就怕有人给你釜底抽薪。一旦没了那火,你就什么也不是了。”
祖逖心里一惊:“谁给我釜底抽薪?”
“到时便知。”
祖逖见郭文说得郑重其事,不由得不信了:“我该怎么办?”
郭文一笑:“谋事在人。”
“结局如何?”
“成事在天。”
“我能够收复晋朝的失地吗?”
“天机不可泄露。”
祖逖无奈,这事不好再问了。又说:“我这里还有一个重伤员,请你看看她能治好吗?”
“可以。”
祖逖把郭文领到青萍的房间,郭文摸摸青萍的脉,又摸摸青萍的头。
祖逖焦急地问:“她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明天。”
祖逖把玉镯拿出来交给郭文:“你看,她是我们祖家的人吗?”
郭文看着玉镯,又看看青萍,点点头,又摇摇头:“算是吧。”
祖逖迷惑了:“怎么‘算是’?”
“她戴着你们家祖传的玉镯,还要给祖家的一个女人养老送终,你说算不算?”郭文说着,站起身来,“我该走了,王安就交给你了,他会对你忠心耿耿,他不但保护你,你的后代还要靠他保护。过一段时间,你会把他还给石勒。”说完,踢踢踏踏地走出去了。
祖逖送出门来,追问:“什么时候?”
郭文头也不回:“很快。”
看着老头的背影,虽然老头给他留下了诸多悬念,他已经感觉到,此人深藏不露,高深莫测,难怪连皇上和丞相都对他如此看重。他对郭文深深地佩服了。
祖逖回到屋里,王安还在地上跪着,他说:“还不起来!你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吧。”
第二天,当太阳照进蓬关西台上青萍住的那间屋子的时候,青萍果然醒了。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男人躺在自己旁边的床上,心里一惊,不禁“啊”了声。祖逖听到声音,立刻醒了,他见青萍醒过来了,高兴地走到她床前,说道:“你醒了?”
青萍看他走近,惊慌地说:“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
祖逖和颜悦色地说:“我是祖逖,我在这儿照顾你呀。”
“你是祖逖?你就是豫州刺史祖逖?”
“是啊。”
“嵩山那里都把你说成神了。你在这儿照顾我?我怎么了?”
“你受伤了,我给你熬药,喂药,换药……”
听到这儿,青萍才感到胸部有些疼痛,想到一个大男人给自己的胸部换药,不禁羞赧地说:“你……”转念一想,人家是豫州刺史,那么大的官儿,在这儿照顾我,怎么还能责备人家?就把说到嘴边的话变了,“谢谢你。”
祖逖这才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青萍。”
祖逖拿出玉鐲:“这是谁给你的?”
青萍看到玉鐲,眼睛一亮,从祖逖手里接过来,珍惜地戴在腕上,说:“我娘给我的。”
“你娘在哪儿?”
“在成皋。”
“银屏是你什么人?”
“我姐姐。”
“怪不得你们长得那么像。是你叫她到成皋去找你娘,是吗?”
“是啊。”祖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有了银屏的下落。
祖逖又问:“你姓祖吗?”
青萍摇摇头。
青萍的记忆在慢慢地恢复,她从银屏想到了那天的战斗,她问祖逖:“陈川那小子怎么样了?”
“他被你杀了啊。”
青萍听了,喜形于色:“这就好了。”心里一阵激动,又晕过去了。
青萍的伤口愈合,是十几天以后的事了。祖逖见她能够自理了,就让桓宣回谯城,让冯宠照顾青萍的饮食起居,自己骑马往成皋去了。他要去找银屏,也顺便到母亲的坟上祭奠一下。
祖逖退出洛阳时,带着母亲和弟弟祖约。到了成皋,母亲病重,不几天就去世了,他悲痛地把母亲葬在城外的一座小山的山坡上,守了几天孝,就带着祖约匆匆离去了。后来,兄弟俩回到老家祖村店,带着一百多户本家和乡亲,长途跋涉到了泗口,被司马睿聘为军咨祭酒,移驻京口,一直没有给母亲上过坟。前些日子在荥阳、洛阳作战,来去匆匆,也没顾得上到母亲坟上看看。这次虽然过了清明节,他无论如何也要给母亲坟上填把土。
祖逖在成皋城外找到了母亲的坟墓,他立的碑还在,坟墓的一侧多了两间房子,也没顾得多问,他给母亲坟上填了土,烧了纸钱,就在母亲坟前跪了下去。等到他站起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站在身后,他们对视了一阵,同时问道:“你是谁?”
还是祖逖先开了口:“我是祖逖。”
老女人惊问道:“你是祖逖?”
祖逖点点头。
老女人上前一步:“小弟,真的是你吗?我是你姐姐呀!”
“大姐?”
老妇人点点头。虽然她和祖逖只是在五十年前在老家祖村店相处过几年,又是同父异母的姐弟,没有很深的感情,但毕竟是骨肉至亲,又是她苦苦等了十几年的骨肉至亲,她还是抱着祖逖哭了起来。哭过以后,她摸摸祖逖的脸,又摸摸祖逖的头发,说:“算起来,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五十六。”
“真快呀,一晃五十年了。小时候,在老家我还抱过你呢。”
祖逖说:“我印象中是有一个大姐,可这么多年一直也没见过。”
“有一次随你姐夫行军,路过上谷,那时候父亲还在上谷太守任上,我们去看了看父亲,当时你还在老家,也没见着。你现在任什么职?”
“豫州刺史。”祖逖答道,“在建业的时候,大哥告诉我说有一个大姐,失散多年了,让我渡江以后留心找一找,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你说的是祖纳吧?他在哪儿?”
“他在朝廷任从事中郎。”
说到祖纳,老妇人又哭了。祖纳是大姐一母同胞的弟弟。
祖逖问:“大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唉!”大姐长叹一声,“你姐夫在长沙王手下为将,他阵亡以后,长沙王就把我们娘儿俩留在王府。长沙王被杀以后,我们在洛阳流落了几年,洛阳陷落,我们就逃出来了,逃到成皋,我和女儿失散了,我找了些日子,没有找到,我不想在城里住,就在城外流浪,偶然看见了继母的墓碑,就在继母的墓旁住下了。我是想,不晓得谁来上坟,我也许会找到家里人。这不,你就来了。”
祖逖说:“我也在长沙王府呆了好几年,怎么就没有见过你?”
老妇人仔细端详着祖逖:“想起来了,我见过你,只是你那时候已经长成大汉子了,我认不出你了,你那时还没留胡子吧?”
祖逖点点头。又问:“你和女儿失散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祖逖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想问:“你女儿叫什么名字?”话到嘴边,又不敢问,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问出来了。
老妇人说:“叫银屏。”
这句话,无疑是一声霹雳,把祖逖震晕了。天下如此之大,为什么和自己相爱相守的竟然是大姐的女儿?他身子晃了几晃,最后还是稳住了。他问:“一直没有找到?”
“前些日子她回来了,说是已经嫁了人,丈夫战死了,她怀了人家的遗腹子。在家住了一夜,说是尘缘已了,自己到明月庵出家去了,等生下孩子,就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了此一生。”
看来银屏还没有说出他们之间的事,祖逖稍感放心。祖逖又问:“大姐还有一个女儿叫青萍?”
老妇人说:“那是我认的义女,人不错,跟银屏长得一模一样,她到嵩山学艺去了。你怎么知道?”
“她从嵩山回来了,前几天到了浚仪,碰上打仗,她受了伤,快好了,过几天我把她给你送回来。”祖逖给大姐留下一些钱,向她告辞:“大姐,改天再来看你,我先去看看银屏。”
大姐问道:“你们认识?”
“她一直跟着我……打仗。”
祖逖在母亲病重期间,曾在成皋住过些日子,他对成皋并不陌生。成皋虽是县城,由于是楚汉相争的重要战场,已经成了历史名城,但由于地处丘陵,城内建筑随地势而建,这里一撮,那里一片,高低错落,倒像一个山村。
祖逖沿着高高低低的土路走到位于城西北角的明月庵。明月庵和洛阳的白马寺一样,是中国最早的寺院,建于东汉永平年间,不过,白马寺住的是和尚,明月庵住的是尼姑。祖逖敲开寺门,开门的是一个小尼姑,祖逖对她说找银屏,小尼姑说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祖逖说是前几天刚来的那个人,小尼姑“噢”了一声,带祖逖进去。明月庵面积很大,进门以后,绕过一个月亮门,就看见一座宏伟的大殿,殿门关着,大殿前香烟缭绕。转过大殿,是几排尼姑的宿舍,小尼姑把祖逖领进一间客房,就出去了。祖逖一路走过来,他发现,这座尼姑庵没有白马寺那样的参天大树,而到处都是牡丹,刚过清明节,向阳处的牡丹已经含苞,还未怒放。
银屏进来了,两个人都非常激动,虽然都已经知道了他们本来的关系,还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分开了。银屏说:“坐吧。”
银屏说:“那天,青萍加入战斗,她告诉了我母亲的下落,我一激动,没有告诉你一声,就骑马直奔成皋来了。见到母亲,我一看墓碑就明白了。”
祖逖激动。
银屏却显得平静。
祖逖说:“都是我害了你。”
银屏幽幽地说:“这也不能怪你,要怪就怪这世道,兵荒马乱,亲人离散,相见不相识。以致酿成大错。”
祖逖问:“怎么到这儿来了?”
银屏说:“我怎么面对我母亲呢?”
“你还年轻,可以从头开始。”
银屏流下泪来:“还有人能替代你吗?我们相守了这几年,这是老天安排的,我知足了。”
祖逖无语。
银屏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了。你要领兵打仗,身边得有个女人照顾你。”
祖逖回答了一句同样的话:“还有人能替代你吗?”\两人泪眼相对,默默无语。在他们不知道自然法则给他们注定的关系之前,他们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可以相知相爱,他们可以结合在一起。当他们知道了他们既定的关系,他们知道还有一个更有力量的伦理纲常挡在他们中间,他们便无可奈何了,他们只能退让,只能分开,并且把以前的结合视为错误。
坐了半天,祖逖起身,知道事情绝对没有挽回的可能,沉重地说:“我得走了,你要保重。”
银屏起身相送。她说:“等孩子生下来,是女孩,我就自己抚养;是男孩,我会派人给你送去。”
祖逖出了明月庵,天下雨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笼罩着他,从此,他要孤身一人了,再也没有一个相知相爱的人陪在身边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汜水河在城边汩汩地流过,他心里也汩汩地流淌着悲哀,绵延不绝。他体验了一把“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意境,一任坐骑信马由缰地向东走去,路过荥阳,他也无心去拜访李矩,迷迷糊糊地回到蓬关。\祖逖回到蓬关,青萍乐呵呵地迎接他:“你到哪儿去了?他们一口一个‘夫人’地叫,叫得人怪不好意思的。”
“你没告诉他们真象?”
青萍摇摇头。
“那好,咱们去雍丘吧。”
“我要回家。”
“回家?”
青萍说:“去找我娘和我姐姐呀。”
祖逖对她说:“你娘知道你在蓬关养伤,等你的伤完全好了,我送你回去。”
青萍高兴地说:“你去了成皋?我娘好吗?我姐姐呢?”
“你娘很好,你姐姐……”
“我姐姐怎么了?”
事已至此,祖逖不得不把他和银屏的事和盘托出。
青萍听了,默默地说:“啊,原来是这样。”
祖逖说:“先跟我回雍丘,等伤好了再走。”
青萍点了点头。
回到雍丘,冯铁和韩潜来看他们,热情地问候初愈的青萍。青萍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们。她根本不认识他们。
祖逖从他们惊疑的眼神里读懂了他们的疑惑,解释说:“夫人受伤得了失忆症。”这才掩饰过去。
晚上,他们必须睡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和银屏一模一样的女人睡在自己身边,祖逖却没有一点感觉。他和青萍商量:“你留下来好吗?”
青萍说:“我才不给姐姐当替身呢。”
祖逖笑了:“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只是不想让将领们知道银屏的事。”
青萍留下来了,她和银屏一样操持家务,和银屏一样照顾祖逖的饮食起居。她和将领们熟悉了,和他们有说有笑,也接受他们无伤大雅的玩笑。在和祖逖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感受到了将领们对祖逖的尊重和爱戴,也感受到了祖逖的人格魅力。晚上他们睡在一张床上,祖逖却从来没有侵犯过她。她对祖逖倒渐渐地产生了爱意,但是,她在陈川那里给银屏当替身,受到了巨大的屈辱,替身的情结一直纠结在她的心里,她不想再当替身了,她要从替身的噩梦中解脱出来,活一回自己。等她的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她怀着矛盾的心情对祖逖说:“我得走了。”
祖逖早就从青萍的神情中看出了她感情的变化,他不能让青萍感情的萌芽再发展,于是他说:“我送你回去。”
青萍说:“不用,我不是过去的青萍了,没人敢欺负我了。”
“那再等一天,明天和冯铁的嵩山营一块走,他们要去虎牢关。”
青萍想了想说:“也行。”
第二天,冯铁率嵩山营出发,青萍一路同行。祖逖把青萍送出城外。冯铁问他夫人为什么要走?他说:“她找到她娘的下落,看她娘去了。”
路上,青萍把她的遭遇对祖逖说了。祖逖说:“怪不得那天你出剑那么狠辣。”
青萍叹了口气说:“我心中的事了了,从此,了无牵挂,只在家陪我娘。”
但祖逖从她回望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牵挂。祖逖嘱咐她:“我和银屏的事不要告诉你娘。”
青萍点点头,骑上马,走了。又是一种失落感在祖逖的心里弥漫。青萍渐行渐远,那个红马白袍的身影,在他的眼里变成了银屏……
直到青萍的身影隐没在天边,祖逖才回去。
祖逖回到他的住处,看着他和银屏睡过的床,看着银屏留下的所有痕迹,还有银屏留下的气息,他的心里一阵哀伤,一阵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