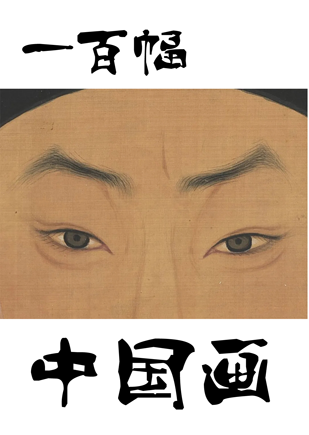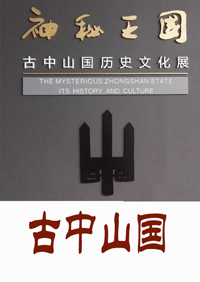第十章 将星殒落
正当祖逖在虎牢关大捷之后,抑制住内心极度的痛苦,打起精神,全力准备渡河北伐,收复失地的时候,晋元帝在他的书房里秘密召见了他的亲信大臣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刁协,尚书仆射戴若思和丹阳尹刘隗。
司马睿这个皇帝当的有点儿费劲,比起几年前祖逖向他要求北伐的时候,显得苍老多了,憔悴多了。那时候,君臣同心,延续晋朝的国祚,颇有一番重整河山的气概。而现在,大局已定,除了祖逖在长江以北孤军奋战以外,国内基本没有战事。一旦安定下来,朝廷内部的斗争便不期然开始了。
司马睿目前最大的心头之患就是王敦了。王敦在被封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坐镇武昌之后,实际上已经把持了东晋的军权,于是他认为自己对朝廷有再造之功,野心开始膨胀,不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他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暗暗与朝廷较劲。王敦原先曾许诺梁州刺史周访,待他平定杜曾叛乱之后,让他任荆州刺史,可是等到朝廷真的任命周访为荆州刺史,他又反悔了,上表让周访留任梁州刺史,自任荆州刺史,元帝只好同意。周访气愤填膺,恨恨而死。朝廷调湘州刺史甘卓继任荆州刺史,甘卓还没有到,王敦已派从事中郎郭舒抢先赴任,等甘卓到任,朝廷为了平衡关系,征调郭舒为右丞,王敦竟然留住不放。于是,元帝开始提防王敦了。
司马睿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王敦推荐沈充代替甘卓为湘州刺史,但元帝偏偏不同意,而是任命谯王司马承去了湘州,王敦忍了。二是疏远了王敦的从弟丞相王导,升他为司空,录尚书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乃明升暗降,外尊内疏,朝廷大事一般不再和他商量了。王导对朝廷可谓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他是吃了王敦的亏了。王导对于宦海沉浮倒不太介意,倒是王敦忍不下这口气,他给朝廷上表说道:“臣从弟王导,昔蒙殊宠,虚己求贤,委以事机,竭诚奉国,遂借私恩,居辅政之重。……顷导见疏外,导诚不能自量,陛下亦未免忘情。天下事大,尽理实难。导虽凡近,未有秽浊之累,既往之勋,畴昔之顾,情好绸缪,足以激励薄俗,明君臣合德之义。……以导之才,何能无失?当令任不过分,役其所长,以功补过。若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效忠于社稷耳。事阙补衮,不尽欲言。”
这篇奏疏意思都在纸上,心怀怨恨,挟制朝廷。元帝看了,也不能不动动心思了。于是他深夜召谯王司马承进宫,拿出王敦的奏疏给他看。并且说:“我待王敦不薄,且一直在忍让他,他却写出这样的奏章,不仅言辞激烈,而且心怀不轨,你说,朕该如何处置?”
谯王司马承看了奏章,低头不语,半天,才说道:“陛下不早日抑制他的权力,致使他野心膨胀,目无朝廷,若再姑息,就离祸患不远了。”
于是,第二天,就有了召见刁协、刘隗,戴若思之事。
司马睿把王敦的奏章给他们看了,说道:“王敦竟敢对朝廷如此骄横!”
刁协说:“今年春天,日中出现黑子,入夏发生地震,终南山忽然崩塌,这些都是不祥之兆。现在王敦反心己露,请陛下早作防范。”
司马睿问:“我们该怎么防范?”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最后,元帝总结道:“就这样吧,以稳固北方之名,命戴若思为征西将军,督司、兖、并、雍、冀五州诸军事,领司州刺史,镇守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刁协留在朝中,早晚与朕共商大事。”
刁协说:“豫州也一并交戴若思统一管辖为好。”
戴若思说:“是,为好。”
元帝说:“豫州刺史祖逖正在北伐中原,与石勒交战,已经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国土,正在规划河北,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干预为好。”
刁协冷笑一声:“陛下有所不知,那祖逖收复了大片国土不假,但他的意图如何,却值得考虑。听说祖逖与石勒已经交了朋友,石勒在范阳为祖逖建了祖坟,在成皋为祖逖的母亲修了墓,并且商定,以黄河为界,互不侵犯,还开通了边境贸易。自古人臣无外交,祖逖此举,恐怕已逾越了为臣之道吧。”
戴若思紧跟着说:“逾越了。”
元帝说:“有这等事?”
刘隗说:“确有其事。”
戴若思说:“确有其事。”
刁协还说:“祖逖北伐军的主力大约有一万多人,再加上河南各地坞主的地方武装,不下十万人,如果他图谋不轨,反过来挟制朝廷,我们将如何应对?如果他与王敦联手对付朝廷,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的十万军队为我所用,那将是扼制王敦的不小的筹码。”
戴若思又赶紧说:“是筹码。”
元帝嘲笑地看了他一眼,摆摆手说:“那就归到戴若思旗下吧。”
三人起身谢恩。
元帝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妥当,对于王敦,还是先安抚一下为好,暂时给他加一个羽葆鼓吹的空衔吧。”
三个人走了,元帝心里很乱,关于对祖逖这样的说法,他还是头一次听到,他想起几年前那个慷慨激昂,主动要求北伐的祖逖,这才几年,他会变成这样?不,不会。不过也难说啊,人心难测,王敦不是也曾一心一意辅佐朕的吗?唉!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前边干事,后边就会有一群人指指戮戮,说三道四,把一说成二,把白说成黑,而且还振振有词,面对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你还真无能为力。如果被上峰听到并且信以为真,你就要倒霉了,轻则声名扫地,重则功败垂成。诽谤一旦和权力结合,它就变成了魔鬼,可以置人于死地。如果事关重大,小则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大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只有年轻人才会说: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只有明智的人才会说:我会把它当成财富,当成前进的动力。但是结果,谁都主宰不了。
拉里拉杂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一句话:祖逖要倒霉了!
从事中郎祖纳到雍丘来了。
这老头子六十多岁了,骨瘦如柴,受不了鞍马劳顿,竟然骑着一头毛驴来了,这让祖逖很感动。他赶紧上前把哥哥搀下驴,扶进他的屋子。建业一别,兄弟俩整整八年没有见面了,都有满肚子的话要说。
虎牢关大捷之后,祖逖写给朝廷一份奏折,把虎牢关的战事和明年渡河的设想向皇上作了陈述。他请桓宣送到建业,顺便给祖纳带去一封信,告诉他已经找到大姐的消息。祖纳接到信以后非常激动,立马就向朝廷请了假,跟桓宣一同来了。
祖纳拍打着麻木的双腿,对祖逖说:“这些年你干的不错,为朝廷收复中原,也为咱们祖家争了光。”
祖逖把这几年进据太丘,兵围谯城,三战蓬关,四败石虎,直至虎牢关大捷一一说给祖纳。
桓宣插不上话,就在一边给他们沏茶水。
祖纳呷了一口水:“近来朝廷里有些传言,说你和石勒成了朋友,是吗?”
“那是石勒一厢情愿,我并没有答应。”
“修墓又怎么回事?”
“那是石勒背着我做的。他是讨好我,向我求和。”
祖纳放下茶杯:“听说你还和他约定以黄河为界,互不侵犯?”
“那不过是双方的缓兵之计。之后不是还在虎牢关打了一仗吗?”
祖纳叹了口气说:“你呀,五十多岁了,还是那么不成熟。你以为忠心报国就会有好报吗?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人首先得学会保护自己。官场上历来是波谲云诡,怎么能干这授人以柄的事情呢?”
祖逖愤愤地说:“我问心无愧。”
“在权力面前,任何人都是弱者,‘问心无愧’只是一种不堪一击的挡箭牌。如果不是桓宣在皇上面前极力为你辩解,你祖逖就不是现在的祖逖了。”
祖逖和桓宣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他们是心意相通的,用不着说什么。
祖纳在雍丘休息了一夜,第二天,祖逖和桓宣陪他到成皋去看望大姐。
祖纳和大姐已经是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姐弟相见,不免抱头痛哭了一场。
祖逖凭感觉知道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的后背,他不忍心过分地辜负她,不由得回望了青萍一眼。青萍报以感激的一瞥。
桓宣也看到了青萍,向她拱拱手:“夫人。”青萍还礼,没有说话。
祖纳和大姐哭过之后,拉着手互相诉说别后情景。祖逖在母亲的塑像前烧了香,焚了纸钱,跪在母亲面前,看见了祖涣的新坟,想起了近来的一系列变故,想到朝廷对他的误解,一阵心酸,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听得在场的人都不禁心酸落泪。桓站在一旁,没有拦他,他理解祖逖的心情,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一面,让他发泄一下吧。青萍拉了他几次,才把他拉起来。
回到雍丘,祖纳告辞,骑着他的毛驴回建业去了。
桓宣也向祖逖告辞,他说:“朝廷派戴若思任征西将军,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领司州刺史,镇守1合肥,皇上命我给他当参军。”
祖逖吃惊地说:“你也要走吗?”
桓宣没有做声。他知道,祖逖的话里,饱和了太多的成分,有惊异,有留恋,有失望,有无奈……令桓宣无法回答,无法面对。最后,他搜肠刮肚,好容易找出了一句没滋没味的话:“我们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我会回护你的。”说出来,马上又后悔了。
祖逖的心刹时被掏空了,他长叹一声:“走吧,都走吧!”
过了几天,戴若思从合肥派人来,请豫州刺史祖逖前去商量军机大事。人家是封疆大吏,官大一级压死人,敢不听命吗?用一个‘请’字已经是格外客气了。
祖逖到了合肥,戴若思先让桓宣接待他。两个患难与共的战友异地相见,自然十分亲热,桓宣乘机对祖逖说:“戴若思这个人,虽然很有名气,但他疏于谋略,更无远见,他的脑袋长在别人身上,别人说什么他就附和什么。前些年陆机到洛阳去,他见陆机的船上东西不少,就带领一帮子弟把陆机劫了。陆机在船上说:‘我看你这人很有才器,干嘛非要抢劫呢?’于是他就把东西还给陆机,随他一起到洛阳去了。在朝廷里他也只知道逢迎皇上,皇上说什么,他也说什么,是一条温顺的狗,深得皇上青睐,这次出镇合肥,明里是抗击外族侵犯,暗里是制衡王敦。”
戴若思进来了。此人倒也气宇轩昂,他对祖逖格外热情,拱手见礼之后,还拉着祖逖的手说个不停:“哎呀老兄,可见到你了,建业一别,转眼就是八年,你怎么一次都没有回去?可见老兄一心扑在收复中原的大业上,这几年的情况,桓参军都跟我讲了,几年奋战,规复河南,老兄功不可没,皇上也大加赞赏。兄弟我这次出镇合肥,督都六州诸军事,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今后还要仰仗老兄多多扶持。今天老兄大驾光临,兄弟我备了一杯薄酒,咱们喝它个一醉方休。请,请。”
酒宴之上,戴若思不断地为祖逖敬酒,布菜,异常地殷勤,桓宣倒乐得在一旁观看他的表演。
酒过三巡,祖逖故意问道:“戴将军,阁下此次出镇合肥,既然是抗击外族侵犯,不知做何部署?”
“啊,不不,”戴若思对随侍在酒桌旁边的官妓使了个眼色,官妓们出去了。戴若思把嘴伸到祖逖的耳朵边上,“兄弟我这次出来,名为抗击外族入侵,实则防范王敦。”
“呃?”祖逖假装不解。
戴若思接着讲了王敦的各种不轨行为,然后说:“这话只有在座的我们三个人知道,事关机密,希望老兄密切配合。”
“怎么配合?”
“请老兄把你的军队全部调往平阳,威慑王敦。”戴若思所说的这个平阳不是后汉的国都那个平阳,而是今天的信阳。
祖逖惊出一身冷汗:“北伐怎么办?北方的大片国土怎么办?不要了?”
“不是不要,事有轻重缓急,如果王敦叛乱,朝廷危急,没了朝廷,没了皇上,我们给谁作臣子去?”
祖逖原以为只是给他派了个顶头上司,受谁领导对他来说倒无所谓,可戴若思还要打他军队的主意,这实际上是剥夺了祖逖北伐的指挥权。事关北伐大业,祖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严肃地说:“北伐军南下,石勒势必乘虚而入,卷土重来,几年来收复的国土又要重新失去,中原百姓就又要生活在石勒军队的铁蹄之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孰轻孰重?孰急孰缓?”
戴若思见祖逖板起脸来,也就针锋相对地说道:“孰轻孰重,皇上说了算,我想,士稚兄不想抗旨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桓宣急忙给祖逖使了个眼色,祖逖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他怏怏地回到了雍丘。
祖逖让于晗把冯铁、韩潜、卫策、冯宠集合到雍丘,向他们通报了合肥之行的结果。话刚落音,几个人立刻炸了锅,由不解到牢骚,由牢骚到愤怒,最后一致决定:不去!
祖逖回到雍丘以后,静下心来权衡了一下,看来事情没有变通的余地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凭一时意气和朝廷对抗,会招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北伐本来是为朝廷收复失地,为北伐再和朝廷闹翻,绝不是明智之举。他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讲了,几个人还是异口同声地说:不去!祖逖没办法,只好一个一个地劝说,他对卫策说,你是朝廷大臣之后,你的前辈历来是忠于朝廷的,你要延续你的家风,维护家族的声誉和地位。他对韩潜说,你出身草莽,好容易改邪归正,在军中谋得一个职位,不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总不能重回白云山吧?他又对冯宠说,你本来是个渔民,是北伐让你改换门庭,由渔民变成了将领,何不忍一时之气,继续谋一个更好的前程呢?看看三个人都有些松动,他扭头要对冯铁说话,冯铁拦住他,说道:“你不必说了,我知道你是好心好意为我们着想,我是个嵩山的百姓,因为敬仰你,因为你抗击石勒,保护百姓,才投奔了你。现在你有难处,我们也不难为你,让他们几个去平阳,服从朝廷调遣。我呢,回我的嵩山,既然朝廷不再保护我们了,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吧,有我和我的嵩山营在,石勒是奈何不了嵩山的。”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几天之后,卫策、韩潜、冯宠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在雍丘集合。经过几年在战争中的发展,每个营也有两三千人了。
祖逖亲自把他们送出雍丘城外,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队伍渐行渐远,看不见了,祖逖还在看着,看着……
忽然,他感到心里一阵强烈的涌动,一股热流涌上喉咙,他没有压住,一口鲜血从嘴里喷涌而出,他眼前一黑,急忙蹲在地下。
冯铁急忙把他扶住,命人抬回住所。
祖逖醒过来,看见冯铁站在他的床前,问道:“你怎么还没走?”
冯铁说:“我走了你怎么办?”
祖逖病了。
几年来,祖逖经过了太多的变故,好友被杀,亲人离散,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倒使得他更加坚强,因为他有他的精神支柱:北伐,收复失地。如今,他的军队被人夺去了,他的事业被人强行中断了,北伐没有希望了,几年浴血奋战的成果将付诸东流,他的精神支柱垮塌了。正如郭文所说的那样,一旦被釜底抽薪,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被自己阵营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打垮了!
这几天,冯铁把他的嵩山营从虎牢关撤回雍丘,以防不测。
冯铁把雍丘、浚仪、尉氏各地有名的医生都请过来为祖逖治病,没日没夜地在他身边侍候,一个多月下来,仍不见起色。急得冯铁束手无策。
一个溽热的傍晚,知了热得躲在树叶下停止了鸣叫。冯铁为躺在床上的祖逖不停地搧着扇子。一辆轿车(注:中国古代一种上面有轿厢的马车。)驰进大门。青萍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跳下车来。
冯铁迎出来,说道:“夫人,你来了?”
青萍点点头,径直走进屋里。
祖逖睁开眼睛,看见青萍,勉强一笑。
青萍说:“我把儿子给你送来了。”说着把婴儿放在祖逖身边。
祖逖撑起半个身子,仔细端详着这个红朴朴的小东西。婴儿看见祖逖,笑了一下,接着“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祖逖问:“我的儿子?”
青萍说:“你的儿子,刚过满月。”
祖逖伸手想抱抱儿子,又抱不起来。青萍把婴儿抱起来,放到祖逖怀里,祖逖高兴地说:“我的儿子,我又有儿子了。看来老天不想绝我祖逖。”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带儿子呢?冯将军,雇一辆轿车,把他送回淮阴去,让许夫人抚养他吧。”
青萍说:“用我带来的车送吧。”
祖逖摇摇头:“不用了。”他知道银屏肯定在车上,是她护送孩子过来的,只是不能见他,银屏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怎么能再让她经受面见许夫人的尴尬?
青萍打发走成皋来的马车,回到屋里,对祖逖说:“我送他去淮阴。”
祖逖感激地点点头。青萍说:“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祖逖想了想说:“叫道重吧。道义为重。”
“好。”
冯铁雇来了马车,顺便还请了个乳母。祖逖对青萍说:“费心了。”
青萍没理他,只说:“走了,道重,我们走吧。”
过了几天,青萍回来了。告诉祖逖,许夫人收下了道重,她很喜欢。
祖逖说:“休息两天,就回成皋照顾你娘去吧。”
青萍说:“不,我不回去了。姐姐说,你在生病,身边不能没有一个女人照顾。”她凑到祖逖耳边说,“这一次,我是心甘情愿为姐姐当替身来了。”
祖逖苦笑了一下,摸了摸青萍的手。
祖逖的病牵延到了九月,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越发沉重了。
这天晚上,掌灯时分,门帘一挑,一个人踢踢踏踏走进来,祖逖睁眼一看,是郭文。祖逖心里“咕咚”一跳,心说:“他是给我送行来了。”
郭文坐在床边:“祖将军,我看你来了。”
祖逖说:“谢谢你。”
郭文又说:“石勒让我代他问候你。”
“他会问候我?”
“是,他是真心诚意的。他说,历数晋朝的文武官员,他最佩服的人就是你。”
“可惜呀,我们今后打不成了。”
“天意难违。”
“你回去告诉他,我病了,他可以乘虚而入。”
“你病了,他知道。但是他说,你们是朋友,他毁过一次约,欠你一个人情,他这次不会趁火打劫,只要你在一天,他绝不踏过黄河一步。”
祖逖笑了笑,没有说话。
说话多了,祖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
突然,他喊道:“冯将军,朝廷来人了,快快接旨!”
冯铁听到喊声,走进来,四下看了看,除了郭文,一个人影也没有,知道他在梦呓。过了一会儿,又听他喊道:“祖士稚谢谢皇上。”
冯铁看见祖逖平时腊黄的脸上显现出了红晕,并且兴高采烈地说:“这回好了,皇上派人前来下旨,答应恢复北伐军,允许我们北渡黄河!好,好……”
祖逖说完,高兴地闭上了眼睛。
同一个晚上。远在武昌的郭璞在大将军府的后花园里夜观天象。郭璞这时已经被王敦从朝廷里要到武昌,任著作郎。他正在凝神之际,王敦在钱凤的引导下走进后花园。钱凤一见郭璞,开口问道:“大将军不日就要有大的举动,命你预测一下成功还是失败。”郭璞说:“说实话还是说好话?”钱凤说:“当然是说实话。”郭璞说:“败。”钱凤说:“你……”郭璞说:“天意难违。”钱凤还要说什么,王敦拦住他,问郭璞:“著作郎还观测到了什么?”郭璞答道:“豫州分野有一颗巨星坠落,折损了一员大将,唉,可惜呀。”“是谁?”“豫州刺史祖逖。”“可惜吗?”“太可惜了。”
王敦眼里露出一道凶光:“著作郎难道就不为自己可惜吗?”郭璞坦然答道:“生死由命。我此生专攻经术,曾以此游历大江南北,也曾在朝为官,又有娇妻相伴,死而无憾。”“你可预测到你的死期?”“今日此时。”“那我就成全你。”钱凤对身后的护卫说:“还不动手!”正在祖逖闭上眼睛之时,郭璞的人头滚落在地。祖逖的死讯传出,豫州大地一片悲声。先是雍丘的百姓听到噩耗之后,纷纷赶来,不论男女老少,跪在祖逖的灵柩前痛哭失声。继而浚仪、尉氏、荥阳、梁国、谯城、太丘各地的百姓也陆续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烧化纸钱的烟尘弥漫在雍丘上空,遮天蔽日。
在祖逖病重期间,雍丘的百姓就从雍丘的一座大庙里伐了几棵粗大的柏树,为他做了一副棺廓,上了几道油漆,此刻就停放在曾经为于晗和张依依举办婚礼的小广场上。
灵堂布置得简朴大方,两旁是冯铁为他拟就的一副满怀激愤的挽联:
大业未了英雄身死
死而有憾
山河破碎百姓涂炭
谁来拯救
后事由冯铁一力主持,卫策、韩潜、冯宠从平阳赶回来了,李矩、郭默、箕澹、赵固从荥阳、河内、洛阳赶来了,桓宣从合肥赶来了,樊雅、谢浮从谯城、太丘赶来了,李产、祖约从淮阴赶来了,他们跪在一侧为祖逖守灵;青萍和张依依在另一侧。
七天之后发丧。本来说好由老文士撰写祭文,但老文士这几天悲痛过度,精神恍惚,居然没有完成,今天一早,他急中生智,找出楚辞中屈原的一篇《国殇》,作了祖逖的祭文。他站在祖逖灵前,神情虔诚,念得抑扬顿锉:“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是一首歌颂为国捐躯的将士的诗篇,当代的读者大概不容易看明白,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拿着吴国出产的戈,披着用犀牛皮制作的铠甲,车毂交错,短兵相接,旌旗蔽日,敌人众多,箭矢交相坠落,士卒争先恐后。敌人侵犯我方的阵地,冲击践踏我方的队伍,左边的骖马(古代的战车一般由四匹马拉着,中间的两匹叫服马,两边的两匹叫骖马)被杀死,右边的骖马被敌人的兵刃砍伤,士卒们埋住战车的两个轮子,系住拉战车的四匹马,拿起鼓槌敲响战鼓,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直杀得天昏地暗,神灵发怒。严酷的战斗中,将士全部被杀死,尸骨丢弃在荒野上.征战的将士不能再回来了,遥远的荒野上一片萧杀景象,将士们虽然牺牲了,仍然带剑持弓;虽然身首分离,没有一点恐惧,真是勇敢而又英武,自始至终凛然不可侵犯。勇士们虽然身死,但他们的英灵永远不会泯灭,他们的魂魄将成为鬼中的雄杰。”
出殡时,张凡老头找到冯铁,他说:“刺史大人的亲人都不在身边,让于晗两口子给他披麻戴孝吧。”冯铁同意了。于晗和张依依扛着引魂幡,走在前面,嵩山营的士兵们抬着祖逖的灵柩,和祖逖一起出生入死抗击石勒的将领们跟在灵柩的后面。送葬的队伍从雍丘城一直排到墓地。墓地在雍丘城外一块高地上,墓地前面,雍丘的工匠们没日没夜地为祖逖建了一座祠堂,塑了像,立了碑。葬礼之后,李矩、郭默、箕澹、赵固、樊雅、谢浮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了,桓宣、冯铁、卫策、韩潜、冯宠和青萍回到祖逖居住的屋子,和祖逖的故居告别。他们整理了祖逖的遗物,除了一把长剑和他随身携带的酒葫芦之外,别无长物,他们交给青萍带走了。之后,桓宣回了合肥,卫策、冯宠、韩潜回了平阳,冯铁又在祖逖的墓前盘桓了一天,带着他的嵩山营回嵩山去了。
几天之后,一个月黑之夜,一个白马红袍的影子飞驰到祖逖墓前,在墓碑前伫立良久,凄然说道:“士稚,慢走,银屏随你去了。”然后,一头撞向墓碑。一缕香魂向夜空飘荡而去……
补 记
祖逖之死,令两个人抚掌大笑。一个是王敦,他素来忌惮祖逖,不敢贸然行动,没了祖逖,他就肆无忌惮了,不久,他起兵叛乱,攻进石头城,杀了朝廷大臣周顗和戴若思,擅自任命了朝廷大臣,然后扬长而去,后来病死于武昌。
另一个是石勒,他在祖逖死后,挥师渡河,轻而易举地侵占了被祖逖收复的中原大地,祖逖几年浴血奋战的成果毁于一旦。当他打到雍丘的时候,他来到祖逖的墓地,在祖逖墓前虔诚地祭祀了一番。
祖逖死后,朝廷命祖约继任豫州刺史。六年以后,他伙同苏峻造反,失败后投奔了石勒,石勒嫌他不忠,杀了他的全家。行刑前,已经是石勒手下的一名高级将领的王安看见囚犯中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经过询问,他知道这孩子是祖逖的儿子道重,于是他把道重悄悄地救出来,托一户人家收养,成人以后,送回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