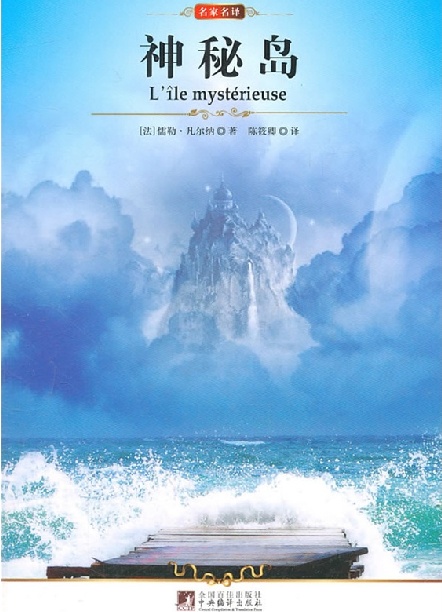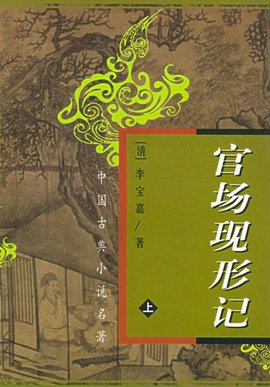人到中年,疲惫是常态:工作、孩子、家庭,三座大山无论哪一座,都足够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过往的人生偶像似乎都不管用了,细细一看,他们在我们这个年纪也难以幸免地一地鸡毛。张爱玲在我这个年纪为了绿卡嫁美国人然后被联邦调查局核查老公欠款案,苦透。林徽因在我这个年纪天天盘算全家生计,“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苦透。周树人在我这个年纪和兄弟们一起奋力凑钱争取全款北京西城学区房。他绝对想不到,过不了几年,房贷没还完,他就要被冤枉看弟媳妇洗澡被赶出家门,苦透。至于萧红……哦,她压根就没活到我这个年纪。
到了这时候,能救赎我的,似乎只有林语堂。
林语堂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东方。纽约大都会艺术馆举办过一场语堂旧藏书画展览,为展览出的书叫Straddling East and West:Lin Yutang, A Modern Literatus(《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一位现代的文人》),导言这样评价林语堂:“中英文写作都好到一个地步,能让沉淀于一种语言中的奥妙与灵光,超脱翻译,化身为另外一种语言,林语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一人。”《纽约时报》的评语是:“集作家、学者、教育家、人文主义者于一身的林语堂博士,为世界上中英这两个最大的语言团体,说中文和说英文的人们的沟通,打造的一座里程碑。”他曾经是派克笔的全球代言人,在中国嘉德香港2021春拍的“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专题中,我们得以看到林语堂当年的代言广告。
在华语世界里,林语堂最多被提起的是“幽默大师”这个称号。实际上,他的幽默是淡淡的,那些包袱到今天来讲都响不了,比起老舍差了很多。对于别人赞美他为“幽默大师”,老林也谦虚地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究其根源,其实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将“humor”定义成“幽默”的人。
1970年,唐德刚到台湾去吃林语堂的饭局,在一家嘈杂的大酒店内,他问侍应生:“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结果侍应生把两眼一瞪,大声反问一句说:“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大陆对于林语堂的认知也不算广泛。我读书时有一大快乐,从语文课本鲁迅文章的批注里寻找老鲁骂人线索,基本得出一个规律:老鲁骂的人,多半都很有趣,写的文章也不错,比如沈从文,比如梁实秋,比如林语堂。
林语堂敢硬杠老鲁,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和老鲁对骂过“畜生”的人。但是老鲁公开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针对林语堂,林语堂就不回应,公开辱骂,对于林语堂来说不够体面。梁实秋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但是老鲁的绰号“白象”,也是林语堂取的。要知道老鲁可是起绰号的圣手,他对这个绰号颇为满意,所以许广平管老鲁叫“小白象”,老鲁后来管儿子叫“小红象”。
老鲁去世之后,梁实秋阴阳怪气在《雅舍小品·病》里讽刺:“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我看了有些反感,反过来看看林语堂,写一篇《鲁迅之死》,字字句句完全深知老鲁,可以说是老鲁知己:“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我有个朋友说,面对世界,老鲁给出的药方是:“战斗吧!破釜沉舟打赢最后一战!”胡适说:“看能把房子修修补补凑合过呗!”而老林则说:“嗨,吃好喝好。”
林语堂绝对是庄子的学徒。
所以他认为,不要为了有用而读书:“人如读书即会有风韵,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唯一目标。唯有抱着这个目标去读书,方可称为知道读书之术。一个人并不是为了要使心智进步而读书,因为读书之时如怀着这个念头,读书的一切乐趣便完全丧失了。犯这一类毛病的人必在自己的心中说,我必须读莎士比亚,我必须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我必须读艾略特博士(Dr. Eliot)的全部著作,以便可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以为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有学问者。”
所以他认为,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生活,“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你这就叫懂得了如何生活。
林语堂看待世界是举重若轻的,但这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悲伤。
嘉德春拍“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的书信里,藏着他巨大的伤痛。1971年1月19日中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宴请林语堂,忽然有人急匆匆跑来报告,工人去打扫林语堂长女林如斯的房间时,发现她吊在窗帘杆上,桌上的一杯茶水尚留余温。次女林太乙回忆,当她们一家从香港赶到台北父母家中时,“父亲扑到我身上大哭起来,母亲扑在妹妹身上也大哭起来。顿时我觉得,我们和父母对调了位置,在此以前是他们扶持我们,现在我们要扶持他们了。”林如斯因为一段不幸的婚姻而长期受抑郁症困扰,最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间,留下的遗书是写给父母的:“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
林太太廖翠凤从此精神崩溃,整日喃喃自语。对人讲话只说厦门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林太乙也曾经问父亲:“人生什么意思?”据说,林语堂沉默良久,而后缓缓回答:“活着要快乐,要快乐地活下去。”
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调整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过着快乐的生活。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所以他平静地处理着女儿的遗物,为女儿编辑遗作并且发表悼念诗。只在写给“国府外交部”自述赴港原因上,林语堂忽然失去了平静,那些句子涂了改,改了划去,长女如斯后面,他始终不忍写出“弃世”二字,直到最后,“丧期”两字,凄凉恳切,令观者动容。庄子在妻子死了之后击盆而歌,林语堂在给甥媳妇陈守荆的信里,故作乐观地筹划着带太太去散心的欧洲之旅,说“只去风景优美之处”。忽然想起《金瓶梅》里,西门庆在李瓶儿去世之后对戏班说,不管演什么戏,“只要热闹”。
但即便如此,他仍旧用一颗真心,温暖着他的读者。1974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八十自叙》,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里面充满真诚。他磊落地说:“我以前提过我爱我们坂仔村里的赖柏英。小时候儿,我们一齐捉鲦鱼,捉螯虾,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的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以前提过,大约指的是他的英文小说Juniper Loa(《赖柏英》)。赖柏英是他的青梅竹马,他邀请她和自己一起走出家乡,外出读书,她却拒绝了。他未知她的生死,仍旧挂念:“柏英不知尚在否,当已七十九,想将来或借苏珍珠转问。”
赖柏英是真名,不过,不知是他年岁已久,还是刻意为之,他真正的恋人其实是赖柏英的姐姐赖桂英。陈煜斓在《李代桃僵话柏英识——林语堂初恋情人考》里查证到,赖柏英比林语堂小十八岁,林语堂去圣约翰读书时,赖柏英尚未出生。同时,根据《八十自叙》里所说,赖柏英“嫁给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而赖柏英的丈夫叫蔡文明,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厦门一所中学教书,并不是商人。反而赖柏英的大姐嫁的是开典当行的人,名叫林英杰。据说,林英杰后来性情暴躁,经常家暴,赖桂英时常对自己的养女说:“如果我当时嫁给林语堂,我也不会现在这么凄惨。”
林语堂在被赖桂英拒绝之后,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爱上了同学的妹妹陈锦端。这一次,郎才女貌,可惜,反对的是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他嫌弃林语堂出身穷牧师的家庭,但陈爸爸的拆散招数非常不同凡响,他把隔壁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林语堂的两段恋情,或因女方不愿离开家乡,或因女方亲属嫌贫爱富而宣告失败,最终,他选择了那个不嫌弃他的姑娘。结婚之后,他把婚书付之一炬:
我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诚然!诚然!
——林语堂《八十自叙》
这是一个承诺,林语堂遵守了一辈子。他无比珍惜这场婚姻。我曾经在阳明山参观过林语堂故居,发现屋子里柚木椅子的靠背上,都刻有一个小篆的“凤”字——这是廖翠凤的名字。他把太太的名字做成家徽,并且告诉大家:“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她也时刻包容他,包容他的童心不改,包容他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停滞写作,她包容他一再讲起他的爱人陈锦端,她甚至会主动讲起陈锦端的故事——这种坦诚,证明了廖翠凤的自信。
世上没有不吵过架的夫妇。假定你们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请你们先别结婚,长几年见识再来不迟。你们还不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性别不同、兴趣不同、本来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假定你们不吵架,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你们此去要一同吃,一同住,一同睡,一同起床,一同玩。世上哪有习惯、口味、性欲、嗜好、志趣若合符节的两个人。
——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林语堂的朋友赛珍珠曾经问:“你的婚姻怎么样?没问题吗?”林语堂笃定地答:“没问题,妻子允许我在床上抽烟。”
当我们对人生充满倦怠的时候,读林语堂的时刻到了。林语堂告诉你,不管我们是有意或无意,在这尘世中一律是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既然是一场戏,不妨潇洒一点,悠闲一点,舒服一点。林语堂说,衣服不妨穿得宽松一点,读书不要想着有什么用,交朋友不要那么有目的性,时常听听鸟鸣看看花朵,而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
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一切满不在乎,而是我们对于人生,用不在乎的态度在乎地生活。要快乐,但这快乐,并不一定代表着财富,代表着爱情,代表着鸡娃。一切都来自你的内心,这答案林语堂在《京华烟云》里已经告诉你了:
人本过客来无处,
休说故里在何方。
随遇而安无不可,
人间到处有花香。
参考文献:
林太乙:《林语堂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陈煜斓:《李代桃僵话柏英识》,文艺报201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