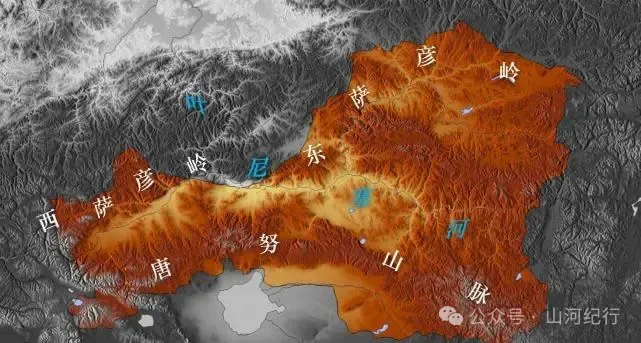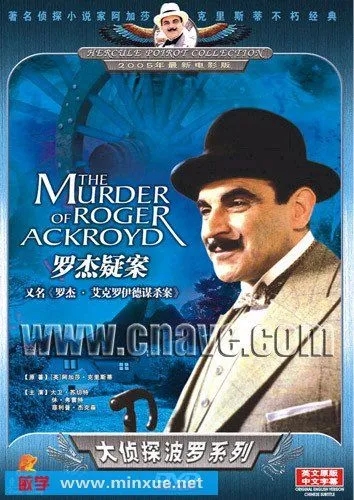弗洛伊德的经典社会学家身份,近些年逐渐为国内社会理论普遍承认。这位近代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和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站在同一时代方阵,面向现代个体、社会与国家的生存困境,寻求生活意义的重建。他的思想亦同经典社会理论的议题存在诸多交涉,不光针对现代社会的秩序与风尚,更是在关乎西方文明之根底问题上展开对话,因为社会学本就是文明研究的学问,弗洛伊德的精神遗产理应被视作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相比任何具体的社会学话题,弗洛伊德的思考方式本身,构成对这门学科的启迪。我们习惯于将包括他的思想在内的一切学问类型化,定义为“一种”学术流派,但恰恰忽视了,他的思考与同时代的现象学革命一样,是正在进行时的存在活动。正像他在《精神分析引论》里讲到的那样,“精神分析之为科学,其特点在于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所要研究的题材”。在这里,方法并非源自科学研究预先的设定,而发端于人对自身生活的世界及其历史的领会。
弗洛伊德之思,充当了我们理解精神分析甚至社会学的题眼。而他的“思”,从一开始就在回应和反思近代西方文明的存在论基础——笛卡尔的“我思”(cogito)。他的精神分析,首先作为自我分析,重新启动了“我思”的进程,只是不像笛卡尔那样在房间里、火炉旁,构建一个人的纯粹思想世界,而是主动将自己抛到社会与文明的洪流里,经历奥德修斯式的冒险。同这个出发点相关,弗洛伊德热衷于自传的写作,如盖伊(Peter Gay)所说,他的成名作《梦的解析》就是一部真正的自传,他也善于为一切关于他人案例的解读点染自己的生活之影。他的“我思”带着无比暧昧(ambivalence)的色彩,既是对现代社会犹如迷宫一般被重重审查机制遮蔽的刻画,也在勇敢地曲折地敞开自己。
这种以自我反思为起点与基础的社会学反思,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学家如米尔斯和布迪厄的思想惯习之中,构成了所谓“社会学想象力”的题中之义。然而弗洛伊德的社会学之思有何更为深刻之处呢?
他的思,由发问发出且随发问开展。不过发问从一开始不等于“一个问题”,更非一个命题,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发问活动本身就是完整的。不过,对弗洛伊德而言更重要的事实是:问的声音是第一位的。譬如,他在讲解精神分析技艺的时候,特别强调,精神分析师促成患者自由联想的时候,不能出现在患者眼前,而只能坐在躺椅背后,通过声音来召唤患者,让其固着的自我历史从无意识的深渊浮现在意识中,变得可视可感。换言之,梦就是问与被问的声音作为氛围(atmosphere)的剧场,是弗洛伊德构建的社会原型(Urbild)。这当然可以归于叔本华和尼采的启示,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叔本华将音乐抬升至形而上学的最高地位,认为只有声音才能呈现意志,而弗洛伊德编织的梦的戏剧,萦绕着尼采沉醉的古希腊悲剧的酒神音乐氛围。
然而,精神分析又是科学。在声音之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问”的关键,在于使自我形成了思维的双方,“我”(Ich)和“他我”(Es),一问一答辩证性地推进,却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问自答,问和答之间是异质的,只有存在着异质性,才有移情和抵抗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有遭遇治疗失败的可能,进而理智地予以对待和解决。这更意味着:在问的开端,承认聆听要比问更原初,此为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之为“科学”(Wissenschaft)的最重要依据。
在欧洲社会学诞生的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紧张的争执,社会学的智识追求之一,便是要调和两者。德国哲学家洛维特(Karl L?觟with)在对欧洲19世纪精神史的重要论述中指出,在古典主义时代的黑格尔和歌德之后,自然与精神合一的世界观分裂了。弗洛伊德则和古典社会学家们一样,坚持不懈地谋求建立总体性的科学,精神分析就超越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问题域。
弗洛伊德的重要进路,就是他的“我思”蕴含着古典文学与人文主义的魅力,而文学弥合了自然和人文的张力。他从灵魂深处聆听到了来自古典文学最隐秘的声音。在《梦的解析》这部有着自传性质的作品里,弗洛伊德声称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那里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梦的终极秘密,呼应了每个人内心里最真实的欲望。但先于戏剧情节而挑动弗洛伊德心弦的,或许是追问人性的永恒声音,就像人面兽身提出的谜题,像俄狄浦斯王对命运的无数次追问,抑或哈姆雷特犹疑不决时的反复、延宕,或仅仅是《哈姆雷特》剧本开篇的那声音——“谁在那儿?”
在盖伊的《弗洛伊德传》里,作者提及歌德的《论自然》对弗洛伊德早年的职业选择影响很大,歌德“对自然的情欲化赞叹和情感上的歌颂,把自然当成一位包容甚至有点专制压迫,又不断更新着的母亲”,令弗洛伊德极为着迷。这个自然的母亲,可谓思的他我甚至社会之文明的原型。在早年写给朋友弗卢斯的信里,弗洛伊德写道:“我将探索自然上千年的历史,或许还能偷听它和人类之间永恒的诉讼,我将和每一个愿意了解的人分享我的胜利果实。”他后来在《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就回应了早年考虑的“必然性”,认为遵循这个必然性来思考,来获知人类神秘的幻想,此幻象乃揭示被文明塑造并改装了的真正知识的起点之所在:“人类中有这么一类人,分配给这一类人的任务不是神,而是一位严厉的女神——必然——让他们讲述他们遭受了什么痛苦,以及什么东西给他们带来了幸福,他们是精神病的受害者,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幻想夹杂在其他事情中间告诉医生,他们希望医生用精神疗法治好他们的病。这是我们的知识的最好来源。”
正是因为聆听对方的声音,灵魂得以激动起来,从黑暗和旋涡一般的无意识中走到意识前台,从无时间的状态中涌现出来,并且在持续涌动,一次次地重演社会和文明进程的戏剧。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所思的一个人的生命史,同整个社会与文明的历史完全一致。灵魂的涌动是有方向的、有规则的,它由幻想(illusion)回溯到人类童年,解开为社会与文明不断固着的情结(症结),也昭示着人类健康的未来。
精神分析的唯一主题即人类的灵魂进程。审视弗洛伊德的社会学之思,提示我们在不断反观社会理论史的时候,倒转发问的方式,即问题的关键不在弗洛伊德何以是一位社会学家,毋宁反过来:社会学何以是弗洛伊德式的?或者借现象学的表述方式来问:社会学何以在弗洛伊德所“投射”的世界中存在?为何需经弗洛伊德这个指引,社会学才通达学术史甚至生活的因缘整体?
来源:中国社科网(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