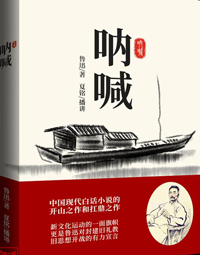王夫之的唯物主义
王夫之(王船山,1619一1692)的哲学,到他身后两百年始为人所重视。船山是一位学者的儿子,他曾应试科举,并在1642年中举人。其时满人已入主中国。当1648年,清军侵至船山原籍湖南,他曾组织一微小兵力抵抗,冀能挽救明朝于危亡。失败之余,他以三十三岁之龄,隐居原籍附近一山中,历四十年之久,一生尽瘁于撰述,著作涵盖古代与当代、道家、佛家以及儒学。
但他为人所不知几达百年之久。他的许多著述―今存者有七十七种―直至19世纪中叶始有出版。而其时引人注意者,仅在于他勇敢的政治学说及其对历史所作的不合正统的诠释。直到今日,他独特的哲学思想始为人所激赏。除了意识形态的考虑以外,船山哲学之重要性实不止一端。
他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宋代唯理派的新儒学与明代唯心派的新儒学,他都攻击,他走向一种新方向。他如此做法―虽非直接影响―为清代的中国思想导夫先路。甚至可以说,船山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时期。
船山反对唯理与唯心两派的中心论旨,亦即理是普遍而超越,并且先于气之说。他以为理同于气、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而只是事物之条理节文。天地间并无超越与抽象之物如太极或天理者。所谓太极、天理以及心、性,俱必在气上说。
这种哲学,大体同于张载。船山确可称为张载之传人。但是实际上船山有超越于张载者。船山所追求的,不仅是物质性,而且是物质的具体性。依船山之说,横渠之太虚并非一抽象之实体,而为具体;因为道家“无”的观念过于抽象,船山乃强烈地予以反对。结果,船山最有名的格言就是“天下惟器而已”。“器”字,大有别于意指物质力之“气” 。气是一种物质力量,意指事物所由构成的一般质料,而器是具体事物,意指殊别的可捉摸的客观对象或系统。
这样理解“器”时,它不仅意指个别的具体事物,更是同样意指体系或建制。器不仅是简单的质料,而且它具有秩序,并表现其内在的理。所以道、理之与器,是一实体的两面。有器必有其理,未有独立于器外之理也。
船山既将理置于次要地位,那么他自然就推翻了宋明新儒家另一主要思想―理欲相对,以及以理制欲。虽说船山也承认人欲必须正当,但他不接受理欲相对立的观点。至于正当的人欲如何可以获致,他肯定了器本身即具有趋于正当的倾向。
在某方面,船山保持了宋明新儒家的传统,并推前一步,此即日新之说。亦如他以前的新儒家,船山视宇宙为一生生不息之历程。在这个历程里,气之阴与阳不断地融合,如是,气与理俱日新不已。这种哲学适用于政府与历史上,导致了反传统而大胆的结论。理既只是存现于具体事物与制度之中,那么宋明新儒家所制定为历史与社会之典范的“天理”,就根本不存在了。不仅如此,现今之器,既不同于往昔,往昔即不能为现今之范例;因之,船山反对封建制度。他也深信时代愈晚,社会就愈文明。这种进步与演化的思想,是不错的。但是他
又认为,既然器从不孤立,而是在时间中彼此关联、不断变迁,此则是依一定之理进行的,这是势,有聪明才智者应顺势。于此,在他的激进哲学里,吾人又见其保守的一面。
由前所述,我们可知,船山远离于新儒家之教的同时,在若干限度内,他仍维持新儒家的传统。他虽明确地反阳明,但仍近于朱熹。在他当时,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他并不是第一个主张理同于气的人。刘宗周( 1578一1645)亦以此教人,与船山同时之黄宗羲也曾有同样的看法。但没有人像他那样以此观念为基础来建立他的全部哲学系统。他之反理而主器,反对天理而主人欲,开启了颜元与戴震的先河,也给予谭嗣同相当的影响。

颜元之实用性的儒学
由于对宋明时代思辨式的新儒学的反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受传教士传人西洋知识的影响,儒学在17世纪乃趋向于实学与客观真理。顾炎武与阎若球这两位当代儒家领导人,攻击宋明新儒学,并且提倡实践的与客观的研究,此外吾人已知王夫之也彻底地与早期新儒学分道扬镰;颜元较之以上诸儒则尤甚。
虽然有此新精神,但那时的一般趋势,还是调停于朱熹的唯理学派与王阳明的唯心学派之间。不过,颜元则全置朱王两派于不顾,而直接追复于孔孟。
颜元认为新儒家的静坐与读书是浪费时间,也是社会退步的确实缘由。在颜元,理、性、命与诚意,以及类似的宋明新儒家核心课题,只能求之于实际学艺中,如音乐、礼仪、农业及兵法。他本人即习医学,后来与门弟子共耕于吠亩。他教人算学、射御、举重、歌与舞等等,他的书院分设经史、文事、武备以及艺能四厅。一如王夫之,他深信理不离于气。他反对宋明新儒家之说,坚主气质之性亦如人性本身一样是善的。
格物并非如朱熹的穷究于理,也非如阳明的省察于心,而是透过真实的经验学习,解决实际的问题。没有人如此毫不调停地反对在他之前已存在了数世纪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地注重实际的经验。然而颜元亦如王夫之,也不能摆脱他那时代的思想模式。
他回溯孔孟的思想。并提倡恢复先秦的井田制度。他称实务为“六府”,即水、火、金、木、土、敦;及“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与“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古代经典中同类的教义。颜元虽具有活力,但他的教义仍被这些保守思想所冲淡,不能发展为一强有力的运动。
虽其弟子李邵阐扬师说,其显赫亦如其师,但颜元的信徒很少。由于他所攻击的目标,像朱熹学说、读书、词章这些仍盛行于儒门之中,因而他这学派并未能持久。他之攻击朱子,也不为人所接受。不过他的新思想却激发了戴震,也大大地鼓动了正在日渐增长的实学趋向。
颜元的哲学思想是十分素朴而肤浅的,他并不真是一位哲学家。
戴震“理之哲学” ——秩序
在18世纪的中国,朱子唯理派的新儒家仍然具有影响力,但其趋势已然反其道而行。这种运动变得非常强烈而有力,发韧于顾炎武与阎若球,他们这时候倾注于研究客观真理而放弃思辨之学。没有证据,学者们拒绝接受任何事务。他们唯一的兴趣,便是从具体事实中去求得真理。因之,此一运动称之为“考证学”。虽然他们兴趣之中心仍在儒家经典,但他们都深人地从事于具体科目的研究,像训话学、历史、天文学、数学、地理、古籍校勘,等等。他们反对宋代的抽象学问,唯理派新儒家便是其中主要的产物,他们也投下心力于汉代的早期经籍研究以求证。职是之故,这种运动亦名汉学。就哲学上的意义来讲,便是反对朱熹,而在其方法学上来讲,采用客观、归纳与批判的方法。整个运动中的首脑人物便是戴震。
事实上,戴震最好称之为考证学派之大师,远甚于他之为一哲学家。但他的考证与哲学实在不能分开,因为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他在数学、天文、水利、音韵、校勘、典籍辨伪等方面都是专家。在这些研究中,他批判地引用演绎法与比较法。和他同时代学者为考证而考证大不相同的是,戴震把这些方法基本上视为显示真理的一种手段。同时,由于他的方法及具体的探讨,他视理为一种对具体日常事务与人事有条理、有系统的安排。很显明地,像这样心态间架的思想家,不会满意一种抽象而超越的理的观念。他说,宋明儒者视理为“必有物焉” ,但对戴震而言,理不过是事物之条理,所谓事物,他认为“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
这种视理为条理的观念可追溯自汉代,所以戴震在这方面并非首创者。但没有人像他把这个观念发挥得这样详尽,也没有人像他一样推衍得这样强而有力。以这样一个理之观念为前提,他进一步认为穷理之道,并非如朱熹所说;理智的思辨,亦非如阳明所说,自心的内省,而是用一种批判地、分析地、不厌其烦地而且客观地来探究事务。
戴震的理之观念,也使得他强烈反对宋明新儒家有关情与欲的见解,他觉得宋明儒把情与欲说差了。在他的信念中,情不得,而理未有可得者,因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事实上,宋明儒从未如此的谴责情与欲,仅谓情欲之私与过甚,而于戴氏所称情欲之爽失,并无不同。不过,这也不容否认,当宋明新儒家比照理欲时,以理为善,而欲为恶,而戴震则不容许这样相反的看待。在这方面,他从孟子的性善说得到支持,而阐释其爽失,乃起于私。戴震既主张理乃情之不爽失者,他不得不预设一种不变的、客观的与必然的理作为准则。这就是他所谓心之所“必然”的理义原则。他并不反对普遍性之真理,除了他坚持这些理,都是确定而内在于具体与日常事物之中。
在另一方面,他传承着宋明新儒家一个重大的思想,但他也是以条理的字义解之。他亦如宋明儒一样,认为宇宙为一生生不已的绵延不断的历程。不过,这一历程,不仅是一种宇宙运作,它还是一种自然秩序,在这秩序中,可见到许多基本道德价值于其中。
戴震或是一位在清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家贫,从未中举。他到晚年始攻击朱子,那时候他才撰写《孟子字义疏证》,下列摘录俱采自该书。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中涵摄着他的大部分哲学思想。
但是,一百年来,这部书并未有任何影响,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学说不够深刻,另一部分原因则由于有清一代,对哲学兴趣亦不够浓厚。不过,到了20世纪,他突然为人所盛道,这无疑是因为他的哲学适合那时代的脉动。

康有为之大同哲学
正如所有儒家一样,康有为(1858一1927)亦试图将儒家教义在政府与社会中付诸实践。但没有一位儒者曾像他这样,为了改革而改变了孔子、儒家经典以及若干儒家基本学说中的许多观念。有许多因素,促使这种改革无法避免。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改革声浪在中国高唱人云,愈来愈感受到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的影响。对佛教的兴趣也正在复苏。古文经学家(主张维持先秦以古文所写的经书)与今文经学家(拥护以汉代隶书写定的经书)两者之间的争辩,再度兴起了。今文经学较占上风,不视孔子为先师,也不视经籍纯为历史载籍,而是视孔子为改革世界的“素王”,认为经籍中寓有他主张改革的“微言大义”。康有为更推波助澜,最后他成为这一学派之中心。除此以外,程颐的唯理主义的热情已经消歇了,学者转而渐趋于陆象山、王阳明的新儒家唯心主义,亦即转向目的取向的行动精神,而摆脱了程、朱冷冰冰的抽象思辨。康有为也深受其师朱次琦的影响,朱次琦为当时名儒,亦为陆王学之热诚崇拜者。由于以上这许多因素的凑泊,使康有为构成他非常特殊的学说,以孔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改造家,历史依三世演进,最后到乌托邦或为大同世,而“仁”就是“以太”与“电” 。
康氏以孔子为有心于托古改制的改革家,由此演至于怀疑尧舜圣王之盛业及其史迹的真实性。这样勇于否定远古相传的儒家的偶像,实质上即直趋于一种革命。康氏高足梁启超所言并不夸大,他说其师三书(译按:指《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书》),如咫风、如火山大喷火、如大地震。但有趣的是,康有为这位改革者,还是必须以古代为根据,而他的权威性本身也要以古代为权威,即使那古代权威根本就是他臆想出来的。
不管他多么保守,也被他历史进化的新观念所抵消了。三世之说并非新创,例如对康氏有重大影响的汉代今文经学派大师董仲舒即主张过。不过康有为并不像董仲舒那样视历史为循环,而视为一种进化。这种思想可能来自西方,但康氏坚以为源自孔子。
有为是在他所注《礼记》一书中,主张三世之说。他说孔子曾主张历史的进化,是由据乱世而至升平世(小康),最后至太平世(大同)。有为赞成其说,并不全是对进化新说之回应,更是为他政治的改造提供哲学根据。在19世纪80年代,有为尚年轻时即热衷于改革运动。他联合其他学者,一再地请求皇帝重造中国。在1898年发动了他戏剧性的百日维新。在这次维新里,他深信中国虽然尚未能进人大同世,但必须进人小康世。诏令已颁,从速进行政治、教育、经济及军事的改革,仿效西洋。
但为保守的慈禧太后所阻而失败,终致迫而逃命。康氏的大同世之说,是如此的激进,以至于他的《大同书》直到1935年(即康氏死后八年)始行问世。在前述《礼运注》里,已寓其义。此注写于1884一1885年。《大同书》虽以19世纪8o年代的初稿为基础,但却直至1901一1902年始完成。
无论如何,他那彻底废除国界、家庭、阶级以及各种差别的思想,相对于他的时代而言,实在太前进了,不易为人所接受。其他哲学家也有过乌托邦的思想,但康有为和他们不同,他吸收多方面的灵感―儒、耶、佛―缀成一个详细的理想社会组织与结构,如公社生活、公立儿童蒙养院、火葬并以其灰烬施肥。
这种乌托邦的哲学,其基础有二,即他的历史进化论以及他对“仁”的解释。康有为以此等同于孟子所称“不忍人之心” 。仁也是一种引力,结合所有人而为一体。它是弥漫各处的创发的力量,它是以太或电,它是生生不息,它是博爱。传统儒家中,爱由亲始,亲亲而仁民,最后仁民而爱物。大同世便是这些逐步拓展的逻辑性的极致。康有为在想象力与行动上,都相当具有革命性,但在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他还都在儒家主流之内。
【编者评述】
康有为综合了所有儒家仁的观念―仁为基本之德性,如仁是“相人偶”,如仁是“泛爱众”,如仁是“生生不息”―使得仁等同于“不忍人之心”,而显得更加有力不过,康有为不只进行综合而已,在西方科学的影响之下,他以仁同于以太与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仁第一次扩展到自然科学的领域中。他为仁增添了新意,如谓仁是吸摄之力量,仁根植于“同类之感”,所以爱由亲始,逐渐伸展至所有的人。这不仅是如孟子或新儒家们之所说,只是自然的道德情操之结果,也是吸摄力量之结果。
冯友兰以为康有为使用以太与电之吸摄观念,实不过将新儒家万物为一体之说,而附之以他并不了解的西洋物理学而已。但是康有为在此中至少引进了三个新的要素:首先,形成一体的过程,包含许多能量;其次,这是一个相互吸摄之结果;第三,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康有为在他仁说中有一缺失,即他并没有把新儒家以生意释仁的思想予以发挥,虽然他已寓有仁为种子的想法。假若他能有所发挥,那么他的学说将更具有活力。
谭嗣同之仁学
谭嗣同可以说是康有为具体而微的复制品。他也像康有为一样,追随陆王的唯心派新儒学,他冶儒、佛、基督教以及西方科学于一炉,他是位改革者,弘扬大同哲学。
谭之哲学思想,表现于所著《仁学》之中。据梁启超说,《仁学》阐扬康有为的基本思想 。谭并未入康氏之门,直到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才认识康有为。维新运动失败,康亡命海外,但谭以三十三岁之年殉难。在殉难前两年,谭经由梁启超得闻康有为之学,便自称康之弟子。自此受康氏之影响,据变为康氏仁学之传承与修正者,而且于1896一1897年,写成《仁学》一书。谭是否读过康之《大同书》原稿,并无明证,但他所闻于梁启超者,大约亦不出于《大同书》之外。
谭之作为康之传承者与修正者,谭之思想并不周全与深刻。其书庞杂而无系统,常被认为是庞杂的幻想。他以仁为博爱、为生生不息、为以太与电、为引力,这些都不过是康有为思想之复述。但谭嗣同也使这些观念更加精确细致。譬如,康有为偶以“通”释仁,谭嗣同则以此为其基本观念或“第一义” 。不过最重要的修正在于,康氏只以仁为以太,谭氏则试图建立某种体系,将仁像以太那样,视为诸元素之元素,视为不生不灭,视为存在与众生的构成分子之来源。如此将仁不仅视为实体之一性质,而且视同实体本身者,他是第一人。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一整部书专论仁之人。
没有其他中国哲学的观念像“仁”这样,经过许多有趣的发展历程。在孔子以前,仁是慈爱的特殊之德。孔子把仁转换为普遍性的德性,为众善之本。在汉代,仁训为爱、情与“相人偶”。在韩愈则训为博爱。宋代新儒家则从多方面作训,有训为公为觉与天地为一体、为爱之德、心之理、为生生不息之德、为生德之种子,等等。迫至康氏,将仁解为以太与电,谭则更谓仁为存在诸要素之不灭要素。谭氏的贡献,将仁之发展历程带到更高阶段。
张东荪之知识论
公元前3世纪以后,再没有像20世纪这种“百家争鸣”的时代了,西洋思想与反传统革命的结合,使得学术思潮向四面八方奔流。对现代西洋哲学的引介,始于严复(1853一1921)在1898年译赫骨黎(Huxle)的《天演论》,接着又译穆勒(Min)、斯宾塞(Spencer)与孟德斯鸠(Montesquicu)诸人的著作。世纪之交,叔本华(Schopenhauer)、康德(Kant)、尼采(Nietzsche)、卢梭(Rous -seau)、托尔斯泰(Tolstoi)与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诸大师的思想也输人了。
在1917年的知识启蒙运动以后,西洋学说输人的步调益为加速。接着的十年,有关于笛卡儿(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休漠(Hume)、詹姆斯(James)、柏格森(Be笔son)、马克思(Marx )等人的著作,都有中文版问世。杜威(Dewey)、罗素(Russell)和德塞斯(Dreisch)来到中国讲学,有许多杂志特刊专题介绍尼采与柏格森。组织了许多学社,甚至学校,以推动一种特定的哲学。几乎西洋思想的每一分支,都有它的代言人。詹姆斯、柏格森、奥坎(Euckeu)、怀特海(Whiehead)、霍金斯(Hocking)、席勒(Schiller)、格林( T . H . Green)、卡尔纳普(Camap)与刘易斯,各有他们的拥护者。一时间,中国人的思想几乎全盘西化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西方思想传布的同时,有人起而努力复兴并重建中国哲学。
吾人已经看到谭嗣同(1865一1898)的尝试。孙中山先生(1 866一1925)把部分儒家伦理,融会于他的政治思想之中。1921年,梁漱溟(1893一1962)保卫儒家的道德价值,其鼓动中国人的程度为当代所罕见。欧阳竟无(1871一1943)与太虚(1559一1947)两大师,许多年来致力于佛门唯识宗的复兴。当梁漱溟激起重估与复兴儒学的热潮时,梁氏并未发展出自己的哲学。欧阳竟无或太虚也都没有对佛家哲学有所增益与创新,虽然太虚亟欲尝试把佛家思想与西洋思想及现代科学予以综合。而真能重建传统哲学,获致具体成就,并能建立一家之言者,得两人焉,一为冯友兰(1895一1990 ),一为熊十力(1884一1968)。很显明地,他们的哲学都分别渊源于两大主要的新儒家倾向,唯理的与唯心的。
提倡西洋哲学的学者,远多于以中国思想为主体的学者,但前者无论在创见上或影响力上,都不及后者,一直要等到马克思主义征服中国后才改观。特别风行的是胡适所介绍并提倡的实验主义,其他如生机说、物质主义以及新实在主义。但这些西方哲学都是原封不动地被移植于中土,而未作任何调适。金岳霖(1895一1984 ),一位逻辑分析的专家,深受格林的影响,曾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逻辑系统和形而上学。
但还有一位,他吸取了大部分西洋思想,建立最具综和性和调适性的系统,而且在倾向于西洋的中国学者之中,最具重大影响的,无可争论的,莫若张东荪(1 556一1973)。张氏是自学的,由报馆杂志的编辑,而升为许多大学的教授与院长。他从未到过西方,但他中译柏拉图的《对话录》和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以及《创化论》,和其他西洋论著,而且他比之他的中国同道所读的西洋哲学之书,恐怕更多。】
他的撰述达十三种,其中他发展了一种系统,可称之为修正的康德主义、认识多元论和泛结构论。张的哲学主要形成于1929年至1947年之间,渊源于康德,但张反对康德将实体二分为散殊与统一,以及将知识的本质二分为所与(Given)与天赋(Innate)。依张氏意,知识乃感觉与料与形式以及方法论设准等的综合产物。感性、知性、心以及意识都是综合体或构造体,而构造体又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他说他已结合西方逻辑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但其系统是自成一家的。他不仅深受康德和休漠之影响,也受杜威、罗素和刘易斯之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张氏渐次地由形而上学转到知识社会学,因而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这和他1934年编纂论文集批判辩证唯物论时的反马克思立场,实是南辕北辙。但他以观念为文化产物的说法,也很容易使他去接受马克思的学说。

新理学:冯友兰
无疑的,冯友兰(1895一1990)是中国过去六十年之中最为突出的哲学家。1930年、 1934年出版两本《中国哲学史》时便崭露头角,1939年出版《新理学》,他的中国哲学大家的地位便稳固建立起来了。这是20世纪中国哲学著作中最具原创力的一种,深得广泛讨论。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同为20世纪中国仅有的展现个人庞大哲学体系的作品。
意味深长的是,冯的体系是唯理新儒学的重建,而熊的则是唯心新儒学的再构。“理学”一词通常指涉宋明新儒学,冯氏明白宣称他的体系乃“接着” ―而不是“照着” ―宋明理学而来的,冯氏哲学建立在四个主要形上概念上,即:理、气、道体和大全。总合说来,此四者盖从“有某种事物”这个命题推演而得,都是形式概念,均只有逻辑含意而无积极内容的空概念;明确地说,都是从主要由程朱理学(兼有道家)发展而来的一个或一组命题中推演出的。
第一个概念“理”,来自程朱“有物必有则”的命题,某事物必定遵循其所以为某事物的理,才能存在。理是自存的、绝对的、无限的,是如公孙龙与西方哲学所理解的一种“共相” (universal)。理既不在世中,也不在世外,因为理自身并不进人任何时间或空间的关系之中。物必须循理,但理不必然会在物中实现,它隶属真际(形而上),而非实际(形而下)。因此,理之全体必然多于在世界中已经实现者,理之总和便是“太极”。
第二个概念“气”,取自程朱学派的命题“有理必有气” 。若欲一物存在则必有其所借以存在的气;此新儒学中之“气”,可拟于西方哲学中之“质料” (matter)作为理借以实现的质料,气具备了存在的特征(译按:即气亦可相对地说为一事物),但其自身却不存在于理或现实世界中,气跟理一样也只是一个形式逻辑的概念。
第三个概念“道体”,出自新理学“无极而太极,的命题,意谓宇宙是透过‘旧新”或无尽活动变化的过程的一种大化“流行” (universal operation)或“大用” (great functioning)。
第四个概念是“大全”、“道”或“天”,在其中,即如佛学或新理学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由于“大全”只是对一切物的共称,而对实际世界并未有所肯定,所以是一个形式的概念。
此概念在西洋哲学中便是“绝对” ( the Absolute ),正如同“理”、“气”、“道体”诸概念可以一一和“存有” (being)、“非存有” ( non-being)、“流变” ( becoming)等概念相比对。“大全”是人生的目标,可以通过格物、尽性、事天来实现,一旦做到了,便可以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最高境界,这就是“大仁”的境界。
以上是《新理学》的大要,之后冯又写了五本书以完结其体系的其他层面。《新事论》(1939年)处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建,是对中国文明与历史的一番简要的解释。《新世训》(1940年)表达了他以儒学为主而融合道家学的伦理思想。《新原人》(1943年)提出四种不同的人生境界的理论,包括从不知所为的蒙昧层次进到谋取自利的功利层次,再进到服务社会的道德层次,最后达到事天而成为“天民”的超越层次。《新原道》(1944年)解释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在《新知言》(1946年)中,冯氏发展出他自己的方法论。这后五本书仅只补充,但未曾改变他的哲学的根本立场。
冯直承他自己的体系是一个“新统”,他的新传统不仅表现中国哲学的复兴,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冯的体系因此不仅仅新,同时也是自孔子,经过宋朝新儒学而传至他本身的道统的延续与重建。撇开这种对于天命的自信感不谈,他的体系之所以是新的,正在于他把西洋实在论与逻辑学的因子,以及道家否定论与超越论的因子,融入传统唯理的新儒学之中。
当然,冯的最大创新是把新儒学的理念变换为逻辑概念,这种改变使得新儒学发生根本的变化,新儒学本质是内向的新理学,现在被一种超越哲学取而代之了。在新理学中,心性是根本的问题所在,对宇宙的形而上思辨,主要是用来帮助理解它们的。现在,冯认为心性隶属于实际的世界,似乎不像他对逻辑概念一样的加以重视。为了强调共相,他在中国哲学看到比实际存在的更多的普遍原则,例如把公孙龙的“指”(记号?)解释成共相,实属臆测。就理而言,若理仅属真际而不蕴涵实际(actuality ),那么现实世界是否是一项意外,甚至于是一种错误呢?实在如何可以既真但又不存在呢?理是事物的道德本质,同时又在我们的本性之中,却又超越于现实世界之外,这如何可能呢?理如果不是内在于事物之中,我们对大化流行(universal operation)和理的直接关联便难以想象。排除了新儒学的内向性,冯氏连带地泯没了新儒学的实践特征与现世特征,这与中国哲学的一贯趋势直接冲突,于是冯所宣称的新传统是否正当便成为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待解答,但更重要的问题却是:冯是否依旧坚持这一套新理学?
他在1950年放弃了新理学,说它正像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是西洋哲学的黄昏一样,不过是中国旧哲学的黄昏。他深深懊恼自己对具体与特殊的轻忽。他把马列主义比做现代医学,而将传统中国哲学比做中古医学。同一年稍后,他更公开放弃了上述五书的主要论题,天民不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是逃避主义。对于《新理学》一书,他认为太过于重视共相,也受到过多的佛道影响,这反映了崩溃中的封建社会。
这样的说法颇难评估。冯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非不可能,早在1939年他撰写《新事论》,就采用唯物史观了。后来他也曾认为道家返本或复归的理念以及日新的概念是辩证的,但1952年,他又坚称中国新旧哲学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比较接近人民。他认为旧的哲学必须加以批判,但对其中的正确部分,仍须加以继承。1957年,他辩说孔子并非唯物论者,而是理想主义者,当孔子说“君君臣臣”时,是要使现实符合抽象观念的要求。在理想(唯心)主义和抽象观念都受到严厉批判之时,冯氏还为二者提出辩护,这似乎显示出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他自己的本来思想仍然没有在他身上消失。
新唯心派的新儒学―熊十力
正如冯友兰之试图重建唯理的新儒学,熊十力(1884一1968)则试图重建唯心的新儒学。他在哲学方面,有八部著作。其整个思想,有系统地表达在《新唯识论》中。
依照《新唯识论》的中心主旨,本体是恒转,其间涵摄“翕”与“辟”,这两者是生生不息的历程。本体是刹那刹那,才生即灭,才灭即生,新新而起,而成万殊。但本体与万殊,或体与用俱是一非二。翕是一种摄聚的趋势,其结果则“假说”为物。辟则是能保持自性与自作主宰的趋势,其结果则“假说”为心。此心乃本心的一部分,心、意与识是其不同面向。
可以看出,翕辟与生生不息之说均源于《易经》。熊先生即说,《大易》是他思想的主要根源。心之分析则得自佛家唯识宗;体用合一,得自新儒家;以及本心之首出性,则得自王阳明。正如所有新儒家,熊氏以本心即仁,而指向天人合一。
熊十力始习佛门之唯识宗,后来觉有不合,转趋于新儒学,并对两者加以批判、综合与改造,复借西方哲学若干因素以自造“新唯识论”。熊氏强调地说,在此处,识之义,并非如唯识宗所谓现象界衍生所自之识心或阿赖耶,而是万有之本心或本体,“唯”者,显其“特殊”义。熊十力对佛家有详尽、审慎而深刻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人。不过,他仍不能摆脱佛氏最重要之弱点,即视外在世界为“假”。在佛教,此“假”字意涵暂时、过渡,甚至是虚幻。熊氏尚未如唯识宗那样视外界事物全然是虚幻存在。不过,熊氏既视具体的物质事物为心之本性之一威胁,他之贬抑外界是显然的。这样便减弱了他的恒转说,因为,恒转必须通过事物,除非具体的物质事物具有本体之真性,否则恒转将是建立在脆弱基础上。
熊十力得益于佛学者,在刹那恒变观念方面,较在唯心观念为多。熊氏以之融通于《大易》的生生不息的思想,并加以推拓。动态变易的观念在新儒家(尤其阳明)中一直很重要,现在熊氏则为之加上形上基础。这部分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主要是柏格森之说。但是熊氏之于西方哲学,批判多于欣赏。由于熊氏不谙西文,而产生了某些误解,而谓在西方哲学中,对通过个人经验而掌握真理(即“体认)不够重视,又过分追求外物,也不了解体用合一。
熊氏虽有这些弱点,但仍推动了新儒家的进步,特别是关于理气合一之说。对朱子的理气二元说与王阳明的气仅是心之一面之说的反对,到此均获解决。熊十力确实没有厘清心与理之关系,但是他却给予唯心派新儒学一个较为坚实的形上基础与较具活力的性质。除冯友兰与熊十力两人以外,在这20世纪,也有其他学者企图重建传统哲学,特别是欧阳竟无、释太虚与梁漱溟诸人。欧阳竟无与释太虚仅重振唯识学派之声光,而于其学则并无新义。梁漱溟将仁解释为动态直观,从而对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但他并没有发展出自己一家之哲学系统,在这方面熊十力做到了。
除此之外,熊十力也比同时其他中国哲学家影响了更多中国年轻一代哲学家。从哲学上说来,《原儒》(1956年)这部书并没有改变他《新唯识论》中的基本论点,但指出儒学在中国依旧是活生生的。
(本文转自漫漫生死道、闻月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