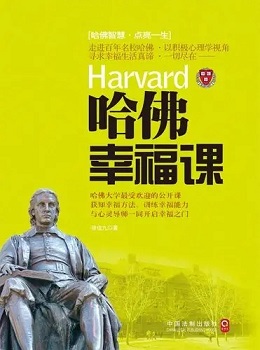一个多月前把这篇诗交给一个朋友去付排的时候,我重读过一次,今天为了做序,我又重读了一遍,几次读后我的脑子都离不开这个悲剧的构成的一点上;我这时的思路狭窄得很,就把这一点谈一谈罢。
我觉得这是一篇史诗(我以为这是可以这样称它的,虽然我也以为它还不是所谓伟大的史诗), 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首先就因为这悲剧在现实上是惊心动魄的。(但诗的到达也就在这里, 除了完成这史诗的那诗的表现以外,我们还不能不深深地感受着诗人的那一贯到底的紧迫的真挚的爱和憎, 以及忧愤的跳跃的情绪, 织成这诗篇的生命和光辉。)我不能不想起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的势力》来, 虽然一是剧本,一是叙事诗,那使人神经战栗的一点是相同的。但它们有绝大的不同,托尔斯泰以农民为对象,着眼在宗教的忏悔。这一篇叙事诗,却以地主和土豪的残酷的剥削和无人性的惨毒, 为罪恶的本体和农村黑暗的主要的根源;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超脱的路了。因为最要紧的是,这个中国内地的地主家庭的悲剧, 固然为地主和土豪阶级的狠毒及其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但尤其这一切都建筑在他们对于农民的残忍的非人的榨取掠夺的制度上面的。
这是不用说的,这里远非阶级斗争的正面图景。并且更不是地主土豪们剥夺和残害农民的正面的和全面的写照。然而却是把地主和土豪们在没落期中的“战斗的”性格勾画出来了,也已经突进和展露了地主阶级的心理和整个意识形态。这种性格和心理, 在阶级斗争的场合则在对农民的压榨和残害上极端暴露出来,现在则在对亲生女儿的谋杀上发展到了高峰。但地主山耳的谋杀亲生女儿, 以及他同时奸污媳妇的乱伦行为, 在他都是从始到终显得很自然的, 而且显得“合理”;这是因为他对于农民的剥夺和残忍都是极自然的,都认为是合理的缘故。他认为一切的重租, 一切的高利盘剥, 一切赚钱办法都“合理”的,所以也都极自然的。一句话,剥削和掠劫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要拼命维护的。但这命根所在的制度, 却在动摇了, 于是自私、卑怯、阴险和毒辣就发展到极端, 一切为着维持剥削制度。地主山耳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榨取,是钱,是家,是名誉。所有这些都来自榨取制度,维护榨取制度就是维护这些一切。因此,要加紧残酷地榨取,要拼命地刮钱,要竭力保持家和名誉,还要维护礼教,也都为了要维护榨取制度。而为了维护名誉而谋杀了亲生女儿,也的的确确是为了维护榨取制度。甚至奸污媳妇,揭穿了说,也为了维护家,于是也为了维护榨取制度呢。
因此,从事实的发展上来看, 谋杀亲生女儿的山耳的性格和心理是自然的;同时,从正在和没落的命运战斗着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看, 则山耳的每一非人的行为也都是极自然的。
所以, 《大渡河支流》所抒叙的地主家庭的悲剧,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中的地主和土豪阶级的一个侧面。这悲剧依然是建筑在非人的榨取制度及其拥护者的意识形态上。
(作者从山耳对农民的盘剥及与胡玉廷的冲突, 发展而到谋杀女儿,这样地来展开山耳的性格,我觉得非常自然和真实, 同时也使结构很完整而自然。)
所谓地主阶级的内在矛盾,也是从对农民的残忍剥削而展开的。由于对农民的剥削过于残忍,使其自私、懦怯、阴险和残酷的特性极端地发展,遂至于发生谋杀亲生女儿及其它种种的灾祸;由于都要残忍剥削农民,遂有地主们自身的相互倾轧;由于地主、土豪等等和农民之酷烈的对立,地主土豪阶级的子弟才有个别的叛逆分子;而尤其对于农民愈加残忍地剥削,而愈加带来对地主土豪阶级以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危殆和恐怖。但虽然这样,在危殆与恐怖的感觉中,地主山耳们却只有日益把他们的黑暗和狠毒向前发展着的。所以, 只有革命才能消灭他们。只有革命才能消灭为罪恶之根源的榨取制度及其阶级, 于是也消灭那意识形态,也消灭这一种悲剧。这是这史诗所没有明言的, 然而是它所能给予的惟一的暗示。
我这样说,并没有忘记篇末的二儿子光宗的一封信。但我以为这只能算是一般地主子弟的一种微弱的叛逆的表示,这样的软弱的“忏悔分子”在现在是颇为普遍的,但决不能作为照着这悲剧的一线光。倘若作为一点光,对着这阶级和这家庭的浓重的黑暗是太微弱了, 而对着整个中国的革命的大火更是太微弱了。这悲剧是绝望的, 照着它的是外面的革命的大火光。这阶级和这家庭是必须全部毁灭的, 由革命去毁灭。自然,二儿子虽是软弱的叛逆,却也到底叛逆了, 然而这家庭和这阶级可决不可能由他而超生。
女儿琼枝和二媳妇,这两个悲剧的主要受难者, 自然更是殉难者了。琼枝是使我们同情的,这是因为她还有善良的性格,而且尤其杀她的凶手,她的父亲,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的缘故。对于二媳妇,我们还更同情,这是因为她比琼枝更默默地受难着的缘故。但她们的善良和殉难, 也决不能挽回这家庭和这阶级。
这悲剧本身注定这家庭和这阶级是绝望的, 并且必须由革命去毁灭的。因此,我以为这悲剧无需于用什么光去照耀,也不必拿光宗的一封信当作这样的一线光。它是绝望的,在革命的大火中它显得更绝望, 而我们却并不绝望。
(自然,这里面的农民也都在阴惨的情景下, 而且并无积极的反抗斗争。但这是在革命以前的落后内地的一般情形,这是完全真实的;而他们就这样被压榨着, 只要革命一发动, 无论然福, 无论谁,都会马上战斗起来了。在今天,我想,谁都不应对他们抱悲观的态度的。)
由于这悲剧在现在的胜利的农民革命中有着这样的意义,也由于诗人之全心的贯注, 诗的高度的到达,这成为一篇很珍贵而重要的史诗,我想读者是马上会发现它的。但关于它在诗坛的影响和地位之类,我们现在不应多说,留给批评家们去谈罢。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读后感,不仅偏于一面,并且很浅薄, 写出来当作序文是要贻笑大方的。但我今天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地向读者介绍, 向作者致敬罢。
1947年9月9日
以上的序文写好后,一个为这诗的出版而尽力的朋友,认为还应该把作者介绍一下,我也觉得这是重要的。只可惜关于作者玉杲,我知道的很少,现在他又在很远的地方,并且无法通信。他只和我通过七八次信,见过两次面,都在两年前。那时他在重庆郊外的璧山“社会教育学院”读书,在1945年暑期毕业后,则到川南的一个中学去教书。两次见面都很匆促,虽都特意来看我的,但他很少说话。给我的印象是:微黑的脸,那时大约二十二三岁,从他简短的语言和眼睛的表情上,似乎是一个在农村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种颇惯于寂寞然而倔强的, 自重而深沉的朴素的性格。现在我竭力回忆当时他说的话,都记不起了, 除了两点似乎还记得清楚:一是他说在璧山有些书看不到,这大概是指那时重庆新出的政治性的书;二是他说他喜欢读涅克拉梭夫的诗,可惜他不能读原文。
在通信上他说的话多一点,记得他曾说过他是不能也不愿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他大概是川西北人,如诗中所示,但故乡的影子常在他的脑际盘旋。又他曾在抗战初期到过西北,也是在信上透露出来的。而有一件事情,使他写了联贯的10多首抒情诗的,是在他把那些诗寄给我看时的信上说的, 即他在西北时有一个最亲近的女友,后来回到后方工作,被人非常残酷地害死了。他曾在重庆版的《文艺杂志》上发表的题为《飞鹰》的3首小诗,也是写他的这一种悲愤和怀念的。……
最早拿这篇诗给我看的,是他的朋友杨子涛,在1944年5、6月间, 因为子涛是一个和我接近的青年。记得我读时是很兴奋的,而他后来又改动过几个地方,就由我介绍给邵荃麟先生在《文艺杂志》上发表的。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他离开四川到北方去,是去年5月间,那时我已来上海,他在动身时曾来信通知,并请托我找地方把他的这篇诗出版及写一点序;在7月间到了目的地,也来过一信,说他的工作是教书,并附来了一首短诗。这信还在, 我现在把附诗重看了一遍,那是怀念留在四川的一个朋友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留在南方
南方有×谋
有大×杀
南方×动
以后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但我想,这诗人如果在以前的他个人的感情上还多少留有一点阴暗的伤感的痕迹,如他未发表的抒情诗所流露,那么他现在一定已经大踏步地越过了。
他的诗留在我这里的,还有两个长篇叙事诗, 《刘老五》和《残夜》,以及一些抒情的短诗。一则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代为投稿,二则我觉得都远不及《大渡河支流》强,这是他自己也同意的,所以都仍搁在这里。
1947年9月10日
雪峰又记
(《大渡河支流》,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出版)
赏析
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291页)中说:“必然性= ‘存在的一般性’ (存在中的普遍性)”这就是说,只有深刻地揭示必然性,才能正确而充分地显现一般性。
艺术典型概括化的根本要求,在于通过对共性特点的展现,深刻地揭示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本质特征或必然规律。
冯雪峰认为《大渡河支流》是“一篇史诗”,原因即是这首诗符合艺术典型概括化的实质:展示必然性。
作者在分析时,认为《大渡河支流》揭示了“地主和土豪的残酷的剥削和无人性的惨毒”是“罪恶的本体和农村黑暗的主要的根源”。这显然是指这首诗具有反映特定生活内容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创作要描写“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并说“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诗学》)《大渡河支流》在这一方面做得是成功的,因为它反映出“这个中国内地的地主家庭的悲剧,固然为地主和土豪阶级的狠毒及其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但尤其这一切都建筑在他们对于农民的残忍的非人的榨取掠夺的制度上面的。”
艺术作品总是要通过客观具体地描绘一定时代的特定的社会生活,着力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典型。在这里,概括化的核心问题便是通过具体人物展示特定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作者认为,《大渡河支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成功的, “地主和土豪们在没落期中的‘战斗的’性格”被刻画出来了, “也已经突进和展露了地主阶级的心理和整个意识形态”。因而,地主山耳的所做所为“从始到终显得很自然的,而且显得‘合理’”。
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通过对具体生活形象的描绘,那么,作品中展示的特定社会现实关系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显得真实。黑格尔说:“日常的外在和内在的世界固然也现出这种存在本质,但它所现出的形状是一大堆乱杂的偶然的东西,……艺术的功用就在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种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因此,艺术不仅不是空洞的显现(外形),而且比起日常现实世界反而是更高的实在,更真实的客观存在。”是的,艺术概括化的灵魂,正是要从包容必然和偶然因素的“日常现实世界”中,描画出“更真实的客观存在”。《大渡河支流》正是这样,“从事实的发展上来看,谋杀亲生女儿的山耳的性格和心理是自然的;同时,从正在和没落的命运战斗着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看,则山耳的每一非人的行为也都是极自然的。”因此,这出悲剧深刻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即“这悲剧本身注定这家庭和这阶级是绝望的,并且必须由革命去毁灭的。”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大渡河支流》由于深刻展示了特定时代社会真实的历史画面,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此才被冯雪峰称为“一篇很珍贵而重要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