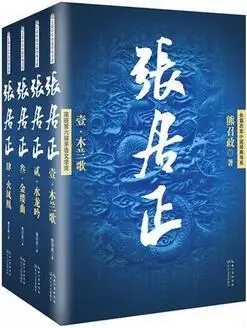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桩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 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读着这部新书,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1979年4月下旬, 我从北京专程去沪, 参加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当我到达几小时之后,他们的儿子,去国20余年的傅聪,也从遥远的海外, 只身归来, 到达生身的父母之乡。50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 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20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 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握手相见,心头无限激动, 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 而此生永远不能再见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 想起傅聪傅敏兄弟童年调皮淘气玩乐的形象。在我眼前的这位长身玉立、气度昂藏的壮汉,使我好像见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静肃、端庄厚憨的姿影, 又像见到了他的母亲梅馥。特别使我高兴的,我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从海外来的那种世纪末的长发蓄须、艳装怪服的颓唐的所谓艺术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态度非常沉着,服装整齐、朴素,好像20多年海外岁月, 和往来周游大半个地球的行旅生涯,并没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从形象的朴实, 见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壮。时移世迁,过去的岁月是一去而不可复返了, 人生的正道,是在于不断地前进, 而现实的一切,也确实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回想过去,也正是要为今天和未来的前进,增添一分力量。
想念他万里归来, 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 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在亲友们热烈的包围中, 他心头的热浪奔腾,是可以想像的。直到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之后, 匆匆数日, 恰巧同乘一班航机转道去京, 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对叙旧的机会。他简单地谈了20多年来在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 和今天重回祖国心头无限的激荡。他问我: “那样的灾祸, 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我不敢对他做任何保证,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 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谈到他的父母, 大家都不胜伤感, 但逝者已矣, 只有他们的精神、遗爱和一生劳作所留下来的业绩, 则将是永远不朽的。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的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我知道他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 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 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献给人民的宝贵的财富。谈话中便谈到了他多少年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我,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
我想起那书信, 因为在1957年的春末,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样,被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他给我谈到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 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我看, 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 叫我一读。在此不久之前, 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 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做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 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一次会议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习惯参加集体活动和政治生活, 但近年来目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切身体会到党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 显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他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 “你看,这孩子在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 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 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我当时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狂风大浪的“反右派运动”, 竟把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进, 在他平素热爱祖国的基础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正在日益浓厚的傅雷, 大笔一挥, 错误地划成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不久, 消息传来, 在波兰留学的傅聪, 又突然自由出走, 去了英国。由于对他父子的为人略有所知,这两件事可把我闹得昏头转向, 不知人间何世了。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 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 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
感谢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同志, 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 负起出版的任务, 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 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 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 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 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 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是体会得多么细致, 多么深刻。儿子在数万里之外,正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奏, 爸爸却好似对即将赴考的身边的孩子一般, 殷切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心脏的律动,设身处地预想他在要走去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 并替他设计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在这儿所透露的, 不仅仅是傅雷的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 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 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当40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识傅雷并很快成为他家常客的时候, 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孤岛,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 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很早发现在幼小的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 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 给孩子订定日课, 一一以身作则, 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 不敢有所任性, 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 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 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 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 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我不知道傅雷有这样的禁例,有一次带了傅聪到豫园去玩,给他买了一支较好的儿童金笔, 不料一回家被父亲发现没收,说小孩子怎么能用那样的好笔,害得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事后才知道这场风波,心里觉得非常抱歉,对傅雷那样管束孩子的方法, 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同时傅聪也正是一个有特异气质的孩子,他对爱好的事物常常会把全神都灌注进去,忘却周围的一切。有一次他独自偷偷出门,在马路边溜达, 观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乐得忘了神,走着走着,竟和路边的电线杆子撞了一头,额角上鼓起了一个包, 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他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上午下午, 几小时几小时的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 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 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但有时却弹出了神,心头不知到来了什么灵感, 忽然离开琴谱,奏出自己的调子来。在楼上工作的父亲,从琴声中觉察异样,从楼梯上轻轻下来。傅聪见父亲来了,吓得什么似的,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这一次傅雷并不是来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复弹奏原来的自度曲,听了一遍, 又听一遍, 并亲自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 还特地给起了一个题目, 叫做《春天》。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聪首次回国时,还问过他多少年来除了演奏之外, 是不是还自己作曲。
傅聪少年时代在国内就闹过一次流浪历险记。1949年上海解放后,傅雷全家从昆明迁回上海,把傅聪单独留在昆明继续学习。但傅聪非常想家,一心回沪继续学习音乐,竟然对父亲所委托的朋友不告而别, 没有旅费, 临行前由一些同学友人主动帮他开了一个演奏会,募了一些钱。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两地闹了一场虚惊。傅雷后来告诉我说: “你看,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
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 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所应该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对待其他一切一般,可看出傅雷是怎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在对社会、祖国与人类世界尽自己的责任的。傅聪在异国飘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吸取了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边, 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与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通过这些书信, 不仅仅使傅聪与亲人之间, 建立了牢固的纽带,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不管国内家庭所受到的残酷遭遇, 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他的祖国,他不受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 没有说过或做过有损祖国尊严的言行。甚至在他的艺术巡礼中,也始终一贯,对与祖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国家的邀请, 一律拒绝接受。直到1979年初次回国, 到了香港,还有人替他担心可能产生麻烦,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但他相信祖国,也相信祖国会原谅他青年时代的行动,而给他以信任。这种信赖祖国、热爱祖国的精神, 与傅雷在数万里外给他殷切的爱国主义的教育, 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的,更不能不使人不去想那一次严重扩大化了的政治运动,20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 是多么的惊人, 而今天终于普遍得到改正、昭雪, 又是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有许多人在那场灾祸中被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 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的英精。在我最熟悉的战友与好友中,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在党外的傅雷也是这样, 虽然我今天已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在他们的后代中, 以及更广大的在10年浩劫中受过锻炼的坚强奋发的青年中,我看见了他们。
我叙述这些回忆和感想,谨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1981年7月5日,北京东郊
( 《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8月版。)
赏析
这篇《傅雷家书》的“代序”,因作者楼适夷与傅雷、傅聪父子相交数十年,相濡以沫,知深爱重,因而全文涵蕴着休戚相关,同舟共济之情,全篇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代序”首揭命题:“一颗高尚的灵魂”,尽管暂时会被污辱,陷入绝境,但随着人间正道的复归与昂扬,终必会光焰复现,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可谓“立片言以居要”。随即通过绵长而波折的“往事”的叙述,边叙事,边抒情,阐明和印证了这一理念与论旨,令人十分信服、感动。
“往事”是从1957年间,傅雷因遭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的误伤与迫害,含冤而逝。致使20年后,亲子万里归来时,见到的已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这是对错误路线的多么沉痛的怆呼和控诉!然则,随着反革命团伙“四人帮”的覆灭,阴霾一扫而空,傅雷等人累累冤假错案终得平反昭雪,正义战胜了邪恶,亦可告慰亡灵,振奋后人了。进而坚定有力地郑重指出:经过“这一场惨烈的教训”,如今全国上下一心,团结奋进,必有勇气和信心,防止妖雾的重现。并寄意深远地强调: “逝者已矣”,但“他们的精神、遗爱”和“业绩,则将是永远不朽的”。充满着积极、乐观的襟怀和旨意。
“代序”进而根据亲身的体察和感受,详叙傅雷如何“平素热爱祖国”,谆谆教子成材,和“闭门译述”、埋头笔耕的高尚、勤勉的思想言行。这部数达三百余封,情真意切的万言“家书”,就是傅雷夫妇高风亮节,毕生劬劳的思想品质和献身精神的明证与实绩。
傅雷是我国声誉卓著、成绩斐然的文学翻译家,从30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倾毕生精力,经心译介了包括罗曼·罗兰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传世名作和《贝多芬传》等传记作品30余部,尚有文艺专著和评论多卷。为我国文化事业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读家书”以“想傅雷”为主轴,因而它的着力点是多方面启引读者以“家书”为窗口,去窥见傅雷的为人和神采。正如“代序”中确切指出的, “家书”中,页页倾注着傅雷怎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在对社会、祖国与人类世界尽自己的责任”。正因这份基于公心的爱心,不仅是与自己的家人,而且也升华为与众多读者和后人之间的“心的结合”,让大众从这份高尚、真纯的爱心中吮吸到精神力量,获得“鼓励与鞭策”, “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与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
这篇“代序”不仅有深刻的思想意义,还有“诗教”般亲切感人的艺术魅力。它词语精切流畅,对比鲜明具体,时时以生动、切实,贴近生活的细节描写,让事实说话,从中阐发了一位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进步文化人怎样敬业乐群,立身处世的生活准则与做人道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 “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从而“显示文人的全貌”。(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书中即使若干断想,只言片语,也往往警辟动人,妙语如珠。如:“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恋爱至上’的看法。‘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也不能侵犯这些原则。朋友也好,妻子也好,爱人也好,一遇到重大关头,与真理、道德、正义……有关的问题,决不让步。”多么坦诚,坚定,有力,真是我们后辈青年处理生活,抉择取舍的座右铭。当然,因为接信人傅聪是一位大有成就的音乐界翘楚, “家书”中以谈乐理,说演奏的题材为多。但十分可贵的是,往往令人能从中深悟崇高的操守和艺德,清晰地看到“在傅聪长大成材的道路上”,处处有着父亲“所灌注的心血”。我们读了“家书”,必将深信“代序”此言不虚:即它无愧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