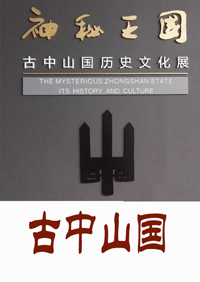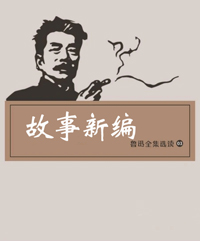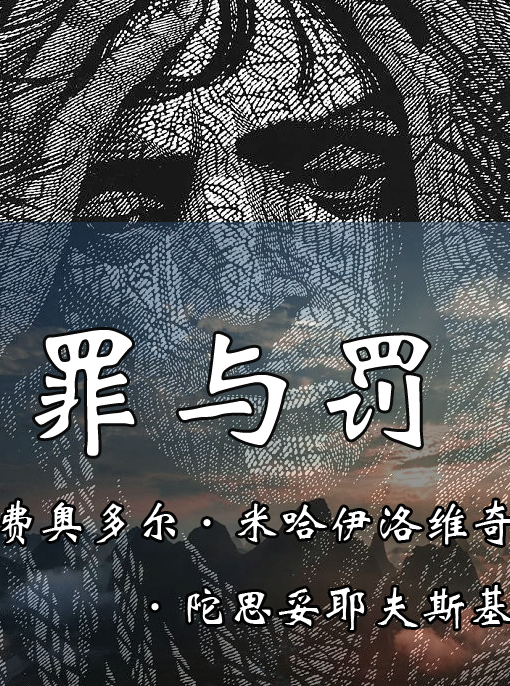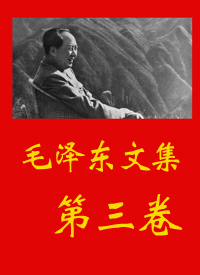第一章 印度洋
现在开始第二阶段的海底旅行。第一阶段以珊瑚公墓动人的场景而告终,感人至深,刻骨铭心。这样看来,尼莫船长的余生都将在这广袤的海洋中度过,他甚至已经在那深不可测的海底中为自己准备好了墓穴。那里,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海怪来打扰鹦鹉螺号船员的长眠。这些船员共患难,同生死!“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一个人也不会有的。”尼莫船长补充道。
他对人类社会依然耿耿于怀,怨恨有加,势不两立。
对我来说,我再也不能满足于龚赛伊的那些猜测了,虽然这个老实人仍坚持他的看法,认为鹦鹉螺号的船长是被埋没了的一位学者,他用蔑视的态度来看待人世间的世态炎凉。龚赛伊还认为船长是一位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天才,由于对陆地已经彻底失望,心灰意冷,才会不得已躲到这里来。在这里,他的本性可以得到自由的张扬。但在我看来,这种猜测只能解释尼莫船长个性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我们被关押在房中并且被强迫睡眠的那个神秘的晚上,船长极其粗暴地从我手中夺走了我正准备向天际观望的望远镜的那种防范举动;鹦鹉螺号那次不可告人的撞船事故竟然造成自己船员受伤致死,所有的这一切都促使我向一种更合乎情理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尼莫船长不仅仅是在逃避世人!他这艘神奇的潜水船,不仅仅是为他追求自由的天性服务,而且还可能是为了实施某种可怕的报复计划,只是我对这个行动计划一无所知罢了。
但现在对我来说,一切还尚不明确。我只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我也仅仅是在如实记录罢了。
再说,我们与尼莫船长没有任何利害瓜葛。他很清楚,我们是不可能逃离鹦鹉螺号的。我们甚至连凭保证就能被假释的囚犯都算不上,因为我们从未承诺要履行什么诺言。我们不过是俘虏,是囚徒,仅仅是出于礼貌才被称作客人。当然,尼德·兰从未放弃过争取自由的希望。只要一出现机会,他就肯定会抓住不放。我可能也会像他那么做。不过,一旦尼莫船长慷慨地让我们了解鹦鹉螺号的秘密,而我却要带着这些秘密逃跑,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内疚啊!对他,我是应该憎恨还是应该赞美呢?他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刽子手呢?再者,说实话,我还是想完成这次环球海底旅行之后再离开,因为前一阶段的旅行实在是太精彩了。我想把地球海底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都看一个遍。我还想看看没有任何人见识过的好东西,为了满足我那强烈的求知欲,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可到目前为止,我到底发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或者说是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只是在太平洋海底穿行了6000法里!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鹦鹉螺号正在接近有人烟的地方。一旦有逃脱的机会,而我却为了自己的好奇心而牺牲自己的同伴,那也未免太残忍了。我应该跟着他们一起逃走,甚至还可能要带领他们逃走。但真的会有这种机会吗?作为被强行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我迫切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但作为学者,作为好奇心强的人,我又担心出现这样的机会。
这一天,1868年1月21日,中午时分,船副如往常一样出来测量太阳的高度。我登上了平台,点燃了一支雪茄,然后看着他如何操作。依我看,这个人显然听不懂法语,因为有好几次,我故意大声说出我的想法,如果他听懂了,肯定会下意识地做出某种反应,但他无动于衷,一言不发。
正当船副用六分仪观测时,鹦鹉螺号的一名水手上来擦拭船灯玻璃,此人身强力壮,曾陪同我们去克里斯波岛进行第一次海底漫游。于是我乘机观察起了这台灯的构造,船灯的凸镜玻璃结构与灯塔相似,聚光效果很好,在有效面上的亮度可增强百倍。电灯的结构非常合理,有利于充分发挥照明能力。由于灯光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光线的均匀度和强度都能得到保证。而且,真空可以减少石墨的消耗,这灯正是靠石墨棒发出弧光。节约石墨对尼莫船长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补充石墨对他来说并不容易。而在真空的条件下,石墨的消耗就微乎其微了。
鹦鹉螺号准备继续海底航行,我便回到了客厅。嵌板重新被关上,鹦鹉螺号一直向西航行。
我们在印度洋5.5 亿公顷的广阔海域中劈波前进,海水是如此清澈透明,以至于人俯身看着水面时都会感到一阵晕眩。鹦鹉螺号通常是在水深100至200米间的地方行驶。几天来一直如此。如果换了别人,也许会觉得度日如年,枯燥乏味,可对于酷爱大海的我来说就完全不同了。我每天在平台上散步,呼吸海洋的新鲜空气,透过大厅观景窗观看水中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阅读图书室里的各种书籍,撰写我的学术论文,所有这些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因此我没有任何闲工夫感到厌倦和烦恼。
我们大家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也完全适应船上的饮食。尼德·兰出于抵触情绪,设法弄出各种菜式,在我看来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此外,在海底恒温条件下,连感冒都不用担心。另外,这里有一种属于石珊瑚目的木珊瑚,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被称为“海茴香”,在船上还有一定的库存,把它和珊瑚虫的肉一起熬烂,还是治咳嗽的一剂良药呢。
好几天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水鸟,有蹼足鸟、大海鸥和小海鸥等。我们巧妙地捕杀了几只,精心烹调,便做成了可口的水禽野味。有些大水鸟远离陆地高飞,经过长途飞行,在波涛浪尖上休憩。我在其中发现了属于长翼科鸟类的美丽非凡的信天翁,它们的鸣叫就像驴的叫声一样刺耳。蹼足家族的代表是军舰鸟和鹲鸟,军舰鸟飞行速度极快,能迅速捕捉水面游鱼,而鹲鸟又名草尾鸟,数量繁多,身上有红色条斑,大小如鸽子,白色羽毛淡淡地染着点粉红色,鲜明地衬托出乌黑的翅膀。
鹦鹉螺号的拖网打到了好几种海龟,它们背部隆起,龟甲很是珍贵。这些爬行动物善于潜游,关上鼻腔外孔的肉阀,就可以在水下停留很久。有些海龟被抓住的时候,还在甲壳里蒙头睡大觉呢,这样可以免遭其他海洋生物的伤害。一般来说,海龟肉不怎么好吃,不过海龟蛋却是上等美味。
谈到鱼类,我们总是赞叹有加,每次通过窗口观看到各种鱼类在水下生活的秘密时,我们总是啧啧称奇。有不少种类的鱼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我特别想要提到的是红海、印度海和赤道美洲海域里盛产的箱鲀。这类海底动物像海龟、犰狳、海胆和甲壳动物一样,身上披有一层既不是白垩质也不是石质,而是真正的骨质的护甲。它们的甲壳有三角形的,也有四边形的。披三角甲的箱鲀中,我注意到其中有几种,身长半分米,肉质鲜美,富有营养,棕尾,黄鳍,我甚至建议把它们引进到淡水中养殖,因为不少海鱼适宜在淡水中存活。再来说说四边甲箱鲀,背上鼓起四个大包,身体下部有白色斑点,它们可以像鸟类那样进行驯养。还有头上带刺的三角箱鲀,头刺是骨质硬壳的延伸,由于会发出呼噜呼噜的怪叫声,所以有“海猪”的绰号。还有一种驼鱼,长有锥形肉峰,肉质粗硬,很难咀嚼。
根据龚赛伊的日记,我还可以列举出这些海域特有的鲀鱼品种,比如红背脊白肚腹的针鱼,这鱼很特别,它有三条特别鲜艳的线纹;还有电鱼,身长7英寸,色彩十分鲜艳;还有些鱼非常特别,比如没有尾巴的卵鱼,像黑褐色的鸡蛋,但身上有白纹;还有浑身长满尖刺的刺鲀,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刺猬,体内吸水便鼓胀起来,形成毛刺林立的刺球;还有海马,各大海洋都有;还有海蛾飞鱼,鱼唇很长,胸鳍宽阔似翅膀,虽然不会高飞,但至少可以腾跃出水面;还有抹刀鸽鱼,尾巴布满环状鳞片;长吻海刺鳅,身长25厘米,味道鲜美,色彩亮丽;青灰色的美首鱼,头部凹凸不平;无数会蹦跳的鳚鱼,身上有黑条纹,胸鳍很长,能在水面上迅速滑行;还有美味的旗月鱼,背鳍和臀鳍高且长;状似顺风高扬的风帆;色彩斑斓的钩鱼,大自然的造化神功让它非常出色,拥有天蓝色、银白色和金黄色;毛翅鱼,鱼翅像丝绒般细腻;还有经常拖泥带水的杜父鱼,走动时会发出微弱的响声;还有鲂 ,它的肝肠都有剧毒;普提鱼,眼睛竟有活动眼罩;最后是射水鱼,竟能在水下捕获水上飞虫,靠的是嘴巴长有一杆可以喷水的长枪,这是夏斯波特(法国军械师,曾为法军发明过新式步枪)家族和雷明顿(美国工程师,曾发明新式步枪和打字机)家族始料不及的,只要喷射一注水就可把昆虫击落。
,它的肝肠都有剧毒;普提鱼,眼睛竟有活动眼罩;最后是射水鱼,竟能在水下捕获水上飞虫,靠的是嘴巴长有一杆可以喷水的长枪,这是夏斯波特(法国军械师,曾为法军发明过新式步枪)家族和雷明顿(美国工程师,曾发明新式步枪和打字机)家族始料不及的,只要喷射一注水就可把昆虫击落。
根据拉塞拜德分类法,鱼类中的第89属是硬骨鱼第二亚纲,其特征是有一片鳃盖和一块鳃膜,在这个属里我看到了 鱼,头上长尖刺,只有一个脊鳍,这些鱼根据所属的不同亚属,有的身披细鳞,有的没有鳞片。第二亚属中有一种两脚鱼,身长3至4分米,饰有黄色条纹,鱼头很古怪。在第一亚属中,有俗称“海蟾蜍”的怪鱼,大脑袋,凹凸不平,面目狰狞,浑身疙疙瘩瘩,布满肿块、角刺和老茧,针刺扎人很危险,形容可憎可怖。
鱼,头上长尖刺,只有一个脊鳍,这些鱼根据所属的不同亚属,有的身披细鳞,有的没有鳞片。第二亚属中有一种两脚鱼,身长3至4分米,饰有黄色条纹,鱼头很古怪。在第一亚属中,有俗称“海蟾蜍”的怪鱼,大脑袋,凹凸不平,面目狰狞,浑身疙疙瘩瘩,布满肿块、角刺和老茧,针刺扎人很危险,形容可憎可怖。
从1月21日至23日,鹦鹉螺号每天日夜兼程航行250法里,即540海里,平均每小时22海里。
我们之所以能一路观赏到各种各样的鱼类,是因为这些鱼群被船的电光所吸引,欣然前来陪伴我们同行。不过,它们大部分都跟不上船的速度,很快就被甩在了后头,而有些则可以紧跟着鹦鹉螺号好长一段时间。
24日晨,在南纬12°5′,东经94°33′,我们看见了基林岛,这是石珊瑚垒起来的岛,岛上有很多高大好看的椰子树,达尔文先生和菲茨—罗伊船长曾到过这岛考察。鹦鹉螺号沿着这个荒岛的悬崖峭壁行驶。拖网打捞起许多珊瑚和棘皮类动物,还有一些软体动物门的新奇贝壳。尼莫船长的宝库里又增加了几样珍贵的燕子螺,我也为它增添了一个斑点星珊瑚,这种珊瑚往往寄生在贝壳上。
不久,基林岛就在天际边消失了,我们取道西北方向,向印度半岛南端开去!
那天,尼德·兰对我说:“到了有文明的地方了,这总比在巴布亚好得多,在巴布亚,碰见的野蛮人比狍子还多!教授先生,在这块土地上,有马路,也有铁路,还有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城市。5海里之内肯定有我们的同胞。嗯!是不是到了该对尼莫船长不辞而别的时候了?”
“不,尼德,不,”我口气坚决地说,“正如你们水手常说的那样,顺其自然吧。鹦鹉螺号正在驶向人口稠密的大陆,它正在返回欧洲,那就让它把我们送到欧洲区吧。一旦到达我们的海域,我们再见机行事也不迟。况且,我认为,尼莫船长虽然允许我们上新几内亚森林打猎,但未必能同意我们去马拉巴尔或科罗曼德尔沿岸打猎。”
“那这样,先生,我们不经他的允许自己走不行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想争论。其实,我心里在想,既然命运把我抛到了鹦鹉螺号船上,那我就应当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充分加以利用。
从基林岛开始,我们的船速总的放慢了。航迹变化多端,不时把我们拉到大海深处。船员几次使用斜板机,通过船内杠杆把斜面板调节到与吃水线斜切的位置上。就这样,我们一下子潜下两三公里的深度,但印度洋海底深不可测,即使可以抵达1万3千米的探测器也鞭长莫及。至于深海层的水温,温度计始终指向4℃。但我注意到,在海水上层,海滩的水温要比外海低。
1月25日,海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鹦鹉螺号在海面上度过了一整天。强大的推进器劈波斩浪,激起阵阵水花高高溅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会不把它当作一条巨大的鲸鱼类动物呢?这一天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我都在平台上。我远望大海。天边什么也没有,只在下午4点的时候有一艘长轮迎面朝西开来。有一阵子,我们可以看见轮船的桅杆,但它看不见紧贴着水面航行的鹦鹉螺号。我想,这条轮船是属于印度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它来往于锡兰与悉尼之间,途中经过乔治王岬和墨尔本港。
下午5点的时候,在热带地区日夜之交的短暂的黄昏来临之前,龚赛伊和我看到了一个新奇的景象,令我们如痴如醉。
那是一种迷人的动物,照古人的说法,碰见它,就预示着将有好运气到来。亚里士多德,阿泰内,普林尼,奥皮恩(公元3世纪希腊诗人)等都曾研究过它的嗜好,恨不能把希腊和意大利学者诗篇中所有富有诗意的言辞来形容它。他们称它为“鹦鹉螺”或“庞比留斯”,但近代科学并没有采用这个名称,而是称它为船蛸。
问过龚赛伊的人都会从这位正直的小伙子那里得知软体动物门分为五个纲。第一纲是头足纲动物,它们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则披着外壳或长着内壳,头足纲动物按鳃的数目又分为二鳃和四鳃两个科;二鳃科又分船蛸、枪乌贼、墨鱼三属;四鳃科则只有鹦鹉螺一属。听完这个介绍,如果还有顽固不化的人把带吸盘的船蛸和带触须的鹦鹉螺混为一谈的话,那就不可原谅了。
这时候在海面上漂浮着的正是一群船蛸。我们估算了一下,有不下好几百条。它们的腕足有根瘤状腺膜,是印度洋特有的品种。
这些美丽的软体动物形态优美,它们将海水吸入外套动力腔管后喷出,以此推动身体向后运动。它们有八根触须,其中六根又长又细,浮在水面上,其他两根如掌状,迎风张开,犹如轻快的风帆。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身上那螺旋状的波纹外壳,怪不得居维埃把它们比作“画艇”。这的确是一条小船。船蛸用分泌物做出自己的外壳,它不把外壳粘在身上,可外壳却时刻装载着船蛸。
“船蛸本来可以自由离开它的贝壳,”我对龚赛伊说,“但它从不离开它。”
“尼莫船长就是这个样子,”龚赛伊把话说到点子上了,“还不如把他的船叫作‘船蛸’号呢。”
鹦鹉螺号在这群软体动物中间差不多穿行了一个小时,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突然把它们吓住了。它们好像听到信号一样,所有的帆一下子都卷了起来,触须都收回去了,身体也都缩起来了,贝壳也翻转了过来,顿时改变了重心,浩浩荡荡的船队一下子消失在水里。这一切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世界上还没有一只舰队可以做到如此步调一致。
这时,夜幕骤然降临,风潮乍起,排排长浪勉力轻拍着鹦鹉螺号的船身。
第二天,1月26日,我们在东经82°上跨越赤道,重新回到了北半球。
那一天,一大群角鲨为我们保驾护航。这种动物穷凶极恶,由于在印度洋大量繁殖,使得这一带海域险象环生。这里有菲利普角鲨,褐色的脊背,白色的肚皮,嘴里有11排牙齿武装;还有眼球斑角鲨,脖子上有一个白圈包着的黑色大斑,活像一只眼球;还有灰黄色角鲨,浑圆的嘴脸有灰斑。这些凶猛的动物经常撞击大厅的玻璃窗口,来势汹汹,让人提心吊胆。尼德·兰见了怒不可遏,恨不得带鱼叉到风口浪尖上去征服这些怪物,尤其是那些一再向他挑衅的星鲨和虎纹大角鲨,星鲨嘴里的牙齿排列得像一幅镶嵌瓷砖画那样整齐,而虎纹大角鲨则长达5米。不过,鹦鹉螺号不久就加快了速度,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游得最快的角鲨甩在后头。
1月27日,在广阔的孟加拉湾海口,我们好几次遇见了凄惨的景象!水面漂浮着许多尸体。那是恒河流域的印度各城市的死人,尚未被当地唯一的收尸者——秃鹫——所吞噬,就让大水冲进了大海。不过,角鲨总会闻风而至,不失时机地来帮助秃鹫为死者办完殡葬后事。
晚上7点左右,鹦鹉螺号在奶海里航行,船身一半在水里,一半露在水面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大海,海水呈乳白色,一眼望去就像牛奶似的。这是月光造成的吗?不是的,因为新月刚出现两天,此时还未从夕阳余晖的光照下的海平线上升起。整个天空虽然夕照犹存,但与白花花的海面相比,就显得黑乎乎的了。
龚赛伊还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不敢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他向我请教这种新奇景象形成的原因。幸好,我可以答得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奶海,”我对他说,“在盎波尼岛海岸和这一带海域中经常能看到这种广阔的白色波浪。”
“不过,”龚赛伊问,“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海水不会是牛奶做的吧!”
“当然不是了,龚赛伊,这种让你感到惊奇的白色海水其实只是无数的纤毛虫在作怪,这种小虫会发光,细如发丝,像无色透明胶,厚度只有五分之一毫米。纤毛虫互相粘连,连成浩浩荡荡的一大片,有好几里长呢。”
“好几里长!”龚赛伊惊呼道。
“是的,好小子,你大可不必费那个心思去计算这些毛毛虫的数量。谅你也算不出来,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的航海家曾在奶海中漂流了40多海里远。”
我不知道龚赛伊是否会听从我的劝告,但他好像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可能正在努力地计算着40 多海里究竟能有多少五分之一毫米的小虫子。而我呢,则继续观察着这海上奇观。只见鹦鹉螺号用它的冲角劈斩着白色波涛,在充满泡沫的奶海中悄悄滑行了好几个小时,就像漂浮在海湾的顺流和逆流相遇交叉时引起的白色泡沫旋涡中一样。
午夜将至,大海忽然又恢复了它平常的本色,但在我们身后,直至海天边际,长天映照着白色的波涛,仿佛久久地沉浸在朦胧的北极光之中。